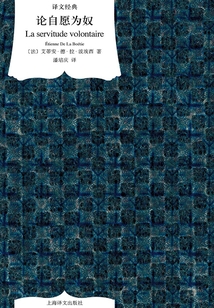
論自愿為奴(譯文經典)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中譯本序
拉·波埃西?不知何許人也。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拉·波埃西的祖國法蘭西,知道的人也不會太多。
1789年7月,法國大革命爆發,革命的基本原則就是自由、平等、博愛。革命后不久,制憲議會就頒布“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確認人生來并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關于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歷史淵源,人們自然會想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至于有影響的人物,人們首先會想到那些主張人的自然權利說的人,如格勞秀斯、洛克、霍布斯、盧梭等。但早在16世紀中葉,有一個年輕的法國學生就已經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倡導博愛,這個年輕人就是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關于拉·波埃西的生平事跡,現代人所知不多。這里,我也只能從介紹拉·波埃西的若干材料中摘取一二。1530年11月1日,拉·波埃西誕生在距離佩里格不遠的薩爾拉小鎮上。他的父親是佩里高爾地方行政長官的副手,但他英年早喪,十歲的拉·波埃西就成為孤兒。之后,拉·波埃西的一個叔父開始負責他的啟蒙教育。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早就影響到小鎮,當地有一位主教是意大利佛羅倫薩梅迪希斯家族的親戚,受過意大利人文主義的熏陶,非常博學,他就希望他所在教區能夠成為佩里格的雅典,藝術和哲學繁榮。拉·波埃西的叔父是教士,酷愛法律和古典文學,拉·波埃西就生活在一個酷愛古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家庭里。
拉·波埃西十分好學,他后來進入奧爾良大學攻讀法律。根據馬基雅弗利關于法蘭西的報告(1510年),奧爾良大學的排名僅次于巴黎大學。法學在當時有了巨大發展,奧爾良大學當時有不少著名法學家。拉·波埃西選擇法律,這意味著他準備以后進入司法界。但就在他念大學的初期,這位只有十八歲的年輕人,寫了一篇論文,后來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這就是《論自愿為奴》。除了法律,拉·波埃西還對古代語言、人文、歷史等深感興趣。閑暇時,他以法語、拉丁語或希臘語作詩,寫過二十多首愛情詩歌,還翻譯過普魯塔克、維吉爾等人的作品。
由于拉·波埃西在大學期間表現出眾,名聲頗佳,他于1553年9月23日獲法學士學位。同年10月13日,國王亨利二世下詔,破例同意拉·波埃西購買由紀堯姆·德·呂爾離開波爾多議會留下的議員空缺;之所以破例,是因為拉·波埃西尚未滿二十五周歲的法定年齡(弗朗索瓦一世統治時期,王國總是缺錢,于是建立了司法官職位的買賣制度)。1554年5月17日,拉·波埃西被正式任命為波爾多議會議員。從1560年起,拉·波埃西受命調解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戰爭。1563年,拉·波埃西罹患痢疾,也有可能受到鼠疫感染,因為他所在的Agenais地區正在鬧鼠疫;拉·波埃西的病情迅速惡化,8月17日,他自知大限將臨,于是非常平靜、安詳地起草了遺囑,8月18日去世,才三十三歲。
在談拉·波埃西時,不可能不同時提到另一個人,他就是法國大文豪蒙田。1557年,拉·波埃西認識了蒙田,兩人一見如故,成為終生至交。蒙田在其“論友誼”(寫于1580年)一文中談道:他在認識拉·波埃西之前就已看過《論自愿為奴》,他正是從該文中知道拉·波埃西這個名字。可以說,《論自愿為奴》在他們的友誼中起了橋梁作用。蒙田對兩人的友誼評價極高,他這樣說:“……這種友誼如此完整,如此完美,可以肯定,即使在書本上也幾乎找不到相似的例子,至于在今天的人際交往中,根本就看不到這種友誼的一絲一毫。必須有各種機遇的巧合才能夠建立這樣的友誼,如果每三百年能夠出現一次這樣的友誼,那就是奇跡了。”“在我談論的友誼中,兩個靈魂相互交融,合為一體,如此完美無缺,可謂天衣無縫。如果有人問我為什么喜歡他,我想這是難以言表的,這似乎超出了我能夠列舉的所有理由,超越了我能夠表達的范圍;我不知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神奇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造就了我們的結合。”拉·波埃西在《論自愿為奴》的最后就談到他對友誼的看法、友誼的定義、友誼的標準、友誼的基礎等,而蒙田在“論友誼”中回應拉·波埃西的友誼論,正是兩個靈魂合二為一的具體表現。兩人的友誼成為法國文壇的佳話。事實上,《論自愿為奴》就可從友誼的角度來理解:友誼只能存在于兩個平等人之間,而奴役則恰恰以不平等的人際關系為基礎;正因為拉·波埃西極其向往人間真誠的友誼,所以他對人們熟視無睹的奴役現象極為反感,誘發了他對人類奴役現象的探討。
拉·波埃西撰寫《論自愿為奴》一文時(大概在1548年),他正在讀大學。什么事件激發了作者的寫作熱情?一個解釋是:1548年,在吉也納爆發過一次反鹽稅暴動,結果遭到無情鎮壓。拉·波埃西可能由此感到震驚,他在文中即表達了一個年輕學生對專制政治的困惑。人們通常認為受奴役是被迫的,拉·波埃西卻相反認為這是為奴者的自愿選擇,因為每個人生來就是自由的。人們總認為權力絕對強大,但他們偏偏忘記了奴役的真正由來:一個人是無法奴役眾人的,除非眾人首先奴役了自己。只要下決心不再接受奴役,君主的權力金字塔就會頃刻瓦解。
《論自愿為奴》是一篇探討專制政治的論文,本為一篇學生習作,僅僅在作者的好朋友,或者在知識界小圈子內傳閱,但在后來的歷史演進中,該文成為一篇著名的抨擊專制制度的戰斗檄文。歷史上常有這樣的現象:一篇小文章,當時微不足道,但它后來卻漸漸受到關注,上升為一種象征、一種號召、一種符號,不斷被賦予新的含義。
拉·波埃西在撰寫《論自愿為奴》時,并沒有后世的革命思想。但隨著歷史的發展,拉·波埃西的《論自愿為奴》被后人視為反封建專制的宣言書,其書也不斷被再版,并被譯成多種外語。歷史證明:拉·波埃西有先見之明,他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的發展趨勢;其《論自愿為奴》是近現代政治哲學的一篇重要文章,后來在不同時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廣泛引用,影響了很多思想家,可謂近現代史上的經典之作。
關于中文譯本和翻譯情況。《論自愿為奴》的原文早在16世紀就已遺失,后人出版該文只能以克洛德·迪皮和亨利·梅斯默的手抄本,或者以16世紀新教徒出版的印刷品為依據。任何手抄本都不可能和原文完全一致;至于新教徒的出版物,由于新教徒當時受迫害,他們選擇《論自愿為奴》的某些片斷,以此抨擊封建專制,肯定按自己的觀點對《論自愿為奴》作過很大改動。19世紀,人們重新找到亨利·梅斯默的手抄本,經過比較,認為此版本改動的地方最少,因而認為該版本最忠實地保存了作者的主要觀點。查理·泰斯特即根據梅斯默版本于1836年以當時的法語翻譯《論自愿為奴》,于是16世紀的法語轉成19世紀的法語。由于《論自愿為奴》有很多版本,光20世紀就有不少今譯本,選哪一版本作為中文譯本的底本?看了好幾個不同版本,我最后選擇查理·泰斯特的譯本,因為該譯本更接近梅斯默版本,其譯注也反映了法國19世紀的情況,正好承上啟下。但在查理·泰斯特的譯本中,有不少地方意思比較難懂,我參考了梅斯默版本,以及若干現代法語譯本,尤其是Gérald Allard的譯本。所以,中文譯本中有四種注釋:1)出版者注,即中文譯本所依據的《論自愿為奴》,Payot出版社,2002年版;2)法語譯注,即查理·泰斯特在轉譯時加上的注釋;3)Allard注釋,即G. Allard譯本的注釋,見《拉·波埃西和蒙田論人際關系》,Griffon d'argile出版社,Ste-foi,加拿大魁北克,1994年;4)中文譯注,這是我加上的注釋。
由于注釋較多,我建議讀者在讀第一遍時可以不管注釋,否則容易打斷思路;讀第二遍,可以參考注釋。如果還有第三遍,可選讀某些片段和若干法語注釋。這當然不是硬性規定,一切由讀者自由決定,我僅僅和讀者分享我的經驗。書中的大部分人名和地名都譯成中文,但有不少人名和地名,對中國人都非常陌生,所以我仍保留外文,這樣并不影響閱讀,甚至更簡單明了。
關于中文譯本的由來。我第一次讀《論自愿為奴》,那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在歐洲留學。一晃近二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在圖書館又看到這本書,借來重讀,又有新的感想。萌發翻譯此書的想法。首先,以前有人翻譯過《論自愿為奴》的若干部分,而且是從俄語譯成中文,和原文有較大距離。其次,鑒于《論自愿為奴》在近現代史上的影響,可說這是一部經典之作。我所謂經典作品的標準,不僅僅看它是否提出了多么完美無缺的理論,得出了多么無懈可擊的結論,更在于看它是否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問題,是否能夠促使后人進一步探索。經典之作總是站在時代前沿,或者預見到社會發展趨向,從而能夠啟發當代人和后人的思想,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我熱情渴望《論自愿為奴》的中文全譯本能夠啟發中國讀者,促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最后,我要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鼎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