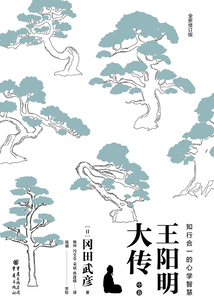
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中卷)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知行合一”說
席元山入門
前文已述,正德四年(1509),貴州提學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陽明的大名,特意前往王陽明的住處,向他請教學問。
席元山(1461—1527),名書,字文同,號元山,四川遂寧人,弘治三年(1490)進士,后升任禮部尚書,嘉靖六年(1527)又加封為武英殿大學士[1]。六十七歲去世,謚號“文襄”。席元山非常推崇陸學,曾著有《鳴冤錄》,為陸學辯解。在晚年時曾推舉王陽明出任大臣。
據《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記載,席元山對宋明理學非常感興趣,他把王陽明迎請到自己的住處,向王陽明請教“致知”和“力行”究竟是一層功夫還是兩層功夫。王陽明告訴他,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為二事,也就是“知行合一”。席元山非常欽佩王陽明,特地請王陽明主持貴陽書院,還親率貴州諸生向王陽明行弟子禮,而且一有空暇,就會前來聽講。王陽明也借此機會,在貴陽大力提倡“良知”說。
但“良知”說是王陽明在晚年提出的,他在貴州時根本就沒有提過“良知”說。《陽明先生年譜》中記載:“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
席元山后來又著有《鳴冤錄》,仔細想來,該文應該是根據《陽明先生年譜》中記載的這次辯論而作。
接著《陽明先生年譜》又記載道:“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同異,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總而言之,席元山師從王陽明之后開始意識到,與其討論朱陸之異同、明辨古人之是非,倒不如判明自己內心的是非。至于王陽明當時悟得的“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席元山又是如何理解的,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席元山對此又是如何認識的,《陽明先生年譜》中一概沒有記載,我們對此也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可以從王陽明與門人徐愛后來有關“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問答中,推測出王陽明和席元山交談的大致內容。
王陽明沒有按照席元山的提問去回答朱陸之說的異同,而只是談了自己所悟到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說。對席元山來說,如果能領悟到“理”存在于“性”中,那么朱陸之異同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明了了。所以說,王陽明雖然看起來沒有回答席元山的提問,但其實已經回答了。
王陽明開口評論朱陸之異同,并且明確表達出自己的意見,那是后來的事了,后文將對此予以詳細介紹。后來,由于弟子們就朱陸同異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王陽明沒有辦法,只好站出來,公開表明了自己對朱陸同異的看法。
那么,王陽明在貴州時為什么不公開表明自己的看法呢?
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王陽明覺得與其爭辯古人做學問的是非,還不如先去體悟圣學,以求得“吾性”;其二,當時朱子學風靡一時,如果大力宣揚陸學的話,勢必會成為眾矢之的,所以,為了避開鋒芒,王陽明沒有公開表明自己的看法。
朱熹和陸九淵的學問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王陽明不得不加入朱陸同異的辯論中。雖然表面上朱子學盛行一時,人們卻不能否認陸學潛藏的事實。自元朝中葉開始,朱陸同異的辯論就已經出現,王陽明自然也不能擺脫這一風潮。
后來,朱熹的高徒陳淳[2]極力排斥陸學,再加上朱子學比陸學更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所以在陸九淵去世之后,朱子學便逐漸興盛起來。陸九淵有四大高徒——沈煥[3]、舒璘[4]、袁燮[5]和楊簡,人稱“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陸九淵死后,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寧波)地區講學,所以陸學主要在四明地區留存下來。由于受陳淳排斥陸學的影響,陸學一蹶不振,逐漸陷入衰敗。至元代,朱子學被指定為科舉之學,迎來了大繁榮,而陸學基本上仍處于隱藏不露的狀態。
朱熹和陸九淵死后,雖然朱子學派極力排斥陸學,但是陸九淵的心學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朱子學。這一過程類似于宋代儒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心學”的形成與發展。在宋代,當時的儒學界也極力排斥禪學和道家之學,卻不知不覺地受它們的影響,最終形成了儒學的“形而上學”和“心學”。朱熹的再傳弟子、著名大儒真德秀[6]可能也是因為受陸學的間接影響,所以才創作了《心經》,論述了從古至今的心法。自宋末一直到元代,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朱陸二學殊途同歸的看法。
元代朱子學的大儒吳澄認為,陸學主張的是“尊德性”,朱子學主張的是“道問學”,二者同等重要,沒有輕重之分,所以吳澄也被認為是陸學派的儒學家。后來,思想界又興起了朱陸同異的辯論。元末的趙東山、明初的程敏政認為,雖然朱子學和陸學存在差異,但它們所追求的結果是一致的。朱子學沒有忘記“尊德性”,陸學也沒有忘記“道問學”。盡管朱熹在年輕時和陸九淵的立場相異,但是晚年他和陸九淵的立場趨于一致。
到明代后,朝廷更加重視朱子學,不僅將其指定為科舉之學,還打壓提倡陸學的人士,從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學興盛、陸學悄無聲息的態勢。但是實際上,不少明朝大儒已經把“心上”功夫當作自己做學問的要旨,出現了重視心學的傾向。朱子學和陸學在暗地里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最終出現了一位專門提倡心學的朱子學者——陳獻章。
清初大儒黃宗羲把陳獻章的心學視作陽明學的先導,但陳獻章的心學是“主靜心學”,而王陽明的心學則是承繼陸九淵,是“主動心學”,二者的方向明顯不同。陳獻章的心學沿襲的是朱子學,因此可以說是“宋學”,而王陽明的心學沿襲的是陸九淵的心學,因此可以說是“明學”。這也恰好體現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別:一個主靜,一個主動。
如果能夠領悟到“致知”和“力行”的本體是統一的,那么理解“知行合一”說就會變得很簡單。如果不是通過這種“體認”,而是單純地依靠理論去解釋“知行合一”,理解起來就會很困難。王陽明曾經從各種角度論證過“知行合一”說。綜合起來看,經他闡述,“知行合一”說的實質已經變得非常明晰了。
在王陽明看來,如果能夠體認到“知行”的本體,那么“知行合一”說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陽明晚年時認識到“知行”的本體就是“良知”。這樣一來,“知行合一”說就變得更加具體了。但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并不是僅僅作為一種知識讓人們去理解的,而是需要人們深切“體認”的。“知行合一”說是王陽明學說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還將予以詳細介紹。
行而知之
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自古以來,雖然眾人皆知“知”與“行”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但一直都是將二者分開,各自論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時代,對“知”與“行”的論述已經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
在朱子學一統天下的時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眾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驚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稱作“王門顏回”的王陽明的高徒、妹婿徐愛,一開始聽到“知行合一”說時,也流露出驚訝的表情。
總的來說,長于理性的人會很難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這和長于智慧的子貢無法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7]是一樣的道理。無怪乎孔子會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誡子貢“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說清楚的。后來,長于德行的曾子繼承了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子比子貢“魯”,即我們所說的愚鈍。當孔子說出“吾道一以貫之”的時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唯”。所以說,子貢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則他應該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與此相反,雖然曾子被視作愚鈍之人,但他其實并不愚鈍,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諦呢?又怎么能參透“一貫之道”呢?
總之,長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會陷入偏見。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朱子學都是“主知主義”[8]的學說。因此,在一個朱子學至上的時代,人們必然難以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徐愛最初也難以理解老師的“知行合一”說,所以曾與自己的同門師弟黃綰和顧應祥[9]展開辯論,試圖去理解“知行合一”說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終不得不直接向王陽明請教。(《傳習錄》上卷)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悌者,卻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地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王陽明從“知覺與好惡之意是一體”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場出發,對“知行合一”說進行了闡釋。
毫無疑問,“好惡之意”其實就是“行”。明末大儒劉宗周也非常重視“好惡之意”,并且將“誠意”視作自己做學問的宗旨,認為“意”非“已發”,而是“未發”,并將“意”視作“心”之本體。
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王陽明雖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但是對于如何修行“合一”的“知”與“行”,并沒有給出很好的辦法。徐愛曾向他建議將“知”與“行”分開來修行,這一建議其實又回到了朱熹的立場上。朱熹堅持“知行并進”論,換句話說,就是堅持“窮理”與“居敬”并進。王陽明對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傳習錄》上卷)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
“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在王陽明看來,“知行合一”原本就是古人的意思,今人將其分作兩件事去做,其實違背了古人本意。古人認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而古人之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則是因為世間總有一些無知的人,所以要既不陷入妄行,也不輕視實踐。古人為了防止世人陷入虛妄,同時也為了補偏救弊,不得已只好必說一個知,方才行得是,又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
總而言之,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是為了幫助世人脫離偏弊,同時也是為了幫助世人脫離朱熹的“先知后行”之弊。
王陽明曾對弟子黃直訴說過自己提倡“知行合一”說的動機:“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還提出了“知行合一”,晚年又提出了“致良知”,這些主張其實都圍繞著一個宗旨,那就是要徹底清除潛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會違背王陽明的本意,也會生出很多弊害。事實上,王陽明的追隨者都違背了王陽明的本意。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他們只相信良知的完美,而忽視了修行。
“知行合一”說的發展
前文已述,王陽明在壯年時曾闡述說:“知行合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到了晚年,王陽明又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說。
嘉靖五年(1526),王陽明曾寫過一篇《答友人問》(《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用以答復友人提出的四個問題。通過《答友人問》,我們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陽明是如何發展“知行合一”說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對此問題,王陽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功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后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陽明反對將《中庸》中的“學問思辨”與“篤行”區分為“知”與“行”。
接下來,王陽明又闡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功夫。”
王陽明通過“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闡明了“知”與“行”原本只是一個功夫,即“知行合一”。這和王陽明壯年時期的“知行論”比較起來,“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知行一體”的精神也更加明確。與其把王陽明晚年對“知”與“行”的闡釋稱為“知行合一”,不如稱作“知行一體”更為恰當。王陽明的“知行論”之所以會發展到這一程度,主要是因為他在晚年確立了“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
王陽明在龍場先是悟出了“萬物之理皆在吾性之中”,也即“心即理說”,然后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但他真正完善“知行合一”說是在晚年。
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給妻侄諸陽伯寫了一篇《書諸陽伯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其中寫道: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于親則為孝,發之于君則為忠,發之于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于吾之一心。故以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
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并進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后,而不免于支離之病者也。
提倡“知行合一”說的王陽明自然會批判將“存養”和“居敬”視作兩層功夫的朱熹,也自然會批評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說。
因此,他在《答顧東橋[10]書》(《傳習錄》中卷)中,曾這樣闡述: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并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無先后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厘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并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王陽明在給顧東橋的答書中闡述了“知行合一”說的主旨,指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并強調說,正因為“心即理”,所以“知行”才是“合一”的。此外,王陽明還基于“知行合一”說的立場,指出了朱熹“心理二分”說和“知行二分”說的弊害。接著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又繼續寫道: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
“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吃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者也。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邪?
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學問即行,行即知
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學問”是“知”,“實踐”是“行”,而且往往將二者區別看待,然而對于王陽明來說,“學問”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陽明曾經系統地論證過《中庸》中提到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之間的關系,從中也可以了解王陽明的上述觀點。
王陽明還從“知行合一”說的立場出發,對朱熹的“知行論”進行過批判,這在上文中已經做過一些介紹,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也對此做過更加詳細的闡述:
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后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
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并進之功,所以異于后世之說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二分”說,王陽明則是基于“主行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合一”說,因此,陽明學被世人稱為“實踐哲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的。王陽明接著又寫了下面幾段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實踐哲學”的特色: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后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后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
學至于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
致良知
王陽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從“心即理”的角度來進一步發展“知行合一”說,并且認為,最終還得靠“致良知”去“窮理”。
所以,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寫道: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悵悵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厘千里之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王陽明指出,如果“盡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在他看來,《書經》(《尚書》,“五經”之一)中所說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致知”中的“知”是指對“是非”先天性的判斷,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讓“知”達到極致,就必須通過實踐,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據《書經》中的“知之不難,行之不易”和《大學》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說”,但王陽明得出的是“知行合一”說。盡管王陽明與宋儒所根據的是同樣的經典,可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作《書朱守諧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
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陸九淵與“知行合一”說
前文已述,王陽明在龍場頓悟時得出“心即理”的結論,所以才得以創立“知行合一”說。但是,陸九淵也提倡“心即理”,為什么他沒能提出“知行合一”說呢?這是因為陸九淵雖然也提倡“尊德性”,但他對于《大學》中“格物致知”的解釋沒能擺脫傳統的束縛。
與陸九淵不同的是,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是徹底的“唯心論”,他明確指出“心即物”。盡管這樣的認識是在龍場頓悟之后產生的,但在龍場頓悟之際,陽明恐怕就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由此看來,王陽明在龍場悟得的“心即理”應該比陸九淵的“心即理”更加“唯心主義”。也正因為如此,王陽明最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晚年對陸九淵的學說極力稱贊,對朱熹的學說則加以批評。曾有友人問他:“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于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答友人問》)
雖然王陽明極力稱贊陸九淵的學說,但他認為陸九淵和朱熹在“格物致知”的解釋方面是相同的,二人體現的都是“主知功夫”,故而提出的是“知行二分”說,而他自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則與二人不同,所以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說。
如上文所述,有人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存在疑問,王陽明的解釋是:“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象山見得未精一處”,是指陸九淵還沒有徹底地實現“唯心論”。王陽明將“心即理”發展為“心即物”,從他的立場來看,雖然陸九淵的學問很深奧,但是仍然沒有達到“精一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