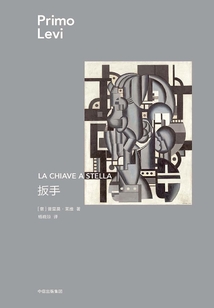
扳手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蓄謀
……這家伙……魯莽的來到了世上……生他之前,我很享受了一番。[1]
——《李爾王》,第一幕,第一景
“不,不,我不能什么都告訴你。我要么跟你說說那些國家,要么跟你說說我經歷了什么事。但對于你,我還是告訴你我經歷了什么事吧,因為這是個挺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真想寫出來,就花點兒心思,好好打磨、修邊兒,把它敲錘成形,這樣你就能寫出一個好故事。雖然我年紀比你小,但我經歷過很多,有很多故事。或許你能猜到那些國家的事,那也沒所謂。但我要是跟你說了那些地方在哪,我就會惹上麻煩:那里的人雖然好,但他們也有點兒難搞。”
我跟福索內才認識兩三個晚上。我們是在食堂里碰巧遇上的,那是我們所在的偏遠工廠專為外賓設的餐廳,我作為一名涂料化學師,因為工作需要到了那里。那兒唯有我們兩個是意大利人。他才來三個月,但他曾因為其他事在那一帶待過,所以他對當地語言掌握得不錯,此外,他本來還會四五種語言,雖然說話時語病頗多,但很流利。他約莫三十五歲,高而瘦,近乎禿頂,皮膚曬得黝黑,胡子總是刮得很干凈。他面相嚴肅,表情相當凝重,沒什么變化。他講故事不是特別擅長。相反,他的語調變化不多,時常輕描淡寫,頗為簡略,仿佛擔心人家覺得他夸張。但他也時常放任自己,于是,不知不覺地,他真的有些夸張。他詞匯量有限,又頻頻用那些爛大街的詞句表達自己,但他自己似乎覺得這些表達新穎又機智。要是聽故事的人沒有笑容,福索內就會把那些詞句重說一遍,就像在跟傻子說話似的。
“……就像我跟你說的,我會在這個行當里,從一個工地到另一個工地,到世界各地的各種工廠和港口,并不是偶然: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有的小孩都夢想進入叢林、深入沙漠、游歷馬來亞,我也有這樣的夢想,不過我想要自己的夢想能夠實現;否則,它們就會像某種你終生患有的病痛或某場手術留下的傷疤,一旦天氣陰潮,又會復發作痛。擺在我面前有兩條路: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富了,然后做觀光客;我也可以做裝配工。所以我就成了裝配工。當然還有其他的路可走:你或許會說,可以去做走私犯,或者諸如此類的行當。但這些不適合我。我想游歷異國,但我也一樣是個普通人。到如今,我已經有了一種沒法安分的性子,一旦被迫安定下來,我就會害病。要是你問的話,我會說,這世界很美麗,因為它總是不同。”
他面無表情地看了我一會兒,眼睛無神,卻稍有異樣,接著又耐心地說了一遍:“一個人待在家里,或許平靜安穩,但這就像吮吸一個鐵做的乳頭。這世界很美麗,因為它總是不同。所以,就像我說的,我去了許許多多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奇遇,但最離奇的故事還要算過去這一年在那個國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能告訴你它在哪兒,但我可以告訴你,它離這兒很遠,離我們的國家也很遠,我們在挨凍,但那里十二個月里九個月都熱得跟地獄似的,剩下三個月會刮風。在那兒的時候我在港口工作,但那兒跟我們這兒不一樣:港口不屬于政府,它屬于一個家族,這個家族的大家長擁有著那里的一切。在我開始工作之前,我得先去拜訪他,得穿得筆挺,打著領帶,跟他吃點東西,說會兒話,抽根煙,樣樣都不緊不慢。你想想!我們可是每分每秒都算好的,我的意思是,雇我們是很花錢的,但我們也為此自豪。這位一家之長有一種一半一半的性格,一半時髦一半老派;他穿一件優雅上乘的白襯衫,連熨都不用熨的那種,但他進了大門之后要脫鞋,他讓我也把鞋脫了。他英語說得比英國人還棒(但這也不是很難),但他不讓我見家里的女眷。他屬于某類進步奴隸主。還有,你能相信嗎?他把自己的相片框起來,每個辦公室都掛,連貨倉都掛,好像他是耶穌基督或者什么人似的。但整個國家大致是這樣:有驢子也有電傳,機場建得讓咱們都靈的卡塞勒看起來都寒磣,但通常,你騎馬就能最快地趕到一個地方。他們那兒夜店比面包房多,但你常常會看到街上走的人有沙眼。
“我不介意跟你說,操縱起重機是個特別棒的活,要是橋式起重機就更棒了;但這不是誰都能干的。這樣的活需要那些懂得其中訣竅的人,能教事物運轉的人,像你我這樣的人;而其他人,那些助手,你隨時隨地都能招到。讓人驚奇之處就在這里。在我說的這個港口,工會的狀況也是一塌糊涂。你知道,在這個國家,你要是偷了東西,他們就會在廣場上剁掉你的手,左手還是右手取決于你偷了多少,也許還可能是一只耳朵,但都有麻醉劑和一流的外科醫生,瞬間就能幫你止血。不,這不是我編的,而且誰要是對有地位的家族出口誹謗,他們就會割掉他的舌頭,絕沒什么‘假如’和‘可是’。
“不過,除了這些,他們還有一些相當難搞的組織,你得應付它們:那里所有的工人都隨身帶著晶體管收音機,像帶著個幸運符一樣,要是廣播上說發生罷工了,那所有事都會停下來,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個手指頭。就此而言,假如他想干點什么,他就很可能要吃刀子,可能不是當場、當時,而是兩三天后;他也有可能被掉下來的橫梁砸到頭,或者喝一杯咖啡就當場倒地不起。我不愿意在那兒長留,但我很高興在那兒待過,因為有些事,你要是沒看見,就不會相信。
“嗯,就像我跟你說的,我在那兒是為了在碼頭上架起重機,那是個大家伙,它有可伸縮的吊臂,妙極了的橋架,四十米的跨度,以及一百四十馬力的升降電機。上帝,多棒的機器啊。明天晚上記得提醒我給你看照片。當我把它完全架上去之后,我們就進行測試,它好像走在天上一樣,像絲綢一樣順滑,我感覺他們都要把我捧成公爵了,我給每個人都拿了酒。不,不是葡萄酒:是他們那兒的酒,他們管它叫卡姆芬,味道像發霉了,但它能讓你平靜下來,且對你有好處。但我漸漸感到有些力不從心。這份活不是那么簡單的;不是技術上的原因,在這方面,從第一顆螺釘開始便一直順風順水。不,是一種你感受得到的氣氛,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空氣中的滯重。人們聚在街角低聲嘀咕,嘆著氣,面面相覷,我沒法理解;墻上不時會貼新聞報紙,大家會圍攏起來讀報,也有人讓別人讀給自己聽;我就被獨個兒扔在一邊,像只呆鳥一樣立在腳手架的最上邊。
“接著暴風雨便降臨了。有一天,我看見他們用手勢和口哨招呼彼此:他們都走了,于是,因為我獨自一人什么也沒法干,我也從塔樓上下來,準備去瞄一眼他們的會議。那是一個建了一半的棚屋:后來他們用梁木和厚木板搭起了一個臺子,一個接一個地來到臺上演講。我不太懂他們的語言,但我能看出他們很憤怒,就像受了冤枉。過了些時候,那個年長的人物上來了,他似乎是個地方帶頭人。他對于自己所說的內容似乎也十分篤定;他語氣平靜,十分威嚴,不像其他人一樣大喊大叫,而且他也不需要這么做,因為他往那一站,其他人就都閉嘴了。他做了一個平靜的演講,他們看起來都很信服;最后他問了一個問題,他們便都舉起了手,喊著我聽不懂的話。當他詢問是否有人反對時,一只手也沒人舉。接著這個老人從前排叫了個男孩過去,給了他一個指示。男孩跑開了,去了工具商店,并立刻就回來了,手中拿著一張那位大老板的相片以及一本書。
“除我以外,還有一位檢查員,當地的,但他能說英語,我們關系還算融洽,因為跟檢查員走得近總歸不會錯的。”
福索內剛剛吃完一份分量很大的烤牛排,但他又把服務員叫了過來,讓她再給他端一份。比起他的金句格言,我反倒對他的故事更感興趣,但他照例要重復自己的話:“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每個圣人都需要蠟燭。因為想和他們走得近,我送了那位檢查員一根魚竿。所以他跟我解釋了情況。簡直瘋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工人們都在要求廚房按他們的宗教習慣給他們做飯。雖然說到底大老板自己也是固執偏信某個其他宗教的,但他兀自拿著一種現代腔調——這個國家里有太多宗教信仰了,要每種習慣都照顧到是不可能的。總之,他叫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告訴他們,要么他們在現在這樣的食堂里吃飯,要么食堂干脆就不辦了。罷工已經發生了兩三次了,但大老板一丁點兒都沒讓步,因為生意進度本來就慢。于是工人們就萌生了跟他動真格的念頭,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要報復他。”
“你說的動真格是什么意思?”
福索內耐心地解釋道,差不多就是給他下咒,用邪惡之眼[2]瞪他,給他下降頭。“但可能不是要他的命。相反,那時他們絕對不想讓他死,因為他弟弟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只想嚇唬一下他,你知道,讓他突然得病,或忽遇意外,讓他改變主意就好,同時讓他明白,他們知道如何讓別人感受到他們的要求。
“于是那位老人拿了把刀,把相框的螺絲擰開。他看起來像是這方面真正的老手。他打開書,閉上眼睛,然后用手指到其中的一頁。接著他又睜開眼,讀了些我和檢查員都聽不懂的東西。他拿起相片,卷起來,用手指用力壓緊。他叫人給他拿了一把螺絲刀,這把螺絲刀已經在酒精燈上燒得通紅,他把螺絲刀捅進了壓平的相紙卷。他攤開相片,把它舉了起來,于是大家都鼓起掌來。相片上有六個燒焦的洞:一個在前額,一個在右眼附近,一個在嘴角,其他幾個洞都在背景上,沒觸到臉。
“然后老人就那么把皺皺巴巴還穿了孔的相片放回了相框,小孩跑去把它掛在了平常的地方,大家都回去工作了。
“唔,四月末,大老板病了。沒人出來公開宣布,但流言不脛而走,這種事情你應該也很明白。起初他的情況似乎很不妙;不,他的臉一點事也沒有:盡管如此,這件事也已經夠怪的了。家里人想把他弄上飛機,送他去瑞士,但他們沒有時間了。是他的血液里生了什么毛病,十天后他就死了。而他本是個皮實的男人,我告訴你,他之前從沒病過,總是坐著自己的飛機滿世界飛,下了飛機就去泡妞,或者從天黑賭到天亮。
“這個家族告工人們謀殺,或者說‘蓄謀殺人’;有人告訴我他們那兒是這樣叫的。他們有法庭,你理解吧,但這些法庭屬于你最好敬而遠之的那種。他們有不止一套法律;他們有三套法律,他們選用哪套取決于哪套能更好地為強勢一方或給錢多的一方服務。就像我說的,這家族的人堅持說這是謀殺:他們有殺他的動機,有讓他死的行動,而他也真的死了。辯護律師說,這些行動不足以致命:它們最多能讓他緊張一下,火大一次,或者起些丘疹。他說,要是工人們把那張相片剪成了兩半或者澆上汽油燒了,那問題就嚴重了。因為這就是降頭起作用的原理,大致就是:一個洞就造成一個洞的破壞,從中剪斷就有從中剪斷的威力,以此類推。聽到這個,我們不禁要笑,但他們都深信不疑,連法官也是,甚至辯護律師們也一樣。”
“那審判最后結果怎么樣?”
“你在逗我嗎?它還在審呢,而且天知道還要審到什么時候。在那個國家,審判沒有能結束的。但我提到的那個檢查員答應告訴我結果,既然你對這個故事感興趣,要是你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訴你。”
服務員來了,端來了福索內點的分量堪稱壯觀的奶酪。她四十歲上下,弓著背,瘦得看得見骨頭,直直的頭發上沾著天知道的什么東西,而她可憐的小臉看起來像怯生生的山羊。她長長地看了福索內一眼,而他回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寫著滿不在乎。她走開之后,他說:“她看起來有點像撲克牌上的梅花J。但是他媽的,生活給你什么,你都得接著。”
他努努下巴指著奶酪,帶著勉強的熱情問我要不要來一點。然后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一邊嚼一邊繼續說:“如你所知,在這里,姑娘們總是缺男人,我們就變得緊俏。生活給你什么,你都得接著。我是說,廠里給你什么,你都得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