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yuǎn)方很近,自己很遠(yuǎn)
曾經(jīng)寫下那么一段大家都不怎么能看懂的話。當(dāng)時(shí)是打橫著來寫的,有個(gè)網(wǎng)友說,你試著把它打豎著寫,那它看起來就像詩了,詩就是這樣“滴”出來的。
那一道白線,像離弦的箭,
劃過城市,劃過村莊。
當(dāng)時(shí)我就在陽臺(tái)上,
看著晾衣架上的衣服,
有水一滴一滴地滴下。
白線拖著長長的尾巴奔向遠(yuǎn)方,
水滴滴下的地方卻看不見痕跡。
小時(shí)候說,長大了我要去遠(yuǎn)方。
現(xiàn)在,終于離遠(yuǎn)方越來越近,
卻發(fā)現(xiàn)離自己越來越遠(yuǎn)。
其實(shí)那段話寫的是高速火車,那天在陽臺(tái)上看著遠(yuǎn)處的高速火車劃過,挺有感觸的。一路狂奔的我們,遠(yuǎn)方在哪里?緩慢是否對我們來說已是一種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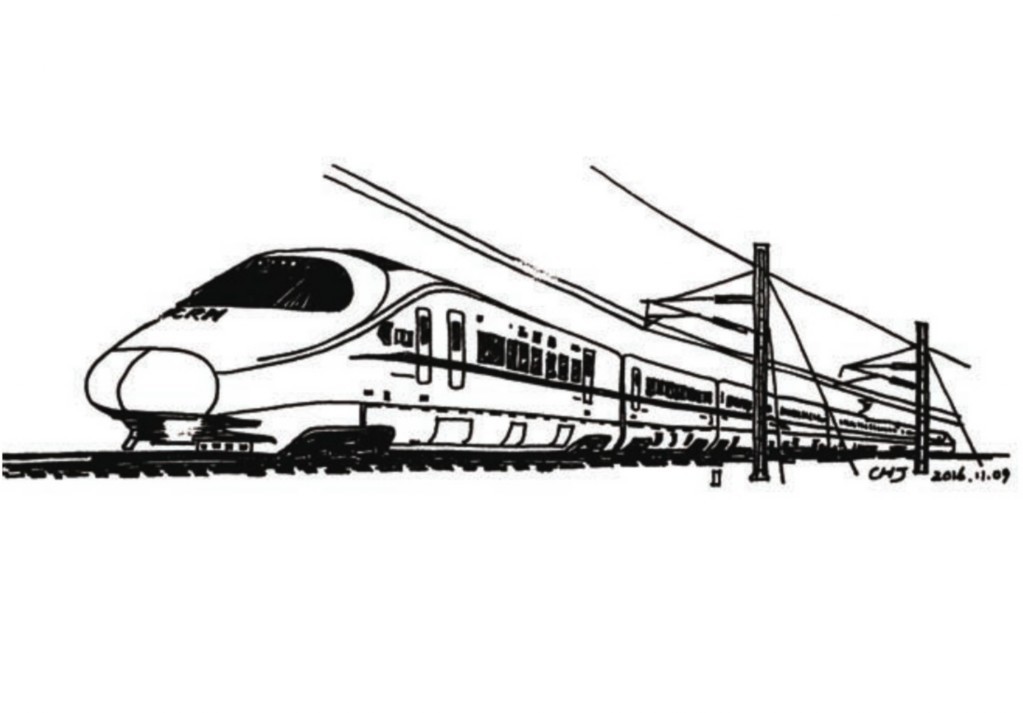
“城市里的人忙,沒什么大事就別讓津回來了。”這是爺爺在的時(shí)候總說的一句話。是的,看看城市里的人,個(gè)個(gè)步履匆匆、神色凝重,見面總問“最近忙嗎?”“忙。”“忙點(diǎn)好。”“忙”成了我們?nèi)松闹髦迹l要是很清閑還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米蘭·昆德拉在《緩慢》一書中寫道:“……為什么緩慢的樂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閑逛的人們到哪去了呢?那些民謠小曲中所歌詠的漂泊的英雄,那些游蕩于磨坊、風(fēng)車之間,酣睡在星空之下的流浪漢,他們到哪里去了?他們隨著鄉(xiāng)間小路、隨著草原和林中隙地、隨著大自然消失了嗎?捷克有一句諺語,將他們溫柔的閑暇以一個(gè)定義來比喻:悠閑的人是在凝視上帝的窗口。凝視上帝窗口的人不無聊,他很幸福。”是啊,是什么讓我們的步履如此匆忙?是什么讓我們頭也不回地一路狂奔。“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城市原有的意義在不斷地消失,過度的城市化讓城市開始異化。
城市,這個(gè)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東西,面臨著一個(gè)人類無法克服的悖論: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聚集在一起產(chǎn)生了城市,但最后城市總會(huì)成為人性的噩夢,因?yàn)槌鞘袩o可避免地造成人與本性的疏離、人與他人的疏離、人與自然的疏離。過度的城市化使得城市變成了一部巨大的“賺錢機(jī)器”。大家聚集在城市里,一部分人賺取另一部分人的利潤,一個(gè)集團(tuán)賺取另一個(gè)集團(tuán)的利潤,為了掩飾它的矛盾,我們美其名曰“共贏”。誰也不想是金字塔最底下的那一層,所以我們只有不斷地往上,我們不能停下來,我們都很忙。我們很少去關(guān)心城市了,城市的天越來越暗淡,我們坐在辦公桌前咳得越來越厲害,好不容易聽說最近經(jīng)濟(jì)在下行,我們可以不用加班了,心里更不踏實(shí)了,當(dāng)心著有一天回來,公司的大門緊閉,才想起上個(gè)月的工資還沒發(fā)。
什么時(shí)候我們才能沒那么忙,停下腳步凝視星空,找回我們自己。每每這時(shí)我總想起在海邊曬太陽老頭兒的段子和那個(gè)少年:某某年少的時(shí)候向往城市生活,毅然走向城市,經(jīng)多年奮斗終于在城市里有了房有了車,生活富庶。有一天覺得城市實(shí)在住不了了,他又回到了鄉(xiāng)下,轉(zhuǎn)了個(gè)圈回來了,可他失去了幾十年。
什么能改變城市?不是“資本”,不是“規(guī)劃”,不是“互聯(lián)網(wǎng)”,似乎唯有“人心”,我們甘于平凡、敢于放慢腳步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