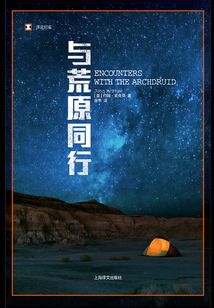
與荒原同行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山脈(1)
冰川峰荒原。小木屋矗立。百米外的土道,綿延穿過喀斯喀特山脈。時值仲夏,森林中孤零零的小木屋,眼望著十分突兀。雖然不過是三平米半見方,卻實實在在有兩層,上面還有一個高聳的尖屋頂。在屋脊之上,還架著一根三米長的木桿。一把雪鏟綁在木桿頂端。在這樣一個清涼的夏夜,那些在木屋前卸下肩上重負的登山客們——正像我們五位現在這樣——抬頭就可以看到那把雪鏟,想象有人在十多米之上的雪地中跋涉,先得找到這把雪鏟,還得一鏟一鏟挖到門邊,不由人心中肅然。這就是奇蘭縣的雪況調查隊在冬天里要使用的小屋。他們得在下雪時測量積雪深度和雪密度,并估算出融雪時的大致徑流。這是因為在華盛頓州這一帶,會積起超乎想象的、超大量的雪。而他們從事的工作,對居住在山腳下的人至關重要,其影響甚至超出了整個山脈地區。
我們當然不是來做雪況調查的。我們都累壞了。從下午三點開始,我們已經連續攀爬了十二公里左右的上坡路。我們中間,一個六十多歲,一個五十多歲。在這仍顯寒冷的山區里,這樣一幢小木屋對于我們整隊人來說不啻是個天堂。除非是在仲夏季節,否則那土路根本無法通行。為了這次旅程,我們不得不等待冬雪融化。小屋登記簿上的一條記錄表明,就在前一周,也就是8月5日,這里還在下雪。把我們吸引到喀斯喀特山脈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很多人都把它們看做是美國境內最美麗的山脈。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堅持認為,這些由火山堆積,又由冰川勒劃成形的巨型錐形山峰,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山脈。1964年,美國國會將這片山區和另外幾個地區撥為永久性荒地,甚至不能開辟為國家公園。除了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任何類別的機械不得入內。永遠不得開發,不得改變用途,不得采伐。然而,在這個叫做《荒原法案》的規定之內,有一個被稱為“采礦例外”的條款,即所有已獲準的開采項目將得以繼續開發挖掘,荒原地區的新的開采申請在1984前仍有可能獲得批準。在冰川峰腳下,就在這片荒原的中心,是一個寬度為八百米的銅礦脈。肯尼科特銅業公司對這部分礦藏握有開采權,可以在任何時間開挖。我們想趁該地區仍然在原始狀態時,到這里來看看。其他人都讓我代他們在小木屋的登記簿里注上他們的名字:查爾斯·帕克,地質學家,礦業工程師,他認為如果在白宮下面發現銅礦,那么白宮就該移走;戴維·布勞爾(David Brower),被美國國務活動家、聯邦議員斯圖爾特·尤德尊為“本國環境保護前沿陣地作用最大的個人”,也是環保組織地球之友的領導人;拉里·斯諾和蘭斯·布里格姆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學生,他們協助安排行程,必要時或許還得實施急救。
一只老鼠從木屋地底下躥了出來,在背包間急速鉆動,然后又躥回到木屋下。我們拾了些干柴,還打來了水。木屋旁有一掛小瀑布,水流湍急,一瀉而下。我們都換上了暖和的衣服和輕便的鞋子。一直穿著斜紋布短褲T恤和灰色意大利皮靴走路的布勞爾,換上了長袖的格子襯衫、布褲和一雙籃球鞋。雖然體型有些走形,布勞爾仍是一個頗有魅力的人。他身材高大。他有著粗壯的骨骼,結實的手腕,健壯的腳踝。他臉色紅潤細致,俊朗英氣,五官精致,比例勻稱,只是都小了點,相對他的體格而言可說太過精巧,或許這正表明他內心情感的細膩。他的聲音平靜深沉,極具說服力。牙齒潔白,微笑令人愉快。他當時快六十了,一頭白發凌亂無序。十九歲那年,布勞爾從大學退學,然后一頭扎進內華達山區。他一生都在捍衛這些山脈以及他所體會的它們所象征的意義。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正是他對山脈的摯愛,把他早早地從它們身邊遠遠拖開,拖進了被稱為摩天大樓的辦公樓中,拖進了國會的走廊上,拖進了臨時辦公的酒店房內,拖進了一場又一場的戰斗,直至形神俱疲(在環境保護的術語中,“戰斗”是環保主義者最重要工作,而環保讀物則是“戰斗陣地”)。由于常年攀登,布勞爾的皮膚帶著山地紅,每當他脫下濕透的襯衫時,就能看到他腹部的肌肉格紋。又有一只老鼠從地底下爬出,環顧四周,鼻尖顫動,然后跑掉了。
布里格姆:“再把你的鼠頭伸出來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布勞爾輕聲回應:“我們,才是入侵者。”
帕克脫掉他的靴子——加拿大制造的重磅皮靴——并換上了一雙涼鞋。他高深莫測地咧了咧嘴。他已經六十多了,也是滿頭銀發。大學時代,他曾經是一位運動員,時至今日,他依然結實精干,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時候會氣喘吁吁。從青年時代到現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歲月都花在了戶外,其中,花在荒原地區的比例最高。那天下午沿著小路上山時,他用手中的地質錘,不停地在一塊塊山巖表面上敲敲打打,還時不時地毫無目的地用地質錘的一端在沿途的樹樁上狠狠來那么一下。這些樹樁都是當初開路時所留下的。
“這是我很久以前養成的習慣——敲石頭,敲樹樁,”他說。
“為什么?”
“科迪亞克熊。我不想驚著它們。在非洲那邊,則是非洲豹和大猩猩。換句話說,不要驚著動物。”
帕克慢吞吞地說著。這并不是因為他有所猶豫,而是他那種與地質紀年相適宜的性格。他的下頜消瘦,灰色的眼睛充滿警覺,笑容有些飄忽不定,并且總是集中在一個嘴角。他比布勞爾長得還要高,從頭到腳都穿著卡其布的服裝,頭上戴著一頂有著長長帽舌的紗卡帽。
從山脈東端往里走不久就到了奇蘭湖。我們在那兒見到一個政府所立的形狀怪異的地標。這是一個標示牌,上面寫著:“你現在進入冰川峰荒原地區。”換句話說,“根據法令,再往前一步,你將進入一個保存完好的獨立世界,你將從文明進入荒原”。來到了這里,所謂荒原是這樣實實在在、觸手可及,就像進入另一個房間那樣。
帕克問道:“他們會讓我把地質錘帶進去嗎?”
“1984年以前都可以,”布勞爾應聲回答。
我們抬腳跨過了地界線。我說:“如果有一把地質錘,即便迷了路,我們也許還能找到一個新的銅礦。”
布勞爾回應:“如果你真的找到新的礦脈,我就在這里守著不讓你離開。”
我們進入了荒原。小道上滿是塵土。覆蓋在土路上的淺棕色的粉末是那么細,甚至不能被稱為砂子。帕克說這就是所謂的冰川粉,含在冰層中的研磨得極細的巖粉。是冰,遠古的冰和現代的冰。在我們的上方,在遠處,是層層疊疊的冰川遺跡——李曼冰川,蝶鞍冰川,瑪麗綠冰川。或許我們還應該期待,有一天會在一個叫什么利潤峰的地方找到一個公司冰川。蔚藍的天空萬里無云,這是喀斯喀特山脈中難忘的一天。布勞爾對沒有下雨有點失望。他解釋說,他不喜歡這種干燥無味的感覺,更欣賞雨后森林中那種水汽蒸騰,葉尖反射著陽光的美景和濕潤的感覺。他說他希望我們能在旅行結束前有幸遇上一場好雨。他步履緩慢地沿著土路上行,盡量保存體力,沿途還不時吃些隨手采來的糙莓和越橘。
“在喀斯喀特山脈沒有什么真正算得上年代久遠的巖石,”帕克一邊說著,一邊隨手在巖石上劃著。他從地上撿起一片淡色的黃綠相間的簾石,放在手中仔細翻看。沿著土路又往上走了二百米后,他用地質錘重重地敲了一塊突出的巖石說:“這是火山巖。”沒過幾分鐘,他又弄得碎石飛濺:“這是接觸巖。”某種程度上,布勞爾給逗樂了。他大笑起來,搖了搖頭。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帕克一起駕車穿越黑丘嶺,他會不時停下車來,坐在地上默默地審視著巖石。作為出生在特拉華州的男孩,他總是在收集不同種類的巖石,同時暢想著大西部的風貌。還在威爾明頓高中上學時,帕克就已收藏有五十多塊礦石。他有赤鐵石,孔雀石,方鉛石,鉻鐵石。“我想學習采礦,也不一定就要學開采地質學,”他說道,“我想深入到山巖內部,了解它們的構造。采礦一直深深地吸引著我。因為都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
土路對面幾里外的地方有一條鋸齒狀的山脊,在傍晚的余暉中泛著淡淡的紅色。“看見那里的紅色嗎?那是黃鐵礦,”帕克一邊指一邊說道,“經常會有銅礦伴生。如果我要在這里尋找銅礦,就到那邊去找。”不過,這里離我們想去看的銅礦地帶仍有十幾公里路要走,因此,我們沒離開原路。
我們在路旁看到了一棵巨大的花旗杉,它的直徑起碼有一米半,看起來才倒地不久。布勞爾說,看見這棵樹倒臥在這里,就可以判定木材公司還沒有機會看到它。這樣,我們才有機會觀察到樹木自然周期中的腐殖階段——森林在用這種方式要回屬于它的那份。這樣的感覺真不錯。如果死去的樹木不能在當地自然腐爛,那么,荒原的生態鏈就會被打斷。帕克沒說話,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心里。他的眼光在一棵杉樹樹樁的方孔處搜索。他用地質錘往樹樁的方向指了指,“那是紅冠啄木鳥。”我們繼續趕路。
來來回回走了一長段之字形的山路后,我們已經在不到四百米的距離中往上攀爬了兩百多米。我們在一條溪流邊停下休息,溪流時不時地漫過堤岸,騰空濺落,直下山腰。放眼四望,喀斯喀特山脈的每一處山坡,都有山泉盤流其間。水流從巖石的裂縫中噴涌而出,越過崖壁邊緣,一瀉而去。水沫四濺,霧氣升騰,飛流直下,純凈,陰寒。在這個地區,有足夠的融雪和降雨灌溉著利伯亞縣全境。當天上不降水時,太陽將高山之上的積雪融化,溪流沿著暗綠色的山坡順勢而下。在山坡的林線之上,在裸巖的襯托下,水流閃閃發光。每一個山地中的凹陷就形成一個小湖。而我們現在,正是在懸崖邊上,回望先前曾經走過的一個特別漂亮的湖泊。它就是哈特湖。涓涓溪流注水入湖,另一邊,湖水翻崖而過,變身為落差極大震耳欲聾的大瀑布。溪流被一系列池塘湖泊所割斷。所有這些形態各異的池塘邊長著榿樹、白楊、英格曼云杉等等;而在周圍的群山上,就在它們的峰線以下,是一片冰川和雪原的世界。布勞爾,就其內心而言可說是一個美學家,并常常樂意討論那些漂亮的景色。而在此刻,他緘口不言。帕克也沒說話。我想起了一位在國家公園服務署工作的朋友的話。他曾經說過:“冰川峰荒原可能就是全國所有國家公園中最美麗的地方了。銅礦開采就像用煤鏟去打一個漂亮女孩粉嫩的臉,或者就像在伊甸園里露天采礦。”
帕克用帽子擦了擦額頭。我把杯子浸入水中,請他喝。他猶豫了一下。“嘿,為什么不呢,”他最后這樣說。他拿起杯子,喝了點水,把杯子放下后他微笑了一下,擦了擦嘴,說:“這可是好東西。”
“這是融冰,是嗎?”
帕克點了點頭,又喝了一小口。
布勞爾也在喝著水。他喝水的杯子和我用的那個一模一樣——都是不銹鋼制,扁扁的,直徑很大,平底,他用一根繩子穿著當拎手——要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布勞爾用的水杯底上,有一行突出的字“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十七年了,布勞爾一直是塞拉俱樂部的執行董事——是它的領導者,主要策劃人,卓越的斗士。到了山中,塞拉俱樂部的登山客們無論吃喝什么東西,都會用塞拉俱樂部的杯子來盛。多年以來,我與布勞爾一起在各地荒原時,也確實從未見過他用其他器皿吃喝任何東西。以往,在上塞拉山區,他偶爾也會用一些薄荷葉片在他杯底的浮凸字母上擦一擦,再添些雪和威士忌,當作一種在高海拔地區的冰鎮薄荷酒來喝。不過在山里,他其實很少喝酒,而這次旅行也沒有準備威士忌。當天晚上,在避雪的小屋中,我們吃了些杯面、牛肉以及巧克力布丁,我們把背囊掛在高處的木椽上后,九點前就早早入睡了。我們睡在木架床上,真不知他們用了什么魔法能在這么狹小的屋子里架起那么多床來。第二天凌晨兩點,我們都醒了,一片漆黑中,有多個亮點在不同高度來回閃爍。
“他媽的是怎么回事?”
“這是什么東西?”
“那里是什么?”
“沒事,四個小可愛。四只非常美麗的棕白相間的草甸鼠,”布勞爾說道。
“噢,我的天哪,”帕克說著,轉身又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