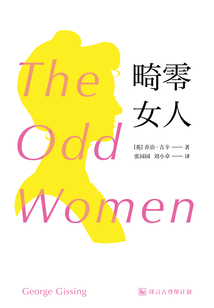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序
張園園
作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畸零女人》的作者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75.11.22—1903.12.28)似乎并不如與其同時期的狄更斯、左拉、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現(xiàn)實(shí)主義巨匠名氣響亮。然而他既是一位多產(chǎn)的作家,也同時涉獵廣泛。從1880年到1903年間,他一共發(fā)表了23部長篇小說,另有12部短篇故事集,死后還有數(shù)部作品出版,主題跨越工人階級的貧苦生活,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地位,還有英國海外僑民的自由思想。他的早期作品并沒有受到多少關(guān)注。直到19世紀(jì)晚期,他才逐漸獲得了應(yīng)有的地位,與托馬斯·哈代和喬治·梅瑞狄斯齊名。正如喬治·奧威爾所稱贊的,他是19世紀(jì)英國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在中國,吉辛似乎“默默無聞”,已翻譯出版的作品僅有其散文集《四季隨筆》《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人》和小說《新格拉布街》(又譯《新寒士街》)。此次有幸翻譯《畸零女人》,譯者希望吉辛的作品和思想能為更多人所了解。
《畸零女人》是吉辛于1893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曾有19世紀(jì)文學(xué)評論家稱其為“被人遺忘的作品”。然而它所關(guān)注的自愿獨(dú)身或最終找到婚姻之外的生活意義的女人——這一在評論家瑪格麗特·平克尼·艾倫(Margaret Pinckney Allen)看來鮮少受當(dāng)時其他作家承認(rèn)的群體——理應(yīng)不該被人遺忘。《畸零女人》探討了人類生活的永恒話題之一——婚姻與愛情,尤其著重討論了女性人生的意義與婚姻的關(guān)系。所謂“畸零”,即孤獨(dú)、孤單,而畸零的女人,按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定義,是那些無依無靠,無法進(jìn)入婚姻生活的女人。在當(dāng)時的社會里,這樣的女人是被同情的對象。因?yàn)楫?dāng)時女人的理想典型是做家中的“天使”,相夫教子既是女人的“sweet vocation”(即甜蜜的天職),也被認(rèn)為可以為女性帶來全部的快樂和滿足感,小說中的男性角色埃德蒙德·維德遜就是這類想法的絕佳代言人。書中部分女性人物因?yàn)槭艿竭@樣或那樣的限制而與婚姻無緣,這是對當(dāng)時男少女多的英國社會的現(xiàn)實(shí)寫照。不過吉辛并沒有拘泥于描述那種在爐邊紡紗織布、孤獨(dú)終老的典型老處女形象,他筆下的女性角色雖然或多或少都在一段時間內(nèi)或是終身背負(fù)著“畸零”的印記,但有的人是被迫單身,有的人則是自愿單身;有的人來自衣食無憂的中產(chǎn)家庭,有的人在底層掙扎并最終墮落風(fēng)塵;有的人雖然步入了婚姻殿堂,但遇人不淑,郁郁而終,有的人盡管孑然一身,卻能有自己熱愛的事業(yè)相伴。這些女人對婚姻和戀愛的態(tài)度不盡相同,而她們的抉擇、成長和命運(yùn)也是本書最值得玩味的部分。
小說著墨最多的兩位女性——莫妮卡·梅頓和蘿達(dá)·南恩——代表了畸零與婚姻的集中碰撞。莫妮卡天生麗質(zhì),在婚姻的角斗場上要比兩位年老色衰的姐姐機(jī)會多得多,家人對她的期待也是“一定得嫁人”。婚前的她性格柔弱,缺乏安全感,在面對倫敦女店員的艱辛生活和孤苦伶仃的人生時心懷畏懼。盡管瑪麗·巴福特小姐的女校讓她擺脫了女店員的身份,為她提供了學(xué)習(xí)深造的機(jī)會,但是她并不愿意繼續(xù),而是嫁給了年長自己很多、也并不適合自己的埃德蒙德·維德遜。婚后,維德遜枷鎖般的妒火卻讓她醒悟,她最終選擇逃離,可惜在生下孩子后一命嗚呼。莫妮卡的死是悲哀的,讓她殞命的不是畸零的生活,而正是婚姻——這一在社會看來締造女性幸福和價值的美麗搖籃。但是在她對婚姻的感悟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她雖然在婚后豐衣足食,但丈夫自私病態(tài)的占有欲讓她恍然悔悟,并終于明白了自己追求的不是安逸富裕,而是真正的愛情。她與丈夫的決裂表現(xiàn)了她的女性意識的崛起。
蘿達(dá)·南恩的形象與前者有很大不同。她的姓氏“Nunn”與“Nun”——即修女——相似,吉辛也許以此來暗示她是小說中探討的遺世獨(dú)立的女性典范。與瑪麗共同運(yùn)營女子學(xué)校的蘿達(dá)獨(dú)立堅強(qiáng),從不想依仗婚姻獲得面包。她要做畸零女人的楷模,讓她們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而不是慘遭嫌棄的對象。她在面對埃弗拉德·巴福特的求愛時不似莫妮卡與維德遜定下婚約時那么倉促;她思索再三,并勇敢地說出自己對事業(yè)的追求。在她與巴福特最后的那場談話里,她邁出了在當(dāng)時社會看來極為超越的一步,要求與后者建立自由結(jié)合,而非締結(jié)法律上的婚姻。然而蘿達(dá)也并非完美無缺,她有著同正常女人相似的對愛情的渴望。在對莫妮卡和巴福特的誤會尚未解除前,她也無法克制內(nèi)心翻江倒海的嫉妒。這都讓這個角色有血有肉,她與莫妮卡的和解也讓人看到了她從略帶虛榮甚至冷酷最終成長為真正理解女性命運(yùn)并為之奮斗的戰(zhàn)士。
小說中還有一位女性角色也不容忽視,她就是巴福特的堂姐瑪麗。瑪麗的溫柔善良與蘿達(dá)起初的激進(jìn)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也是畸零女人中的一員,但是她思想成熟,內(nèi)心包容,目標(biāo)明確,可以說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畸零是否一定意味著人生的失敗?作者的回答應(yīng)當(dāng)是否定的,從造成莫妮卡悲劇人生的婚姻和瑪麗、蘿達(dá)等女性充實(shí)的獨(dú)身生活中可見一斑。不適合的婚姻是“將就”的,是一種“恥辱”,而沒有壓迫、彼此尊重的關(guān)系才是值得我們推崇的婚戀。比起“兩個魔鬼過日子”,畸零的人生未嘗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除了對獨(dú)身女性這一群體的生活狀態(tài)的討論,誠如評論家斯坦利·奧爾登(Stanley Alden)所說的,吉辛寫人,寫生活,寫倫敦的一街一景,也將自己的經(jīng)歷揉進(jìn)小說。書中對倫敦女店員艱辛生活的描寫是對那個時代的生動反映:簡陋的住所,繁重的工作,粗鄙的環(huán)境,還有迷霧籠罩的倫敦仿佛讓人身臨其境。而小說中某些女性的剪影也能折射出作者的個人經(jīng)歷。吉辛只活到了46歲,有過兩段并不幸福的婚姻,最后在貧困和疾病纏身中逝世。他的第一段婚姻在世人看來并不光彩,謠傳他當(dāng)時的妻子瑪麗安·海倫·哈里森是一名妓女;為了能讓她從皮肉生意中解脫出來,吉辛甚至偷竊他人財物,最后鋃鐺入獄。然而婚后的瑪麗安酗酒成性,從小說中酩酊大醉的弗吉尼亞·梅頓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她的影子。而從小說中那些因?yàn)槟抑行邼松悴磺暗娜说睦又校x者也能看出吉辛與貧窮終其一生的斗爭。
當(dāng)然,吉辛也有他的局限。他畢竟不是女性主義作家,無法從根本上解析導(dǎo)致某些女性的悲劇的本源。他通過小說人物道出的對女性的辛辣諷刺(如針對巴福特的嫂子湯姆斯太太和朋友的妻子波普頓太太)夾雜著對自己不幸婚姻經(jīng)歷的悵惘。盡管《畸零女人》表達(dá)了對獨(dú)立女性的尊重和欽佩,但就連小說中女性解放的旗手蘿達(dá)也承認(rèn),有一些女性確實(shí)拖了男人事業(yè)的后腿,不過卻很少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即女性教育本身的嚴(yán)重缺失以及社會對女人角色的狹窄定義。在蘿達(dá)與巴福特有關(guān)男性失敗婚姻的交流中,兩人只是將婚姻的失敗歸結(jié)于女人的俗不可耐和男人社交圈的有限,卻并未真正觸及問題的本質(zhì)——男權(quán)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盡管如此,作為一部兩個世紀(jì)前的作品,《畸零女人》中所涉及的婚戀問題仍然為現(xiàn)代人所探討。吉辛借小說女主人公莫妮卡和蘿達(dá)之口,表達(dá)了對女人生命價值和婚姻本質(zhì)的理解,其思想的進(jìn)步程度足以令現(xiàn)代人側(cè)目。書中提起的一些想法就算是在兩百年后的今天也似乎并不一定能為所有人心平氣和地全盤接受,比如在蘿達(dá)眼中應(yīng)當(dāng)廢除的“女人不結(jié)婚就會荒廢一生”的舊思維,如果女人認(rèn)為婚姻是個錯誤,“她就有權(quán)擺脫這個束縛”,婚姻“試試又沒什么害處”等等。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已經(jīng)比兩個世紀(jì)前更加自信和自由,家庭也已經(jīng)不再是女性的唯一舞臺。比如小說中蘿達(dá)意欲嘗試、但最終未能實(shí)現(xiàn)的“自由結(jié)合”已經(jīng)在歐美國家屢見不鮮,人們也越發(fā)能以心平氣和的態(tài)度去對待那些選擇“獨(dú)善其身”的女人。在中國,我們似乎能為畸零女人找到一個有趣的同義詞,那就是“剩女”。有一天,當(dāng)人們談起這些暫時或決意獨(dú)身的女性時,會不會不再將她們的婚姻狀態(tài)作為定義她們畸零與否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讓我們拭目以待。
畸零也好,嫁娶也罷,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尋生活的意義。但愿我們能撇開形式的枷鎖,但愿我們追求的是永遠(yuǎn)不會畸零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