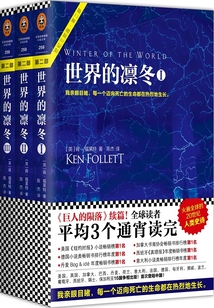
世界的凜冬(全集)
最新章節(jié)
書(shū)友吧 122評(píng)論第1章 1933年,柏林(1)
【紀(jì)念我的祖輩
湯姆和米妮·福萊特
亞瑟和貝茜·埃文斯】
卡拉知道父母快要吵架了。走進(jìn)廚房,她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敵意,如同二月暴風(fēng)雪前刮過(guò)柏林街道的寒風(fēng)。她真想轉(zhuǎn)身就走。
卡拉的父母很少吵架。他們大多數(shù)時(shí)候如膠似漆,好得有點(diǎn)過(guò)了頭。每當(dāng)他們?cè)谌饲坝H吻的時(shí)候,卡拉都覺(jué)得渾身不自在。她的朋友們覺(jué)得這很奇怪——他們的父母從來(lái)不這樣。她曾經(jīng)問(wèn)過(guò)母親一次。母親笑著對(duì)她說(shuō):“我們剛結(jié)婚,你父親就參戰(zhàn)了。”盡管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yǔ),但卡拉的母親出生在英國(guó),“我留在倫敦,你父親回德國(guó)參了軍。”這件事卡拉聽(tīng)了無(wú)數(shù)遍了,但母親不厭其煩地講,“我們本以為戰(zhàn)爭(zhēng)最多會(huì)持續(xù)三個(gè)月,結(jié)果我卻五年沒(méi)見(jiàn)到他。那時(shí)我老是在想,只要能摸一下他,我就滿(mǎn)足了。現(xiàn)在,我就是喜歡和他親熱。”
父親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母親是我認(rèn)識(shí)的最聰明的女人,”幾天前,他就在這間廚房里告訴卡拉,“所以我娶了她,這和……沒(méi)有關(guān)系。”他的聲音變小,和母親鬼鬼祟祟地笑著,就像十一歲的卡拉根本不懂性事。這太讓人尷尬了。
不過(guò),他們偶爾還是會(huì)吵架。卡拉知道他們什么時(shí)候會(huì)吵。現(xiàn)在,兩人眼看就要起沖突了。
他們坐在餐桌的兩頭。父親穿著灰色西裝、漿白襯衫,戴著黑色的絲綢領(lǐng)帶,和以往一樣神情嚴(yán)峻。盡管發(fā)際有些后移,馬甲下面的小腹有些微微隆起,但他的外表還是一如既往的整潔。可以看得出,他正盡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卡拉很熟悉這種表情。當(dāng)家人們做了觸怒他的事情時(shí),他總是這種表情。
父親手里拿著一份母親供稿的雜志。她在《社會(huì)民主黨人》雜志社工作,以“茉黛女士”的筆名為雜志撰寫(xi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閑話(huà)專(zhuān)欄。父親大聲朗讀起來(lái):“德國(guó)新總理阿道夫·希特勒閣下在興登堡總統(tǒng)[1]的招待會(huì)上完成了外交舞臺(tái)上的首秀。”
卡拉知道,總統(tǒng)是一國(guó)之尊。但他超然于日常的政務(wù)之上,只是扮演裁判官的角色。總理是政府的實(shí)際掌控者。盡管希特勒已經(jīng)當(dāng)選為總理,但他的納粹黨還沒(méi)有在議會(huì)取得多數(shù)席位——因此,至少現(xiàn)在,其他黨派還能控制納粹的倒行逆施。
父親像被人強(qiáng)迫談?wù)撓滤览锏奈畚锇阏Z(yǔ)帶反感:“他穿著燕尾服正裝,似乎非常難受。”
卡拉的母親一邊啜飲著咖啡,一邊看著窗外,似乎對(duì)大街上戴著手套和圍巾匆匆上班的行人很感興趣。和父親一樣,她也在強(qiáng)裝鎮(zhèn)定。卡拉很清楚,母親只是在等待合適的時(shí)機(jī)而已。
女仆艾達(dá)穿著圍裙,正在料理臺(tái)前切奶酪。她把一個(gè)裝著奶酪的盤(pán)子放在卡拉父親的面前,但他看也不看。“希特勒先生顯然對(duì)身著粉紅天鵝絨禮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大使夫人伊麗莎白·塞魯?shù)俜浅8信d趣。”
母親總喜歡對(duì)別人的穿著評(píng)頭論足。她說(shuō)這有助于讀者想象出筆下人物的形象。她也有一些非常不錯(cuò)的衣服,但時(shí)世艱難,母親已經(jīng)有好幾年沒(méi)買(mǎi)新衣服了。這天,她穿著一件大約在卡拉出生時(shí)買(mǎi)的天藍(lán)色羊絨長(zhǎng)裙,看上去非常苗條。
“身為一名猶太人,塞魯?shù)俜蛉耸莻€(gè)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希特勒相談甚歡。她乞求希特勒停止煽動(dòng)對(duì)猶太人的仇恨了嗎?”讀到這里,父親把雜志往餐桌上狠狠一摔。
好戲就要開(kāi)始了,卡拉心想。
“你知道這會(huì)惹惱納粹。”他說(shuō)。
“這正是我要的效果,”母親冷冷地說(shuō),“我情愿封筆也不寫(xiě)討好他們的東西。”
“別把他們?nèi)敲耍侨喝朔浅NkU(xiǎn)。”
母親的眼里滿(mǎn)是怒火。“沃爾特,不要對(duì)我發(fā)號(hào)施令。我知道他們很危險(xiǎn)——這正是我要和那群人對(duì)著干的原因。”
“我只是覺(jué)得沒(méi)有惹惱他們的必要。”
“你應(yīng)該在議會(huì)向他們發(fā)起攻擊。”父親是社會(huì)民主黨的議員。
“我只做理性的討論。”
又搞這套,卡拉心想。父親理性、謹(jǐn)慎,同時(shí)遵紀(jì)守法,而母親激進(jìn),且我行我素。父親沉靜地堅(jiān)守著自己的原則,母親則咄咄逼人地宣揚(yáng)自己的主張。他們永遠(yuǎn)無(wú)法取得一致。
父親補(bǔ)充道:“我不會(huì)故意惹那些納粹黨人發(fā)狂。”
“可能因?yàn)槟愀静荒軐?duì)他們?cè)斐扇魏蝹Α!?
父親被母親的快速反擊惹怒了,他高聲說(shuō)道:“用這種閑聊式的專(zhuān)欄文章就能摧毀他們了嗎?”
“我在嘲笑他們。”
“你是在攻擊他們。”
“這兩種我們都需要。”
父親越發(fā)生氣了。“茉黛,難道你不知道這樣做是在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險(xiǎn)中嗎?”
“正相反,不嘲笑才是真正的危險(xiǎn)。你難道沒(méi)有想過(guò),如果德國(guó)變成一個(gè)法西斯主義國(guó)家,我們的下一代會(huì)是什么樣嗎?”
這類(lèi)爭(zhēng)論總讓卡拉覺(jué)得不舒服。她不愿去想家人會(huì)陷入危險(xiǎn)。生活應(yīng)該一如既往。她希望每天早晨都能坐在廚房里,和分坐在餐桌兩邊的父母,以及在料理臺(tái)前忙碌的艾達(dá)待在一起,當(dāng)然還有她匆匆下樓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為什么要改變呢?
每天早飯時(shí),父母都會(huì)討論一些政治問(wèn)題。卡拉覺(jué)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們正計(jì)劃著讓德國(guó)變得更好。但最近這種交談?dòng)悬c(diǎn)變味了,他們似乎認(rèn)為德國(guó)正被一種可怕的危險(xiǎn)籠罩,卡拉卻想象不出這種危險(xiǎn)是什么。
父親說(shuō):“為了壓制希特勒和他的黨羽,我真的已經(jīng)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樣。但你總以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親的臉因憤怒而變得鐵青,“而當(dāng)我有所行動(dòng)時(shí),你卻譴責(zé)我把這個(gè)家置于險(xiǎn)境。”
“我這樣說(shuō)是有理由的。”父親說(shuō)。爭(zhēng)吵剛剛開(kāi)始,但這時(shí)埃里克晃蕩著書(shū)包像小馬駒一樣沖下樓梯,奔進(jìn)了餐廳。他比卡拉大兩歲,今年十三歲,上嘴唇已經(jīng)長(zhǎng)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須。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樣的日子已經(jīng)一去不返了,自從長(zhǎng)個(gè)兒以后,他就裝出一副認(rèn)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樣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實(shí)上,卡拉比埃里克聰明得多,知道很多他無(wú)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經(jīng)。
“你剛才彈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問(wèn)母親。
兄妹倆時(shí)常被母親的鋼琴聲吵醒。這架施坦威鋼琴和這棟房子都是他們的父親從自己的父母那里繼承來(lái)的。母親說(shuō)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彈一會(huì)兒琴。這天,母親彈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鳴曲和一首爵士樂(lè)。“這首爵士樂(lè)叫《猛虎》。”她告訴埃里克,“你想來(lái)點(diǎn)奶酪嗎?”
“爵士樂(lè)是頹廢的音樂(lè)。”埃里克說(shuō)。
“別瞎說(shuō)。”
艾達(dá)把一盤(pán)奶酪和切碎的香腸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進(jìn)嘴里。卡拉覺(jué)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難看。
父親的表情突然變得非常可怕。“埃里克,這些胡說(shuō)八道是誰(shuí)教給你的?”
“赫爾曼·布勞恩說(shuō)爵士樂(lè)是黑人發(fā)出的噪聲,根本不能算是音樂(lè)。”赫爾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親是納粹黨的一員。
“赫爾曼應(yīng)該嘗試一下。”父親看了母親一眼,神情緩和了些。母親對(duì)他笑了笑。父親接著說(shuō):“多年前你媽媽曾經(jīng)想教我彈拉格泰姆[2],可我總是掌握不好節(jié)拍。”
媽媽又笑了:“簡(jiǎn)直是對(duì)牛彈琴。”
爭(zhēng)執(zhí)結(jié)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氣。她感覺(jué)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氣地說(shuō)。
“才不是呢,”父親循循善誘地說(shuō),“如果一個(gè)黑人孩子在優(yōu)渥的家庭里長(zhǎng)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說(shuō)不定比你還聰明呢。”
“你胡說(shuō)。”埃里克有點(diǎn)氣急敗壞了。
母親插話(huà)進(jìn)來(lái):“傻孩子,不能和爸爸這樣說(shuō)話(huà)。”她的火已經(jīng)發(fā)完了,此時(shí)的語(yǔ)調(diào)里帶著一絲倦意,“你和赫爾曼·布勞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shuō)什么。”
埃里克說(shuō):“雅利安人是最優(yōu)秀的人種——我們將統(tǒng)治世界。”
“你的納粹朋友根本不知道歷史,”父親說(shuō),“德國(guó)人還生活在洞穴里的時(shí)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紀(jì)時(shí)曾統(tǒng)治世界——那時(shí)穆斯林已經(jīng)學(xué)會(huì)了算術(shù),而德國(guó)的王子們還不會(huì)寫(xiě)自己的名字。一個(gè)人是不是聰明,和種族無(wú)關(guān)。”
卡拉皺著眉頭問(wèn):“那和什么有關(guān)系呢?”
父親慈愛(ài)地看著她:“這是個(gè)很好的問(wèn)題,你能提出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就已經(jīng)很聰明了。”父親的贊賞讓卡拉很開(kāi)心,“文明興衰起伏——中國(guó)人、阿茲特克人、羅馬人都曾經(jīng)歷過(guò)——但其中的原因誰(shuí)都說(shuō)不清楚。”
“都快點(diǎn)吃完,穿上外套,”母親說(shuō),“你們要遲到了。”
父親從馬甲口袋里拿出懷表,揚(yáng)起眉毛看了一眼:“還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蘭克家去,”母親說(shuō),“她們學(xué)校停課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爐——我打算讓卡拉和弗里達(dá)待上一天。”
弗里達(dá)·弗蘭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們的母親也是密友。弗里達(dá)的母親莫妮卡,年輕時(shí)甚至還和卡拉的父親談過(guò)戀愛(ài)——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達(dá)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檳后告訴她們的。
父親問(wèn):“為什么不讓艾達(dá)照看卡拉?”
“艾達(dá)要去看醫(yī)生。”
“哦。”
卡拉希望父親追問(wèn)一下艾達(dá)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卻像早就知道了似的點(diǎn)點(diǎn)頭,把表收了起來(lái)。卡拉打算開(kāi)口問(wèn),但又覺(jué)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問(wèn)母親,然而卡拉很快就把這事給忘了。
爸爸穿著黑色的長(zhǎng)大衣先出了門(mén)。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們一樣隨意地搭在頭上,好像隨時(shí)會(huì)掉下來(lái)似的——然后跟著父親走了。
卡拉和母親幫艾達(dá)收拾餐桌。卡拉和艾達(dá)的感情非常好,上學(xué)之前,因?yàn)槟赣H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達(dá)看護(hù)著。艾達(dá)還沒(méi)結(jié)婚,她二十九歲,長(zhǎng)相普通,不過(guò)笑起來(lái)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羅·胡貝爾約會(huì)過(guò)一段日子,但這段感情無(wú)果而終。
卡拉和母親站在走廊的鏡子前戴帽子。母親的動(dòng)作不緊不慢。她選擇了一頂深藍(lán)色窄邊圓呢帽,樣式很大眾,不過(guò)她刻意斜戴著,看起來(lái)有幾分俏皮。卡拉把編織絨線(xiàn)帽戴在頭上,尋思將來(lái)能否像母親這般有風(fēng)格。媽媽看上去像個(gè)戰(zhàn)爭(zhēng)女神,脖子、下巴和顴骨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來(lái)的。她迷人極了,沒(méi)錯(cuò),但確實(shí)談不上漂亮。卡拉和母親一樣擁有黑色頭發(fā)和綠色眼眸,但比起雕像倒更像是個(gè)胖娃娃。她曾偶然偷聽(tīng)到奶奶對(duì)母親說(shuō):“看著吧,丑小鴨終有一天會(huì)長(zhǎng)成白天鵝的。”卡拉還在等著那一天的到來(lái)。
等母親打扮好以后,母女二人一起出門(mén)了。她們家位于市中心的米特老城區(qū),在一排優(yōu)雅高大的連棟住宅之中,這些房子是當(dāng)初為了像卡拉爺爺那樣在附近的政府大樓上班的高官和軍隊(duì)官員建造的。
卡拉和母親先搭乘電車(chē),沿著菩提樹(shù)下大街往前,然后轉(zhuǎn)乘地鐵從弗里德里希大街坐到動(dòng)物園站。弗蘭克一家住在柏林西南市郊的勛伯格。
卡拉盼望著見(jiàn)到弗里達(dá)的哥哥,十四歲的沃納。她喜歡沃納。有時(shí)卡拉和弗里達(dá)會(huì)想象著嫁給對(duì)方的兄長(zhǎng),做鄰居,彼此的孩子也成為好朋友。弗里達(dá)認(rèn)為這只是個(gè)游戲,但卡拉暗自當(dāng)真了。沃納英俊成熟,一點(diǎn)兒不像埃里克那么蠢。卡拉臥室的玩具小屋里放了張迷你床,床上并排睡著一對(duì)玩偶夫婦,卡拉私下里把他們叫作“卡拉和沃納”,沒(méi)人知道這個(gè)秘密,連弗里達(dá)都不知道。
弗里達(dá)還有個(gè)七歲的弟弟阿克謝爾,但他生下來(lái)就脊柱開(kāi)裂,必須長(zhǎng)年接受治療。現(xiàn)住在柏林市郊的一所特殊醫(yī)院里。
一路上,母親都想著心事。“希望一切都能順利。”下地鐵時(shí)她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語(yǔ)。
“肯定順利,”卡拉說(shuō),“我和弗里達(dá)會(huì)玩得很開(kāi)心。”
“我指的不是這個(gè),我是說(shuō)那篇關(guān)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們會(huì)有危險(xiǎn)嗎?爸爸說(shuō)的是對(duì)的嗎?”
“你爸爸通常都是對(duì)的。”
“如果惹惱了納粹,我們會(huì)怎么樣啊?”
媽媽古怪地盯了她好一會(huì)兒,然后說(shuō):“老天,我?guī)銇?lái)的是個(gè)怎樣的世界啊!”接著,兩人都不說(shuō)話(huà)了。
步行了十分鐘以后,她們抵達(dá)了一座掩映在大花園里的別墅。弗蘭克一家很有錢(qián),弗里達(dá)的父親路德維希,擁有一間生產(chǎn)收音機(jī)的工廠。車(chē)道上停著兩輛車(chē),閃亮的黑色大轎車(chē)是弗蘭克先生的,已經(jīng)啟動(dòng)了,排放著一團(tuán)團(tuán)尾氣。司機(jī)瑞特穿著一身制服,褲腿塞在長(zhǎng)筒靴里,手拿帽子隨時(shí)準(zhǔn)備為雇主打開(kāi)車(chē)門(mén)。他鞠了一躬,說(shuō):“早上好,馮·烏爾里希夫人。”
另一輛是只有雙人座的綠色小車(chē)。一個(gè)留著灰白胡子的矮個(gè)子男人拎著皮箱從別墅里出來(lái),坐進(jìn)車(chē)?yán)锖螅隽伺雒弊酉蚰赣H致意。“不知道洛特曼醫(yī)生這么早來(lái)干嗎。”母親不安地說(shuō)。
她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弗里達(dá)的母親,高大的滿(mǎn)頭紅發(fā)的莫妮卡走到門(mén)口,臉色蒼白,神情焦急。她沒(méi)有招呼母女倆進(jìn)門(mén),而是像擋著她們似的站在門(mén)口。“弗里達(dá)出麻疹了。”
“太可憐了!”母親說(shuō),“她怎么樣了?”
“她又發(fā)燒又咳嗽,病得相當(dāng)重。不過(guò)洛特曼說(shuō)她會(huì)好起來(lái)的。但她必須接受隔離。”
“這是自然,你得過(guò)麻疹嗎?”
“得過(guò),小時(shí)候得過(guò)。”
“你們家的沃納也得過(guò)——我記得他當(dāng)時(shí)身上滿(mǎn)是可怕的疹子。你丈夫得過(guò)嗎?”母親問(wèn)。
“魯?shù)蟍3]小時(shí)候也得過(guò)。”
兩位母親把目光投向卡拉。卡拉沒(méi)得過(guò)麻疹。她意識(shí)到,這意味著自己沒(méi)法和弗里達(dá)一起玩了。
卡拉很失望,但母親受到的打擊更大。“這周的雜志是選舉特刊——我可不能請(qǐng)假。”她似乎心煩意亂。大人們非常關(guān)心下周舉行的大選,卡拉的父母擔(dān)心納粹會(huì)在選舉中獲勝,從而取得政府的主導(dǎo)權(quán)。“另外,倫敦有個(gè)老友今天會(huì)來(lái)看我。不知道能不能讓沃爾特請(qǐng)一天假,照看下卡拉?”
莫妮卡說(shuō):“為什么不打個(gè)電話(huà)給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