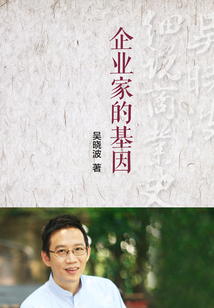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8評論第1章 企業家人物傳
王石的“基因”是哪里來的?
我對百年中國公司史的關注,最初是被萬科的王石勾起來的。2004年的深秋,王石來杭州,約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很快,這一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閑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蕩三十年》的寫作,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氣質,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在過去的十來年里,最頻繁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體是清末胡雪巖、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實在很難從這些商人事跡中尋找到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基因,它們更多是傳統農業社會及官商文明的產物。那么,中國企業家的生命基因到底應該從哪里開始追源?
后世史家常常喟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后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兩個國家——美國與日本——也剛剛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美國在1861年結束了南北內戰,在當時,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的3%,全美超過8000人的城市為141個,鋼鐵產量還不足100萬噸。1865年,后來成為美國第一個首富的、30歲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伙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提出購買機器、投資建鐵廠。1871年,J.P.摩根與人合伙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其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胡氏家財2000萬余兩,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那么,百年之后,為什么摩根仍在華爾街,而“紅頂商人”已成江南舊事?
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幾乎就在曾國藩發動洋務運動時,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正發生驚天動地的事情。一個叫西鄉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條鐵路、第一家現代銀行、第一家紡織工廠的出現,都與中國十分接近。那么,為什么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比美國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國公司的衍變,最讓人唏噓的是,它的演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體的輪替所打斷,根據我的計算,幾乎每隔30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革命性的顛覆。過去,中國企業家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也顯得十分的曖昧。根據黃仁宇的看法,“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費正清則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經濟,至少在1911-1949之間,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
也許從三十年來看,我們取得了無人可比的商業奇跡,不過,如果把歷史的寬度拉開,我們的驕傲會削弱一點,而不安和憂慮則會加重。王石在數年前的那道追問,會不會成為一場商業反思的起點?
胡雪巖是怎么破產的?
近現代商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發生在1884年,主角是當時首富胡雪巖,結果是他倒掉了。
胡雪巖活著的時候就已是一個傳奇。他靠為左宗棠采運軍餉起家,在短短20年內一躍成為全國首富,還是清朝300年唯一被賜穿黃馬褂的商人。1882年,胡雪巖手握1000萬兩以上的巨額現金,是去辦洋務,還是倒賣生絲,竟一時躊躇。
胡雪巖對洋務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的時候,所有購買外商機器、軍火事務都是由他一手操辦。1882年1月,他給恩公左宗棠寫信,表示愿意出資獨力建設長江沿岸電報。可是,當時主管洋務的卻是李鴻章,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死對頭。這讓深諳官場門道的胡雪巖十分遲疑。
第二條路就是倒賣生絲。自晚明以來,江浙一帶就是全國紡織業的中心。而19世紀60年代之后,英美各國開始在上海開設機械繅絲廠,中國傳統手工繅絲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根本無法與機械繅絲競爭。洋商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興旺百年的江南紡織業迅速沒落。
目睹此景,胡雪巖認為商機浮現。繅絲產業蒸蒸日上,而原材料生絲卻價格日跌,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據他的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另外,還有資訊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里,歐洲農業遭受天旱,生絲收成減產。基于這些判斷,首富胡雪巖出手,高調做莊。百年企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爆發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購進生絲8000包,到10月達1.4萬包。晚清學者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記錄了這場商戰的慘烈: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向胡說愿加利一千萬兩,胡非要一千二百萬兩不可。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巖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則邀請絲業同行合議,共同收盡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
一開始,胡氏戰略似乎奏效。西方學者斯坦利在《晚清財政》一書中記錄,1882年9月,上海一級生絲價格已高漲至17先令4便士,而在倫敦交易所的價格僅為16先令3便士。國內價格反超國際期貨價。1883年8月,大商戰進入決戰時刻,胡雪巖前后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屏氣而作壁上觀。
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之一,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暫緩,消息傳回中國,軍心開始動搖。更大的變數是,中法因越南問題交惡,爆發戰爭。1883年10月,法國軍艦駛抵上海吳淞口,揚言進攻江南制造局,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爆發,貿易全面停頓。
世事如此,胡雪巖已無力回天。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巖不得不開始拋售,損失以千萬兩計。生絲對搏失利,很快影響到“堅如磐石”的錢莊生意,可怕的擠兌風潮出現了,先是杭州總舵關門,繼而波及北京、福州、鎮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個字號。12月5日,阜康錢莊宣告破產。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對胡雪巖革職查抄,嚴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從,在圣旨到來之前,就非常“及時”地郁郁而死了。
“紅頂商人”以一種莽撞和壯烈的方式挑戰英美紡織公司,這應該是傳統商業力量在技術和工業模式都處絕對劣勢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絕地反擊。他的破產,宣告了傳統商人階層的集體殞落。“三大商幫”中的兩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紡織業徹底崩盤。
杜月笙販毒記
杜月笙建的杜氏祠堂成了遠東最大的地下嗎啡和海洛因加工廠;甚至有人說,當時全球每8包海洛因中有7包出自杜月笙。
鴉片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符號化的商品”。在19世紀初,英國商人靠它敲開了封閉的帝國大門,造成白銀大量外流,終在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19世紀末,英國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鴉片生意,而生意猶在,成為各地軍閥最重要的稅收來源。
1927年,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國禁煙局(后來更名為全國禁煙委員會),名為禁煙,實則專營。根據當時的規定,鴉片煙癮富有者每年要繳納30元的注冊費,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煙局買到鴉片煙并可免被拘留,那些臨時吸食的人則每袋征收0.3元。這一“禁煙政策”使得吸食和銷售鴉片在華東一帶再次成為合法而公開的生意。僅1929年,國民政府從上海、江蘇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萬元禁煙稅。《時代》在1931年4月的報道中諷刺地評論說:“如果精明的宋部長真的把鴉片裝在他的財政部的戰車上,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就能找到一種平衡中國預算的方法。”
政府販毒,當然需要一個商業上的合作者,被選中的人就是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這是一個很多年后仍然難以準確評價的人,他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領袖、政府的忠誠合作者、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眾多企業的所有者和一個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這些顯赫的頭銜:法租界公董局華人董事、上海總商會監委委員、上海中匯銀行和東匯銀行董事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華豐造紙公司董事,以及上海急救醫院董事長、上海正始中學創建人等等。唯一當面采訪過杜月笙的外國記者伊洛娜·拉爾夫·蘇絲在《魚翅與小米》一書中記錄了第一次見到此人時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長長的雙臂毫無目的地來回擺動。鴨蛋形的頭顯得很長,頭發卻剪得很短,前額好象向后去了一大塊,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黃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嘔的煙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只軟弱無力的冷冰冰的手。”因為與蔣介石關系密切,杜月笙被授予少將軍銜。全國禁煙局成立后,他被任命為領導者。
杜月笙的膽大妄為,在后世人看來十分具有戲劇性。曾經是蔣介石經濟顧問的英國人弗雷德里克·李茲·羅斯記錄了一個故事:孔祥熙是蔣介石的“連襟”兼財政大管家,是極其霸道的一個人。1928年,孔的夫人宋藹齡在跟杜月笙的交談中透露政府將在外匯交易中采取某種應急措施,杜回去后當即進行投機操作。
誰料,政策突變,杜月笙損失了5萬英鎊。杜要求賠償,孔祥熙斷然拒絕,“那天晚上,一口頭號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門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銀行董事會緊急會議,一致同意補償在外匯市場上蒙受損失的“愛國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東的家鄉高橋建成杜氏祠堂,轟動一時,據稱有8萬人參加了落成慶典。蔣介石親送匾額“孝思不匱”祝賀。席盡人散后,這個豪華的祠堂就成了遠東最大的地下嗎啡和海洛因加工廠。
除了在國內販售,杜月笙的鴉片生意還融入到了全球市場,在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當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這條通暢的“全球銷售網絡”: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內管理,這就構成了一個從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伊洛娜·拉爾夫·蘇絲認為,“杜月笙是強大的國際販毒集團的中方伙伴,這個集團的活動范圍已擴展到加拿大、美國和拉美各國”。美國警方曾經收繳到來自中國的毒品,“海洛因盒子上都打著全國禁煙局的各種官方印記”。有人甚至計算,當時全球的8包海洛因中,就有7包出自杜月笙。
靠蔣介石慷慨的毒品專營,杜月笙賺到了最多的錢,他以同樣的慷慨方式回報前者。在1935年,他出資向美國柯蒂斯·賴特公司訂購了120架軍用飛機,全數捐贈給國民政府。1936年,為了慶祝蔣介石50大壽,杜月笙送飛機一架,并將之命名為“上海禁煙號”。
虞洽卿怎樣“背叛”了自己
近段時間,在研讀民國商業史的時候,我常常好奇地想要知道,在1927年2月的一個春夜,商人虞洽卿與同鄉蔣介石到底進行了怎樣的一番對話?在我看來,整整80年前的那場至今無從得知細節的對話,對中國商人階層的集體命運造成了讓人扼腕的改變。
那場神秘對話的背景是這樣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抵達南昌,劍鋒直指上海。在此背景下,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代表上海商人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見北伐軍總司令、比他小20歲的寧波老鄉蔣介石。
這時候,擺在虞洽卿們面前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其一,上海當時的實際控制人軍閥孫傳芳提出了一個“大上海計劃”,建議由軍人、文人和商人組成一個治理集團;其二,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組織也在積極活動,上年10月,共產黨人周恩來組織發動工人進行武裝暴動,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積極籌劃第二次行動;其三,就是投靠以三民主義為號召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日后可見,上海商人對舊式軍閥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作為既得利益階層,他們與勞工階層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則上也南轅北轍。虞洽卿理想中的出路是實現上海自治,在他看來,與同鄉蔣介石結盟,將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標。
虞洽卿與蔣介石在南昌相晤甚歡。沒有確鑿的史料顯示,他們具體達成了怎樣的默契,不過,日后事態的演變可對此進行清晰的推測。
3月21日,上海勞工發動武裝起義成功,暴動者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虞洽卿被任命為19位臨時政府委員之一。對此任命,他不置可否。
3月26日,蔣介石軍隊進城。當晚,虞洽卿即趕到楓林橋公署拜見蔣介石。其后數日,他接連安排上海各界行業公會的大商人與蔣一一會面,眾商人承諾向蔣認捐500萬元,“用于維持上海安定”。便是在商人階層的合謀與支持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民黨部隊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工人武器槍支1700余條,死傷300余人。當日,虞洽卿等4個名列臨時政府委員的知名商人宣布辭職,國共破裂與工商決裂同時昭示天下。
追求自治的上海商人最終選擇用一種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解決”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之間的矛盾,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切齒黯然的諷刺。他們借蔣氏的槍炮爽快地達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們不會想到的是,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劇的開幕。
“四·一二”事變后不久,蔣介石即以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名義,下令將上海總商會及會董一體解散。之后,蔣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牽制的策略,與一個又一個商人組織分別談判,使其不可能進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進國民黨的機構中。那些不順從的商人則被認定為賣國的“買辦型商人”,受到打擊或者清理。1927年7月,蔣介石頒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從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業組織都要受到上海市社會局的監督。行業間一切職業上的爭端,都要由市政府來解決,收集各種經濟統計資料,辦理各種慈善事業,也都由市政府負責。
這些接踵發生的突變,顯然大大出乎虞洽卿的預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獨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團體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資本主義。自1911年之后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繁榮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國學者瑪麗·貝熱爾評論說,“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斯言悠悠,可謂泣血之論。
再說席家
上海出現的第一家外資銀行是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稱東方銀行、東亞銀行),開設于1847年,它進入中國后就開始發行鈔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帶。隨后,外國銀行相繼進入,上海漸漸成為遠東最重要的金融重鎮。到1890年前后,沿外灘一帶,已經集中了眾多外國銀行,黃浦灘12號為英資匯豐銀行、14號德資德華銀行、15號華俄道勝銀行、18號英資麥加利(渣打)銀行、31號日資橫濱正金銀行,其他還有英資有利銀行、法資東方匯理銀行等等。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控制了中國金融的命脈。
在這些外資銀行中,以匯豐銀行最為顯赫。時人稱,“蓋吾國關稅之收入,必解至匯豐,故匯豐操縱金融之勢力尤偉”。它長期控制中國對外匯率,一直到1935年,匯豐每日的外匯牌價仍被視為上海市場的正式牌價。在匯豐的壯大過程中,東山席家的功勞最為突出,從1874年起,席氏祖孫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襲匯豐大買辦的位置前后長達55年,這是一項十分驚人的記錄。
席正甫只在老家東山鄉下讀過幾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頭腦機靈,善于經略中洋和官商關系。在促成李鴻章的200萬元鹽稅擔保借款的當年,他就被提升為大買辦,從此,匯豐等外資銀行代替已顯頹勢的山西票商成為了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臺袁樹勛是換過貼的結拜兄弟,這讓匯豐在上海官場有了特別的優勢。當時,朝廷最炙手可熱的兩個漢臣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關系一向惡劣,席正甫卻跟他們以及他們的“錢袋子”盛宣懷和胡雪巖都保持了很不錯的交往。在李鴻章的保舉下,他還被授予二品銜紅頂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匯豐銀行先后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干線的貸款,其獲利之厚非常驚人。
席正甫為人極其低調,很少參加社會公共活動。這個隱身在幕后的人數十年中卻默默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家族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界逐一滲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
除了子孫繁茂之外,席家還與當時上海的一些望族結成了“姻婭聯盟”,如席家與另外一個買辦世家沈家的關系就盤根錯節,不但男女婚姻頻繁,甚至席正甫的一個同父異母弟弟席素恒還過繼給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遜洋行擔任大買辦長達35年。在19世紀末期,沙遜與匯豐、太古和英美煙草號稱英資在中國的四大壟斷集團,席家與沈家的結姻讓匯豐與沙遜在業務上互通有無,更加強勢霸道。
席家與民國顯要的關系也是十分復雜親密。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國大學同學,還有一個孫子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的弟弟宋子良。這使得匯豐在清廷滅亡之后,仍然能夠與民國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席氏子弟曾當過中國銀行的官股董事、總經理、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還出任中央造紙廠的廠長。
如此錯綜龐雜的生意和社會關系,讓席家變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虛言。在買辦階層崛起之前的兩百年間,國內商業多為晉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別在長江流域,靠販鹽和生絲買賣起家的徽商勢力最盛,然而到19世紀后期,買辦財勢已隱然超越,當時上海便有諺語稱,“徽幫人再狠,見了山上幫(指東山幫),還得忍一忍。”因為幾輩人在銀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專業上的能力獨步天下。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隨外資銀行退出了內地,他們投資的地產和實業股份也全數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種“席家本幫菜”流行于滬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間。喜歡它的時尚人士不少,卻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來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