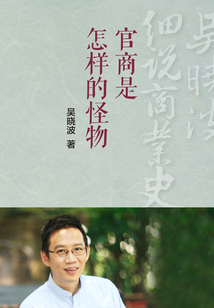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7評論第1章 官商人物傳
蔣經國“打虎”是怎樣慘敗的?
蔣經國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黨國軀體”上實施了一次電擊。可是,接下來的一只“老虎”終于是他打不動的了。
一個國家如果搞市場經濟,會有好壞之別。最壞的那種,就是官僚資本與市場資本的劣性組合,一旦這種資本組合成為定勢,經濟就將不妙。我這樣說,大家沒有感覺,好吧,說一個六十一年前發生在上海的“打虎”故事給各位聽。
話說1948年,國民政府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在經濟治理上則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為了控制物價飛漲、打擊投機倒賣,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的大兒子、時年38歲的蔣經國親自督戰上海。8月20日,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了十萬青年大檢閱,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沿路高喊“嚴格執行八一九限價”、“不準囤積居奇”、“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幾天后,他兩次率領上海六個軍警單位,全副武裝地到全市的商品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進行搜查。
蔣經國深知改革的對象到底是誰,他在日記里寫道:“擾亂金融市場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始。”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只都是“老虎”。
8月21日的《大公報》刊出記者季崇威的新聞稿稱:“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從南京乘夜車抵滬,一個上午向市場拋售3000萬股永紗(永安紗廠),照昨天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大約可獲利四五千億元。”
此文一出,市場嘩然,幣制改革為國家核心機密,竟然有人搶先得悉倒賣獲利,蔣經國用槍逼著交易所交出賬目,查出19日拋售股票的兩個大戶,一個名叫李國蘭,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陶供出自己是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機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被處決。另一個大戶名叫杜維屏,竟然是中國黑社會老大、蔣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兒子。蔣經國也不手軟,下令逮捕杜維屏,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8個月。
小蔣連小杜都敢打,算是動了真格,在隨后一個多月里,64名參與投機的商人被關入監獄。在他的鐵腕打擊下,上海的物價一度穩定,市民們乖乖地排隊將手中的黃金、美鈔換成金圓券。蔣經國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日夜輪番接見滬上企業家,奉勸他們把硬通貨拿出來。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
蔣經國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黨國軀體”上實施了一次電擊,他希望有奇跡能夠出現。可是,接下來的一只“老虎”終于是他打不動的了,它的名字叫揚子公司。
揚子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沒有生育,對這個大外甥視如己出,最是寵愛。在過去的幾年里,揚子公司一直是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業,它又是上海最囂張的囤積大戶。10月7日,蔣經國終于對揚子公司動手了,他下令搜查揚子公司上海總部并查封該公司的所有倉庫。第二天,國內各大報爭相報道“揚子公司囤積案”,“清算豪門”之聲陡起。
宋子文是個什么樣的“怪物”?
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產的流失為對照的,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
傅斯年稱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宋子文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因此傅斯年說:“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宋子文“走開”半年后,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去接見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談在廣東開礦的事宜,接著跟潘宜公司接洽黃埔港的建設工程,決定把海南的鐵礦石賣運日本。以他過往的行為來看,實在分不清這些到底是公事還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跟孔祥熙一樣,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至今是一個謎。《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亞洲《華爾街日報》則把他列入人類歷史上曾經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后人研究宋子文這個“大怪物”,不僅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錢,更在于他是一個怎樣的“制度性產物”。
在中國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于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制度層面進行反思和杜絕。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事實上,在中西方的哲學傳統中,思想家們從來不相信有一種“徹底的惡”。中國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學里,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惡意”來描述惡行背后、可理解的動機。因此阿倫特認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對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須建立在對經濟制度的研究上。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臺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談及孔宋模式與制度的互動。他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確實沒有問題,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著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就能得到外匯。每個人都得先申請進口必要的貨物,但他們卻有優先進口權,因此,盡管他們的確從中國人民的血汗中發了大財,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為。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在近現代的百年企業史上,出現了三個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巖,二是盛宣懷,三是孔宋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他們的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
通過胡、盛及孔宋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暴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中央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力不是在減弱,而是在逐漸加強,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制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現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來進行——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因為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產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臺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后,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并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嘆,孔宋下臺,官僚資本“未傷毫末”。
在某種意義上,對孔宋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
中國相紙之父
年輕的林希之決定了“要在感光材料方面為中國人爭一口氣”。然而在文革中,他的生命與事業都走到了最黑暗的盡頭。
1949年6月2日,中國第一張原始性氯素相紙在廣東汕頭市德興路86號一間簡陋的化學實驗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時年28歲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應熙,出生富商家庭,1946年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化學系就讀。念書期間曾有一個外籍教師在他面前譏誚過中國工業的落后,這件事一直刺痛著他的心。他說:“外國人能做的事,難道中國人就不能做嗎?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為中國人爭一口氣。”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鄉汕頭,專心致志地開始了感光化學實驗工作,籌辦起“公元實驗室”。他追捧的偶像是美國企業家喬治·伊士曼,后者在1886年發明了卷式感光膠卷,從而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照相的歷史。
1952年10月,公元實驗室制成中國第一張性能接近進口相紙的感光印相紙。次年4月1日,中國第一家感光企業——汕頭公元攝影化學廠建立,林希之任副廠長、總工程師。1954年7月,私營的公元廠第一批參加公私合營,林希之設計研制成功“空氣調理干燥法”生產工藝。1956年,公元廠成功組織研制了黑白膠卷、黑白電影正(負)片、黑白高速照相膠片、X光膠片、印刷制版系列膠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電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廠的努力下,中國靠進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從此逐步扭轉,不久便有相紙、膠卷出口遠銷國外。
林希之身體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結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經營工作更是讓他的健康狀況非常不好,近乎傷殘。他的夫人回憶,林希之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由于右臂無力,經常會從車上跌下來,他從地上爬起來,又繼續趕路。這在汕頭,竟成一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既有外僑關系又是“反動權威”的林希之從一開始就遭到殘酷迫害,他被關進“牛欄”,一次又一次地抄家,科技資料被銷毀,器材被砸爛。生在他喉頭的一顆惡瘤日漸增大,后來竟像雞蛋一般,使他難以進食,時常吐血、盜汗、痙攣、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欄”里,就把他放了出來。林希之一回到家,就忍著劇痛,又埋頭工作。他把家中的幾個收音機拆成零件重新組合,拆了又裝,裝了又拆,研究一種提高軟片感光度的新技術。
10月,48歲的林希之在自家老宅樓梯下一個沒有陽光的小黑屋里去世,他的生命與事業都走到了最黑暗的盡頭。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沒有完成任務。”
至80年代,汕頭公元的主要產品已發展至黑白相紙、人相膠片、膠卷、X光膠片和印刷制版膠片等五大類42個品種,相紙產量居全國首位。1986年,國家投入9億多元巨資,公元引進了日本富士膠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產線,但由于種種因素,投產不到一年就陷入停產、半停產困境。到90年代初,公元負債高達48億元。1994年,國務院作出決策,公元以1.8億美元的價格將彩色生產線轉讓給美國柯達公司,而柯達的創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喬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達因連年虧損,宣布永久關閉公元廠。
2003年,財經作家袁衛東受柯達邀請,撰寫一本關于柯達在中國的書籍。他到汕頭采訪,意外地“發現”了久被遺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書中寫道:
“在木棉花盛開的初春,穿過臟亂的露天市場來到民生路24號,這是公元創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們幾乎難以辨認,因為那里幾乎是廢墟。我想起一個月前,在羅切斯特飄雪的清晨,一行中國記者參觀喬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傳記中關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靜靜躺在那里,仿佛時間還停留在一個世紀前充滿風琴聲的日子。而在房間里靜靜綻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雛菊,讓我莫名的感動。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對締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這里,是苦澀,是對歷史驚人的遺忘和冷漠,甚至踐踏這是一代中國人的悲情。”
后來的中國人不應該忘記林希之。盡管以成敗而論,這個性情溫和、命運悲慘的客家人什么也沒有留下。
那個提出蘇南模式的人今年99歲了
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但他憑借自己的敏銳,最早提出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1939年,29歲的費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經濟》一書,日后它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其實沒有“江村”這么一個村莊,它的原型叫開弦弓村,在距離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蘇省吳江市震澤鎮。
這本書的誘因是一個青春悲劇。1935年秋天,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做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王同惠為了救他不慎墜淵身亡。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費孝通來到開弦弓村,在這里,他開始了一次細致的田野調查。3年后費孝通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它被看成是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不過,它的經濟學意義從未被發現。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到1970年代,沒有一個國家嘗試在農村培植自己的工業基礎,因為這是反大工業的,是可笑的。
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而他的觀點在經濟學界受到關注是從批判開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歸的開弦弓村做調研,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膽地設問說,“現在土地制度變了,每個農戶都擁有了土地,怎么還是缺糧食呢?”他的結論是“問題出在副業上”。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這樣的觀點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隨后的反右運動中,費孝通被劃為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慘度日。
1978年,費孝通始得平反。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農村企業”成了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蘇,家庭副業的收入占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吳縣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1983年底,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
1986年,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于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正是在這次調查后,他提出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長模式,都出自費孝通之觀察,斯人貢獻,以此為大。
費孝通長壽,逝于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我曾在1997年訪問過費老,面對后輩小生,他耐心以對,反復說的一句話正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日后,每當談論農村問題,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自問,“費老會怎么看這個問題呢?”最近這段時間,老是聽到工業品下鄉、大學生下鄉的新聞,我總覺得不是根本之道。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寫道,“由于家庭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他說得多好,這段話應該重申一萬遍。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走了費孝通指明的這條道路,一開始就是鄉鎮企業崛起的過程,是農民在鄉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區才剛剛萌芽。農村要振興,首先要振興農村的工業經濟。
遙想1936年的那個開春,當費孝通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么靈巧的一個組織,哪里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
比孔子更像個思想家
孔夫子只提目標,對如何實現目標卻毫無所知。
中國古代達人當中我比較不欣賞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腸很好,很有涵養,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陳。有人講他是思想家,可我覺得他其實是思想家中的戰略家,或者通俗地說,他是位領導。孔夫子只提目標,對如何實現目標卻毫無所知,這是領導的典型特征。我最欣賞的一位則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標,也不想實現什么目標,能耐也只有一樣:會寫《紅樓夢》。他在這本書的結尾說,這本書就是幾個孤獨的老朋友一起讀讀的,酒余飯飽,雨夕燈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們,一邊兒玩去吧,咱不稀罕你們品題傳世。
在我看來,這就是用了兩千年,生活的真相終得以浮現紙面。這真相就是,人類乃萬物之靈,但他們是有限而悲哀的萬物之靈。做個個人主義者,總是比做一個大同主義者靠譜。人類這東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們了解的要復雜,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癡惘先賢那樣大發宏愿,明智的人就該問他一句:這是人該干的事嗎?這也是一種生活真相。
我是一個自然主義者,把自己看作是跟一棵丁香樹或者一個小便池同等的東西,只有當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無限欣賞自己的時候我才無限欣賞自己。當然這要感謝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這就是我的人生觀。這種人一不小心墜入惱人的凡塵,就會表現得像個孤僻的個人主義者,這也不賴。我不喜歡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歡管任何人。我覺得倘若一個人有點兒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對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頭腦是多么貧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這樣的人也許愿意騎上一頭豬去浪跡天涯,讓他做個PPT或者寫幾本精裝書去教訓他人卻萬萬不能。
因此我從不掩飾地對于宣告式口吻的厭憎,憎屋及烏,也厭憎學生會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當然可以講得入情入理,比如此類生物“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鉆營”啊,或者那個故事,“從前,有一個下流島,島上有一種下流猴”等等。但我更滿意于自己有權選擇不講。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有一個像喇叭花一樣自然的頭腦所以我就是厭憎,請問尊駕,你管得著喇叭花怎么想嗎?
這是個輕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輕薄也比人為的莊重要好。這一點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講過一個他心目中的完美社會,說是暮春時節,春服既成,成人五六個,孩子六七砣,在河里洗個澡,領略了自然之美,唱著歌就顛了。這夢想太和諧了,閃爍著黃金時代的光澤,算是理想國的山東版。可是我覺得它太馴化了,真正的好世界應該保留對于不馴化者的寬容。
我倒是愿意設想這樣的場景:天氣好的時候,城里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念詩的唱歌的全來了,丑態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會出錢,市民們點心隨便吃,汽水隨便喝。貪財的小老百姓都出來擺攤兒,而武功最高強的城管們也不來踢他們的攤子。高臺之上有一個集智慧與美貌于一身的偉大人物在演講,說的是銀河系的和平與發展,這邊廂卻有個流氓搭張吊床,高臥酣眠,睡到一半兒還支起身子罵人:“怎么這么吵?”于是警察弟弟們紛紛感到很囧。其實這場景在這個地球上并不稀罕,但我覺得它就叫偉大社會。
我這么說倒不是因為我想做那個流氓,雖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謝上蒼,倘若有一天這個社會真的來到我們身邊,我也早就騎頭豬走遠了,那時你可以去冰川盡頭去找我。
依據奧卡姆剃刀原理,通往這個社會的法門必是簡明的,我看只要有這一條就差不多夠了:消解權力。借助現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標又提出解決方案,比孔子更像個思想家。不過孔子仍是偉人——孔子的意見中至少有一點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應該有個好天氣。我想,一個人愛過一個好天氣非同尋常,這至少說明他懂得愛。可惜歷史上總有太多的“大人先生”們舞蹈于云端,遮蔽了本該如此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