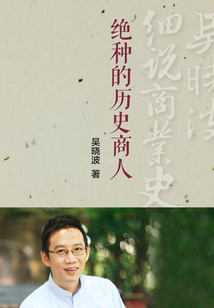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企業家的命運
是誰發明了鹽鐵專營?
這種巧妙曲折的治國理念一直延續數千年,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為各種不可或缺的專賣商品支付著變相的人頭稅。
我提過一個觀點:西方諸國與中國相比,在治國經濟策略上的最大差異在于,前者完全依靠稅賦為政府的主要收入,而后者的政府收入則由稅賦和專營收入兩項構成。在本文中,我們要說說這一中國式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叫管仲。
管仲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齊國,那是春秋年代的初期。齊國的疆界并不大,卻在管仲的治理下成為最強的國家,齊桓公因此被視為春秋五霸之首。
齊國的強大,與管仲實行的經濟政策有關。他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主義實踐者,在放活微觀的同時,十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制。他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產業管制政策便是鹽鐵專營,它幾乎成為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經濟保障。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自西周以來,就有一些諸侯國將鹽鐵經營收歸國有,然而從來沒有人將之視為國策,絕大多數的治國者仍然以征稅——特別是農業稅為國家最主要的收入。管仲最大的創新在于他在稅賦收入之外增加了專營收入,并將之制度化。
管仲以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
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征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于煮些白開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于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于人頭稅的征收總額。
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后世之人學管仲,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多入歧途。
比如鹽業。齊國濱海,是產鹽大國,食鹽是最有競爭力和價格話語權的戰略商品。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開放鹽池讓民間自由生產,然后由國家統一收購。為了維持國家對鹽的壟斷權,防止鹽價因生產過度而大跌,管仲下令對煮鹽的時節進行控制,只準在頭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正月這四個月的農閑季節煮鹽,到了仲春二月,農事開始,就不許聚眾煮鹽。由于控制了鹽業的銷售和產量,進而控制了價格,齊國的鹽銷售到國外去,可以抬高到成本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
在冶鐵業上,管仲實行的是國有民營。他首先嚴厲地強調了國家對所有礦山資源的壟斷,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臺法令宣布,只要一發現礦苗,就馬上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禁止擅自闖入。
在壟斷了資源之后,管仲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并對所生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在這些前提之下,管仲開放冶鐵作坊業,允許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鹽鐵專營的做法并非始自管仲,卻是在他那里形成了制度化并取得顯著成效,它對后世政權產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響。它形成一種獨特的中國式經濟制度,從而增強了國家管制經濟的能力。從管仲的論述中可見,他事實上是將鹽鐵的專賣看成為變相的人頭稅——因為鹽鐵的不可或缺性,國家通過對之控制,實際對每一個人變相地征收了稅賦。這種巧妙曲折的治國理念一直延續數千年,始終存活。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為各種不可或缺的專賣商品支付著變相的人頭稅。
企業史上的女富豪有哪些?
10月,胡潤發布了一張全球百富榜,其中,中國女富豪的數量之多為全球之冠,在20位擁有10億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來自中國。讀到這條新聞突然想到:在中國的企業史上到底有哪些女富豪?
一部兩千年的中國企業史,到處是面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別來論,女性則更寥若晨星。
在史書記載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區一個名字叫清的寡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寥寥76個字記錄了她的事跡。寡婦清的家族從事的是“丹穴”業,也就是采煉丹砂,因掌握了獨特的開采和冶煉技術,所以傳及數代而不墜。寡婦清不但操持家業,還組織了私人武裝以保衛家財。
女性經商最活躍的時期是在唐代,這不足為奇,因為連第一個女皇帝也是在那時出現的。在當時第二大商業城市洛陽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個寡婦,從事的也是冶煉業。因為錢賺得實在太多了,還被人告發惹上了官司。
在長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歷貞元年間,從事造船業。當時所造的大船最多能載八九千石,所謂“水不載萬”,然而俞大娘造出來的航船卻可達萬石。據說船上可以種花果、蔬菜,駕駛船只的工人就有數百人之多,船員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進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間,每來往一次,就能獲得巨利,這種船直接以“俞大娘”來命名。
除了從事大規模制造業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書中還出現過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據《太平廣記》等書的記載,她們所從事的商業買賣大多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品緊密相關,有以賣菜為生的“賣菜家嫗”,“鬻蔬以給朝夕”,也有賣花、化妝品和經營餐飲業的。《唐代墓志匯編》中還提及過一位楊氏是種植業的高手,“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固得水旱無懼,吉兇有資”。
女子經商之風自漢唐之后一直縷縷不絕,據《中國經濟史》作者侯家駒的考據,“在北宋,婦女還從事茶肆、食店、藥鋪之經營,并作小販、賣卦及牙人。”但是到了12世紀的南宋時,風氣終于大變。當時出現了一股禮教運動,對女性的約束大大增加,從此女性被關在宅門之內,再也無法在商場上有所作為。
宋元之后的明清兩朝,像寡婦清、高五娘和俞大娘這樣的女中豪杰已成絕響。不過到了19世紀初的清朝后期,在南方卻冒出來一個鄭一嫂,她從事的是十分兇險的海盜業——在西方企業史上,海盜從來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約精神的企業家。
鄭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膚黝黑但天生麗質,少女時是海船上的妓女,后來嫁給了南中國海著名的海盜鄭一。鄭一在廣東沿海一帶組成了一個海盜聯盟——紅旗幫。全盛時期,紅旗幫下分黑、白、黃、藍、青五旗,擁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盜眾一度多達10萬之眾。據英國學者康士坦的《海盜史》記載,其規模在當時世界上堪稱第一,竟大過著名的北歐海盜。紅旗幫專劫官船、糧船及洋船,活躍于粵東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紅旗幫“向商漁鹽米各船收保險(護)費”,名目為“號稅”、“港規”、“洋稅”,“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由于條文清晰,數萬海盜過的是有規有矩的非法生涯,紅旗幫儼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盜集團。
鄭一嫂與張保仔的勢力實在太大,引來朝廷的多次圍剿。1808年,清軍以八萬兩白銀為代價,邀集英國及葡萄牙海軍對紅旗幫發動總攻擊,張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從二品千總,任澎湖副將,鄭一嫂授誥命夫人,至是,粵東一帶海盜活動平息。1822年,張死于任上,鄭一嫂則定居澳門,開設賭場,得享天年,如果從淵源上來看的話,她還是澳門賭業的開山鼻祖之一。
“單干專家”的命運
四個“單干專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卻能在最艱困的時代發出最清醒而勇敢的聲音,所謂士者,大抵如是。
在“大躍進”及其后的大饑荒時期,有四位來自民間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產到戶”的主張,他們因此被蔑稱為“單干專家”,生命飽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氣最大、行動最早。27歲的李云河時任溫州地區永嘉縣委副書記,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報》上發表調查報告《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這是全國第一篇公開論述包產到戶的文章。1958年2月,李云河被開除黨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職勞改的下場。
1960年之后,隨著全國性大饑荒的爆發,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開始顯現。就當安徽和廣西等地嘗試“包產到戶”時,在浙江則先后出現了三位民間理論家。
1962年4月,溫州瑞安縣隆山畜牧場的獸醫馮志來完成長篇論文《半社會主義論》。他寫道:“我認為包產到戶確實是唯一出路。這樣做,完全是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這是6億人民的呼聲!”文章完成后,馮志來孤身北上,將文稿分送給了中共中央、《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兩個月后,他又撰寫更為尖銳的《怎么辦?》,再次投書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為“右派”,在武裝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義烏縣喬亭村改造。
幾乎就在馮志來寫《半社會主義論》的同時,寧波嵊縣農技站的蠶桑技術員楊木水寫出了《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的萬言書,文內列數了包產到戶的13個優越性。楊木水從小在孤兒院長大、沒上過任何正規學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顛三倒四,卻句句直擊弊病根源。
楊木水將文章寄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毛澤東主席,同時,還輾轉寄了一份給嵊縣老鄉、經濟學家馬寅初。由馬寅初轉呈,高層終于看到了這份萬言書。1963年春,楊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緩,罪狀是“惡毒攻擊黨的路線政策,鼓吹包產到戶,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
紹興新昌縣新溪公社的干部陳新宇的際遇同樣悲慘。1961年6月,陳新宇根據下放勞動時調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寫出了《關于當前農村階級分析問題》和《關于包產到戶問題》兩篇文章,從階級分析的角度闡述了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陳新宇將兩篇文章分別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報》。1966年之后,陳新宇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前后被揪斗120次,抄家7次,監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全國上下猛烈批判以“包產到戶”為代表的“單干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會議期間,毛澤東對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說:“你們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干理論家,必須徹底批判!”這“兩個半單干理論家”指的就是馮志來、陳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楊木水。
不過,李云河和“兩個半單干理論家”都活著看到了包產到戶在中國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這一制度激活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轟隆隆地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寫專著《中國農村戶學》,提出“家庭工業加專業市場”的經濟發展思路,這幾乎就是“溫州模式”的萌芽之說;1975年,服刑12年的楊木水出獄,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從此游走江湖,當起了草藥郎中,他有一個專治支氣管炎的草藥秘方據稱十分有效;發誓終身不娶的陳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勞改的十多年中,他寫過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獲平反,從此隱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被遣返回義烏的馮志來在1983年獲平反,被調入縣經濟研究中心,成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晚年結集出版文集《興市邊鼓集》。
四個“單干專家”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無高深修養,卻能在最艱困的時代發出最清醒而勇敢的聲音,所謂士者,大抵如是。
最后的孫冶方
寫出一部“社會主義經濟論”似乎沒有太大的困難,但在事實上它卻怎么也走不通。對歷史的梳理常常要具體到一個個歷史人物,孫冶方便是一個令人尊敬又心酸的人物。
1979年年底,孫冶方剛剛動完一個大手術,醫生用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從肝區割下一個裝滿四寸盤子的大腫瘤。孫冶方虛弱至極,健康狀況十分不樂觀。他當時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醞釀了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出來。他向中科院經濟所點名要幾個熟悉他的理論的學者來協助他完成此書。
很快,經濟所派出了一個由吳敬璉、張卓元等組成的7人寫作小組來執行這個重要的任務。他們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北京飯店租了一個套房,每天到病房與孫冶方交談,進行錄音和記錄。吳敬璉回憶說,那些日子,孫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搶救室”,每次他們去的時候,一到門口就能聽到貝多芬交響曲,那種洋溢著樂觀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孫老最喜歡的。
過了一個冬春,寫作組整理出了15萬字的大綱,一共有20多章。接著,孫冶方出院。再接著,工作陷入難堪的泥潭,原因是,從孫冶方到寫作組都發現了孫式理論的矛盾點。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狀況感到不滿,開始尋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在這方面,孫冶方的勇氣和成就無疑是最大的。
按孫冶方的設想,要寫出一部結構嚴密、邏輯一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似乎沒有太大的理論困難。可是,在事實上,它卻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孫冶方就打算按《資本論》的程式編寫這部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近40人的寫作班子,攻關兩年,竟無功而返。到1964年,作為民主主義者的孫冶方已經深感他的思想與現行體制的矛盾。他曾說,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自己寫文章經常是思如泉涌,一揮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門口,寫一頁,排字工人排一頁;而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寫文章變得很難,有時候一篇文章要寫幾個月,怎么也寫不出來。隨后他被批判入獄,在牢中面壁七載,日日苦思,默寫85遍腹稿,自以為已想通所有關節,可瓜落蒂熟,但是卻沒有想到還是拓進艱難。這種致命的痛苦對于孫冶方來說,甚至大于軀體的病痛。
時間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孫冶方因肝癌擴散再度住院,眼看來日無多,他提出加快創作的進度。7月,他帶著寫作組一行人前往青島,住進海軍療養院“閉關”寫作。伴隨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孫冶方為自己的理論建構做最后一次沖鋒。由編寫組分頭寫作的章節都已寫出,但怎樣把這些“部件”聯結成一個邏輯一貫的體系?編寫組一遍接一遍推演討論,可是仍然寸功難奪。
青島歸來之后,孫冶方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任務不可能完成。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后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絕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1982年11月,臥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吳敬璉和張卓元執筆寫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對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表達了無比的樂觀,同時也沉重地指出,“必須對舊管理體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個月后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后,我的尸體交醫院作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于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孫冶方這樣的謝幕方式,即使在今天,已然足以讓人落淚。
觸破窗戶紙的人
此刻的吳敬璉已經超越了上一輩經濟學家在舊框架里尋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他是真正觸破了那層窗戶紙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氣氛仍然緊張,不過,微妙的轉機悄然在南方出現了。
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先后發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資”的詰難。
對時政變化十分敏感的吳敬璉則已經嗅到了新的空氣。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憶說,在后來的一年多時間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辦了一本雜志,寫了一篇長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場研討會,寫了兩份建言書。這些工作環環相扣,無一不在中國當代經濟改革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我們且一一細說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方案”。1990年秋冬之際,就在與“計劃派”論戰最激烈的時候,吳敬璉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組員為他的老同事張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輕一輩的學者。他們以整體配套改革為基本理念,分別從企業、價格、財政、稅制、金融等多個方向進行拓進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措施和時間表。日后我們將看到,當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時候,這個總體方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并最終改變了中國改革的路徑。
接辦的一本雜志,是由經濟學家蔣一葦創辦于1988年的《改革》雙月刊。蔣曾任中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以首倡“企業本位論”而聞名。他的思想頗為開放,一直主張要給企業以自主權,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吳敬璉接手雜志后,定題組稿,幫助培養一批特約撰稿人,事必躬親,投入巨大精力。在整個90年代,《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思想重鎮,吳敬璉以及多位學者的最新觀點大多首刊于此。
從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歲高齡的鄧小平南下視察,發表“南方講話”。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在煥然一新的大轉折的前夕,吳敬璉發表的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經濟理論上的依據,“吳市場”之名迅速為公眾所知曉,他成了全國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
3月14日,在鄧小平南方視察的講話還沒有在國內報刊上得到正式報道的情況下,由吳敬璉任主編的《改革》雜志和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聯合舉辦了一場“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這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后,國內最先作出反應的大型學術活動。會上,眾多學者均一吐為快,表達了加快改革之意。
4月30日,吳敬璉寫成一份題為《關于計劃與市場提法問題的建議》的建言書,寄送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這封信中,吳敬璉回顧了10多年來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多場爭論,然后明確建議中央,應當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他從理論的高度上十分尖銳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市場化取向的道路,已經無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論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個決定性突破的時刻。他說:“其實,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直認為商品生產或貨幣經濟同社會主義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條主義的傳統觀念,即使采用‘商品經濟’甚至‘商品生產’的提法,也無法走出由于陳腐的教條與現實生活脫節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將‘市場經濟’改變為‘商品經濟’,并不能解決問題。”
多年之后的人們,細讀這段文字,仍然會為吳敬璉的赤誠和勇敢所感動。由這一段論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經超越了上一輩經濟學家在舊框架里尋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論家的意義上,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和義無反顧,他是伸出手指頭,真正觸破了那層窗戶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