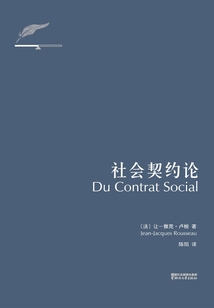
社會契約論
最新章節(jié)
- 第21章 附錄:盧梭生平大事年表
- 第20章 LIVRE IV(5)
- 第19章 LIVRE IV(4)
- 第18章 LIVRE IV(3)
- 第17章 LIVRE IV(2)
- 第16章 LIVRE IV(1)
第1章 導(dǎo)讀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18世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xué)家、教育家、文學(xué)家。他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qū),是杰出的民主政論家和浪漫主義文學(xué)流派的開創(chuàng)者,是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歌德在評價伏爾泰和盧梭時寫道:伏爾泰終結(jié)了一個時代,盧梭卻開創(chuàng)了一個時代。
這,是我們從歷史書中讀到的盧梭。
而這部《社會契約論》卻讓我們讀到了一個更加真實生動、有血有肉的盧梭——一個作為社會人的盧梭,以及一個作為自然人的盧梭。
作為自然人的盧梭
盧梭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相比于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巨擘,盧梭的偉大實在來得坎坷。
他是瑞士日內(nèi)瓦一個鐘表匠的兒子,母親在他襁褓中便不幸去世,給他留下的是滿柜書籍。盧梭的童年是在閱讀古希臘、羅馬著作中度過的,因此在寫作《社會契約論》和其他論著時,關(guān)于先哲和歷史人物的典故總是信手拈來。他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學(xué)院派教育,青年時期輾轉(zhuǎn)于威尼斯、巴黎等地,一度不得不靠做家仆來糊口。1750年,38歲的盧梭以論文《論科學(xué)與藝術(shù)》在文壇學(xué)界一舉成名。與狄德羅共同編纂《百科全書》、寫作《論科學(xué)與藝術(shù)》之后,他也獲得過贊譽和追捧,但他靦腆真誠、不愿曲意逢迎的性格卻讓他始終游離于上流社會之外,最終遭到排擠,選擇到鄉(xiāng)村隱居。
跌宕起伏的一生讓盧梭的思想和寫作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獨樹一幟的自然氣息。他在游歷與漂泊中親身體驗人間冷暖,上流社會的浮夸和虛榮對于盧梭來說,不僅是口誅筆伐的對象,更是導(dǎo)致他最終出世隱居的切膚之痛。自覺被人類厭棄和背叛的盧梭,轉(zhuǎn)而在大自然中尋找心靈的故土—《社會契約論》正是他在隱居生活中的作品,遠離塵囂反而讓他能夠更加清醒地觀察和剖析人類社會。這種自然主義的態(tài)度,讓盧梭在不斷開拓思想深度的同時,始終保留著某種天真而坦誠的氣質(zhì)。盧梭在藏書室里度過了童年的大部分時光,在他眼中,閱讀是一件像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情。他深愛的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在《社會契約論》中隨處可見:普魯塔克、卡里古拉、呂庫古……暴君和先哲仿佛都是盧梭再熟悉不過的朋友,引經(jīng)據(jù)典,渾然天成。因此,《社會契約論》不僅是一部政治理論經(jīng)典,也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更遙遠時代的窗口。
作為社會人的盧梭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以縝密的思維、嚴謹?shù)倪壿嫼筒讲綖闋I的論證展現(xiàn)了讓人高山仰止的民本思想。顧名思義,《社會契約論》旨在研究社會的組織和運作—“我寫作本文是想探討,從人類的實際情況和法律的可能性出發(fā),在社會秩序中,是否存在一種合法又可靠的政府管理規(guī)則。”全書共分為四卷,其各自闡述的內(nèi)容構(gòu)成了一個起承轉(zhuǎn)合的邏輯結(jié)構(gòu):
第一卷從相對模型化的視角闡述了社會結(jié)構(gòu),并且拋出了全書的核心—契約精神。盧梭將家庭看作社會的雛形,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guān)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依靠契約精神來維系的,這與中國古代“家國同構(gòu)”的思想似乎不謀而合。契約精神是盧梭“主權(quán)在民”主張的內(nèi)核和基礎(chǔ),也是理性思想的精髓。在依據(jù)契約精神構(gòu)建起的理想社會結(jié)構(gòu)中,人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構(gòu)成了一個整體(主權(quán)者),主權(quán)者代表所有個體的共同利益,具有公共意志;這樣一來,社會中的人便成了同時擁有個人獨立意志和社會公共意志的雙重主體,失去了自然人的自由狀態(tài),卻獲得了公民自由和社會權(quán)利。
這一理想結(jié)構(gòu)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主權(quán)者”的概念,第二卷便由此入手,集中闡述了主權(quán)者的種種特征。主權(quán)者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仿佛一種精神人格—看似十分晦澀難懂,不過類比自然界中的生物現(xiàn)象可以幫助我們更形象地理解這一概念:主權(quán)者仿佛海洋中無數(shù)小魚構(gòu)成的龐大魚群,在掠食者眼中便成了一個仿佛具有行動意識的整體。大魚群的運動遵循自然和物理法則,主權(quán)者的運轉(zhuǎn)則有賴于法律。需要注意的是,主權(quán)者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家,二者相互區(qū)別又彼此聯(lián)系:主權(quán)者是國家得以形成的基礎(chǔ),但是國家作為實體,在實際情況中往往與理想的公共意志相違背—人人皆為決策者的社會在客觀上畢竟難以實現(xiàn)。
這樣一來,便順理成章地進入第三卷,具體討論了幾種不同的政府形態(tài)及其運作形式,即民主政府、貴族政府和君主政府。這一部分內(nèi)容非常有意思,將“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人數(shù)的多寡作為區(qū)分的依據(jù)。仔細想來,這種模式絕不僅限于政府的構(gòu)成;相反,即使在兩百多年后的今天,這種思路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企業(yè)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
最后,作為收尾,第四卷介紹幾種社會組織制度和宗教信仰。早期信仰新教、后轉(zhuǎn)而皈依天主教的盧梭,對于宗教的看法洋溢著自然主義的理性色彩。盧梭信神而不信教:相信世間有凌駕于人力之上的存在,但卻反對在神學(xué)和教會中徒然虛度時光。
起承轉(zhuǎn)合之間,盧梭以近乎上帝視角的清晰思路,有理有據(jù)地為我們梳理了社會的來龍去脈。
翻譯的思路和初衷
在此之前,國內(nèi)已有數(shù)個譯本,其中尤以商務(wù)印書館何兆武譯本為經(jīng)典之作。今次之所以再度重譯盧梭這部《社會契約論》,是想要更加貼近現(xiàn)代讀者。時代在變幻,社會在發(fā)展,語言也在演化。作為年輕一代的譯者,雖然沒有前輩泰斗的淵博學(xué)識,但這并不妨礙我在閱讀盧梭作品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為他的慎思明辨拍案叫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他的真摯坦誠而感動。我想,這樣純凈而深刻的閱讀體驗,是值得與讀者分享的—盧梭不僅僅是歷史書上的一個必考條目,也不僅僅是學(xué)術(shù)界奉為圭皋的一個濃縮了理性思想的政治符號,他和我們大家一樣有過迷惘落拓的青年時代,有過路漫漫其修遠兮的痛苦,有過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求索。這一譯本想要讓讀者呈現(xiàn)的,便是一部文字簡潔、思路清晰明確的《社會契約論》,讓盧梭離我們更近。
譯者:陳陽
2016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