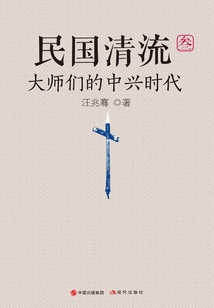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 第37章 尾聲
- 第36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5)
- 第35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4)
- 第34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3)
- 第33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2)
- 第32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1)
第1章 民國二十年(1931)(1)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xué),拉開“北大中興”序幕。九一八事變喚起國人和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機(jī)爆發(fā)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嚴(yán)刑峻法,嚴(yán)加控制言論。7月,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幾百冊《新月》被抄沒。王造時登上書生論政舞臺,在《新月》發(fā)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暢淋漓,譏諷當(dāng)局,是《新月》論政時代結(jié)束前最為響亮的鳴鏑。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xué),選聘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等著名學(xué)者到北大執(zhí)教,一時間,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北大中興”。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胡適等知識分子在關(guān)乎國家存亡的歷史關(guān)頭,以一腔愛國熱忱投入這場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
此時的周作人是以大時代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時說,當(dāng)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xiàn)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tài)度為宜”。其散文中溫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漸漸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歸》《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論詩學(xué)門徑》《論中國詩的出路》。沈從文《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nóng)的〈揚(yáng)鞭集〉》《論中國的創(chuàng)作小說》等論文發(fā)表,創(chuàng)作小說《夜?jié)O》《三三》《虎雛》《黔小景》等。胡適發(fā)表評論《評〈夢家詩集〉》《以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論牟子〈思想論〉》《辨?zhèn)闻e例——蒲松齡的生年考》《〈醒世姻緣傳〉考證》等,出版《淮南王書》。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胡適重返北京大學(xué)
1930年11月30日,胡適在北方凜冽的寒風(fēng)中,抵達(dá)北平,卜居后門內(nèi)米糧庫四號。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遷居上海,已過三年半。其間,胡適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為董事會董事,胡適北上參加了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xué)院校董事會議。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啟超,不料他趕到時,梁氏剛剛病故幾個小時,他悲痛中參加其大殮。后又去北京大學(xué)舊地重游,感觸良多,賦詩《三年不見他》感懷:
三年不見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見他,
這久冷的心又發(fā)狂了。
我終夜不成眠,
縈想著他的愁、病、衰老。
剛閉上了一雙倦眼,
又只見他莊嚴(yán)曼妙。
我歡喜醒來,
眼里還噙著兩滴歡喜的淚,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
1930年6月和10月,胡適受邀到北平演講與參加學(xué)術(shù)活動,同時也為來北平尋租新房。胡適在日記中說,他每次演講都是人滿為患,一次到協(xié)和醫(yī)學(xué)校用英文演講,聽眾仍將會場擠得滿滿的。通常,關(guān)于哲學(xué)之類學(xué)術(shù)性很強(qiáng)的演說聽眾總是寥寥無幾,然而北平的學(xué)術(shù)界、教育界,總是熱情地擠進(jìn)會場,去聽胡適的演講,顯然是對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滿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對社會國家的責(zé)任也更重,因為人對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負(fù)這許多人的期望呢?”胡適常用“凡執(zhí)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這句話自勉、約束、鞭策、砥礪自己,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勇敢無畏地奉獻(xiàn)自己的才智。這句話是在給張學(xué)良的信中說的。今天聽來,仍擲地有聲。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胡適開歡迎會,他的學(xué)生傅斯年發(fā)表熱情而真誠的歡迎詞,令胡適頗為動容。胡適致答詞曰:“生平抱三個志愿:一,提倡新文學(xué);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國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實行無力’八個字作為我的定論。”
四天后北京大學(xué)為他舉行歡迎會,北大代理校長陳大紀(jì)、哲學(xué)系主任張真如等參加。胡適致答謝詞曰:“我們當(dāng)前的問題是社會、國家、人生、思想,我們應(yīng)該注意活的問題,不該專研究過去歷史上死的問題。古代的成功或失敗,僅是我們的指導(dǎo)和教訓(xùn)。我們應(yīng)該領(lǐng)導(dǎo)社會思想,研究中國當(dāng)前的社會問題。”
12月17日夜,胡適在北平的米糧庫四號宅第,燈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歡聚于壽宴,賀詩拜壽,在生日蛋糕上點起四十支紅燭,舉杯用英文唱壽誕之歌,為胡適四十大壽祝福。那夜,飄起紛紛揚(yáng)揚(yáng)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適到北京大學(xué)任教,幾經(jīng)推辭,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學(xué)校長也是他的經(jīng)年老友蔣夢麟的堅請,受聘為北大文學(xué)院院長兼中國文學(xué)系系主任之職。
胡適到北大后,蔣、胡二人多次圍爐商議,擬就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發(fā)展的周密計劃。他們再次打出老校長蔡元培“教授治學(xué),學(xué)生求學(xué),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略,兼設(shè)“校務(wù)委員會”取代過去的“校評議會”。改文、法、理三“科”為“三學(xué)院”,定周炳琳為法學(xué)院院長,劉樹杞為理學(xué)院院長。蔣夢麟自唱白臉,負(fù)責(zé)“辭退舊人”,請胡適唱紅臉,“選聘新人”。胡適如炬慧眼,“選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湯用彤等著名學(xué)者、教授到北大執(zhí)教。一時間,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為“北大中興”。
胡適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七章),也由新月書店正式出版。胡適身在北平,忙于辦學(xué),仍不忘為自己在上海發(fā)動的人權(quán)輿論辯護(hù)。是年年初,胡適致信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強(qiáng)調(diào)“《新月》同人在提倡這種個人簽名負(fù)責(zé)的言論自由”,“此類負(fù)責(zé)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fā)表,不可加以壓迫”。
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第八區(qū)黨部,將寫文章批評國民黨的羅隆基告到上海警備司令部,指責(zé)羅隆基“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羅隆基遂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適多方營救下,羅被保釋。不久,羅又寫《我的被捕的經(jīng)過與反感》。當(dāng)局又以“挾忿詆毀”為由,強(qiáng)令光華大學(xué)開除羅氏。為此,胡適曾代光華大學(xué)校長草擬了一個《上蔣介石呈》,直接向蔣介石解釋其事緣由并為羅隆基鳴冤,“今有一事上陳,即教育部飭令光華大學(xué)撤去羅隆基教員職務(wù)是也。羅隆基在《新月》雜志發(fā)表言論,意在主張人權(quán),間有批評黨治之語,其措辭容有未當(dāng)。惟其言論均由個人負(fù)責(zé)簽名,純粹以公民資格發(fā)抒意見”,擬請免職撤換處分,以示包容云云。
當(dāng)時的光華大學(xué)校長張壽鏞,極力支持胡適,他以校長的身份,給蔣介石上書,力保羅隆基。但翌年1月,當(dāng)局還是以“言論謬妄”,強(qiáng)令光華大學(xué)辭退羅隆基的教職。羅繼續(xù)在上海主編《新月》,依然鋒芒畢露地發(fā)表他的書生論政。5月,汪精衛(wèi)在上海《民報》發(fā)表文章說,中國當(dāng)時有三種思想鼎足而立:共產(chǎn)主義、《新月》派和三民主義。
張壽鏞雖多年在朝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適的一邊。張壽鏞(1875—1945),字伯頌,號泳霓,浙江鄞縣(今寧波)人。乃明末抗擊清兵的英雄張煌言的后裔。張煌言,崇禎時的舉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與錢肅岳等官吏倡議奉魯王朱以海監(jiān)國。清兵入浙東,軍敗又隨魯王逃浙閩沿海,后入據(jù)舟山。永歷八年(1654),錢肅岳率軍北伐。張率軍經(jīng)寧國、徽州北上。因鄭成功兵敗,深入無援,又返回浙東,居懸岙島(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張蒼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張壽鏞出身名門,曾在江蘇、浙江等地為官。民國后,歷任浙江、湖北、江蘇、山東四省財政廳廳長。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張壽鏞為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后辭去官職回上海創(chuàng)辦光華大學(xué),親任校長,并兼教授。他雖純?yōu)橹袊鴤鹘y(tǒng)文化哺育的學(xué)者,卻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華,中西合璧,辦學(xué)有成。但他對中國文化最突出的貢獻(xiàn),是窮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編輯、出版了《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搜集了鄞縣歷代文化散佚的文獻(xiàn)一百七十八種,極具文獻(xiàn)價值,堪稱文化瑰寶。藏于寧波天一閣。
兩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陳布雷回信給胡適稱,“此事部中既決定,當(dāng)不能變更”,并表示愿意與胡適等人建立“一個初步的共同認(rèn)識”。胡適立即從北平再致信陳布雷:“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rèn)識’必須建筑在互相認(rèn)識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帶上《新月》兩份,分別送給陳布雷和蔣介石,希望二人瀏覽這幾期《新月》的言論。胡適還在信中表示,他們看過之后,“該‘沒收焚毀’(國民黨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jiān)槍斃,我們都愿意負(fù)責(zé)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
這信,一如胡適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論義正詞嚴(yán)、理直氣壯、毫無顧忌,文章筆勢酣暢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適自己被政治沖撞得鼻青臉腫、鮮血淋漓,卻一直對蔣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學(xué)新學(xué)期開始,胡適開講“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綻放時,他收到在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做工的吳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自己正在作《胡應(yīng)麟年譜》的情況。胡適對胡應(yīng)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這方面的文章。見信中吳晗尋出吳之器為胡應(yīng)麟所作的傳,推斷出“胡氏的卒年是在萬歷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歲”,與自己推斷相關(guān)甚微,甚是高興。他在給吳晗的信中說:“我記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應(yīng)麟年譜》,我聽了很高興。”但指出“你信上在萬歷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適夸年輕的明史研究者吳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寫定時我很想看看”,并邀請他“星期有暇請來談。羅爾綱君住我家中”。
胡應(yīng)麟,字元瑞,號石羊生。浙江蘭溪人,與胡適同鄉(xiāng)。萬歷中舉,屢試進(jìn)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圖書四萬余卷,從事著述。其幼能詩,承建安七子詩風(fēng)而有變化,著有《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很有學(xué)術(shù)價值。
四個月后,吳晗再次寫信給胡適,告之蔣廷黻先生勸自己研究明史。胡適致信吳晗說:“蔣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信中說,“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xué)所能整理”,“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jìn)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xùn)練方法”。
信中還以自己多年治學(xué)經(jīng)驗,從五個方面解答了吳晗所提的幾個問題,并將有關(guān)學(xué)者謝國楨、孟森及其著作介紹給吳晗。最后告誡:“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xùn)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xué)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
其實,二十幾天前,胡適為了安排吳晗的學(xué)習(xí)及工作,已給兩位老朋友翁文灝、張子高寫信,向他們推薦吳晗。信中說:“清華今年取了的轉(zhuǎn)學(xué)生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xué)轉(zhuǎn)來的。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xué)生,中國舊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幾種研究,都很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yīng)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jī)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jī)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jī)會,就不能入學(xué)了。我勸他決定入學(xué),并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胡適還建議請清華的教授讀吳晗的《胡應(yīng)麟年譜》,“也許他們用得著這樣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應(yīng)麟年譜》。
胡適對吳晗無私的關(guān)心和指導(dǎo),使他受益終身。幾年后,吳晗成為一位頗有成就的明史學(xué)者。
成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學(xué)者從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大肆拆毀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吳晗因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雜文《燕山夜話》等,與鄧拓、廖沫沙同時獲罪,死于非命。
1980年,臺灣《傳記文學(xué)》第三十七卷第二期,發(fā)表了湯晏的文章《從胡適與吳晗來往函件中看他們的師生關(guān)系》。確定了師生關(guān)系,又有什么意義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在全國開展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吳晗對恩師胡適照樣是口誅筆伐,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體悲劇。
是年,胡適還曾復(fù)信聞一多、梁實秋,有意牽頭《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可惜,種種原因,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實秋一人窮畢生心血,獨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亞全集》。
在北大教學(xué)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適應(yīng)丁文江夫婦之邀,帶兒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蘇泰興人,地質(zhì)學(xué)家。1921年與胡適同辦《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滬商埠總辦。5月,他在上海各團(tuán)體歡迎會上發(fā)表演說,其中有“鄙人為一書呆子,一個大傻子,決不以做官而改變其面目”等語。1926年7月,魯迅曾在《馬上支日記》一文中,一口氣批評了陳源、胡適、牛榮聲、劉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魯迅于1931年12月寫的文章《知難行難》中,針對《申報》一則電文,“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奉蔣如,對大局有所垂詢……”,再次對丁、胡進(jìn)行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