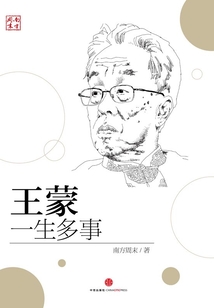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8章 沒有去新疆的16年,就沒有現在的王蒙(2)
- 第7章 沒有去新疆的16年,就沒有現在的王蒙(1)
- 第6章 是政治更是人生(3)
- 第5章 是政治更是人生(2)
- 第4章 是政治更是人生(1)
- 第3章 “老王”說事(2)
第1章 不是我個人被架在十字架上
盡管王蒙給自己對號入座是“寫小說的”,但所到之處,人們對他的標簽和介紹不出窠臼地仍然是“前文化部長、全國政協常委”。王蒙畢竟與普通作家有所不同,他還有秘書隨行。
灰白的頭發,略顯沙啞的嗓音,他自己也提醒“我已經74歲了”。
從東莞他下榻的酒店的大廳里我們坐的位置看過去,逛完市容回到酒店的王蒙,正端步穿過大廳,頸項和上半身略朝后挺著,器宇軒昂卻又步履略為遲緩。
王蒙從部長位置下臺后,幾度被熱罵,從“堅硬的稀粥”,到“躲避崇高”,到“推薦剽竊的80后作家入作協”……他19歲寫《青春萬歲》,是不是從80后作家身上看到某種自己當年少年成長的影子呢。面對“八面來封”,他自比關漢卿的“銅豌豆基因”:“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
王蒙經歷不可謂不多“拐點”:“他當了八年共青團干部。他當了二十年右派與摘帽右派。他當了一年生產大隊副隊長。他當了十年中央委員。他當了三年半部長……”他自己的快板式數點,乍聽起來,有點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詞的排比句式。
王蒙自稱“九命七羊”,這正是他在花城出版社新出的自傳第三部的書名。他自我解釋:“貓有九條命,狗有九條命,我也有九條命,九條命就是九個世界,東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七羊,就是吉祥”。總之,“王蒙永遠不會吃癟”。
書的責任編輯田瑛先生說,王蒙三部自傳的版權是花城出版社2005年花了200萬預付稿費“中標”的,當時王買一棟500萬元的別墅缺口200萬元。
被王蒙稱為“很小兒科的愛好”的語言,也是王的“九命”之幾: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英語、俄語、日語,到伊朗訪問講了7分鐘波斯語。
王蒙的寫作跨越了半個多世紀,有人說他最好的作品是《青春萬歲》,有人說是《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有人說是寫新疆《在伊犁》系列,有人說是意識流小說如《夜的眼》等,還有的說是《活動變人形》。
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認為,寫于1988年6月的小說《十字架上》是王蒙最好的小說。高利克驚異于王蒙對《圣經》和基督教的理解。“這是第二次令我心動,第一次是小說發表不久,我收到香港基督教一個機構的來信,要求授權翻譯此篇作品。”王說。“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的”,對王蒙自己來說,他樂觀,是“被逼得樂觀”,“被迫樂觀”。
王蒙這次來為東莞市的“華語之顛——文化周末大講壇”做開壇之講,結合自身政治經驗,講解“《紅樓夢》中的政治”,如同說書。最后,在一個恰到好處的地方戛然而止:“探春打了王善寶家的一個嘴巴,那個嘴巴清脆的響聲,余音繞梁,響徹了三百年!——”然后,身體往后稍微一靠,享受著聽眾嘩嘩的掌聲。他自稱這種演講是“鍛煉肺活量的有氧運動”。
人們說他聰明甚至“過于聰明”,他自我辯護是“二桿子脾氣”:“有很多冒傻氣的東西我都寫到了”,“也有各種慚愧”。他在第一部自傳《半生多事》中透露他父親日記中的隱私:“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他遂把父親當作反面教材:“一輩子不做父親那樣的人,不做對不起女人的事。”
5月30日上午,演講前,王蒙在他下榻的房間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王蒙夫人“芳”(崔瑞芳、芳蕤)在旁。“芳”隨同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夫唱婦隨,作家張賢亮說,“王蒙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不需要有緋聞”。
王蒙招呼記者:“要喝水那邊有開水,你們自己倒。”
文學把自己提升到彌賽亞的位置是一種悲哀
記者:王蒙先生,你作為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在新疆那樣一個伊斯蘭教少數民族地區生活了一二十年,同時你的小說《十字架上》又解讀《圣經》。我就在想,這三者之間,你找到什么樣的共同點、公約數?
王蒙:我覺得從人們的社會理想,包括對國家和民族的愿望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年輕時候自己經歷了,也參與了——雖然是在自己非常年少的時候——這樣一個人民大革命,而且相信這樣一個人民大革命能夠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親人帶來新生——確實也帶來了——我想這在當時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生活的事情,完全是實際生活的一種表現。
在新疆我對伊斯蘭教的了解,也更多是和民族問題放在一塊的,新疆是維吾爾自治區,它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這些民族都是穆斯林,都是伊斯蘭教徒,我受到他們感染的更多是他們生活比較簡樸,注意衛生。伊斯蘭教確實有一種——張承志寫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清潔的精神》,咱們管伊斯蘭教叫清真古教,“清真”在阿拉伯語的經文里頭實際是一個專門的名詞,就是清潔,做人要做到干干凈凈;而伊斯蘭教最反對的是邪惡、骯臟。把清潔當作一種價值觀念,甚至是相當核心的價值,這是伊斯蘭文化的一個特點,我覺得我們也是可以對它有所了解、有所借鑒的。我常常很感嘆,因為新疆農民的生活條件并不好,但是新疆這些少數民族是最注意洗手的,他一天不停地洗手,這對抵御“非典”都有很大的好處(笑)。
基督教的情況并不一樣,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因為我的中學本身是個教會學校,也有少量的周末傳教的活動,我參加過一次,一次還跟著學唱贊美詩,后來沒有什么興趣,因為當時我正是追求革命,就再也不參加了。但是在我擔任文化部部長的期間出訪一些歐洲國家,歐洲國家到處都是教堂,到處都是和耶穌、圣母有關的繪畫、雕塑……當然你也很感嘆,這些東西作為歐洲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覺得我們現在對這些東西都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
記者:《十字架上》是一篇1980年代的小說,你為什么要寫這個小說?漢學家高利克評價認為它是你最好的小說。你理解的十字架和西方人或者基督教世界理解的十字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你寫這個是不是和當時你自己的命運體驗有關?
王蒙:我想是這樣子,其實我這個書里(指《九命七羊》——編者)都寫了,再多作解釋會有點畫蛇添足,我想人們對于一個所謂彌賽亞——實際彌賽亞用中國話說就是救星——對于救星的向往、追求、信賴乃至于對救星的失望和不滿足,這既是常常有的現象,也是一個又可愛又可憐的事情,所以我想,這種現象不管它的出發點多么好,但是它會達到相反的效果,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反正有些話,尤其是對一些小說,自己也不必對它作最確切的解釋,如果你做了最確切的解釋,別人閱讀起來會味同嚼蠟。
記者:你寫到了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在懷念八十年代浪漫、光榮與激動人心的時候,你自己的感受是被架在十字架上的,是這樣嗎?
王蒙:其實我說的不是我個人被架在十字架上,而是說對于一個社會的進步、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是不能夠把力量寄托在一個超人間的力量上面,不能夠寄托在一個超現實的與形而上的一個救贖上面,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記者:那你當時是不是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彌賽亞的?
王蒙:是。越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農業的國家,特別容易產生彌賽亞情結,就是期待救星的出現。但是這個和現代的理性的法理的國家并不是一回事。
記者:你在書中提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現了非彌賽亞情結的突破性進程,怎么樣理解?
王蒙: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個是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一個是發展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建設和市場經濟不是彌賽亞的,因為彌賽亞主義者往往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是一種通過政治或道德的審判,來救贖、創造一個人間的天堂。而這個經濟建設和市場經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天堂不是用道德或政治的洗禮就可以形成的,而是通過一種發展,尤其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更多的是按照經濟的規律來的。但這些并不要緊,因為我無意在這個書里頭作一個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論述,而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個實際經驗、體會和遭遇。
記者:就你所說,這種彌賽亞情結發生了變化,那么,文學拯救的意識和功能是不是完全喪失了呢?在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物質主義語境下,文學應該起什么作用?
王蒙:我想文學拯救的功能在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但是這種拯救的功能我并不想把它想得過于絕對化,所有的文學作品對于人的精神都是一種救贖?這不一定。有些文學作品,比如說它表達那種強烈的憤怒和批評,它很難起到救贖的作用,而更多是一種暴露或者譴責。比如說閱讀《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一類的作品恐怕起不了什么救贖的作用,但是它也算是戳穿這個社會上一些丑陋的洋相,所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文學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帶有一種救贖的色彩,有的是帶有一種補充的色彩,比如說大家都耽于市場經濟下的競爭,但是文學作品還能呼喚一點人的純情和善良,或者是美的夢幻,所以說有的是一種補充,有的是一種回歸,在東莞是最有體會的,因為我們今天的成績都是改革開放、開發、經營的結果,但是文學作品有時讓你回歸到相對比較自然、比較純樸的狀態,甚至讓你忘記一下公司啊、股票啊,就是說也起回歸的作用。
這里我還有一個想法,也許說出來不是很好聽,就是有一些作家,對自己精神救贖的作用的估計是不是過高?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抱著一種準彌賽亞精神所寫的作品,他自己以為他在充當彌賽亞的角色的作品,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接受、傳播和認同,我想這樣的一些例子俯拾皆是,我就不具體地談人了。前好幾年我就在報紙上看到,報道四個最重要的,可以說是當紅的中年作家去簽名售書,結果受到冷落,然后這四個作家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每個人都大罵一頓,中國讀者的水平太低。我想讀者水平永遠不會很高的,而中國讀者的水平不一定非常高,美國讀者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你看看美國的電視劇和好萊塢的電影就知道他們是什么水平。文學把自己提升到一個彌賽亞的位置,它和讀者之間會形成一個很大的落差,這是一個悲哀。
(作者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