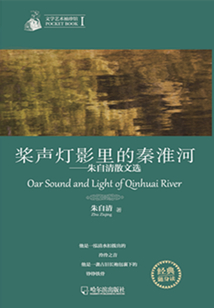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4評(píng)論第1章 前言
朱自清死后一天,北平街頭,一群小學(xué)生哄搶著一張報(bào)紙,其中一個(gè)驚慌地喊道:“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這一句話炸開在車馬喧囂的街頭,忽驚醒眾生,才知道君子其永逝,往日里漫長(zhǎng)的背影竟驀地被人們想起。后來,沈從文也追憶起這位當(dāng)年的同儕,他在《不毀滅的背影》中娓娓道來:“《毀滅》與《背影》的作者,站在住處窗口邊,沒有散文沒有詩(shī),默默地過了六年。這種午睡剛醒或黃昏前后鑲嵌到綠蔭窗口邊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個(gè)老同事記憶中,一定終生不易消失。”
這是不毀滅的背影,然而斯人已逝,影跡徒留,卻如月沒在闌干中,只把花香抑在黑暗下,搖曳難尋,氣為之滯。這是讓人想來便覺無比惆悵的景況,遠(yuǎn)行者背影凄迷,后來人在漸漸忘懷,至如今已一甲子時(shí)間了,拾掇前塵,恐怕該是走進(jìn)那方被歲月壓得漫長(zhǎng)的背影,尋住那人,再話巴山的時(shí)候了。
1898年11月22日,戊戌肅殺,正是北國(guó)露重霜濃之時(shí),江蘇東海城中卻誕下一名男嬰,初名朱自華,這就是以后的朱自清先生了。朱氏一門,本是紹興大姓,只因朱自清的祖父與父親先后宦居海城與揚(yáng)州,所以朱自清的前半生大多數(shù)時(shí)間都生活在揚(yáng)州城中安樂巷里。
少習(xí)經(jīng)史,工詩(shī)能文,在傳統(tǒng)家族中成長(zhǎng),深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朱自清,年尚少時(shí),便已經(jīng)根基扎實(shí),頗負(fù)才名。14歲上進(jìn)入當(dāng)?shù)刂袑W(xué)學(xué)習(xí),18歲上即考入了北京大學(xué)預(yù)科,第二年升入了本科哲學(xué)系,三年之后,朱自清便以優(yōu)異的成績(jī)修完全部課程提前畢業(yè)了。可以說,負(fù)書北大的幾年,正是朱自清一生學(xué)問的始翔處,這幾年間,朱自清順風(fēng)順?biāo)粌H學(xué)業(yè)優(yōu)長(zhǎng),在畢業(yè)的前一年,還出版了自己的處女詩(shī)集《睡吧,小小的人》。更是在入學(xué)之前,娶得了鄉(xiāng)里同庚武鐘謙為媳婦,齊家治平,一路之上順風(fēng)順?biāo)?
北大畢業(yè)之后,朱自清回歸揚(yáng)州,先后在江浙一帶多所中學(xué)任教。這一段時(shí)間,他加入了文學(xué)研究會(huì),積極參加風(fēng)靡一時(shí)的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與俞平伯、葉圣陶等人創(chuàng)辦《詩(shī)》月刊,發(fā)表了長(zhǎng)詩(shī)《毀滅》,并刊刻出版了個(gè)人新詩(shī)集《蹤跡》。作為新文學(xué)早期的重要詩(shī)人,朱自清開始以其詩(shī)名引人注目,也給當(dāng)時(shí)憤有余而力不足的文壇,帶來了些許鼎革的新鮮氣息。
當(dāng)然,朱自清最負(fù)盛名,也是讓他得以躋身現(xiàn)代文壇大師地位的是其散文的創(chuàng)作。朱自清的散文創(chuàng)作初為人知始于1923年,他發(fā)表的第一篇較有影響力的文章便是《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這篇文章代表了朱自清散文的早期風(fēng)格,正與其為人相似,是“拙誠(chéng)中又嫵媚(沈從文語(yǔ))”,而文章中如水波湯漾般流露出的細(xì)膩綿密,更是為人注目與玩味,頗受方家肯定。
從此之后,朱自清逐漸棄詩(shī)從文,將注意力轉(zhuǎn)移到了散文創(chuàng)作上。到了1928年,已經(jīng)被清華大學(xué)聘為文學(xué)教授的朱自清,出版了散文集《背影》。《背影》中包括了朱自清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這些名篇的誕生,意味著朱自清的散文創(chuàng)作已經(jīng)進(jìn)入了成熟與鼎盛的時(shí)期,而他的名字也將在文學(xué)史上占有沉甸甸的分量。這一時(shí)期的散文,褪去了早期的些許浮躁,從氣質(zhì)上逐漸變得洗練圓融而暢美,其創(chuàng)作的題材也產(chǎn)生了一些變化,從早期表現(xiàn)較多的世道流離與現(xiàn)實(shí)破瑣,如《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白種人——上帝的驕子》等等,轉(zhuǎn)向了對(duì)人倫輾轉(zhuǎn)、親情冷暖的觀照,如《背影》《兒女》等等。文字上的變化自然也是朱自清人生階段改變的心境反映,之前的青年學(xué)生,如今已經(jīng)變成了大學(xué)的教授。當(dāng)時(shí)少年,如今成了負(fù)擔(dān)家庭的男人,面對(duì)自己家中的種種頹敗變化,此間的心境想必早已嘗知現(xiàn)實(shí)的澀苦,再不如少年時(shí)那般閑情冶游與針砭褒貶了。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鳴之,此于朱自清是人生的不幸,于文學(xué)史卻正是一樁幸事,其間遷變因果,實(shí)在是耐人尋味。
正是在這一段時(shí)間,發(fā)生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朱自清的發(fā)妻武鐘謙因勞累過度而得癆病過世,朱自清痛不欲生,幾為斷腸;第二件事是,兩年之后,朱自清經(jīng)好友葉公超介紹結(jié)識(shí)了第二任妻子陳竹隱,同年,朱自清旅歐進(jìn)修,翌年,朱自清回國(guó)任清華大學(xué)文學(xué)系主任,并與陳竹隱結(jié)成了伉儷。這兩件事一悲一喜,悲喜相繼,而朱自清的生命與他的創(chuàng)作也在這悲喜相交中,發(fā)生了極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與陳竹隱結(jié)婚之后,已經(jīng)進(jìn)入而立之年、經(jīng)歷過人生悲喜的朱自清,變得愈發(fā)沉謹(jǐn),將更多的精力轉(zhuǎn)向了研究學(xué)問,而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雖然不曾停歇,但可以說,已經(jīng)進(jìn)入了衰年,雖然其風(fēng)范猶在,然生動(dòng)與靈氣同鼎盛時(shí)已難匹敵。不過,甚值一提者,乃是在此時(shí)期,朱自清出版了《歐游雜記》與《倫敦雜記》兩本記錄自己旅歐印象的散文小集,這兩本小集可說是朱自清散文創(chuàng)作生涯中較為別具一格的作品。
可惜可嘆的是,《倫敦雜記》之后,朱自清的作品便愈發(fā)鮮見了。這其中的原因,怪不得先生本人,其可罪者,正在這時(shí)代的顛亂。抗戰(zhàn)爆發(fā),偌大的華北,已經(jīng)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朱自清先生跟隨著清華諸校南遷的隊(duì)伍,一路顛沛,避禍昆明,成為了諸校改組后西南聯(lián)大的中國(guó)文學(xué)系主任。當(dāng)是時(shí),時(shí)艱歲苦,聯(lián)大八年摧折,讓他本就不好的身體愈發(fā)虛弱。抗戰(zhàn)勝利之后,朱自清隨校遷回北平,然而將息未得,內(nèi)戰(zhàn)又起。在兵熾烈、物價(jià)飛漲的日子里,人口眾多的朱家陷入了困窘的生活境地,不時(shí)地挨餓,這讓朱自清久積的胃病愈演愈烈。最后,朱自清先生又因聯(lián)名抗議并拒食美援面粉而忍饑挨餓,以至于胃病復(fù)發(fā),溘然長(zhǎng)逝。那一天是1948年8月12日,一代散文大家于貧病中死于北大附屬醫(yī)院病床之上,享年不過五十歲。
古人說,“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zhǎng)”。雖然先生已逝去,但是想起斯人斯事,尤堪擊節(jié),在那漫長(zhǎng)而偉岸的背影中,留給后人可以瞻知的,除了雋永的文氣,更是其為人之風(fēng)范。譬如聞一多先生被暗殺之后,雖然朱自清先生與其相交平平,但是感其氣節(jié),竟不顧生命之危險(xiǎn),參加紀(jì)念聞一多的追悼會(huì),并力主為聞一多修集。可惜的是,《聞一多全集》剛交付梓,尚未出版,朱自清先生卻已然駕鶴。后來,朱自清先生的弟子王瑤在悼念先生之時(shí),引用了一句當(dāng)年朱自清先生悼念聞一多先生的名言:“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我們確是不甘心的,怕我們這些后來人在大步向前的同時(shí),忘記了回首反顧,忘記了背后那一個(gè)漫長(zhǎng)的背影,忘記了背影中雋永的文章與閃光的靈魂。鑒于此,編者輯此小集,選編收錄了朱自清先生一生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以饗讀者。當(dāng)然,我們的工作或有疏漏,祈愿讀者與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