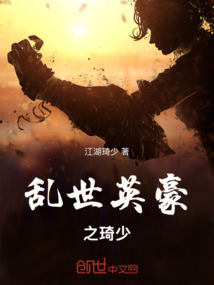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序:龍潛隋興,雙星墜世
開皇元年,春。
長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尚未褪去北周舊朝的塵霜,卻已被新朝的龍旗染得通紅。楊堅身著玄色龍袍,站在太極殿的丹陛之上,望著階下叩首的文武百官——有隨他從北周戰場拼殺出來的老將,如手握“破陣槍”的賀若弼,甲胄上還留著平齊時的箭痕;有楊家宗室的子弟,像他的侄子楊雄,腰間懸著祖傳的“青鋒”,那是當年跟著他在尉遲迥叛亂中斬將奪旗的兵器;更有謀士高颎,捧著新擬的《開皇律》,眼神里是對太平的期盼。
誰還記得二十年前,他還是北周的隨國公,跟著周武帝宇文邕南征北戰?那會兒他身邊,除了賀若弼、韓擒虎這些悍將,還有楊家的親族——堂兄楊弘提著大刀守在他身側,堂弟楊爽雖年幼,卻已跟著在軍營里學騎射,喊著“要幫叔父打天下”。
打天下,從來不是易事。
他記得攻北齊時,齊軍據守晉州,城墻高厚,賀若弼帶著敢死隊爬云梯,被箭射穿了左臂,硬是咬著牙斬了守將;他記得平定尉遲迥之亂,楊弘率楊家私兵死守武陟,三天三夜沒合眼,甲胄都被血浸透,見了他只說“家宅尚在,國公放心”;他記得周靜帝年幼,朝堂暗流涌動,高颎深夜叩門,低聲道“國公若不承天命,恐生大變,楊家上下難安”。
于是才有了禪讓那一日,周靜帝捧著玉璽的手在抖,他接過時,指尖也沉——那不是玉璽的重,是天下的重。身后楊家子弟的甲葉輕響,賀若弼等將軍按刀而立,他知道,這天下,是他帶著這些人,一刀一槍、一步一血拼出來的。
“國號隋。”他當時只說了這三個字,聲音不高,卻讓整座大殿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風。
就這么,隋朝立了。
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轉眼便是開皇十八年。
楊堅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需親上戰場的隨國公,鬢角有了霜色,卻依舊每日五更起,批閱奏折到深夜。長安的宮墻高了,楊家的子弟散在各地為官,賀若弼、韓擒虎成了柱國大將軍,高颎做了尚書左仆射,天下也算太平——除了偶爾北邊突厥擾邊,南邊陳朝殘余作亂,倒也無大事。
只是這年的八月,有些不一樣。
入秋以來,天就透著詭異。先是連續半月白日無云,卻不見烈日,只灰蒙蒙一片;后是夜里星子亂移,太史局的博士們捧著星圖急得滿頭汗,只說“紫微星旁有異星,軌跡不定”。楊堅召了太史令來問,老太史顫巍巍道:“陛下,此乃……雙星并出之兆,或吉或兇,未可知也。”
楊堅沒說話,只是望著窗外的天。他打了一輩子仗,不信鬼神,卻信天道有常。這異象,是福是禍?
直到八月十六這日。
午時三刻,日頭正盛,卻猛地暗了下去——不是烏云蔽日,是天頂像被蒙了層黑紗,連太陽都成了個模糊的光暈。緊接著,一道紫氣從東南方沖天而起,直上云霄,在空中散成兩道,一道往東北去,一道往西南去,快得像流星,卻帶著淡淡的金芒。
“天!那是什么!”長安街頭的百姓仰頭驚呼,小販扔了攤子,書生忘了趕路,連皇城根下巡邏的禁衛都停下了腳步。
同一刻,太極殿里,楊堅正握著朱筆批奏折,忽覺殿內一暗,抬頭見窗外紫氣乍現,筆尖一頓,墨滴落在“突厥求和”的奏折上,暈開一小團黑。他猛地起身,走到殿門口,望著紫氣消散的方向,眉頭緊鎖——那兩道氣,一道往太原,一道……不知去了何處。
而此時的太原,李家府邸正是熱鬧。
李家是關隴大族,李淵時任譙州刺史,雖不在家,府中卻因夫人生了二胎而喜氣洋洋。產房外,大公子李建成才七歲,抱著母親的衣角踮腳望,奶娘抱著剛換的襁褓布,丫鬟們端著熱水匆匆忙忙。
“哇——”
一聲響亮的啼哭劃破府院,正好是午時三刻,天暗紫氣現的那一刻。
穩婆抱著孩子出來,滿臉堆笑:“恭喜夫人!是位二公子!眉眼周正,哭聲洪亮,將來定是個有出息的!”
李夫人躺在床上,雖虛弱卻笑了,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臉:“生在這時候,天有異象,倒是個奇日子。”她望著窗外還未散盡的淡紫光暈,心里莫名一動——這孩子,或許真不一般。
無人知曉,同一刻,同一分,同一秒,距太原千里之外的陳朝故地(此時已屬隋),一處貧民窟里,也有一聲啼哭落了地。
貧民窟在江邊,低矮的草屋歪歪扭扭,四處是爛泥和垃圾。南風碩是個老實的農民,前幾日剛從田里回來,淋了場大雨,正發著熱,此刻卻撐著身子守在草屋門口,手緊緊攥著衣角。他媳婦難產,已經折騰了大半天,接生的婆子是鄰舍的大娘,沒什么章法,只在里頭急喊“使勁!再使勁!”
天暗下來的時候,南風碩嚇了一跳,以為要下暴雨,趕緊往屋頂看——怕漏雨。就在這時,屋里“哇”地一聲,孩子哭了。
大娘抱著個紅通通的小娃出來,滿身是汗:“生了!生了個小子!南風家的,你媳婦命硬,沒事!”
南風碩一下子沖過去,也顧不上臟,盯著那小娃看。小娃不胖,小臉皺巴巴的,卻睜著眼睛,黑亮黑亮的,正望著他。窗外那道往西南去的紫氣,恰好在草屋頂上散了,一縷淡淡的金光落在孩子額頭上,快得像錯覺。
南風碩搓著手,又看了看屋里虛弱的媳婦,咧開嘴笑了,眼角的皺紋堆起來:“生在這時候,又是個小子……就叫琦吧,南風琦。”
琦,是美玉的意思。他這輩子沒見過美玉,只聽村里教書先生說過,他希望這孩子,將來能像美玉一樣,別再像他,一輩子困在這爛泥里。
太陽重新亮起來時,紫氣已散,天恢復了正常。
太原李家的二公子,還沒取名,正被奶娘抱在襁褓里,暖烘烘的;貧民窟的南風琦,被他娘摟在懷里,蓋著打了補丁的舊棉被,也安穩地睡了。
沒人知道,午時三刻那一瞬間的天生異象,將這兩個孩子的命運,悄悄纏在了一起。
楊堅在太極殿上站了許久,最終只對太史令說:“記下今日異象,存檔。”他沒再多問,轉身回殿里繼續批奏折——天下事多,他顧不上一道說不清的紫氣。
賀若弼在府里教兒子練槍,聽見下人說午時異象,只哼了一聲:“天有異象常有,不如手上的槍實在。”揮槍挑落兒子手中的木槍,“再來!”
楊雄在楊家祠堂祭祖,望著祖宗牌位,低聲道:“愿楊家安穩,隋朝永固。”也沒把那點天變放在心上。
只有貧民窟的南風碩,抱著兒子南風琦,對著重新亮起來的太陽,憨憨地笑:“琦兒,以后好好長大。”
長安的龍旗依舊飄著,太原的李府喜氣未消,江邊的草屋炊煙漸起。
一個在朱門,一個在陋巷;一個生而便有世家光環,將來或入朝堂,或承家業;一個生而便處泥濘,未來或耕于田,或浪于江。
可命運這東西,從來由不得人算,這兩個孩子的路,才剛要開始。江湖的刀光劍影,朝堂的波譎云詭,楊家的興衰,李家的崛起,還有那藏在市井、隱于山林的武林門派——終有一天,會因他們二人,攪成一團。
而此刻,南風琦在娘懷里咂了咂嘴,李家二公子在襁褓里伸了個懶腰。
天,晴了。
(前序完)
《雙璧同生》第二章:稚子奇稟,高僧識璞
開皇十九年,春。
江邊的貧民窟里,草屋前的泥地上,南風琦正扶著墻根挪步。他才剛滿半歲,襁褓還松松垮垮掛在身上,小胳膊小腿細得像蘆葦桿,卻穩穩地踩著泥地,一步一晃地往灶臺挪——他娘正在灶臺前熬稀粥,陶罐咕嘟冒泡,熱氣混著米香飄出來。
“娘。”
一聲軟糯卻清晰的喚,讓正攪粥的南風氏手猛地一頓。她回過頭,看見兒子正仰著小臉看她,黑亮的眼睛眨了眨,又喊了聲:“粥,要溢啦。”
南風氏慌忙轉回去關火,手背擦了擦眼角,心還突突跳。這孩子打生下來就透著邪門。別家娃半歲還只會躺著蹬腿,他滿月就能穩穩地抬著頭看天,四個月時扶著炕沿能坐得筆直,如今才半歲,竟能走路,還會說整句話了。
“琦兒慢點,地上滑。”她把兒子抱起來,用粗布巾擦了擦他沾泥的小腳,“才多大點,就不安生。”
南風琦往她懷里蹭了蹭,小手指著窗外:“阿爹,回來?”他爹南風碩前幾日去江邊碼頭幫工,說好今日回。
話音剛落,草屋門“吱呀”開了,南風碩扛著半袋糙米進來,臉上沾著汗和灰,一進門就笑:“我兒這鼻子靈,爹剛到門口就知道了?”他放下米袋,伸手抱過兒子,掂量著:“又沉了點,好,好。”
鄰居張大娘正好路過,聽見屋里動靜,探進頭來:“他嬸子,你家琦兒又說話了?哎喲,這娃真是……莫不是天上的星宿落了凡?”她嘖著嘴,看南風琦的眼神又驚又奇,“我家虎子都一歲了,還只會‘啊啊’叫,你家這半歲就跟小大人似的,邪性,邪性。”
南風氏笑著擺手,心里卻也犯嘀咕。這孩子不僅說話早,眼神也清亮得嚇人,看人時直勾勾的,像能看透人心似的。夜里不哭鬧,要么安安靜靜躺著看屋頂,要么就睜著眼聽她和他爹說話,仿佛都能聽懂。
日子一晃,南風琦滿了一歲。
此時的他,早不用人扶,在貧民窟的窄巷里跑得利索,跟個小炮仗似的。更奇的是嘴甜,見了誰都能嘮上兩句。張大娘縫補時,他蹲在旁邊看,能指著針線說“大娘,線歪了”;路過賣豆腐的王老頭,他會仰著脖子喊“王爺爺,今日豆腐香”;連碼頭扛活的糙漢們,他都能湊過去,問“叔叔們累不累,歇會兒吧”。
有回南風氏織布,線斷了好幾回,急得嘆氣。南風琦搬個小板凳坐在旁邊,小手托著下巴看了半晌,突然說:“娘,線要順著勁兒拉,別太用蠻力。”南風氏一愣,試著按他說的做,果然順多了。她瞅著兒子,越看越覺得陌生——這哪像個一歲娃,倒像個揣著老魂的小大人。
到了兩歲上,南風琦又添了新本事。
貧民窟外有條小街,街口有個老秀才擺了個識字攤,教幾個富家孩子念書。南風琦每天幫娘撿完柴,就蹲在攤外聽。老秀才念“床前明月光”,他聽兩遍就跟著哼;念“關關雎鳩”,他看一眼竹簡上的字,下次再路過,竟能指著字念出來。
老秀才驚得胡子都抖了,拉著他問:“你識得這字?”
南風琦點頭:“先生念過,看一眼就記下了。”
“那你會吟嗎?”
他歪著頭想了想,望著江邊的晚霞,脆生生念:“夕陽鋪水中,半江暖半江……嗯,涼?”雖改了原句,卻也貼切,把老秀才驚得直呼“神童!真是神童!”
從此老秀才常把他叫到攤前,教他念詩認字。南風琦過目不忘,教一遍就會,不過半年,常見的詩書竟能背下十好幾首,有時還自己瞎編兩句,雖稚嫩,卻有模有樣。
街坊們更覺得這孩子不一般,有人說他是“文曲星下凡”,也有人私下嘀咕“太過聰明怕不是好事”,南風氏聽了,只把兒子看得更緊,反復叮囑:“琦兒,在外別太顯露,安安穩穩的就好。”南風琦似懂非懂,卻乖乖點頭。
這年秋天,鄰居家添了個女娃,比南風琦小一歲,爹娘給取名“阿禾”。阿禾剛會爬時,南風琦就常蹲在她家門檻上看,阿禾哭了,他就拿自己撿的小石子哄;阿禾學走路摔了,他就扶著她的胳膊慢慢教。倆孩子湊在一塊兒,一個沉穩得像小大人,一個軟乎乎黏人,倒成了貧民窟里一道稀奇的景致。
轉眼又是一年,南風琦三歲了。
開春時,南風碩覺得碼頭幫工掙的錢不夠養家,聽說北邊修運河缺人手,工錢給得多,便跟南風氏商量著要去。南風氏雖舍不得,卻也知道家里窮,咬牙應了:“你在外當心,家里有我和琦兒呢。”
爹走后,南風琦更懂事了。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幫娘掃院子、撿柴火,娘織布時,他就坐在旁邊遞線軸、理線頭,小手靈活得很。有時娘織到深夜,他熬不住打盹,也硬撐著睜著眼:“娘,我陪著你。”
貧民窟里的其他孩子,三歲正是瘋跑打鬧的年紀,滾在泥里捉蟲,爬到樹上掏鳥窩,唯有南風琦,總是安安靜靜地干活,要么就抱著阿禾教她認地上的草名,瘦小的身子透著與年齡不符的沉穩。
這日午后,南風琦幫娘把織好的粗布送到街口的布莊,往回走時,路過自家草屋旁的老槐樹下,見一個老和尚站在那兒。老和尚穿一身洗得發白的僧袍,背著個小包袱,眉眼溫和,額上有淡淡的戒疤,像是走了遠路,臉上帶著倦色。
見南風琦過來,老和尚合掌行了個禮,聲音沙啞:“小施主,老衲趕路至此,口干舌燥,不知可否討碗水喝?”
南風琦沒遲疑,轉身跑進屋里,從灶臺上拿起一個粗陶壺,又拿了個碗,倒了碗水遞過去:“大師,喝水。”
老和尚接過碗,喝了兩口,緩過些勁來,低頭看他。這孩子雖穿得破舊,補丁摞補丁,卻干干凈凈,眼睛亮得像秋水,見了陌生人不怯不躲,眼神里透著股通透勁兒,不像尋常農家娃。
“多謝小施主。”老和尚把碗遞還給他,目光落在他手上——那是雙小孩的手,卻因常干活,指節有些泛紅,掌心還有薄繭,可偏偏手指修長,骨節分明,看著就不一般。
老和尚心里一動,又問:“小施主,可否讓老衲看看你的手相?”
南風琦眨了眨眼,他聽過街坊說“看手相算命”,卻不知這和尚要做什么,但見他和善,便伸出小手:“可以呀,大師。”
老和尚輕輕握住他的手,指尖觸到他手腕時,猛地一頓。隨即他指尖微動,順著他的掌紋、骨節細細摸過,又搭了搭他的脈搏,原本平和的眼神漸漸變了,先是驚訝,再是震動,最后竟難掩激動,呼吸都略急促了些。
這孩子……
他掌心的紋路清晰,卻隱隱透著一股氣感,搭脈時更明顯——尋常三歲孩童經脈未通,氣血微弱,可這孩子的經脈,竟已通了七處!雖未全通,卻已是天縱之資,再看他的骨骼,肩寬腰窄,腕骨清奇,竟是百年難遇的練武坯子!
“奇才……真是奇才啊……”老和尚喃喃自語,盯著南風琦的眼睛亮得驚人,“八脈七通,骨相清奇,天生的武學根器,老衲竟能在此遇到……”
南風琦被他看得有些發愣:“大師,我手怎么了?”
老和尚這才回過神,松開他的手,合掌道:“小施主,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南風琦。”
“南風琦……好名字。”老和尚點點頭,又問,“你娘在家嗎?老衲想與你娘說幾句話。”
南風琦領著他進了屋。南風氏正在織布,見兒子帶個和尚進來,忙停下手里的活:“大師是?”
“老衲慧覺,自少林寺而來。”慧覺和尚合掌行禮,目光落在南風氏身上,語氣鄭重,“女施主,老衲方才見令郎,發現他是百年難遇的練武奇才,八脈七通,骨相清奇,乃是天生的‘武骨’,若能得名師指點,將來必成大器。老衲斗膽,想收他為入室弟子,帶他回少林寺學藝,不知女施主肯不肯?”
南風氏愣住了,手里的線軸“啪”地掉在地上。她看看和尚,又看看兒子,搖了搖頭:“大師,不行啊。琦兒還小,他爹又不在家,我……我離不開他,他也離不開我。”她把南風琦拉到身邊,緊緊攥著他的手,眼里滿是不舍,“再說我們是農家,學什么武啊,安安分分過日子就好。”
慧覺也不著急,耐心道:“女施主莫急。令郎這般根器,若埋沒在市井,實在可惜。少林寺乃佛門清凈地,老衲定會悉心教導,不僅教他武藝,也教他讀書識字,斷不會虧待他。待他學成,若想回來,老衲絕不阻攔。他是天生的武材,若不習武,恐辜負了這身天賦啊。”
他又說了許多,講少林寺的規矩,講習武并非只為打斗,也能強身健體,將來能護自己、護家人,甚至能做些俠義事。南風氏雖不懂“武骨”“根器”,卻見這和尚不像壞人,又看兒子聽得認真,心里漸漸動搖——她也知道兒子不一般,總不能讓他一輩子困在這貧民窟里,跟著自己受窮。
“娘。”南風琦拉了拉她的衣角,仰著頭,“我想去。我學了本事,就能保護娘,還能等爹回來。”
南風氏看著兒子清亮的眼睛,又看慧覺和尚誠懇的神色,終于紅了眼眶,抹了把淚:“大師……那……那你可得好好待他。他要是想娘了……”
“女施主放心,”慧覺忙道,“老衲定會視他如己出。日后若有機會,也會讓他回來探望。”
定下了去意,南風氏連夜給兒子縫了件新布衫,又把家里僅有的幾個銅板塞在他兜里。第二天一早,南風琦去跟阿禾告別。阿禾還不懂“分別”是什么,只抱著他給的小石子,仰著臉問:“琦哥哥,你要去哪?”
“我去學本事,”南風琦摸了摸她的頭,“等我學好了,就回來教你打壞蛋。”
阿禾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我等你。”
慧覺和尚背著包袱,牽著南風琦的小手,往江邊的路走去。南風氏站在草屋門口,望著兒子瘦小的背影,直到看不見了,才捂著臉哭出聲。
南風琦回頭望了望自家草屋,又望了望阿禾站的方向,然后轉過頭,跟著慧覺往前走去。他不知道少林寺有多遠,也不知道“習武”是什么,只知道娘答應了,大師說能學本事,那便去學。
江風拂過,吹起他的衣角,也吹起了他往后數十年,與江湖、與命運糾纏的開端。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