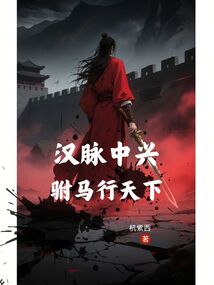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洛陽火光
夜風從宮城方向灌來,帶著嗆人的焦糊味,像誰把一口黑鍋扣在了城上。屋脊瓦一片片炸開,火星往下砸,街巷里人馬嘶叫攪成團,哭聲罵聲像水汽一樣在冷風里亂撞。東市口那邊半扇門拍得“砰砰”響,紅影映在門楣上,把牌匾上的字照得歪歪斜斜。
衛淵是被冷醒的。身下不是床,是一層麥秸敗草,背后硌著兩截車轅。周圍人的腳步、牛喘氣聲、男人女人的哭罵一起砸進耳朵,他愣了半刻,心跳得厲害。鼻子里全是潮火味,夾著牲口騷。伸手一摸,指腹摸到的不是被子,是粗糲的草繩。他忽然明白:那場始料不及的劇烈眩暈不是夢——他真的不在教室里了,不在現代了。
衛淵哆嗦著坐起,額頭冷汗一層。他努力把碎裂的記憶拼到一起——三十多歲,大學歷史系老師,講的是魏晉隋唐的政治與財政,帶研究生,備課備到凌晨,午后給本科生上“東漢末至三國政區變遷”。講到董卓入洛陽、廢少帝、迎獻帝那一段,黑板上寫下“中平六年”“初平元年”,學生提問:老師,董卓到底啥時燒的洛陽?衛淵說:初平元年冬,西遷長安之前。話剛落,眼前一黑,心口像被人結結實實捶了一拳。然后,就是這團火。
為什么偏偏是自己?為什么偏偏是這段歷史?還有,衛淵低頭,他先下意識摸袖口——粗布短褐,線腳起毛;手腕處別了一小塊歪角銅片,背面刻著兩個字:宣陽。像坊門上給差役看路用的識牌。他又摸到三枚沉甸甸的五銖,邊沿磨得亮,再往里一摸,指尖碰到一截冰涼的金屬條,心口“咚”的一跳——打火機。袖子一扣,他立刻把它按在腕窩里,像捂住一條命。他摸摸臉,顴骨高、下巴尖,指腹刮過還帶青春刺。不對勁的地方太多,但最刺眼的是,他不再是三十多歲的自己,而是個十七八歲的半大小子。
這不是夢。他需要盡快知道的,是這里的時間、地點,和他該以什么身份活下去。
先認時、認地、認人。他抬頭看天,風硬、露涼,泥皮凍得發白,是冬臘的脾氣;宮闕那邊在燒,御道傳來鼓聲,先短后長,像在冷鍋上敲三下又拖一長線——讀詔。耳邊有人嘟囔:“何太尉叫閹豎害咧。”又有人接:“袁本初帶人殺閹人。”再有老漢壓低聲道:“董仲穎西來,成皋那邊都打翻了。”三句話像三顆釘子,把時間釘住——中平六年秋冬之交,公元一八九年。書上那條“加速下墜的長坡”,眼下就在腳邊。
他抬頭看天。風硬、露涼、泥皮凍白,是冬臘的脾氣;宮城方向一片臟紅,瓦脊“叭叭”炸響,火星像雨點往下掉。御道那邊有鼓,先短后長,讀詔。巷口有人嘟囔:“何太尉叫閹豎害咧。”又有人接:“袁本初殺閹人。”再有老漢壓著嗓子道:“董仲穎西來,成皋都打翻咧。”三句話像三顆釘,把時間釘住——中平六年秋冬之交,公元一八九年。講臺上被他稱作“加速下墜長坡”的那一行粉筆字,此刻變成火、灰、血和冷風。
他吸了一口氣,胸口發疼,腦子卻像進了冷水,反而清。衛淵給自己定了個“五分鐘—一小時—一天”的適應表:
第一步,五分鐘內確認身份與可用資源:十七歲的身架,能走能寫;三枚五銖,一截坊識;陌生卻干凈的里衫——不是最低等的流民;一個絕不能露的“火種”。
第二步,一小時內給自己掛一條“秩序上的繩”:找里、找亭、找司隸或金吾衛的公文腳,哪怕只是個“臨時抄”的活計。沒有名籍的人,在亂世里就是任人捉的影子。
第三步,一天內穩住胃和水:灶、鹽、沸水、廁與井的距離,越早立規矩,越不死人。史書里那些“荒政條目”,放到地上就是活命條款。
想清楚這三件,他才真正看見火。
北面天被燒成一團臟紅。街上人馬擠成疙瘩,誰都只顧自己。東市口一扇半門“砰砰”亂甩,紅影把牌匾照得歪斜。一個大胡子漢子擠過來,肩頭搭著半張羊皮,氣息白得像噴霧:“小子,你坐俺車輪底下咧。”他順手把葫蘆塞過來,“渴不?剩半口。”
“多謝大哥。”衛淵借勢往墻根一縮,避風,順嘴問:“往哪走?”
“西門。弘農那邊。”大胡子抖抖肩,“晚一會兒,城門要關死。”
他不再追問。這會兒嘴問不如手做。他把目光掃到巷里一間半開著門的藥鋪——昨夜他就是在那門檐下躲了一覺。灶里還藏著一星紅,門里探出個瘦老頭,眉眼卻亮,是掌柜成大。衛淵拱手:“成大爺,借壁一用,寫兩句給大家看。”
“寫。”老成把灶里一截炭頭遞出來,眼皮一挑,“你手穩,字直。”
衛淵把一塊舊門板豎到門側,刷刷寫下四行大字:井在上風,廁離十步,婦孺在內,壯丁輪守。字不漂亮,但硬。他又在另條木片上刻四字:門外不接。把條橫在門檻,留半寸縫。
“誰識字,過來念。”他抬聲。一名瘦高少年挪過來,接炭頭,第一遍結巴,第二遍順了。圍著的婦人一聽“婦孺在內”,本能往里挪,抱孩子的先進去;壯漢不服也只好讓半步。老成“哼”了一聲:“牌子立著,人心才不軟。”
井在北角,風順。兩位守井的老嫗縮在井欄邊,一手抄袖,一手拎繩。衛淵帶著瘦高少年、藥鋪小伙二旦擦井欄、理井繩,把三家為一結的麻繩穿過手腕,活扣一拉就緊。他指井柱:“上風口打水,別對屋門。水舀上來先過布,再煮,得見大滾,不是冒氣就停。”
“鹽有沒?”二旦問。墻影里探出半張笑臉,是個荊楚腔的商販,眼縫瞇著,嘴角彎著:“郎君,鹽是一撮,絹是兩尺,先拿用。欠賬寫半名,至春分償。”尾音拖圓,“活路呀——水是命根子也。”
“多謝。”衛淵接小包,把銅壺安在矮灶,壺嘴抹油灰,火口壓低,煙順梁走。灶省柴,火穩,婦孺先喝水,一圈圈輪。
人擠得正熱鬧,巷外擠進兩名披灰褙子的男人,袖口收得緊,笑溫溫:“諸位依法守井,功在社里。掖庭小令囑我等接失散內眷,章在此。”袖里一翻,亮半枚磨圓的銅章。
“掖庭接人,自有竹牌,不露章。”衛淵用木條往前頂半寸,擋住他視線,“牌呢?”
“忘在門里。”對方笑不動。后頭那條影子忽探手,去抓墻邊一名抱包的婦人。徐州口音的壯漢整個人橫過去,肩如門,砰的一聲把那人撞在牌柱。二旦抄起門閂往地上一橫,咬字:“門外不接。”眾人像草墻合攏,把門里那一塊空地護嚴實。披灰褙子的笑意淡了半指:“幾位誤會。”衛淵亮出袖里一角紙——方才從巷口掠過的青褙子書吏塞來的小條:太學生守井,司隸存案,照簿補給。他指“存案”二字,尾音收直,不留縫:“此處只守,不接。”
那兩人腳跟在門檻上一頓,拉同伴退去。臨走時腳尖在石上點了一下,像在心里刻記號。
巳時將近,御道鼓聲再起,字句被風掰碎,只剩“奉”“遷”“位”。青褙子書吏又從巷口掠過,袖口墨漬未干,眼下青。他一見牌,腳步一頓,再塞來一條:“博士(注:官職-國家的學官/專家官)處言:坊中有牌有簿者,三日一抽,送尚書臺印驗。”關東腔,尾音緊。老成把紙按在牌腳,笑出了褶子:“有這個,挨罵也不心虛。”
“照簿”三個字是鑰匙。衛淵立刻把舊紙抄成“口簿”“食簿”“守更簿”,空出欄:戶名、口數、丁口、老弱、所至;另頁寫“更次、驗人、簽”。他把簿壓住,朝十步外一名膀闊腰圓的徐州人擺手:“大哥,借你肩膀。”徐州漢子應一聲。衛淵把十枚細竹穿繩編號,交給他與二旦,“袖里各揣一串,誰排到袖上一點,點過靠墻坐;誰往里擠,門閂橫一橫。棍子是力氣,竹簽是規矩。”
矮個太學生抱木杵過來,低聲:“博士讓我守井,抄牌。”他指“守井四則”,再看“門外不接”,眼睛里亮了一下,“字寫得直。”
“直,是給后來的人一眼照做。”衛淵把“謹守”兩字再描厚。
申時前后,一隊金吾衛自坊門外擦過。為首黑面闊口,關西腔短響。他看牌,丟四字:“夜里莫出。”像把釘子釘空氣里。二旦嘴快:“爺,有印不?”黑面隊長橫掃一眼,鼻翼一張:“明日貼。”隨從小吏當場遞半張未寫完的告示,印腳“金吾衛”,紅得刺眼。走時,隊長又瞥牌腳那張司隸紙,鼻翼輕動,像嗅墨香。
暮色壓下來。灶口壓低,壺嘴抹油灰,煙走梁;小祠里清出一角,婦孺靠墻坐。衛淵把十枚“門引”分成兩串,串在門背;又換三根長麻繩,交給二旦、徐州漢子和那瘦高少年,“夜里守口,各執一端。”他把門閂尾端裹布,免得夜里一橫傷人;把“慢并”(注:文里是口令+口頭禪,意思就是:放慢、拉開、別擠)兩個字貼墻,問“慢并”的,指牌;不問的,也看見。
一更將打,門縫外傳兩短一長的敲擊。二旦貼著門縫回兩短一長,里頭那只手摸到竹片,輕掐一回,再回握一下。門縫一線,人影像魚順水滑進。衛淵不看,落筆記:二更初入十一,退一。那“退一”是個半大子臨陣腿軟,站在門縫前不動,眼白發亮。他不勸,把人帶回井邊,遞一盞熱水,寫“退”,不寫評語。
第二撥轉后溝時,泥里絆腳。瘦高少年拋麻繩前后接力,二旦在后敲節:“慢——并,慢——并。”角門里那只手敲一下鐵鉤,像問;里頭人輕輕“嗯”一聲,像答。第二撥進完,風往回灌,火苗抖了一抖,又穩住。
第三撥臨檢。兩名關西甲士折回來,刀背在掌,視線冷硬:“何人?”衛淵舉牌,指“守井四則”,再指“司隸存案”,尾音盡量穩:“守口先。”為首黑面闊口盯牌,目光滑過“門外不接”,停半息,又落在簿頁露出的“戶口、丁口、老弱”。那眼像刀背緩緩在紙上壓。衛淵只露角,不露全。黑面闊口鼻翼一動,啞聲:“嗯。走吧。”四字像把刀背收鞘。
末更將盡,角門里遞出一只小布包,里面兩雙凈鞋、一撮鹽,底下壓一條薄紙:夜里暗號改一長一短,勿聲張。掖庭小令署。二旦把紙遞給衛淵,眼睛亮。他一言不發夾進簿里,心口那截宣陽銅片冰涼。他知道,這不是給誰的私信,是給會守規矩的人一條活路。
夜更深,火堆旁影子一層層堆。臨近五更,遠處木輪轔轔壓過青石。巷口掠過一隊押車兵,皮甲黑緊,刀鞘長,馬蹄聲短促。兩輛小車的簾子拉得死緊,簾角被風掀起一線,那線里露出半寸細綾,團壽老花,金線壓邊。火光一閃,那團壽邊角像隱隱壓了個“萬”字的半撇半捺,轉瞬又收回簾里。衛淵把目光垂下,像沒看見,只把竹簽在簿角輕點:某更有官車過,簾角壓綾。
天邊泛白。青褙子書吏第三次掠巷口,照舊塞紙:太學生守井,司隸存案,照簿補給。尾筆收緊,像把這一夜扎住。尚書臺的人午間到,不進門,先看牌,再看簿,笏板角在“二更初入十一、退一”那行輕輕一點:“直。”又指“門外不接”問“何據”。衛淵亮司隸回執半角,指“存案”;把金吾宵禁告示釘上,指“印腳”。尚書吏嗯一聲,在簿角蓋小印,印泥淡,落紙硬。臨走盯“門外不接”一眼,淡淡道:“有法源,方敢寫硬。”袖擺一收,走得像一條直線。
人心被這幾錘子釘住,井邊更齊。徐州漢子提小罐坐十步外,照看“誰排到袖上一點”的規矩,嘴里嘟囔:“牌子硬,人心才不軟。”老嫗把井繩結打得挺;矮個太學生把“門引樣式”抄在竹片背,點小小“星眼”。有人問“星眼啥”,二旦瞪眼:“你懂個錘子,就曉得假的沒點。”眾人笑。
午前,縣廷差吏來驗簿。四十來歲鄭吏,臉白胡細,手里一方小印,印面刻“洛陽縣吏承發”。他掃兩眼,忽問:“這‘庚申’二字寫得清,誰筆?”
老成用下巴點衛淵。鄭吏把袖里一條竹簡往案上一拍:“抄一份令。”竹簡展開,上寫:“令:坊門自今至朔,申嚴夜禁。漏未盡者,不得開門。違者,笞。里正晝三巡、夜兩巡,遇火舉刁斗。”字不長,三四十個。衛淵執筆,下筆壓腕,收鋒短,字不飄。鄭吏“嗯”一聲,把簡收起,又在簿角咔噠蓋印,給他一枚五銖:“筆札之費。”
“愿不愿暫寫‘外臺抄’?”鄭吏看他一眼,“回縣廷稟,可掛個名籍。”
“愿意。”衛淵答得干脆。名籍就是繩,抓住繩才能往上爬。
午后風緩,陽光斜在破墻,照出一層淡白。矮個太學生抱一摞竹片跑來,興沖沖:“博士說:太學有書要轉到鴻臚庫房,怕火。有人沒?”老成撇嘴:“我這破鋪子抽不開人。”他看向衛淵,“你去一遭,把命拴住。回來還得抄簿。”
“去。”衛淵卷袖。門口那輛獨輪小輿靠墻躺著,輪鐵箍緊,輿把順手。他拉著太學生,一趟趟把書匣往鴻臚寺小庫搬。匣上貼“左氏”“禮記”“周禮”的破簽,簡尾編繩早斷,補的麻線一截截露外。巷口有騎軍掠過,旗上一個“并”字,馬蹄短急,塵土打臉生疼。矮個太學生縮了一下:“聽說并州有個呂奉先,方天戟,扛鼎。”衛淵不接,只把輿把握穩。那些名他認識;這些路他更熟。他知道刀口往哪邊轉,也知道自己手上拿的是竹片、簿冊、繩子。
黃昏,最后一匣書也搬進庫。鴻臚寺寺人怯怯在小札角上摁了個私印。太學生塞兩枚五銖:“先生,博士囑托,給個辛苦。”衛淵收一枚,退一枚:“夠了。回去還要抄簿。”
回到坊口,黑面隊長正把新的“夜禁告示”釘墻,抬下巴給他看:“字識不?”
“識。”衛淵笑,“守口先。”
黑面隊長鼻翼一動,像笑了:“你這小子,嘴直。”
夜里風又緊。二旦把更牌架在門背,刻一橫八小口,小木丁插第一口,誰值更誰挪一格。衛淵把“護糧小史”的小木牌跟口簿壓一起,又把“濾布—大滾—加鹽”的三連寫在竹片上,交給最老實的少年:“你的活。”
“先生,我記了。”少年握竹片,臉上帶著火光烘出的紅。
這一整天,他從“我到底在哪里”為起點,走到“我現在該干什么”的位置。適應不是把心捏硬,而是把手伸出來干活。他把名字寫進了坊簿,也把自己穩穩系在洛陽的制度線上。火還在燒,風還在刮,明天未必更好,但他已經知道要怎么活:靠寫得直的字,靠說得清的理,靠一根根看似不起眼的繩,把人和秩序一線線攏起來。
他靠著門柱坐下,閉了閉眼。心里那張“適應表”又彈出來,在最后一行添了個小字眼:留中——凡要緊之事,先留中,用流程卡住。想完,心口里那點亂像被手輕輕按住。
遠處鐘鼓再響三下。小祠里孩子哭聲停,老人翻身,熱窩底下的溫氣往上冒。宮城方向的紅低了半寸,井里水在壺嘴翻出細白泡,像在輕輕說話。衛淵摸了摸袖里的宣陽小銅片,冰;摸摸簿角,硬;摸摸那截絕不能露的火種,冷。他對自己說:先把今天的線拴牢,明天再接下一根。至于夜里掠過那簾角里的一寸細綾,他只在簿上留了一個點,不評、不斷、不追。記下,等它自己露出更多線頭。屆時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