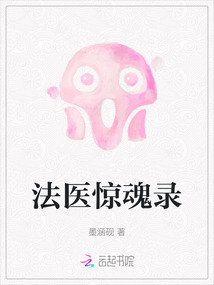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盲盒剖開藏舊物 老祖宗深夜“串門”
太平間的敲門聲停得像被掐斷的琴弦,周明抱著鐵盒子的手緊得發(fā)白:“走、走了?老祖宗轉(zhuǎn)場了?”
“轉(zhuǎn)場也得留個(gè)話。”我把玉佩塞進(jìn)證物袋,拎著解剖刀往太平間走,“法醫(yī)得聽全尸體的話,老祖宗的更不能漏。”
剛推開門,寒氣裹著尸蠟的油膩味撲面而來,墻上溫度計(jì)卡在12℃,指針還在顫,像被凍住了似的。裝女尸的冰柜門開著道縫,白霧絲絲縷縷飄出來,在應(yīng)急燈下發(fā)著冷光,活像游來游去的白蛇。
“老祖宗想透透氣?”我伸手去關(guān)門,目光突然釘在女尸臉上——她嘴角的笑意深了些,緊閉的眼皮裂了條縫,黑黢黢的眼窩正對著我。
周明在身后吸冷氣:“她、她看我呢!我可沒說她壞話……”
我沒理他,盯著女尸攤開的手。剛才攥死的黑匣子掉在冰柜底,紅布爛成碎絮,露出半張“李”字紙,還有沓棉紙裹著的硬物。鑷子掀開棉紙的瞬間,我心猛地一跳——銀簪,簪頭蓮花缺了角,正好對上匣子上的花紋。紅繩系著的鈴鐺,竟和巨人觀刀上的是一對,只是這鈴鐺刻著“蘇”字。
“蘇?”我忽然想起她袖口的盤扣,歪扭的針腳像匆忙縫的,難道是她自己繡的?
周明湊過來:“定情信物?老祖宗想跟夫君重逢?”
“重逢個(gè)鬼。”我捏著銀簪翻轉(zhuǎn),簪尾刻著“官”字,“這是官造的,尋常人戴不起。鈴鐺是一對,搞不好……”
“哐當(dāng)!”解剖室突然巨響,像器械車翻了。周明蹦起來:“巨人觀越獄了?”
沖回去時(shí),解剖臺空了!地上只剩攤黃水混著黑泥,水果刀插在地板縫里,紅繩還在晃。周明聲音劈叉:“跑了?化成水了?”
我摸了摸黃水,竟帶點(diǎn)溫度。墻角通風(fēng)口的柵欄沾著青黑皮屑,像是被硬擠過去的:“不是跑的,是被拖走的,或者自己鉆進(jìn)去的。”
周明臉綠了:“他那體型鉆通風(fēng)口?卡成肉罐頭還差不多!”
走廊盡頭突然“咚”的一聲悶響,像重物砸地。我和周明抄起止血鉗沖過去——是檔案室。
門虛掩著,透出昏黃的光。推開門,塵封味混著腐敗氣撲面而來。月光下,巨人觀趴在地上,后背裂著大口子,旁邊蹲著個(gè)穿白大褂的人影,正用放大鏡瞅尸體背。
“誰?”我大喝著舉起止血鉗。那人回頭,月光照亮臉——是退休的王老頭!
他去年手抖退休,深居簡出,怎么會(huì)在這?他卻招手:“小川快來,這尸體背上有東西!”
湊過去一看,尸體后背皮膚里嵌著木牌,血污糊著字。王老頭擦凈,露出“李崇德”三個(gè)字。我心里咯噔,這不是那半張紙上的“李”字可能對應(yīng)的名字嗎?
王老頭推了推老花鏡:“乾隆年間的知府,暴斃后棺材里只有官服,傳說是貪了貢品被滅口,尸身扔江里了。”
周明咽唾沫:“巨人觀是他后代?帶著木牌死了?還被老祖宗認(rèn)親?”
“不止認(rèn)親。”王老頭指向巨人觀脖子,腫脹的皮膚有道勒痕,邊緣有繩印,“他是被勒死的,肚子上的刀是后插的,想偽裝自殺。”
我想起那刀的角度,像個(gè)標(biāo)記。正想說什么,太平間又傳來“篤篤篤”的敲門聲,更急了,像有人在里面拼命撞。
王老頭臉色驟變,抓起油燈就跑:“壞了!老蘇要出來了!”
“老蘇?那具女尸?”我跟上追問。
“她叫蘇婉,李崇德的小妾,也是我家祖上的遠(yuǎn)親。”王老頭頭也不回,“她發(fā)現(xiàn)李崇德貪贓,藏了證據(jù),被滅口時(shí)連贓物一起封進(jìn)棺材。我祖上是仵作,受她所托藏了半塊玉佩,說若她出事,讓后人憑玉佩找證據(jù)揭穿李崇德。”
沖到太平間,敲門聲急得像擂鼓,冰柜門搖搖欲墜,白霧里竟夾著血絲。王老頭照向門縫,臉慘白:“她指甲在流血!”
我拉開冰柜門,血腥味混著尸蠟味沖過來。蘇婉的手抬到胸前,蠟化的指尖滲著暗紅血珠,嘴里卡著半塊玉佩——和巨人觀肚子里的那半塊嚴(yán)絲合縫!
“兩塊合起來是鑰匙。”王老頭掏出個(gè)布包,里面是本賬冊,“李崇德貪了宮里的和田玉,藏在護(hù)城河底暗格。蘇婉知道位置,才被滅口。”
周明指著蘇婉腳邊,一串濕漉漉的腳印延伸向解剖室,沾的黑泥和巨人觀身上的一樣:“是巨人觀把玉佩塞給她的?他不是被勒死了嗎?”
“他是被滅口的,但不是李崇德的人。”我拼合兩塊玉佩,背面顯出“河底三尺,蓮開見玉”。“他在找證據(jù),殺他的人不想讓當(dāng)年的事敗露。”
“哐當(dāng)!”太平間窗戶被撞開,暴雨灌進(jìn)來,油燈瘋狂搖晃。河面漂著個(gè)黑東西,閃電照出是口棺材,棺蓋敞開,里面堆著白玉,閃著慘白的光。
王老頭指著棺材咳嗽:“那是蘇婉藏的贓物棺!怎么自己浮上來了?”
我突然想起蘇婉袖口的盤扣,歪扭的針腳根本是河道路線圖!巨人觀肚子上的刀,角度正指肋骨下三寸,對應(yīng)“河底三尺”。
“有人早找到了贓物,殺巨人觀是嫁禍,把棺材弄上來想偽裝水鬼作祟。”我抓起解剖刀,“去河邊,能把兩百斤巨人觀塞進(jìn)通風(fēng)口、讓棺材浮上來的,不是鬼神。”
周明腿肚子轉(zhuǎn)筋:“去河邊?萬一他又跑出來……”
“他不會(huì)跑了。”我看了眼蘇婉,她嘴角的笑意淡了,眼窩也不那么黑了,“他該做的做完了。該我們替老祖宗算賬了。”
暴雨里,護(hù)城河蘆葦叢傳來拖拽聲。我和王老頭沖過去,撥開蘆葦,看見艘漁船,船尾麻繩扎進(jìn)水里,一個(gè)穿雨衣的人影正用錘子往水里釘東西——是刑偵隊(duì)那個(gè)吐得昏天黑地的實(shí)習(xí)生!
“是你殺了巨人觀?”我踩上船,看見船板上的黑布袋,露出的白玉正是贓物。
實(shí)習(xí)生扯下雨衣,脖子上掛著塊同料玉佩:“他活該!非要翻李家舊賬!這玉是我家傳的,憑什么交出去?”
“李家后人?”王老頭抖著賬冊,“李崇德貪贓枉法,你還想護(hù)著?”
“那是我祖宗!”實(shí)習(xí)生突然從船底掏出把刀,“誰擋路誰死!蘇婉的尸蠟是我弄出來的,想引你們發(fā)現(xiàn)玉佩,再嫁禍給她‘顯靈’,沒想到你們來得這么快……”
他揮刀沖過來,我側(cè)身躲開,解剖刀劃向他手腕。周明不知何時(shí)跟過來,抱著鐵盒子砸在他背上。實(shí)習(xí)生踉蹌著栽進(jìn)水里,被王老頭扔出的繩套纏住。
警笛聲由遠(yuǎn)及近時(shí),雨小了些。河面上的棺材靜靜漂著,月光照在白玉上,映出蘇婉銀簪上的蓮花影。
太平間里,蘇婉的眼縫合上了,嘴角那抹笑意徹底消失,蠟化的臉上竟顯出幾分安寧。周明看著她,突然嘆了口氣:“老祖宗,賬清了。”
我把兩塊合起來的玉佩放在她手邊,又將那枚銀簪輕輕插進(jìn)她蠟化的發(fā)髻——簪頭缺角的蓮花,正好對著黑匣子上的紋樣,像終于拼完整的拼圖。
解剖室的燈重新亮起,照亮地上的黃水痕跡,像條干涸的河。王老頭摩挲著賬冊:“百年了,總算給蘇婉和我祖上一個(gè)交代。”
周明突然指著通風(fēng)口,柵欄上的皮屑不知何時(shí)消失了,像從未有過那具巨人觀。他打了個(gè)寒顫:“他……真的走了?”
我望著窗外漸晴的夜空,月光透過云層,在地上投下片清輝:“嗯,帶著該帶走的,走了。”
后來,那批和田玉上交了國庫,實(shí)習(xí)生因故意殺人被捕。李崇德的貪腐案終于在百年后昭雪,蘇婉的尸蠟被妥善保存,成了法醫(yī)中心最特殊的“標(biāo)本”。
周明再?zèng)]提過辭職,只是每次路過太平間,都會(huì)往蘇婉的冰柜前站一站,有時(shí)還會(huì)帶朵蓮花。他說總覺得老祖宗在看他,得好好干活,別讓她笑話。
而我每次解剖時(shí),總會(huì)想起那個(gè)暴雨夜——有些真相,哪怕隔了百年,哪怕藏在尸蠟與巨人觀背后,終究會(huì)被鑷子尖挑出來,在月光下顯露出本來模樣。就像蘇婉袖口的盤扣,歪歪扭扭,卻終究指向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