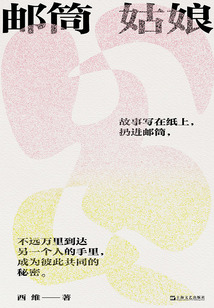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住所
傍晚時分,金色的夕陽斜斜地照在煤爐子上,劉老伯給阿莉講了個故事。
“郵筒姑娘呀,她會從投信口探出腦袋問你討要信件,你要是看到她,會發現,她很瘦,因為餓壞了,瘦得像一張餅。不過,一般人常常看不到。”
劉老伯臉上沒有那副和孩子們講故事時略帶夸張的慈祥表情,倒像是回憶什么令人難忘的憂傷往事。他一邊說,一邊用火柴點著一小塊廢舊自行車內胎,將它塞進爐子里已經架好的柴火堆里。
“瘦得像一張餅,哈哈,阿伯,哪有人會瘦得像一張餅呢。”阿莉打趣道。
“是一張餅!你只是沒見過。”他有點生氣,不說了,專心侍弄他的煤爐子。
孩子們就快放學了,等煤爐子燒旺,燒一壺晚上要用的熱水,再把一口大鋁鍋架上,孩子們就會圍在爐子邊,等著那鍋青菜肉絲面出鍋。
一人兩筷子,哧溜哧溜吃完面,小家伙們就鉆進炊煙飄蕩的暮色中,各回各家了。在院子里時,他們熱鬧得像一群剛出殼的小雞。待暮色漸沉,小雞回籠,院子就寂靜無比了。
算起來,這還是阿莉第一次聽別人談起她——郵筒姑娘,這故事和所有的道聽途說一樣不可信。
吃完晚飯,劉老伯就回自己屋看電視去了。這是個有點脾氣的倔老頭兒,有時候不討人喜歡,但在幾天前,他收留了阿莉。
那時候,阿莉饑腸轆轆,循著香味來到院子里,站在西北角離柴房不遠處的一個燒得正旺的爐子邊,順手把一只差點掉進爐子里的小蛾子給抓住。她拍了拍手心沾上的粉灰,和拿著鹽罐子從屋里走出來的劉老伯打了個招呼。
之后,她吃了一碗面,住進了劉老伯那些空房間中的一間。他信了她的話,以為她是找不到工作,剛剛去附近一家工廠面試又被拒了的剛畢業的大學生。
住到劉老伯家之后,阿莉便時不時乘上一輛開到市區的公交車,去找工作。這也挺好,她本來沒想過工作的事,有事可做總比無所事事混吃等死要好得多吧。
她覺得劉老伯應該向她收點租金。除了孩子們,他可不是對誰都那么大方。他家中幾乎沒什么客人,脾氣又怪。不去村里的老年活動室,不去橋頭整日搭在那里的棋盤邊湊熱鬧,也不去找哪個在河埠頭洗菜的老太太搭訕。他把時間花在那幾壟地里,種點毛豆花生,青菜土豆。剩下的時間,他到各處去收集柴火。不過,塑料瓶硬紙板箱之類的他倒是從不拿回家。至于他到底多大歲數,阿莉也不清楚。
“你大概七十五吧?”阿莉問。
“你說多少就多少。”他用一種不肯定不否定、不生氣不高興的語氣回答她。說這話的時候他還在分神,好像阿莉提醒了他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似的。
“我可對你的秘密沒興趣呀。”——按照她以前的脾氣,她就直接這么說了。可今非昔比,不是嗎?
不僅劉老伯老了,她也老了,不僅是老了,還即將邁入墳墓。最后一個郵筒消失的時候,她就沒了,或許還撐不到那個時候。做人嘛,也不一定能熬到最后一條經脈枯竭才閉眼吧。
阿莉不記得曾經見過劉老伯。真要說見過,那他就是她見過的無數沒留下印象的陌生人中的一個。
在劉老伯還是小年輕的時候,她的日子還真是風生水起活色生香啊。她喜歡住在鬧市區十字街口的墨綠色大郵筒里。她的住所總是和沿街的店鋪、靚麗的櫥窗一道,進入某張有特殊意義的照片,在某本影集里得到保存。那些墨綠色的郵筒常常被撐得多一封信都放不下。她每天都過得心滿意足,每天都能從那眾多的信件中發現有趣的事情。而那些五花八門透著玫瑰與蜜汁味的情書也著實好好地滋養了她的皮膚,粉粉嫩嫩、吹彈可破。要是她愿意,她還可以趁著夜色,到江邊的公園或是咖啡館去邂逅一位漂亮的情人。那時,她在不同的城市擁有不同的住所,有鬧市公寓也有鄉間別墅。有男人們送的,也有投資所得購買的。她心血來潮,還會把鑰匙扔給街頭某個無家可歸的人讓他去住幾天。她不可能整日整夜地待在那些房子里。她總是適時結束一段關系,然后消失得無影無蹤。某些深陷愛情的男人,會把寫滿思念話語的信件扔進某個她正在小憩的郵筒,剛好落在她的手臂上。她讓它去往那個已經沒有收信人的地址,轉上一圈,再重新蓋幾個郵戳,原路返回。當她厭煩了喧囂與繁華,就喜歡去某個閉塞的地方,比如海島,或是海邊小鎮,躲在郵筒里聽優美的潮聲。
這天,她拿著一封寫給自己的信,問劉老伯,鎮子上的郵局在哪里。劉老伯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和她說了個地址,又說,那地方現在是郵政儲蓄所,還能不能寄信,他不清楚。
“你們年輕人又時興起這個了?我都多少年沒寄這玩意兒了。”他說。
阿莉笑笑,伸了伸舌頭。
一個鐘頭之后,阿莉回來,劉老伯端坐在堂屋里抽煙斗。
“寄了嗎?”
“沒有。您說對了,成郵政儲蓄銀行了。”她聳了聳肩,“只能寄錢,不能寄信。”
劉老伯點點頭,吧嗒吧嗒地繼續抽著煙,沒再說話。
下午,生爐子煮面、等著那些放學來的孩子時,他便和她講起了郵筒姑娘的故事。
今非昔比啊!她坐在劉老伯的院子里哀嘆。看著老伯的母雞領著小雞群從她的面前氣勢威武地走來走去。
不管怎樣,如今唯一能令她感到溫馨的居所,恐怕就是這幢墻粉都掉得斑斑駁駁的舊屋子了。她受夠了之前那些顛沛流離的日子,常常是某一次外出游蕩回來,便發現她的那個綠色小房子被整個挪走了,地面上空空蕩蕩,鉚釘被拔去,凸起的粗紋螺釘被大錘子敲得貼在了水泥地上。
連一只母雞都比不過,她感慨著“今非昔比”,朝著從柴房里出來的劉老伯撇撇嘴。
“姑娘,不管你家以前多有錢,現在也不能再像大小姐一樣啊,實際一點。找個踏踏實實的工作做吧!”
他還為她操心呢,語氣上有那么點父輩的恨鐵不成鋼的意味。被收留的那天,她和劉老伯坦言“身世”:她家原來很有錢,可是父親生意失敗自殺,母親改嫁,她窮得差點連高中都沒讀完,幸好遇上一個像劉老伯這樣的好人,在她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資助了她。多年來,她一直擅長說這樣的謊、演這樣的戲。盡管劇情很狗血,劉老伯居然相信了。她本來想編得更加完整更加生動,用豐滿的細節讓整個故事栩栩如生。可劉老伯聽了幾句就信了,她花時間想的那些細節都沒能派上用場。怎么能這么好騙,她氣得不想再和他多說了,卻被對方看成女孩兒的羞澀與矜持,和對陌生環境的不習慣。頭幾天,劉老伯每天早晨給她煮一個自家母雞生的蛋,再倒一碟美味鮮醬油,讓她蘸著吃。
她不該和劉老伯說謊。不過,她第一次和人打交道,就是從編故事開始。首先是她的名字,她給自己取過無數個名字,從那些信封上選她喜歡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有時候用官家小姐的名字,有時候用鄉下姑娘的,為了配合名字她還得給自己編造一個個令人信服的身世。郵筒里應有盡有,千百個身世千百個身份,她信手拈來,用她聰明的腦袋瓜子盡情加以靈活組合。
有一段時間,她去女子大學上了幾年學,輕而易舉地就拿了兩個專業的學士學位。古典文學和經濟學。這倆專業是她搓了一堆小紙團抓鬮抓出來的。她在學校的表現令全校師生都詫異和敬佩,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投機取巧了。她的歲數比他們都大不是嗎?在這個世界上待這么久,學起什么來不是輕而易舉啊。況且,郵筒里還真是應有盡有。當一個年輕的記者慕名前來采訪,問她,有什么秘訣要告訴讀者嗎?她回答:郵筒是個百寶箱。那么您的座右銘呢?生命是綠色的。她又說。采訪結束后那個年輕的男人請她去喝咖啡,之后又請她看電影。她知道他在追求她。問及原因,他說,她是他見過的最具幽默感的才女,長得又美。一點不像他認識的那些書呆子。
這真好笑。她去學校上學就像去玩,讀書沒什么挑戰性,久了也沒什么樂趣。她的問題就在這:干什么都不長久。她從沒有想過去干什么工作。干不到兩個月就得厭煩。因此,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玩,用五花八門的身份去認識五花八門的人。
所以說,揮霍是每一個物種的天性。生命用揮霍的方式展示它的熱情。
她很有投資頭腦,用那些五花八門的所得,經由她廣博的人脈去投資,大部分都挺順利。所以,她擁有了那些盡可以去揮霍的資產。于她來說,投資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既然沒有固定的職業,總得做點什么。在書信密集郵筒林立的時代,那些身外之物常常令她感到充實,甚至有那么點驕傲。可如今,書信不再,已成擺設的郵筒一個個消失,那些花費心思置辦的產業就像是空蕩蕩的巢穴,黯淡無光,讓她感受到了這世間最大的虛無。她總算能體會那些富翁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形容枯槁,又沒有一個能給予溫暖的親人,對一切都無能為力的感受了。
現如今,無處可去,寄居在劉老伯家,曾經風光無限而今竟淪落至此,不免令人唏噓。
不過,也沒人會唏噓。誰知道她的故事?就算她告訴別人別人也不信。她的假身份,她編的那些故事,人們倒是信以為真,可她要說幾句真話,別人卻當她是編故事。
很多年前,她在某個郊區的酒館遇到一個作家。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作家扯著她的手開始互訴衷腸。她將手從他的手底輕輕滑出,手心朝上,舉過他的眉心,再朝著那只留在桌上的尷尬右手反扣而下,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肚輕輕碰了碰對方食指和中指凸起的關節,隨即將手收回到自己的酒杯前。她笑盈盈地說:“給你說個秘密呀,剛才我說自己無父無母,是個孤兒,那是因為我是郵筒里長出來的,郵筒,你知道嗎?就是你給女孩子寄情書、給出版社投稿件的那玩意兒。”聽到這,作家就笑了。他點點頭。帶著微微的醉意頗具耐心地聽她把那個自說自話的故事講完。她說了大概二十分鐘,足夠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梗概了。
“嗯,謝謝你給我講了這么好的一個素材,看來美瀾你真是很在意我們之間的情誼呢!”作家說,“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
一個在酒館門口守候多時的車夫把他們送到了她在城西的一處居所。道別時,他趁機吻了吻她的臉頰,她沒有拒絕,因為這時候的這個男人,和所有愛情故事里的經典情人形象十分吻合。天氣很冷,他的長圍巾搭在脖子上,隨著風飄來飄去。在他輕輕抱住她的時候,她問:“你會寫那個故事的是吧?”
“會,我一定寫,你會是我第一個讀者。”他激動地帶著這個承諾離去。她覺得他這個承諾至少要比他對愛情的承諾可靠得多。不多久,這位作家又找了個姑娘。看那郵筒里隔日一封的情書就知道了。小說嘛,他說他在寫,又說寫完了可是還得改。不過,在他所有寄給出版社、雜志社的稿件中,都沒有寫這故事的,連皮毛也沒有。
她對那個作家簡直是失望透了。她覺得他只不過是運氣好而已。在那個年代,有人給他出書,又恰好有人愿意看。他那并不出眾的文采,那些無病呻吟的文字,騙人眼淚的故事,就是一般般不是嗎?況且他還是個懦夫。戰爭開始后,他就去求一個通過曲里拐彎的渠道結識的權貴,尋求他的庇護。費盡了口舌,他如愿得到了一張去往國外的船票。就一張。他給他的情人寄了一封信,說上天待他不薄,沒有讓一個有前途的作家毀在炮彈之下,為了那些能夠傳世的作品,他必須活著。他的確是活著了。他寫那場戰爭的作品也留了下來。到如今他的作品也總是出現在一些文學必讀經典的名單里。不過,他的情人最終沒能收到那封信。那個裝了信的郵筒很快就被一枚空投炸彈給炸飛了,連同一只瘸了腿、因饑餓和傷病而奄奄一息的流浪狗。
倘若她不是對什么事、什么人都只有短期的熱度,她自己也可以去寫一本書。可她終究連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她想過的事情倒是挺多:成為作家,給自己寫本書;成為一名生物學家,研究自己是個什么樣的物種,和她一直扮演的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物種有什么區別和關聯;成為一名物理學家,研究一下自己是怎么產生的,又會用一種什么方式離開這個世界,也就是消失、滅亡、死。她去某位正處于事業上升期的物理學助理教授的實驗室玩,也向他請教過類似的問題。他沒像那個一門心思只想著和她談情說愛的作家一樣對待她的這類話題,而是非常認真地說他個人相信這類事物的存在。某種能量場。如果足夠強大的話,有轉化成物質的可能。大概就是這意思。她聽得興奮又入迷,差點就去當了他的學生。最后,她還是做了他的女朋友,談了兩個月的戀愛。那期間,她又覺得物理學研究簡直枯燥透了,很快喪失了熱情。那時候她叫Andrea,身份是一個有留學背景的商人的女兒。
住在劉老伯家期間,阿莉總會想起以前的事情,既像是昨日,又十分久遠。她成了個無所事事總是回憶過往的老人家了,盡管她仍有一張年輕的臉。她本可以再用這張臉去和男人們廝混,但從某一刻起,她突然就沒了興趣。她的身體失去了點什么——生命力,像株無精打采即將要旱死的植物,還怎么散發著香氣去吸引昆蟲呢?她失去了旺盛的精力,沒有了超凡的自信,她現在一點不覺得那些男人可憐,她倒是覺得自己挺可憐的,稀里糊涂地就要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到時候是變成一團霧氣在太陽底下蒸發,還是變成一個石塊,又或者是一具會隨著時間發臭腐爛的尸體——要是這樣她得躺到一個花園里去死,菜地也行,給泥土增加點養分。
“阿莉,想什么呢?你的面涼了。天冷,你快點吃。”劉老伯在她吃飯分心時數落她。
“啊。我在想我死的時候要躺在一個園子里,給那些花花草草增點肥。哈哈。”阿莉捧起面碗,哧溜哧溜地扒拉那碗即將涼透的面條。
“你這腦瓜子,不想點好的。這么年輕,說這個。什么死不死的,呸呸!我都還沒死呢。”
“您哪會死,您長命百歲啊。好人都長命百歲的不是?”阿莉已經很習慣和他開玩笑了。
“你們這些小孩子,往后還有一大段的日子要過呢。等挨到我這把年紀,就不那么隨隨便便地去說那個字了。要忌口,有些話不要隨便講。”
可阿莉決定任性一回,繼續這個話題。說起來,他們從沒什么共同的話題,也很少能真正聊到一塊兒去。大部分時候只能談談院子里的雞、地里的菜,還有村里的孩子們。劉老伯對自己的過往守口如瓶,極少談及他的過去。恐怕就是因為這個怪脾氣,才交不到什么朋友。
“那,您怕死嗎?”阿莉問。
“閻王爺要來收我了,我就跟著他去。怕不怕都得去。”劉老伯把灶臺前的零散柴火都收攏到一塊兒,靠墻腳放好,拍拍手,端了把沒靠背的木椅子坐到了阿莉的斜對面,似乎不是為了和阿莉閑聊,而只是為了盯著她把剩下的面條吃完。
灶膛已經冷了。今天他沒生煤爐子,在這口土灶上燒了晚飯。他煮了一大鍋蠶豆,準備明天趁著太陽好鋪散在竹匾里曬干,給那些孩子們做零食。蠶豆煮好他又煮了一大碗蘿卜燒肉,之后,就是那鍋青菜面條。今天是周六,孩子們不上學,院子里沒有放學后的熱鬧。
“哦。您就沒有放不下的?你兒子、孫子。”阿莉朝堂屋里望了一眼,客堂里那舊得不像樣的鏡框里,有個穿水兵服的小男孩,劉老伯臥室桌子上臺板下也壓著張照片,上面有個穿著毛絨絨小熊裝的小男孩。
“他們也顧不上我。我想那么多作甚?”劉老伯表情嚴肅,語氣倒像是個孩子。
阿莉沖著那張刻意板起的嚴肅的臉笑了笑,將碗收起,泡在了廚房窗口的水池子里。
“是你不愿意和他們一塊兒住嘛……”阿莉走到了廚房門口,抬起頭看了看被屋檐遮住了一半的天空,本應該出現的十五圓月被云層給遮住了,屋檐一角露出的不規則灰暗云塊讓人感到一種昏昏欲睡的倦怠。遠處傳來了一陣狗吠和幾個人急促的腳步聲。
她想出去走走,一只腳邁出門檻后,又回了頭。
“我去散會兒步。您別偷偷把我的碗洗了啊,留給我哦!”她朝著劉老伯做了個鬼臉。
劉老伯低著頭在點他的煙草,沒看她。等他抬起頭,阿莉早已經沖到黑漆漆的院子外了。
這時候,村子里最熱鬧的地方就是村口的小賣部,這是每日信息匯集的場所,擠滿了吃完晚飯后過來閑聊、拎市面的人。阿莉從小賣部門口的人群前經過,沿著村道繼續朝東走,五香瓜子和榴蓮糖的氣味與清涼的晚風一道撓著她光滑的鼻梁。有人注意到了她,大部分人則沉浸在飯后的話語消遣中。他們閑聊的話題,無非就是誰家的媳婦和婆婆吵架,誰家的男人睡了誰家的女人,又或者誰家的孩子讀書讀到國外去了。這些話題許多年來幾乎沒有什么變化。離開人群,阿莉一直走到沒有路燈照耀的地方,往南沿著田埂路拐了個彎,聽著耳邊時斷時續的秋蟲的叫聲來到了一條小河邊。河邊,是菜地。她踏著菜地松軟的泥土伸手探尋,很快拔起了一根肥碩多汁的白蘿卜。
她在黑漆漆的河邊啃完了蘿卜,坐在了一團露水還沒來得及洇濕的雜草上。到了該回去的時候她才戀戀不舍地朝著燈光的方向走去。
被路燈照耀的身體在砂石路面上投下的影子仍舊修長勻稱,她心知,能這樣自在游蕩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每每想到此,她就心痛不已。在她即將發出一個自怨自艾的哀嘆聲時,有個身影快步穿過身后的那條窄巷。她在夜露、青草和從村民的屋子里溢出殘羹冷炙混雜的氣息中辨認出了一個男人的氣味,并懷著一種警覺的好奇心追隨著它。穿過窄巷,繞過兩面院墻后,她看到那個影子進到了一座院子的西北角,手摸索到一個方匣子處,接著是金屬發出的細微摩擦聲。隨即,那個黑影蹲在一株柚子樹的陰影里等待。她也陪著他一起等待。片刻后,他拉開沒有上鎖的前門溜進臥房去摸了一個女人的臉。阿莉用最快的速度推上電閘,接著把臥房外電燈的開關弄得啪嗒啪嗒響,那間隔三段長三段短,于是,三長三短的燈光暢通無阻地漏進了那間沒關門的臥房——不關門大概是為了方便逃跑。那個男人驚惶逃出,在翻墻的時候還摔了一跤。
阿莉開心又興奮。除了談情說愛,把人嚇一跳也是讓她心情變好的方法之一。
月亮出來了。明亮的大圓盤靜靜地懸在頭頂的蒼穹。她扔下驚恐之中瑟瑟發抖哭泣不已的女人,拖著月光下淡淡的影子越過月季花叢,跟上了那個男人,來到了村北的一座亮著燈的房子里。
男人進了大門后就徑直走進了堂屋。阿莉在院子里待了會兒,看了看他家的雞舍——里面養了兩只鴨,都已經睡著了。阿莉又看了看他院子里種的植物,長及小腿的土豆叢和長在瓦盆里的萬年青,還有墻角的一叢雞冠花。南邊有一叢叫不出名字的藤蔓植物占據了一大面院墻,黑魆魆的一大片。
看夠了這些植物她才用了她的老伎倆——現在她心力不足,不能常用——縮成信件一般半透明的薄片,從西邊洞開的窗戶擠進去。她悄無聲息地躲在角落觀察,見男人在廚房里抽煙。不是什么好煙,味道嗆人。抽完煙他找了一口不銹鋼雙耳鍋,放了半鍋水,在煤氣灶上放好,打了火。接著他從地上的塑料框子里選了兩株青菜。他將五六株青菜全都看過之后最終選了兩株,洗凈,切好,從冰箱拿出兩個雞蛋,打在碗里。他做這些的時候手仍舊有些發抖。
他煮好了一碗青菜雞蛋面。在起鍋前,嘗了一小口,對自己未完全失去水準的表現還算滿意。接著,他將面條端到了二樓西南邊的一個房間門口,敲了門進去。
隱隱約約地能聽見那里傳來的對話。父子之間最平凡最瑣碎的那種。
男人很快下了樓,坐在了客廳的木沙發上,打開了電視機,將聲音調到一個不影響樓上孩子學習的音量。他點起了煙,卻沒有看電視,而是盯著那個浸泡著幾個煙蒂的茶杯發呆。
阿莉猶如夜蛾一般,又從西邊那個洞開的窗縫悄悄地離開了。
第二天是個雨天。雨不算大,但是也足夠奏出一曲優美宜人的晨間睡眠曲。以前,阿莉最喜歡在這樣的雨天睡覺,綿綿密密淅淅瀝瀝,嗅著濕潤的帶著泥土芬芳的雨水味,她伸了一個又一個的懶腰之后,繼續她幽深的睡眠。
她在劉老伯燒早飯的時候起床,到廚房去和劉老伯打了聲招呼,他甚至都沒抬頭看她。雖然他的耳朵有時候不好使,但阿莉認為他不是沒聽見,是還在生她的氣:這么個不聽勸阻不知好歹的小妮子,他一定是哪根筋搭錯了才收留她的。到如今也沒找到一份正經的工作,白吃白喝白住,還讓他操心。
昨晚她回來的時候他還沒睡,連瞌睡都沒打。往常他一邊看著電視一邊打著瞌睡,總是她悄悄地到了他的床邊,將枕頭旁的遙控器拿起來,關了電視。房間瞬間變得黑暗的那一刻,他或許還睜開了眼睛,乖乖地由她幫他脫了外套,鉆進被窩兒。等她邁出門檻,合上房門時,那頭就已經響起呼嚕呼嚕的鼾聲了。而昨晚,她回來時,他正盯著一個他明顯不愛看的節目——唱歌選秀,一個小女孩咬著嘴唇聽著一個頭發染白了一綹的中年男評委嚴肅地批評她表演的某個瑕疵。她到他房門口道晚安時心里居然有了一點緊張,她可從沒怕過誰呢。她站在門口,咬著嘴唇,聽完了他那一頓劈頭蓋臉的數落,又灰溜溜地從他的房里撤出來。
看來,她得去找個工作來交差了,按時把薪水領回來。在這幢房子里,她得學著像一個普通的姑娘那樣生活。這樣也挺好,有人管著她,一個不同于以往的管家啊,女仆啊,露水情人之類的人,而是一位長輩。
他今天沒什么事,最多穿著雨衣到菜地去拔幾棵菜。她本來可以陪著他在家聊聊天的,最近他的話比以前多了起來,會和她說說他年輕時的事。她還問起他那過世的妻子,他說她是個好女人,把他照顧得很好,除了過于寵溺他們的獨生子,其他都無可挑剔。阿莉問她是不是他這輩子最喜歡的人。他說不是,最喜歡的姑娘嫁到了隔壁村,死后就埋在兩村之間的那塊墓地。他有時也去看她一眼。
劉老伯的番薯粥熬好的時候,她也已經洗漱完畢,換上了一套干練的衣服。她端起正在松木飯桌上冒著熱氣的番薯粥,鼓起腮幫子輕輕地吹著。
“我今天要去面試啦!”她說。
他的頭始終埋在番薯粥白蒙蒙的霧氣里,過了片刻,才抬起頭,看了她一眼,點了點頭,端著粥慢騰騰地走到桌邊坐下。
不知道是過于專注還是分了神,粥掛了一滴到他黑白相間的胡子楂上也渾然不覺。
喝完粥,阿莉穿過院子,朝著大門走去。到門口,她回了頭,他正在堂屋深處的陰影里看她。她向他揮了揮手。
番薯粥將阿莉的肚子攪得脹鼓鼓的,讓她打了一個又一個飽嗝。出了村子,她沿著往城區的馬路毫無目的地走了一段,聞了一陣子汽車尾氣刺鼻的氣味。她望了望道路兩側已經結了穂的稻田,和零星幾個在菜地里忙碌的農人,一個久違的念頭又悄悄地爬上了她的心頭——她會不會就這么離開然后再也不回來,就像之前的無數次那樣。離開這個村子,離開劉老伯,換一個新的地方,新的環境,新的名字。這念頭曾多次點燃了她內心的熱情,讓她一次又一次躊躇滿志地去尋找新生活。
她頭一回為這個想法而感到憂慮。她不知道該往哪里去。隨隨便便跳上一輛車?去城里,或是別的地方。再去找那些她不知找了多少次的,只不過是換了一張臉換了一件衣服換了一個職業的男人,再去哪所學校混個輕而易舉的學位?又或者是去找個工作做做,就像,她剛剛答應劉老伯的那樣。他昨晚像訓斥他的親兒子那樣訓斥了她。他每一個衰老的毛孔每一根血管都被那些話撐得脹鼓鼓的。他最后停下來的時候,有那么一點挫敗感,那么一點羞愧。她能想象他當年和他的兒子說類似的話時的表情。無法抑制的情緒將那些話帶到峰頂,然后砸下來,與一個年輕的身體碰撞。他似乎是贏了,他的孩子離開了他,離開了安樂窩,去了一個十萬八千里外的城市討生活。他的孩子不僅討到了生活,也討到了老婆。阿莉看到了老人家壓在他臥室桌子臺板下的那些照片。婚紗照,孩子滿月照,周歲照,紅領巾照。
他覺得,她也會那樣離開他。
她慢慢地往回走,沿著出來的路走回去,過了村委會,過了一座架在灰綠色水面上爬滿藤本植物的石橋,路過那晚被人騷擾的獨居女人的院子——女人正在雨棚下晾衣服。阿莉又回到了那個她熟悉的院落。院子的鐵門上了鎖,劉老伯大概是出去了。她便離開了那房子,坐上了一輛開往城區的公交車。
公交車經過鎮子街道的時候,她看見了劉老伯,他還戴了頂滑稽的絨線帽。車子靠站后她下了車,在一個充值送豪禮的巨型手機廣告牌的遮擋下,看向對面快遞轉運站里劉老伯一字一句地復述著一個聽來有點拗口的地址。收快遞的小姑娘費了點工夫才填好了快遞單,將那些筍干、豆角干、蘿卜干之類的東西裝進一個結實的紙箱。箱子好貴,劉老伯念叨。
不過,他從快遞站出來時心情似乎不錯,路過食雜店的時候還買了一包他常抽的那個牌子的香煙,又在一家超市買了幾盒牛奶。買牛奶的時候他似乎與人有點爭執,收銀員找不開他給的一百元,但他買完香煙的零錢又只夠買一盒牛奶,他說一盒不夠,起碼三盒。
牛奶是買給阿莉的。劉老伯自己從來喝不慣那奶腥味。他執意要買三盒。
“找不開錢開什么店呢!”劉老伯的聲音很大,也很不客氣,甚至很不講理。剛才的好心情完全沒了影。
“大爺,我也沒辦法,現在都手機掃碼,誰還用現金啊。您年紀大了也不能不講理,我一個打工的,老板不給我零錢,我有什么辦法。”年輕的店員姑娘也毫不客氣。
周圍的人來勸架,年輕的、年紀大的各執一詞。
路邊賣自產蔬菜的老婦人上來拉開劉老伯,嘆了嘆氣:“老哥唉,咱老了就該認命,你看我菜籃子上掛的那個碼,我兒子的。我也弄不會那些。弄不會,菜都賣不出去啊。那咋辦呢?兒子給搞了個碼掛那兒,收錢時方便了。可是啊,我也見不著錢啊。錢在我兒子那。我得去問他要啊!”
老婦人搖搖頭,拍了拍劉老伯的手背,不再說了。
劉老伯愣了一會兒,放下兩盒牛奶,把剛才買煙剩下的錢給了收銀的那位姑娘。很快,人群就散去了。街市依舊熱鬧,就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
最后,他撐起了雨傘,急急地走向馬路對面的公交站,上了一輛回村的公交。車子開動時,他一個趔趄,長柄雨傘差點被他給扔出去。身旁的年輕人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穩住了他的步子。他有點不好意思,不住地點著頭,嘴巴動著。他茫然地望向窗外,并沒有發現人群中的阿莉。
阿莉熟門熟路地鉆進了一輛開往城區的藍色寶馬轎車的后備廂,在一個豪華果籃飄出的香甜氣味中晃晃悠悠地來到了市區某家醫院的停車場。車停穩后,男人按開了后備廂的按鈕。她伸了個懶腰,在男人取出果籃和禮品盒之前偷偷地溜了出來。百無聊賴的她尾隨男人到了十一樓的某間豪華病房。她認出了躺在病床上的那個六十歲出頭的男人。那曾經也是個帥小伙兒,寫得一手好字。那些字寫在一張張白底紅格的稿紙上,寄往遠方的戀人。這種熱辣辣的情意大概持續了三四年。阿莉曾經為他們之間的愛情大發感慨,著實感動了一番。可惜,姑娘后來沒能來到他的城市,她身不由己,在她的家鄉嫁了人,他的最后一封信寫滿了帶著心痛的祝福。后來,他大概再也沒有寫過什么情書,阿莉漸漸地就把他給忘了。看來,他那副聰明的腦子和執著的精神并沒有虧待他,多年下來,功成名就,他現在躺在病床上,周圍堆滿了那些有求于他的人送來的花里胡哨的禮品,走廊里放了一長溜的鮮花。來看他的那個男人走后,他給一個叫瑩瑩的女孩發信息,用一種嗔怪的語氣說她近來都沒來看他。瑩瑩說,她最近都在相親。“沒辦法,年紀大了,我媽著急。”她發來個語音。“找到合適的,我就嫁,不等你了。”又是一條語音。他放下手機,沉默了一會兒后,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讓她把書房靠西第二排書架右數第三本書給他帶過來。“很久沒看書了,看看吧。”掛了電話后,他自言自語地念叨著。之后,他閉上眼睛想要睡一會兒,卻一直翻來覆去,找不到舒服的睡姿。
阿莉沒耐心看下去了。她離開了住院部,來到了門診,到了人群川流不息的走廊。那時,墻邊就多了個做等待狀、低頭看著手機的女孩——手機是她剛剛從那個藍色寶馬轎車后備廂搞來的。在后備廂待著無聊的時她順便玩了一會兒,看了里面的一些照片。照片里有幾個風格不同但都很漂亮的姑娘,有幾張照片是不同的女孩在同一個地方拍的,郊區的某個仿古景點。
阿莉掂了掂那只輕薄的黑色手機,她以前是有多討厭這玩意兒,將她此時此刻的處境都怪罪于它。
她把那薄薄的黑色小方塊放進了衣兜,它簌地就滑了進去。安安靜靜,像個懂事的小孩。她要把一個撿來的孩子變成她自己的,去手機店給它換張卡。
然后,去和劉老伯告個別,說她已經找到工作了,在市區。為了上班方便,打算在市區租房子住。他會恭喜她的。他恭喜她的時候,她就告訴他她會常常來看他。
曾經有那么一刻,她差點以為她也會需要那樣的生活:有一個老人像家長一樣管著自己,又不失關心,平淡知足不寂寞。他也需要她。大概是這樣。但實際上,她只會把好好的日子給攪亂了。她真的會把他當成長輩嗎?他光著屁股和一群同樣光著屁股的小孩跳進村頭的小河時,她不知在哪兒和哪個男人一起喝著冰鎮飲料談情說愛呢。她倒是有可能在路過鎮上某個供銷社時心里一熱買一打棒冰分給那些曬得黑不溜秋盯著她碎花連衣裙看的孩子們。
早年有段時間,她總是到鄉下來。在那之前,她只愛在城市里待著。城里的各種熱鬧場所,僻靜清幽鬧中取靜的所在,圖書館、劇院、公園、落滿法國梧桐葉的道路。那些地方角角落落里都會有郵筒,各式各樣的郵筒,里面塞滿了各式各樣的信件,散發著清新撲鼻令人心滿意足的氣味。
她去鄉下拜訪一位作家。他每天在豬圈喂豬,剁豬草剁得雙手起泡。他給她的回信寫得艱難,信紙上沾了血漬。她帶著藥品和補品去看他。從他開始往郵筒里寄稿紙投稿時她就注意到他的文字了。可惜,他出了名沒多久后就被趕到豬圈喂豬了。
“被趕到這里每天和豬在一起也不失為一件幸事。它們多淳樸單純又善良啊。”他在信里曾說。
她看了他養得胖胖的豬。在他的指引下認識了豬場周圍野地里的豬草。薺菜、馬蘭頭、草籽頭之類的,還有一種叫鳳眼藍的植物,第一眼見到時她的確被它的美驚到。穗狀花序,藍紫色星星一般,一簇簇鋪就在水塘里,圓形的濃綠的葉片,微微有點風就搖曳生姿。“這是外國植物,引進到這里來是給它們做飼料的。”他用那只包扎著紗布的手指了指豬圈的方向。
到后來,這些水生植物被人叫成水葫蘆,水葫蘆成片成片在大大小小的水域肆虐的時候,她仍舊忘不了第一眼望見時的驚艷。
藍紫色的眼睛,明黃色的瞳仁。
“帶著某種灼人的熱烈。卻是藍色的。比紅、橙更甚。”他這么說。這個時候他開始像位作家,身上那種被養豬場的生活蒙住的灰撲撲的東西終于露了個小口。他每天撈起這些藍眼睛和它們碧綠的身體,用一把巨大的鍘刀將之鍘碎。
“你也有一雙這樣的眼睛。”他瞇起他有點水腫幾乎看不見眼球的雙眼,盡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和她說。
沒錯。丹鳳眼。曾經流行的古典美人的眼睛,標準的那種。她買了一盒又一盒的脂粉來讓它們變得更漂亮點。
“噢,謝謝。”她說。
為了表示謝意——更多的是同情——她提出幫他鍘豬草,他的手還纏著舊布條,卻拒絕她替他換藥,說他自己來,手爛了,嚇人,別弄臟了她。那鍘刀她沒弄幾下,手臂就酸得抬不起來了。她便痛恨那些豬的巨大胃口。
“即使從早弄到晚,它們也吃不飽。”他倒是有點同情它們。
三個月之后,她接到了他離世的消息。有人通知她去取遺物,有幾本書是留給她的,遺書里是這么寫的。她去看他時,他大概就不想活了吧。這么想的時候,她流了幾行眼淚。
十多年后,那片被鳳眼藍占據的水塘被填平了——那時這種叫“水葫蘆”的生物已經遍布大小河流——養豬場被拆了后蓋了個廠房,生產豬飼料。藍眼睛不再成為豬的食物。那本來也沒什么營養,低蛋白。無人看管、自此再沒人看上的它們終于野成了氣候,肆無忌憚、不依不饒、不休不止地繁殖,在這片異域他鄉的廣袤水域,日漸強大。
相比較這些充滿野性又十分強大的物種,她的那些郵筒算得了什么呢!經歷了不到一百年的繁榮便沒落。
“有郵筒沒郵筒的地方都有水葫蘆吶。”也不知作家死前下了什么咒,她無奈地想。
劉老伯的村子就在豬飼料廠往西三千米。飼料廠早就倒閉,那地方現在是機械廠,做汽車配件。村子里有幾個年輕人在那工作。那天她就是尾隨一個穿藍色工裝,留小平頭的年輕人乘著公交車到了劉老伯的村子。因為那年輕人的身影,和死去的作家有幾分相像。
要是作家沒死,他們還會保持聯絡嗎?說不準。十年,二十年,一個個的十年過去,無數人埋進生活的褶皺之中。她能記得起多少個?
她用手捏了捏頸部的皮膚,緊致之中略帶綿軟松弛,依然帶著點彈性。
一只雄性黃毛土狗看了她一眼,扭頭小跑而去。她站在路邊看著黃狗消失的背影,發出大限已到的感嘆。
之后,她看到那個大開的院門,聞到了青菜面的香味。那時,她感到了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