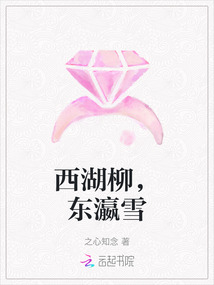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2022年秋-2023年春)
一
杭州的秋,是入了骨的。2022年的秋意,來得格外分明,仿佛要將前些年的混沌與壓抑都滌蕩干凈。西湖的水,在十月的光影里,斂去了夏日的喧囂,沉淀出一種深邃的藍綠,倒映著岸邊層林盡染的斑斕。北山街的梧桐葉,由青轉黃,再浸染上熱烈的紅,風一過,便簌簌落下,鋪滿青石板路,踩上去是沙沙的微響,帶著一種時光流轉的靜謐。空氣里彌漫著清冽的桂花甜香,無處不在,絲絲縷縷,纏繞著行人,也纏繞著這座剛從沉寂中蘇醒過來的城。
李硯清沿著楊公堤緩步而行,手中提著一個素雅的竹編茶盒。他剛結束上午在藝校的越劇身段課,眉宇間還帶著一絲授課時的專注。年近不惑的他,身姿依然挺拔如西湖邊的水杉,穿著合體的深灰色棉麻中式立領外套,襯得他本就溫潤的氣質更添幾分儒雅。他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骨子里浸潤著這方水土的靈秀與從容。家族幾代與戲曲結緣,祖父曾是杭城有名的“書場先生”,父親也是越劇院的琴師。硯清自己,雖未登頂紅氍毹成為名角,卻在藝校里默默耕耘,將一腔對傳統藝術的摯愛,化作桃李春風。他愛戲,也愛茶,總覺得這兩者骨子里相通,都講究一個“韻”字,是時間沉淀下來的風致。
手機震動,是單位領導發來的信息:“硯清,下午兩點,茶葉博物館‘和敬’茶室,日本茶道交流團的李莉央女士到了,由你負責對接全程。資料發你郵箱,務必周到。”后面附了一個名字的日文拼寫:Riō Li。
“李莉央…”硯清低聲念了一遍,名字里有種奇特的融合感。他點開資料,照片上的女子穿著素色和服,正襟危坐于茶席前,神情專注地操作著茶筅。她面容清麗,眉目疏朗,眼神沉靜如水,仿佛周遭一切都與她無關,只專注于手中那一碗碧綠的茶湯。氣質是清冷的,像早春未化的雪,又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資料顯示她是日籍華裔,日本某個古老茶道流派的重要傳承弟子,此次帶隊來杭進行為期數月的深度茶文化交流。
硯清收起手機,目光投向煙波浩渺的西湖。亞運的氣息已悄然彌漫,城市在精心裝扮,但西湖的底色,依舊是那份穿越千年的從容。他想,這位李莉央女士,跨越山海而來,不知在她沉靜的眼眸里,杭州的秋,西湖的水,會映照出怎樣的模樣?而茶,這門東方共通的古老藝術,又將如何在他們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二
中國茶葉博物館坐落在龍井路旁,依山而建,林木蔥蘢。午后陽光透過高大的喬木枝葉,篩下細碎的光斑,落在蜿蜒的石徑上。“和敬”茶室位于博物館深處一處僻靜的院落,白墻黛瓦,飛檐翹角,推開雕花的木門,一股混合著上好木料、陳年茶香和山間清氣的寧靜氣息撲面而來。
硯清提前一刻鐘到達,仔細檢查了茶席布置。紫砂壺、青瓷盞、竹茶則、素凈的茶巾…一應器物都透著古樸雅致的氣息。他特意選了一泡今年清明前的獅峰龍井,芽葉細嫩,色澤翠綠,期待著用它來開啟這次跨越文化的對話。
兩點整,茶室的門被輕輕拉開。李莉央出現在門口。她換下了資料照片里的和服,穿著一身剪裁得體的月白色亞麻長衫,配著深灰色闊腿褲,長發在腦后挽成一個簡潔的發髻,露出光潔的額頭和修長的脖頸。比照片上更顯清瘦,也更清冷。她微微頷首,用清晰但略帶生硬的中文說道:“您好,我是李莉央。勞您久等。”
“李女士您好,我是李硯清,這次交流活動的對接人,歡迎您來到杭州。”硯清起身,微笑著伸出手,目光溫和而真誠。
莉央伸出手與他輕輕一握。她的手微涼,指尖有薄繭,是常年習茶留下的印記。“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她的中文咬字清晰,帶著一種獨特的韻律感,目光快速而禮貌地掃過茶室,最后落在硯清臉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審視。
落座后,短暫的寒暄略顯拘謹。硯清介紹著茶室的環境和這次交流的初步安排。莉央安靜地聽著,偶爾點頭,目光沉靜如水,仿佛在丈量著空氣中無形的距離。硯清注意到,她坐姿極為端正,背脊挺直,雙手自然地交疊置于膝上,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透露出一種刻入骨髓的儀態感。這是一種長期嚴格訓練的結果,帶著東瀛特有的克制與秩序。
“李女士一路辛苦,先嘗嘗我們杭州的春茶吧。”硯清適時地轉移話題,手上動作行云流水般展開。溫壺、燙杯、取茶、投茶。碧綠的龍井茶針落入溫熱的紫砂壺中,發出細微的沙沙聲。他懸壺高沖,水流如銀練傾瀉,茶葉在壺中翻滾舒展,一股清冽鮮爽的豆香混合著板栗香瞬間升騰彌漫開來。
莉央的眼神微微亮了一下,鼻翼不易察覺地翕動,顯然被這純正馥郁的茶香所吸引。她專注地看著硯清泡茶的動作,雖與日本茶道繁復嚴謹的“點前”截然不同,但那份對水、火、器、茶的掌控與敬意,卻是相通的。
“這是今年的獅峰龍井,”硯清將一盞清透碧綠的茶湯輕輕推到莉央面前,“‘院外風荷西子笑,明前龍井女兒紅’。都說這明前龍井,帶著春山的氣息,也帶著西湖的靈氣。您嘗嘗。”
莉央雙手捧起茶盞,并未急于品嘗。她微微低頭,先嗅聞茶香,神情專注得如同在進行某種儀式。然后,才小口啜飲。茶湯入口,她的眉目似乎舒展開來,清冷的臉上掠過一絲極淡的、幾乎難以捕捉的暖意。
“很…好。”她放下茶盞,斟酌著中文詞匯,“鮮,甘,活。水好,茶更好。”她頓了頓,補充道,“杭州的水土,很養茶。”
硯清笑了,溫和的笑意驅散了初見的些許生疏:“是啊,一方水土養一方茶,也養一方人。這西湖的山水,龍井的云霧,是這茶魂的根。”他指著窗外隱約可見的遠山輪廓,“您看那邊,就是龍井村的方向。改日,我們可以去源頭看看。”
“我很期待。”莉央的回應簡潔,但眼神里的光又亮了幾分。血緣里那份對故土的模糊牽引,似乎在這盞茶香里,變得具體了一些。
茶過兩巡,氣氛漸漸松弛。硯清聊起杭州的秋,說起滿覺隴的桂花雨,說起斷橋殘雪的傳說。莉央聽得認真,偶爾會問一兩個問題。當硯清無意間哼起幾句越劇《梁祝》里的“十八相送”選段,那婉轉悠揚的唱腔在靜謐的茶室里回蕩時,莉央眼中閃過一絲明顯的驚訝和好奇。
“這是…什么?”她問。
“哦,是越劇,我們浙江的地方戲,用吳語演唱的。”硯清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唱的是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一對戀人生死相隨,最后化蝶雙飛,算是個凄美的傳說。剛才唱的是他們分別時的唱段。”他簡單講述了梁祝的故事。
莉央靜靜地聽著,眼神飄向窗外搖曳的竹影,片刻后,輕聲說:“很美。像茶道里說的‘一期一會’,每一次相見,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要傾注全部的心意。”她的聲音很輕,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卻帶著一種沉甸甸的分量。
硯清微微一怔。他第一次聽到有人用“一期一會”來詮釋梁祝的悲情,如此獨特,卻又如此貼切。那一刻,他感覺眼前這位清冷的茶道師,內心或許藏著一個極為豐富而敏感的世界。茶煙裊裊,隔著小案,一種基于共同文化底蘊的微妙共鳴,悄然滋生。茶煙引路,原來知音之遇,并非只在弦歌,亦可在一盞清茗的浮沉起落之間。
三
交流項目正式啟動。最初的幾天,硯清作為向導和文化顧問,陪同莉央及她的團隊穿梭于杭州與茶相關的各個角落。
他們去了龍井村。沿著蜿蜒的山路向上,兩側是連綿起伏的茶園,深秋時節,茶樹依舊蒼翠,只是少了春日采茶的熱鬧。山風帶著涼意和草木的清氣。在一戶世代種茶的老茶農家,莉央仔細詢問著龍井茶的種植、采摘、炒制工藝,對“抖、搭、捺、拓、甩、抓、推、扣、壓、磨”十大手法聽得尤為專注。她甚至嘗試在老師的指導下,感受那口燒得滾燙的大鐵鍋的溫度,笨拙而認真地模仿著“抓”和“抖”的動作,額角沁出細密的汗珠,神情卻無比專注。硯清在一旁看著,覺得她此刻褪去了清冷的外殼,更像一個對未知充滿熱情的學生。
“火候最難,”老茶農用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感嘆,“差一分則生,過一分則焦。全憑手上功夫和心里那桿秤。跟你們點茶一樣,講究個‘心手合一’吧?”
莉央用力點頭,用日文向同伴翻譯著老人的話,眼神里充滿敬意。她拿起一片剛炒制好的茶葉,對著陽光細看其色澤和形態,又湊近深深嗅聞,仿佛要將這凝聚了陽光雨露和匠人心血的精華刻入記憶。
下山時,夕陽將遠山和茶園鍍上一層溫暖的金色。莉央走得慢,時不時回望那片蔥蘢的茶山。硯清走在她身側,遞給她一瓶水。
“謝謝。”她接過,喝了一小口,望著山下的村落和遠處如帶的西湖,忽然輕聲說:“根,很重要。”這句話沒頭沒尾,但硯清卻聽懂了。她是在說茶,也是在說自己。這龍井山上的茶樹,根系深扎于這片獨特的紅壤;而她,雖遠在異國,血脈里終究流淌著東方的基因,對這片茶的原鄉,有著本能的親近與探尋的渴望。
四
另一日,他們拜訪了致力于復原宋代點茶的專家。在充滿古意的茶寮內,碾茶為末,注水擊拂,看著茶湯表面漸漸泛起如“疏星淡月”般的白色沫餑(茶沫)。莉央對這種古老技藝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她本就精于日本抹茶道(源于宋代點茶),此刻更覺淵源深厚。
“真是奇妙的連接,”在嘗試點茶后,莉央看著碗中細膩的乳白色泡沫,難得地主動開口,眼中閃爍著發現珍寶般的喜悅,“雖然器物、流派、儀式細節不同,但追求茶湯的精純、意境的和諧,這份心意是相通的。就像…”她似乎在尋找合適的比喻,“就像不同的河流,最終都匯入同一片大海。”
硯清正用小茶匙輕輕撥弄著茶湯表面的“湯花”,聞言抬頭看她,眼中滿是贊賞:“說得好。茶道無國界,其魂在‘和、敬、清、寂’。無論是宋時汴京的斗茶,還是東瀛的茶之湯,抑或是杭州茶館里一杯尋常的龍井,本質都是借由這一片樹葉,安頓身心,溝通天地人情。”茶之為道,至簡至深。一葉沉浮,照見的是千古人心對寧靜與美的共同渴求。他這番話,仿佛道出了莉央心中所想,她看著硯清,嘴角第一次清晰地向上彎起一個柔和的弧度,像初春湖面漾開的漣漪,雖然很淡,卻足以驅散深秋的涼意。硯清的心,莫名地輕輕動了一下。
五
情感的微妙變化,常在不經意間的獨處時刻悄然滋長。
一個微雨的午后,原定的行程因雨推遲。莉央提出想隨意走走。兩人便撐著傘,沿著楊公堤漫步。雨絲如霧,將西湖籠罩在一片朦朧的水墨畫境中。堤岸兩側高大的水杉和梧桐,在雨水的沖刷下,色彩愈發濃烈深沉。湖面上,幾只水鳥在煙雨中低飛,劃破水面的平靜。
他們走得很慢,傘下的空間有限,彼此能清晰地聽到對方的呼吸聲和雨滴落在傘布上的沙沙聲。莉央似乎很享受這雨中的寧靜,話很少,只是專注地看著雨中的湖光山色,眼神里帶著一種難得的松弛。
“喜歡雨中的西湖?”硯清輕聲問。
“嗯,”莉央點頭,聲音也放得很輕,仿佛怕驚擾了這份寧靜,“很安靜。像…茶室里點完茶后,主客靜坐,聆聽余韻的時刻。”她停頓了一下,補充道,“在日本,京都的雨,也很美。但感覺…不同。”
“怎么不同?”
莉央思索片刻:“京都的雨,像…精密的工筆畫,帶著禪寺的檀香和庭院的苔蘚氣。這里的雨,”她伸出手,接住幾滴從傘沿滑落的雨珠,感受著那份微涼,“像寫意的水墨,有山水的磅礴,也有…生活的煙火氣。”她指了指遠處雨霧中若隱若現的蘇堤,和堤上匆匆走過的行人。
硯清笑了,為她的敏銳感知:“‘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杭州人總說,西湖的雨,是老天爺賜的靈氣。”
莉央也微微笑了,這次的笑意停留得久了一些。兩人繼續在雨中漫步,沉默不再尷尬,反而有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流淌。雨絲斜織,傘下的世界隔絕了喧囂,只有雨聲和彼此近在咫尺的呼吸。硯清能聞到她身上傳來的極淡的、混合了茶香和一種清冷木質調的香氣。他不動聲色地將傘向她那邊傾了傾。
六
還有一次,是在靈隱寺。深秋的靈隱,古木參天,楓葉流丹,黃墻黑瓦的殿宇在肅穆中透出莊嚴。他們并非專程禮佛,而是感受這千年古剎與茶文化的淵源(靈隱禪茶自古有名)。在飛來峰下的冷泉亭畔小憩時,恰好聽到寺內傳來悠揚渾厚的暮鼓聲。
咚——咚——咚——
鼓聲沉穩而遼遠,一聲聲,穿透層疊的林木,在山谷間回蕩,仿佛能滌蕩塵世的煩囂。莉央閉目聆聽,雙手輕輕交疊置于膝上,神情異常寧靜安詳。許久,鼓聲漸歇,她才緩緩睜開眼。
“這聲音…很安心。”她輕聲說。
“晨鐘暮鼓,警醒世人。也像是給忙碌的心,一個休止符。”硯清看著遠處香煙繚繞的大雄寶殿,感慨道,“茶道里講‘和敬清寂’,佛門里求‘明心見性’。有時候,一碗茶,一聲鐘鼓,都是讓人回歸本心的引子。”
莉央側過頭看他,眼神清澈:“李老師,您似乎…總能將很多事情,看得很通透。戲曲,茶,還有這…禪意。”
硯清搖搖頭,笑容溫和里帶著一絲自嘲:“哪里是通透。不過是生在杭州,長在杭州,這些山水、文化、人情,就像呼吸的空氣,早已融入骨血。看得多了,經歷了一些事,就慢慢明白,人生在世,與其執著于外物得失,不如像這西湖的水,隨物賦形,像這寺里的鐘鼓,守時守分,像這一杯清茶,濃淡自知。”所謂通透,有時不過是與生活講和,在煙火塵囂中,為自己尋得一處安放靈魂的山水庭院。他這番有感而發的話,像是說給莉央聽,又像是說給自己。
莉央沒有立刻回應,只是默默地看著他,眼神里多了一絲復雜的探究和…不易察覺的共鳴。或許,在她獨自異國求藝、肩負傳承重任的歲月里,也曾無數次在茶室的靜默中,尋求過內心的安定。這一刻,在靈隱寺的暮鼓余音里,隔在他們之間的那層無形的薄冰,似乎又消融了一些。
七
項目進行到后期,一個春寒料峭的傍晚,硯清在南山路一家頗有格調的老唱片咖啡館約莉央小聚。這家店以收藏大量老唱片和播放懷舊金曲聞名。昏黃的燈光下,黑膠唱片在唱機上緩緩旋轉,流淌出費玉清清亮悠遠、飽含深情的嗓音:
“真情像草原廣闊,層層風雨不能阻隔…總有云開日出時候,萬丈陽光照耀你我…”
熟悉的旋律讓硯清微微一怔。莉央也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側耳傾聽。這首歌是《一剪梅》,費玉清的代表作之一,其旋律和歌詞中蘊含的執著與深情,曾打動過無數人。
“這首歌…很特別?”莉央敏銳地察覺到硯清神色的細微變化。
硯清沉吟了一下,坦誠道:“嗯,唱歌的這位費玉清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歌手。他的歌聲干凈清越,臺風儒雅,更重要的是…他一生未娶,據說是因為年輕時一段刻骨銘心卻無疾而終的感情。”他沒有說得太具體,只是模糊地帶過,“有人說,他把所有的深情都化在了歌聲里。這首《一剪梅》,尤其唱出了那份‘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
莉央靜靜地聽著,目光落在旋轉的唱片上,若有所思。咖啡館溫暖的燈光柔和了她清冷的輪廓。她端起咖啡杯,卻沒有喝,只是感受著杯壁傳來的溫度。
“把一生的深情,寄托在藝術里…”她低聲重復著,像是在咀嚼這句話的分量。片刻后,她抬起眼,看向硯清,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種深沉的、近乎坦露的感慨:“茶道,對我而言,也是如此。它不僅是技藝,是傳承的責任,更是…安放我所有孤獨、困惑和熱愛的容器。”她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一種沉甸甸的真誠。這或許是她第一次,在一個相識不久的人面前,如此直接地袒露內心深處的柔軟。
硯清的心被輕輕觸動。他看著她,在昏黃的燈光下,她清麗的面容仿佛籠罩著一層柔光,那層拒人千里的冰霜似乎徹底融化了,露出了底下細膩溫潤的質地。他忽然覺得,眼前這位來自東瀛的茶道師,內心深處或許也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往,一份同樣深沉卻無處安放的情感。
“藝術和茶道,都是渡己渡人的舟楫。”硯清的聲音也放得很輕,帶著理解和尊重,“能找到一個可以寄托靈魂的所在,是幸運的。”
唱片里的歌聲還在繼續,深情而略帶憂傷的旋律在小小的空間里流淌。兩人沒有再說話,沉浸在各自的思緒和這由音樂與咖啡香共同營造的靜謐氛圍里。窗外,南山路的霓虹初上,車流如織,而窗內,時間仿佛慢了下來。一種超越了文化背景、基于對生命深處孤獨與熱愛的深刻理解,在無聲中悄然建立。
八
項目臨近尾聲的一個春日,西湖已是桃紅柳綠,一派生機盎然。莉央的項目意外獲得了短暫的延期。午后,她邀請硯清來到他們初次見面的“和敬”茶室。這一次,沒有旁人,只有他們兩人。
茶室里,莉央親自布置了茶席。她換上了一件淡雅的藕荷色茶服,動作嫻熟而莊重。所用的茶器,硯清認出是她珍愛的一套,其中一只茶碗釉色如深秋夜空,碗壁一側有一道天然流釉形成的淡金色痕跡,宛如一彎殘月,極具韻味。
“這只碗,名為‘殘月’。”莉央注意到硯清的目光,輕聲解釋,“殘缺有時,亦是一種圓滿。”她的語氣平靜,卻蘊含著某種哲理。
水沸了。莉央開始點茶。這一次,她的動作比以往任何一次公開演示都更加從容、專注,帶著一種近乎虔誠的寧靜。取茶粉、注水、調膏、擊拂…每一個步驟都一絲不茍,卻又行云流水,充滿了韻律之美。茶室內靜得只有水沸的松風聲和茶筅擊打茶湯的沙沙聲。
硯清靜靜地看著。陽光透過雕花窗欞,在榻榻米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也落在莉央低垂的眼睫上,給她清冷的側顏鍍上了一層柔和的金邊。她的神情如此專注,仿佛整個世界都凝聚在眼前這一碗小小的茶湯里。他忽然理解了什么是“一期一會”的極致——此刻,此地,此人,此心,皆是唯一,不可復制。
茶湯點好了,細膩的翠綠色沫餑覆蓋碗面,如春湖初漲,碧波凝脂。莉央雙手捧起茶碗,恭敬地奉至硯清面前,眼神清澈而明亮,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柔和暖意。
“李硯清先生,”她的聲音清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鄭重,“這一碗茶,敬…知遇。”
硯清心頭一震。他雙手接過茶碗,指尖感受到碗壁微溫的暖意和莉央指尖殘留的微涼。他沒有立刻飲下,而是凝視著碗中碧波蕩漾的茶湯,感受著那份沉甸甸的心意。然后,他緩緩將茶碗轉了三圈(日本茶道禮儀,欣賞茶碗),才分三口,細細品盡。鮮、甘、活、韻在口中層層綻放,而比茶味更深的,是那份被鄭重交付的理解與情誼。
飲盡茶湯,硯清從隨身的布袋中取出一個細長的錦盒,輕輕推到莉央面前。“莉央小姐,”他第一次省略了姓氏,“一點心意,不成敬意。”
莉央打開錦盒,里面是一把素雅的蘇杭折扇。潔白的扇面展開,上面是硯清親筆題寫的一行清俊小楷,是一首意境深遠的古茶詩:
“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
欲知禪味足,盡在苦甘間。”
落款處,是他的名字“硯清”,并鈐有一方小小的朱砂印:“守拙”。
莉央的手指輕輕撫過扇面上墨跡未干的詩句,又撫過那方小小的印章,眼中似有晶瑩的水光一閃而過。她抬起頭,看向硯清,嘴角揚起一個清晰而溫柔的笑意,如同西湖春水上綻開的第一朵睡蓮。
“謝謝。很美。我…很喜歡。”她將折扇小心地合上,珍重地握在手中。
窗外,西湖春水初生,波光瀲滟。茶室里,茶香氤氳,無聲的情愫在碗底沉浮的詩句間,在折扇開合的清風里,悄然釀成。他們相視而笑,許多未盡的話語,仿佛都已融在這一盞茶香,一紙墨痕,和這滿湖的春光里了。有些情意,無需宣之于口,便已如春茶入水,葉脈舒展,滋味自現,悄然浸潤了時光的杯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