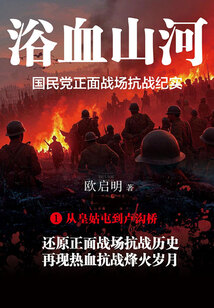
浴血山河: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抗戰(zhàn)紀(jì)實(shí)1·從皇姑屯到盧溝橋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狼子野心
“大陸政策”和“滿蒙政策”
日本和中國作為東亞的近鄰,在很早的時(shí)候就有來往,最早可追溯到漢光武帝時(shí)期。到唐朝時(shí),兩國來往更加頻繁。日本經(jīng)常遣使來唐學(xué)習(xí),并由此引發(fā)大化改新,日本開始在文化、政治和經(jīng)濟(jì)等方面全面向中國學(xué)習(xí)。
有些東西可以通過學(xué)習(xí)來改變,有些東西卻沒辦法改變。中國土地廣闊,資源豐富,而日本則地域狹小,資源貧乏,這極大限制了日本的發(fā)展。這是自然賦予的條件,是沒辦法改變的。于是一些日本人的目光開始向外轉(zhuǎn)移,想要擴(kuò)大日本的領(lǐng)土,增加日本的發(fā)展空間。這種想法后來慢慢形成了日本的大陸政策。
大陸政策的雛形,是十六世紀(jì)后期豐臣秀吉對朝鮮和中國采取的策略。當(dāng)時(shí)豐臣秀吉打算占領(lǐng)朝鮮和中國,并將都城遷移到中國大陸,以大陸管理整個(gè)帝國。那時(shí)中國正是明朝時(shí)期,國力比日本要強(qiáng)不少,朝鮮則是大明的藩屬國。當(dāng)日本人踏上朝鮮的土地后,大明直接出兵將日本人趕了回去。此后豐臣秀吉病死,日本進(jìn)入一段兩百多年的閉關(guān)鎖國時(shí)期。直到十九世紀(jì)六十年代明治天皇即位,日本開始改革,才走上了新的發(fā)展道路。
明治天皇執(zhí)政初期,便確定了“大陸政策”,要向大陸進(jìn)行侵略和擴(kuò)張。侵略方針分為南進(jìn)和北進(jìn)兩派,支持北進(jìn)政策的主要是陸軍,支持南進(jìn)政策的主要是海軍。北進(jìn)派主張先侵占朝鮮、中國,然后向北進(jìn)攻蘇聯(lián),最后稱霸整個(gè)亞洲大陸。南進(jìn)派主張先侵占朝鮮、中國,然后向東南亞擴(kuò)張,稱霸西南太平洋。這兩種政策的共同之處,就是要侵占朝鮮和中國,因此侵略中國是其不變的目標(biāo)。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實(shí)力大增,稱霸的野心加劇,開始逐漸實(shí)施對外擴(kuò)張的策略。
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打敗大清帝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根據(jù)條約,清政府要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雖然后來在德、法、俄三國干涉下,清政府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但日本已對東北三省勢在必得,多年來仍處心積慮地想要侵吞東北。這一戰(zhàn)讓日本得到大量賠款和臺(tái)灣等戰(zhàn)略要地,因此日本的實(shí)力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對外侵略的野心也更強(qiáng)了。
1904年,日本和俄國為爭奪在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利益而爆發(fā)戰(zhàn)爭。雖然清政府聲明保持中立,但怎奈戰(zhàn)爭是在東北的土地上進(jìn)行的,東北人民飽受戰(zhàn)亂之苦。戰(zhàn)爭最終以日本獲勝結(jié)束,日俄兩國于1905年在美國簽訂《樸茨茅斯和約》,俄國將其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權(quán)益讓給了日本,同時(shí)承認(rèn)日本在朝鮮享有卓絕的利益。此時(shí)日本已經(jīng)很大程度控制了朝鮮,到1910年,日本完全兼并了朝鮮。
在東北,日本為維護(hù)其殖民利益,以保護(hù)南滿鐵路的名義,逼迫清政府同意其在鐵路沿線駐軍。最初是每五十米駐兵兩人,總共六個(gè)大隊(duì),后來增加到一個(gè)師團(tuán)。俄國占領(lǐng)這個(gè)地區(qū)時(shí)將其定名為“關(guān)東州”,日本沿用了這個(gè)名字,因此駐扎在這里的部隊(duì)便被稱為關(guān)東軍。從此日本在東北立足,為后來日本進(jìn)一步侵略東北提供了條件。
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中的勝利,讓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國力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同時(shí)其野心也更加膨脹。
1915年,日本向時(shí)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意圖控制山東、南滿和蒙古東部的軍事、政治、財(cái)政等。雖經(jīng)袁世凱政府的爭取,刪除了一些條款,但最終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還是讓日本取得了這三個(gè)地區(qū)的大部分權(quán)益。其中在山東,日本繼承了德國的一切權(quán)利;在南滿,日本得以延長租借地和鐵路期限,日本人可以任意居住、往來,經(jīng)營農(nóng)工商和租借土地;在蒙古東部,日本人可以與中國人合辦農(nóng)業(yè)及附屬工業(yè)。這樣一來,日本在經(jīng)濟(jì)層面實(shí)現(xiàn)了對滿蒙的入侵,接下來就要等待時(shí)機(jī)進(jìn)行軍事入侵了。
1927年7月25日,日本內(nèi)閣首相田中義一秘密呈遞給昭和天皇一份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xì)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這份奏折的核心是,先奪取東北三省及蒙古,這就是所謂的“滿蒙政策”,然后再吞食華北,進(jìn)而占領(lǐng)全中國,以此為跳板,征服世界。
此后,日本軍部尤其是關(guān)東軍中較青壯派軍人,更加積極地籌劃侵吞東北。當(dāng)時(shí)正值東北軍對抗北伐軍作戰(zhàn)失利,日本欲籠絡(luò)張作霖,但遭到拒絕。1928年,趁張作霖退回東北,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日本本想趁張作霖之死造成的混亂,出兵占領(lǐng)東北,但張作霖之子張學(xué)良聯(lián)合東北當(dāng)局穩(wěn)住了局勢。
之后,張學(xué)良繼承其父執(zhí)掌東北政權(quán)。張學(xué)良身負(fù)國仇家恨,且面臨“東北何去何從”的緊迫問題。經(jīng)過反復(fù)權(quán)衡,他最終決定維護(hù)國家統(tǒng)一,歸順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擺脫日本的欺凌。但這一決策不僅遭到日本的阻止,東北內(nèi)部的頑固勢力也極力阻撓。最終,張學(xué)良沖破重重障礙,于1928年12月29日通電改旗易幟,宣布東北四省(包括熱河)歸屬國民政府。至此,國民政府終于完成了北伐的任務(wù),實(shí)現(xiàn)了形式上的國家統(tǒng)一。
“石原構(gòu)想”
東北易幟打破了日本分裂中國的陰謀,卻沒有終止其侵吞東北的腳步。
1930年,一場世界性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爆發(fā),日本也深受影響。當(dāng)時(shí)日本政府面臨著相當(dāng)多的困難,比如經(jīng)費(fèi)縮減、政府機(jī)構(gòu)改革、軍隊(duì)縮編以及軍人退休金的問題等。這些問題讓日本內(nèi)部矛盾重重。日本軍方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嚴(yán)重,越來越多的人向政府施壓,要求實(shí)行對外擴(kuò)張策略。
日本民間的一些人也認(rèn)為必須對外擴(kuò)張,才能解決或緩解日本國內(nèi)的矛盾。他們覺得最合適的目標(biāo)便是中國東北,這里距離日本本土近,土地廣闊,只要能在這里扎根,便能為日本獲取極大的發(fā)展空間。因此很多人移民東北,立志把東北變成日本人的天下。這些人組織成立了“滿洲青年聯(lián)盟”,試圖通過輿論來改變?nèi)毡緡鴥?nèi)對于滿洲問題的認(rèn)知。
然而此時(shí)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卻是妥協(xié)和協(xié)調(diào),不主張對外擴(kuò)張,這種政策被稱為“軟弱外交”。日本國內(nèi)的激進(jìn)派人士對幣原外交多有指責(zé)。
對于滿蒙問題,日本內(nèi)部的分化很嚴(yán)重,即便是在軍方內(nèi)部,也存在種種分歧。最明顯的是日本陸軍中央部和駐扎在東北的關(guān)東軍之間意見不一致。
1931年6月,日本陸軍中央部組織了一個(gè)委員會(huì),召集陸軍重要人物研究滿蒙問題的形勢和對策。最后形成了一份《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其中規(guī)定在未來的一年內(nèi)要隱忍自重,如果中日雙方發(fā)生了糾紛,要當(dāng)作局部問題進(jìn)行處理。當(dāng)年8月,日本陸軍中央部再次召開會(huì)議,研究滿蒙問題。這次做出的決議與之前并無太大不同,只是將之前決定的入侵時(shí)間1932年,延遲到了1935年。
與此同時(shí)關(guān)東軍參謀部也在對此進(jìn)行研究,他們卻認(rèn)為滿蒙問題必須立即著手解決。關(guān)東軍之所以如此著急入侵東北,一是因?yàn)楫?dāng)年發(fā)生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已經(jīng)讓中日雙方產(chǎn)生了足夠的對立;二是因?yàn)楫?dāng)前世界其他強(qiáng)國都忙于處理國內(nèi)事務(wù),英國正計(jì)劃拋棄金本位,美國盛行孤立主義,蘇聯(lián)正謀劃建國計(jì)劃,幾大強(qiáng)國均無暇顧及中日沖突;三是因?yàn)槭Y介石為了“剿共”,抽調(diào)了大批東北軍入關(guān),導(dǎo)致東北防守空虛。這些原因都讓關(guān)東軍認(rèn)為入侵東北的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
在關(guān)東軍方面,主導(dǎo)入侵東北計(jì)劃的是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作戰(zhàn)參謀石原莞爾。九一八事變的計(jì)劃藍(lán)圖,便是石原莞爾繪制的。
石原莞爾從小受到武士道精神熏陶,長大后進(jìn)入日本陸軍士官學(xué)校學(xué)習(xí),之后考入日本陸軍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duì)司令部工作,隨后他用了一年多的時(shí)間對中國的湖南、四川、上海、南京等地進(jìn)行考察,搜集了大量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情報(bào),并初步形成了侵略中國大陸的思想。
1928年,石原莞爾擔(dān)任關(guān)東軍作戰(zhàn)參謀,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文章,闡述入侵中國東北的理論,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石原構(gòu)想”。這個(gè)構(gòu)想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一戰(zhàn)只是歐洲諸國的決戰(zhàn),并非真正的世界大戰(zhàn),下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才會(huì)是真正的人類決戰(zhàn),這場決戰(zhàn)將會(huì)以日本和美國為中心,日本如果要對美國作戰(zhàn),就要立即對中國作戰(zhàn),如果對中國作戰(zhàn),就要先占領(lǐng)滿蒙,如此才能恢復(fù)日本的繁榮。
1929年7月,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組織了一次“北滿參謀旅行”。兩人帶領(lǐng)關(guān)東軍參謀們踏遍東北各省,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查,搜集了相當(dāng)多的情報(bào)。在此過程中,石原莞爾第一次向眾參謀闡述了自己的“最終戰(zhàn)爭論”和“滿洲土地?zé)o主論”。就連參謀旅行的最高負(fù)責(zé)人板垣征四郎也認(rèn)真聽取他的講述。在長春名古屋旅館,石原莞爾向其他參謀散發(fā)了自己撰寫的《戰(zhàn)爭史大觀》,其中提出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決滿蒙問題,這將成為日本的根本國策。一路上他還不斷闡述自己的理論,他認(rèn)為要消除當(dāng)前日本國內(nèi)的不穩(wěn)定因素,唯一的辦法就是對外擴(kuò)張,但是大部分日本人還沒能理解滿蒙問題在戰(zhàn)略和經(jīng)濟(jì)上的意義。基于這些理論,他制作了一份《關(guān)東軍占領(lǐng)滿蒙計(jì)劃》,其中提出了解決中國軍隊(duì)、管理東北地區(qū)和發(fā)展東北經(jīng)濟(jì)的具體辦法。
板垣征四郎很欣賞他的想法,但是日軍參謀本部和陸軍部卻不支持這樣的主張,主要是怕美國和蘇聯(lián)干涉。石原莞爾并不放棄,后來又和板垣征四郎組織了多次參謀旅行,搜集關(guān)于東北的情報(bào)。他和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在滿蒙問題方面達(dá)成一致,形成了一個(gè)地下組織,每次聚會(huì)都要討論如何占領(lǐng)和管理滿洲。從1929到1931年的兩年時(shí)間里,這個(gè)以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為核心的組織逐漸制定出了完整的入侵中國東北的計(jì)劃。
相比于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更注重研究中國人的心理。他對中國政治人物和民眾的心理十分了解,很清楚中國人的弱點(diǎn)在哪里。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對關(guān)東軍做戰(zhàn)斗動(dòng)員時(shí)說:“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yè)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職業(yè)。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lián)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gè)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gè)自治部落的地區(qū)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對民族發(fā)展歷史來說,國家意識(shí)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quán),誰掌握軍權(quán),負(fù)責(zé)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從“大陸政策”到“滿蒙政策”再到“石原構(gòu)想”,最終形成完整的入侵東北的計(jì)劃,日本入侵中國的思想和理論不斷完善,只等時(shí)機(jī)合適,便要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
日本為侵略東北所做的軍事準(zhǔn)備
發(fā)動(dòng)九一八事變前一年,日軍已開始為侵略東北做準(zhǔn)備。在旅順、大連的租借地區(qū),日軍不斷增加兵工廠和倉庫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在南滿鐵路比較大的站點(diǎn),以建設(shè)商用倉庫的名義,建設(shè)兵營,為增加軍事人員做準(zhǔn)備;以建立哨所的名義,在鐵路沿線的橋梁處設(shè)立防御工事,其中設(shè)有炮臺(tái)。在事變臨近時(shí),日軍的調(diào)動(dòng)十分頻繁,武器裝備的配備比之前更加充足。為增加士兵斗志,日軍在內(nèi)部不斷宣傳侵占東三省對日本的好處,以及軍人的義務(wù)。與此同時(shí),日軍還給沈陽附近的日韓僑民發(fā)放槍支,組建自衛(wèi)警團(tuán),讓僑民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可以保護(hù)自身。
為降低東北軍的警惕,日軍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進(jìn)行了五十多次演習(xí)。到9月份,日軍更頻繁地進(jìn)行實(shí)彈演習(xí),東北軍和百姓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了槍炮聲。因此當(dāng)日軍炸柳條湖鐵路,向北大營發(fā)起進(jìn)攻的時(shí)候,沈陽軍民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日軍又在演習(xí)了。
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之后,日軍加速進(jìn)行軍事上的準(zhǔn)備。他們認(rèn)為進(jìn)攻沈陽必須有巨炮,于是向陸軍中央部申請了兩門24厘米口徑的榴彈炮,從日本神戶用船運(yùn)到大連港。由于需要保密,因此在布置這兩門炮時(shí),日軍都穿著中國勞工的衣服作業(yè)。當(dāng)時(shí)正是夏天,當(dāng)?shù)匕傩沼型砩显谕膺叧藳龅牧?xí)慣,日軍在晚上的作業(yè)很難不被發(fā)現(xiàn)。于是日軍用大箱子把榴彈炮罩起來,謊稱是日軍高官的靈柩。以修建游泳池的名義,挖了一個(gè)直徑五米,深一米的坑,作為布置榴彈炮的基礎(chǔ)。為了遮蔽施工人員的行動(dòng),他們還利用三個(gè)晚上的時(shí)間做了一個(gè)七米高的鋅板房。一些好奇的百姓不知道日軍在干什么,有時(shí)會(huì)湊上去看,往往遭到日軍的驅(qū)趕。中國飛機(jī)在上空偵察時(shí),也會(huì)被日軍用防空武器威脅。為了萬無一失,除了炮兵外,日軍還教普通陸軍士兵如何操作榴彈炮,并在上面做出標(biāo)記,只要按照標(biāo)記操作,就能命中目標(biāo)。等一切都準(zhǔn)備好后,日軍對外宣稱這是陣地高射炮,也就是用來打飛機(jī)的。東北軍方面感到有些奇怪,于是在附近設(shè)了一個(gè)觀察哨,用來監(jiān)視日軍的行動(dòng)。
與此同時(shí),東京軍事參議官會(huì)議通過了“常駐滿洲師團(tuán)設(shè)置案”,從日本本土調(diào)了一個(gè)師團(tuán)駐扎在南滿鐵路附屬地。南滿鐵路沿線原本由日軍“滿鐵守備隊(duì)”負(fù)責(zé)警衛(wèi),其兵力為一個(gè)聯(lián)隊(duì),大約相當(dāng)于一個(gè)團(tuán)。在沿線的各個(gè)車站駐扎有中隊(duì)、分隊(duì)、小隊(duì)等,分別相當(dāng)于連、排、班的編制。鐵路上有鐵甲車日夜巡邏。租界中駐有日本憲兵和警察,負(fù)責(zé)維持治安。新的師團(tuán)進(jìn)駐后,強(qiáng)占附近民田,加鋪鐵軌,將原本只是雙軌寬度的道基拓展了一丈多。
駐沈陽日軍還向東北軍提出互相參觀學(xué)習(xí),并進(jìn)行聯(lián)歡活動(dòng)。其實(shí)日軍的真實(shí)目的是要對東北軍駐地進(jìn)行偵察,為之后開戰(zhàn)做準(zhǔn)備。但是東北軍方面沒有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同意了這次互訪活動(dòng)。東北軍方面參加互訪的是上尉以上軍官,日方是少佐以上軍官。日本軍官對東北軍駐地營房和周圍駐地都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觀察,而當(dāng)東北軍軍官參觀日軍駐地時(shí),卻發(fā)現(xiàn)到處都貼著“禁入”的字樣,大部分地區(qū)都不能參觀,只能了解大概樣貌。東北軍并沒有因此停止互訪。日軍則越來越放肆,除了軍官以外,還有普通士兵經(jīng)常以“參觀”的名義,組隊(duì)來北大營鬧事。東北軍官兵對此都?xì)鈶嵅灰眩巧霞売胁坏挚沟拿睿瞄L王以哲經(jīng)常告誡下級軍官和士兵,不要鬧出事來,所以大家只好對日軍的各種行為忍氣吞聲。
1931年8月1日,曾任張作霖顧問的中國通本莊繁代替菱刈隆成為關(guān)東軍司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認(rèn)為入侵的時(shí)機(jī)即將到來,于是更加積極地進(jìn)行軍事部署。
8月8日,關(guān)東軍駐沈特務(wù)機(jī)關(guān)長土肥原賢二回國,聯(lián)絡(luò)軍部首腦,游說日本參謀本部對東北出兵。同時(shí),為了給下一步侵略行動(dòng)制造輿論,關(guān)東軍在東北繼續(xù)從各個(gè)方面肆意挑釁。
到9月份,關(guān)東軍方面的部署已基本完成。此時(shí)中國內(nèi)部各派軍閥明爭暗斗,國民黨集中精力對紅軍進(jìn)行圍剿,政府無暇顧及東北的局勢,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認(rèn)為入侵東北的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
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變前幾個(gè)月,日本在東北極力挑起事端,制造發(fā)動(dòng)事變的借口。
1931年4月,中國人郝永德在日本人的慫恿之下,騙取了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nóng)民的土地,隨后私自轉(zhuǎn)租給188名朝鮮人。當(dāng)時(shí),吉林省政府規(guī)定:“凡是雇傭朝鮮人10人以上不滿20人者,必須要經(jīng)過縣政府批準(zhǔn);雇傭朝鮮人超過20人,必須經(jīng)過省政府批準(zhǔn)。”所以,郝永德把土地轉(zhuǎn)租給188名朝鮮人的合同是不合法的。
這188名朝鮮人在租用土地之后,為了種植水稻,私自挖掘水渠,截流筑壩。但這一工程損害了下游農(nóng)民的利益,于是當(dāng)?shù)剞r(nóng)民聯(lián)合起來告到了省政府。吉林省政府做出批示:“朝僑未經(jīng)我當(dāng)局允許,擅入農(nóng)村,有背公約,令縣公署派員同公安警察前往勸止,令朝僑出境。”然而這些朝鮮人背后有日本人撐腰,日本駐長春領(lǐng)事田代重德不僅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還命令他們必須繼續(xù)筑壩修渠。這種做法激起了民憤,7月1日,當(dāng)?shù)?00多名農(nóng)民聯(lián)合起來,拆除了朝鮮人修筑的水壩。想要找茬的日本人當(dāng)然不會(huì)放過這個(gè)機(jī)會(huì),7月2日,日本人派出警察鎮(zhèn)壓拆除水壩的農(nóng)民,遭到激烈的反抗。日本人增加了武裝警察的數(shù)量,保護(hù)朝鮮人重新修筑了水壩。
一名朝鮮記者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在報(bào)紙上發(fā)表在報(bào)紙上發(fā)表了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的新聞,引起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憤恨。7月3日,日本人在朝鮮挑起了一場慘烈的排華運(yùn)動(dòng)。排華運(yùn)動(dòng)從仁川開始,隨后蔓延到漢城、新義州、平壤等地。其中平壤最為嚴(yán)重,朝鮮人手拿兇器,在大街上見到中國人就殺,還闖到中國人的住處和商店,殺人、搶劫、打砸。據(jù)統(tǒng)計(jì),在這次事件中,有1500多名華僑傷亡,損失了大量財(cái)產(chǎn)。
排華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方面有人主張實(shí)施報(bào)復(fù),以顯示中國人民的力量。但是這個(gè)主張最終沒有獲得認(rèn)可,因?yàn)槟菢又粫?huì)讓朝鮮的無辜民眾受害,而日本則可以從中得利,甚至以此為借口向中國發(fā)動(dòng)侵略,所以目前只能忍耐。
后來,那名朝鮮記者了解到真相,在報(bào)紙上發(fā)表了聲明,承認(rèn)自己捏造假新聞。這導(dǎo)致日本人的陰謀敗露。事情到了這個(gè)地步,正常情況下應(yīng)該是日本人出來道歉并賠償,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追究責(zé)任。但是軟弱的國民政府卻只是派出了一個(gè)專員與日本人進(jìn)行交涉,雖然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卻沒有得到日本人的回應(yīng)。面對這種情況,政府也沒有拿出新的辦法,只是繼續(xù)交涉。直到日本人發(fā)動(dòng)九一八事變,政府都沒有得到合理的答復(fù)。
萬寶山事件本是民間普通的用水糾紛,完全可以通過調(diào)解妥善解決,日本人卻故意擴(kuò)大矛盾,制造事端。這件事還未平息,又發(fā)生了“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guān)東軍參謀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受上級之命,偽裝后潛入興安嶺屯墾區(qū)從事間諜活動(dòng),刺探軍情。但是因?yàn)樾袆?dòng)不夠隱秘,中村震太郎和他的同伙被中國屯墾區(qū)第三團(tuán)士兵發(fā)現(xiàn),并搜出調(diào)查筆記、軍用地圖、測繪儀器等多種特務(wù)活動(dòng)罪證。調(diào)查之后發(fā)現(xiàn),中村震太郎等人確實(shí)是間諜,于是第三團(tuán)團(tuán)長關(guān)玉衡下令將中村震太郎等人槍決。
本來槍斃中村震太郎等人這件事是保密的,日本方面也不知道他們?nèi)チ四睦铮顷P(guān)玉衡有個(gè)小妾是日本人,她向朋友透露說自己的丈夫殺了日本人。這個(gè)消息很快傳到關(guān)東軍耳朵里,于是關(guān)東軍開始策劃如何利用這次事件挑起爭端。關(guān)東軍主張出兵攻占洮索鐵路,但是這個(gè)建議被幣原外相否決,最終還是決定走外交途徑解決。
雖然沒有用軍事手段,但在外交上日本人同樣蠻橫。中村震太郎的間諜罪人證、物證俱全,受到中國官兵嚴(yán)懲,這是合理合法的。但日本人拒絕認(rèn)同調(diào)查結(jié)果,抓住“東北軍殺死日本人”這件事情大做文章,強(qiáng)詞奪理,污蔑關(guān)玉衡團(tuán)長是因?yàn)樨潏D中村震太郎的錢財(cái)而謀財(cái)害命。日本駐沈陽總領(lǐng)事林久治郎在與東北軍負(fù)責(zé)人交涉時(shí)非常強(qiáng)硬,要求東北當(dāng)局正式道歉,嚴(yán)懲責(zé)任人,還要承諾保證日僑生命財(cái)產(chǎn)安全。
7月7日,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到北平與張學(xué)良商討對策。最后沒有辦法,只好將關(guān)玉衡撤職查辦。
日本在交涉中村事件時(shí),不遵照兩國的外交程序,不斷向東北政府施壓,威脅要對華出兵。在日本國內(nèi),政府籌集了5萬日元的喪葬金,在東京為中村舉行隆重的葬禮,大肆宣傳中村事件,激起日本人民仇恨中國的情緒。日本政府還將中村事件拍成影片,并在其中介紹了各種東北風(fēng)俗,引起國民對滿蒙的好奇。日本第9師團(tuán)到處散發(fā)傳單,傳單配有滿蒙地圖解釋日本對滿蒙的特權(quán),宣揚(yáng)滿蒙地區(qū)關(guān)系著日本的國防安全。第12師團(tuán)在大阪舉辦滿蒙展覽,宣揚(yáng)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等等。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稱中村事件是“對日本皇軍的進(jìn)攻”,還稱“這是解決滿蒙問題的絕好機(jī)會(huì)”,意圖以此為借口向中國發(fā)動(dòng)侵略。
之后日本又多次挑起事端,東北形勢非常緊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