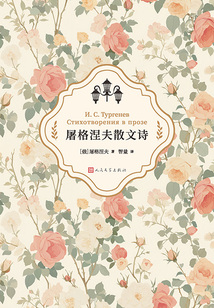
屠格涅夫散文詩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屠格涅夫散文詩談片
1877至1882年間,遠居巴黎的屠格涅夫于衰老多病的晚年陸續(xù)寫下八十余則帶有詩性與哲理的簡短文字,此乃作家人生末歲的感懷與沉思的零星記錄,多為對往事的回憶,對所歷事物的隨感,也有對未來的展望,其書寫形式多為抒情自白和哲性思索。這些隨意而成的文字作家本人并不打算發(fā)表,只是“以詞的圓潤和朗聲自娛”[1],但顯現(xiàn)其間的那份真摯的情感,深刻的論理,以及藝術上的精雕細琢,對大自然的敏感與獨特描繪,構(gòu)成他生命與藝術的絕唱,也于不經(jīng)意間為俄羅斯文學創(chuàng)立了一種嶄新的體裁,即散文詩。
* * *
《散文詩》是屠格涅夫人生的最后一部杰作,也是其一生創(chuàng)作的獨特總結(jié),“像是對屠格涅夫既往作品所作的回應”[2]。就其思想立意,散文詩《瑪莎》《菜湯》《兩個富翁》與作家本人的《獵人筆記》很是接近,一道揭示“老爺和農(nóng)民”的關系甚或探討二者精神世界誰更富有的命題;從《門檻》與《做臟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中我們可以讀到小說《處女地》的作家宏旨,后者反映了那個年代革命者與民眾之間的相互隔膜與不理解,“白手人”的事業(yè)在民眾看來只是誰也不需要的暴動,而俄羅斯莊稼漢對民粹派的苦難與犧牲不寄予任何同情,且專等享受革命者的犧牲。其實這種悲劇在小說《父與子》巴扎洛夫與村民的矛盾中也已經(jīng)得到了預演。同樣,從《門檻》女革命家身上我們同時看到《前夜》中“新人”葉蓮娜的動人形象,兩部作品中的“對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前夜》中的對話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愛情,那么《門檻》中時隔二十年的新女性所追求的則是革命事業(yè),由此顯示出了俄國社會生活的發(fā)展,同時我們看出,及至晚年的屠格涅夫,仍記得文學使命在于“反映時代前進的新動向和新趨勢”[3];散文詩《基督》是《獵人筆記》中《活尸》女主人公露凱莉亞基督夢的兌現(xiàn),凸顯其作品中基督教因素的深沉含義;論及自然景色描寫,散文詩系列開篇《鄉(xiāng)村》分明是《貴族之家》中的大自然復現(xiàn),與第二十章中拉夫列茨基回歸故里之心情構(gòu)成和鳴,展現(xiàn)的是令每一個俄羅斯人倍感親切的俄羅斯鄉(xiāng)村立體畫圖!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小說熱衷探討的生、死、愛等主題,在散文詩中也得到了鮮明再現(xiàn)。屠格涅夫的神秘小說《夠了》和《幽靈》中的主題也讓其散文詩鳴響著宿命的調(diào)子,凸顯生命的虛浮、死亡的命定難逃,讓人生徒勞的思想在散文詩中形成死亡的人格化形象。比方說散文詩《老婦人》《蟲》中一切都是虛妄的“煙”與“霧”,致人死亡的毒蟲,將人帶向墳墓的老太婆,而且死亡總是作為夢境、夢幻,其形象總是令人吃驚地具體;《老人》《沒有個窩兒》《當我不在人世時……》《“玫瑰花兒那時多美,多鮮艷……”》《當我獨自一人……》,則與同時期寫下的神秘小說達到了形神呼應。涅茲維茨基甚而將屠格涅夫近乎同一時期寫下的神秘小說《愛的凱歌》、《死后》(《克拉拉·米利奇》)與《散文詩》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其一道“運用宇宙舉隅法來寫愛、幸福與義務,寫大自然、天空、星辰,同時還有祖國俄羅斯、藝術、女人、青春……‘生命的神秘力量’、死亡……”[4]。另外,愛之歌在散文詩《麻雀》中鳴唱得最為嘹亮,我們重又看到《獵人筆記》中的獵人,溫和善良,目睹麻雀母親舍身救子他得出了一生思索的總結(jié),即愛“比死和對死的恐懼更強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愛,生命才得以維持、得以發(fā)展”,這一愛的墓志銘是對作家既往小說愛的描寫的概括與升華。
* * *
在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史上,屠格涅夫散文詩最受追捧之時當為“白銀時代”,這些微型作品曾讓各流派詩人和作家沉醉其中。
象征派領袖人物梅列日科夫斯基明確表態(tài)他尤為喜歡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喜歡其如夢似幻的縹緲神秘的愛情描寫,以及通過象征、夢幻、預感等手段表現(xiàn)出來的神秘傾向,自覺認識了又一個屠格涅夫,宣稱,屠格涅夫創(chuàng)作中的“小不點兒”(散文詩)比那些嚴肅的社會典型,如羅亭、拉夫列茨基、英沙羅夫等更珍貴,更不朽。此等觀點帶動了一批象征派詩人對屠氏散文詩的狂熱崇拜,如巴爾蒙特、別雷、安年斯基、勃洛克等等。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對詩人謝韋里亞寧的撼動是根本性的,原本狂放自傲的自我未來派詩人正是因為此,后期的詩作就其音調(diào)來說散發(fā)著屠格涅夫“迷人的憂郁”,一改以往橫沖直撞的怪異詩風,而具備高品位的質(zhì)樸和矜持。謝韋里亞寧臨終前以散文詩《“玫瑰花兒那時多美,多鮮艷……”》為底色,囑咐在其墓碑上刻下詩行:“玫瑰花,將是(屠氏用的是過去時)多么鮮艷,多么美麗,/它被我的國家拋至我的靈柩”。
屠格涅夫與布寧有著同樣的創(chuàng)作軌跡,即以詩歌登上文壇,以小說家彪炳于世,接近晚年都走向詩與散文的合成,前者的體現(xiàn)形式是散文詩,后者則是微型小說,但屠格涅夫的許多散文詩,如《瑪莎》《施舍》《菜湯》等因其情節(jié)性與故事性被稱“短小精悍,猶如微型小說,而且往往只限于敘事狀物……”[5],而兩位作家詩化散文的追求也使得布寧的散文有詩歌一樣的勻整深邃,詩歌有散文一樣的質(zhì)樸曉暢。俄羅斯研究家們索性把布寧的一大部分“微型藝術佳作”,如《金龜子》《美人兒》《頭等車廂》《羅鍋背的羅曼史》《一封信》《前夜》《鶴》等歸屬于散文詩之列,它們具備屠格涅夫的抒情特質(zhì),其間包含著哲理和箴言,兩位大師的抒情滿載著詩的語匯、獨特的句法結(jié)構(gòu)以及特定的語言節(jié)律,他們的微型作品一般由兩個層次構(gòu)成,先是敘事,后是一番哲理思考和箴言式的結(jié)論。此外,無論就其景致描寫、場景構(gòu)筑、語言特色等等,布寧的小說《安東諾夫卡蘋果》都與屠格涅夫散文詩《鄉(xiāng)村》極其接近,兩部作品像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取自同一幅畫面,像是同一構(gòu)思的復制,是將細節(jié)和結(jié)構(gòu)拆開而進行的獨特的詩的對話。詩情畫意再現(xiàn)屠格涅夫散文詩中故園俄羅斯美麗的還有布寧的微型小說《書》《仙鶴》《小教堂》《螞蟻大道》等,借助其于異國孤獨漂泊中抒發(fā)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
順帶說明的是,盡管布寧的大部分微型小說寫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且被公認為作家人生向晚之作,但就其自身的內(nèi)容,就其總體情調(diào)卻又常常被列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文學范疇,其首要原因是,布寧是在革命年代離開俄羅斯的,他不可能理解和評價俄羅斯后來所發(fā)生的一切,因而“對他說來,‘生活的鐘點已經(jīng)停止’,他的記憶已被對他未逃亡之前的那個時代的印象所填滿,他能夠描寫的似乎只能是這段生活”[6]。
兩位文學大師的文字都有著“詩的情思,詩的意境,詩的手法”,詩的哲理與概括,同時有散文的自由(不受詩的格律制約),散文的細膩,散文的精確。兩位藝術家或是觸景生情,或是以情狀物,其文字都具備了散文詩的真摯、簡潔、多主題、多聲部的美學特征。
* * *
屠格涅夫是以他的散文詩亮相中國的。1915年,劉半農(nóng)從英文翻譯并發(fā)表了屠格涅夫四首散文詩,即《乞丐》《瑪莎》《傻瓜》《菜湯》。自此,屠氏散文詩在中國不斷被翻譯,百年來已出版三十幾個版本,彰顯了其在中國的強大生命力和獨特的思想藝術魅力,并擁獲了一批崇拜者,如魯迅、郭沫若、巴金、陸蠡、麗尼等名家。
人們常將魯迅的《野草》和屠格涅夫散文詩作比較,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最鐘情的屠格涅夫散文詩是《老婦人》《世界的末日》《骷髏》《做臟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門檻》《蟲》《大自然》等,并受其影響寫出了自己的散文詩,如《復仇(其二)》《過客》等等,魯迅一些關于“夢”的散文詩無疑也是從屠格涅夫散文詩中得到啟發(fā)。正是《做臟活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觸發(fā)了魯迅小說《藥》的創(chuàng)作動因,乃至人物設計、行文結(jié)構(gòu)都有明顯的傳承,其中“國民性”弱點以及先覺者與愚民“隔膜”的悲劇揭示,體現(xiàn)了中俄兩國文學在這一主題和立意上的一脈相承。
* * *
《散文詩》雖是屠格涅夫垂暮之年的作品,卻如夕陽勁照,煥發(fā)經(jīng)久不衰的思想與藝術生命力,它為作家一生創(chuàng)作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它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深受我國讀者的喜愛。今天的《屠格涅夫散文詩》重新出版便是明證。
注釋
[1]《屠格涅夫作品與書信全集》(三十卷),莫斯科—列寧格勒,科學出版社,1967年,第18卷,第205頁。
[2]格·比亞雷:《屠格涅夫》,見《俄羅斯文學史》,莫斯科—列寧格勒,蘇聯(lián)科學院出版社,1956年,第8卷,第391頁。
[3]朱憲生:《天鵝的歌唱:論俄羅斯作家》,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頁。
[4]亞·涅茲維茨基:《十九—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評論集萃》,納爾奇克,“捷特拉格拉夫”資助出版,2011年,第248頁。
[5]金留春:《詩人屠格涅夫(代前言)》,見《屠格涅夫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第5頁。
[6]列·尼庫林:《契訶夫·布寧·庫普林:文學肖像》,莫斯科,蘇聯(lián)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18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