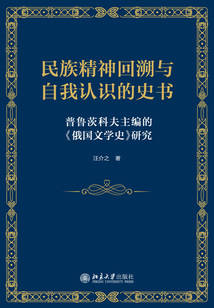
民族精神回溯與自我認識的史書:普魯茨科夫主編的《俄國文學史》研究
最新章節
- 第35章 注釋
- 第34章 后記
- 第33章 西方文學史 文化史名人譯名表
- 第32章 《牛津俄國文學史》目錄[256]
- 第31章 《劍橋俄國文學史》目錄[255]
- 第30章 《俄國文學史》目錄[253][254]
第1章 前言
在我們的北方近鄰俄羅斯的那一片廣袤無垠的土地上誕生和發展的文學,是這個民族思想文化的藝術載體,也是世界文學史上奇特的精神文化景觀。早在12世紀,古代羅斯的長篇史詩《伊戈爾出征記》,就在歐洲中世紀文壇熠熠生輝,但在此之后,俄國文學卻似乎沉寂了500余年。18世紀初彼得大帝厲行改革,大大推動了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壇上開始出現一批有建樹的詩人和作家,不過在整個這一世紀中,俄羅斯仍未能產生出足以和同時期西歐文學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直到19世紀初,情況才發生根本的變化:俄國文學仿佛從沉睡中一躍而起,以詩人普希金為先導,形成了一個名家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迅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之一,且一發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不是在西歐各國文學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個歐洲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的。
俄羅斯文學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杰出的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說過:“俄羅斯文學不是產生于令人愉悅的創造力的豐盈,而是產生于個人和人民的痛苦與多災多難的命運,產生于對拯救全人類的探索。”[1]家國不幸詩人幸,民族的苦難與擺脫這種苦難的追求,積淀為獨特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由其所孕育的俄羅斯文學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義內涵、“為人生”的主導意向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由于俄國傳統哲學不發達,文學不得不承擔在別的國度通常是由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所擔當的任務。對于俄羅斯人來說,“文學是唯一的講壇,可以從這個講壇上訴說自己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2]。文學也就因此顯示出與歷史、倫理、哲學、宗教的不可分離性。作家們的使命意識和人文情懷,使俄國文學始終是一種“介入”的文學。文學所造成的“精神氣候”,不僅對特定時期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和演變產生了直接影響,而且往往作用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運行。19—20世紀俄羅斯文學作為民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面臨著這一進程中始終不可繞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如東西方之間的道路選擇,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的輕重緩急,統一意志與個性自由的沖突和兼顧,知識階層價值與作用的認定和發揮,以及同關于現代化的過程、方式和后果的反思相關的憂患意識與鄉土情結的體認和疏泄等。俄國文學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呈現和表達顯示出它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成為現代化運動生動的藝術錄影,而且為總結和反思這一行程的歷史經驗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參照,并由此獲得了它史詩般的厚重感、沉郁蒼涼的底色和永恒的藝術魅力。
回望中外文學交往史,人們不難發現,俄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系最為密切。這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一種無論你怎樣淡化它都客觀存在的史實。這種關系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中俄兩國地理上是近鄰,國情彼此相近,兩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進入20世紀,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為民族的命運而思慮,都欲喚起民眾意識的覺醒,推動本民族走向現代。我國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的開拓者們就敏銳地注意到俄國文學的特點。李大釗曾經指出:“俄羅斯文學之特質有二,一為社會的色彩之濃厚,一為人道主義之發達。”[3]現代文學史家鄭振鐸也曾寫道:“俄國文學所以有這種急驟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摯的與人道的精神,使她懇發了許多永未經前人蹈到過的文學園地,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4]正因為如此,中國新文學在吸取外來文學的養分、建構自身之初,便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認定“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5],特別注重攝取俄羅斯文學。于是,中國新文學中便清晰地顯示出俄國文學的滲透與滋養,呈現出與俄國文學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調和特色。
俄國文學不僅直接影響了中國新文學的格局與進程,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審美情趣,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優秀讀者。20世紀中國的文學翻譯史表明,在我國出版的全部外國文學翻譯作品中,從國別的角度而言,俄羅斯—蘇聯文學作品在長時期內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這些作品不僅滋養了我國幾代文學工作者,而且曾經廣泛影響了成千上萬普通讀者的精神生活和人生道路。有許多優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和這個民族所提供的同樣出色的戲劇、電影、繪畫、音樂、芭蕾舞作品一樣,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經典。
然而,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中俄文學關系的蜜月期似乎已經過去。這或許是中國文學擺脫早年文藝思潮制約的一種表現,因為它難以忘卻“一邊倒”所帶來的負面后果。中國當代作家和讀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世界,注意吸收各國作家的藝術經驗。于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俄羅斯—蘇聯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開始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在世紀晚期的蒼茫暮色中,這種曾擁有強大藝術吸引力的文學仿佛漸漸淡出我國一般讀者的視野。這也許并非一種令人遺憾的現象。遺憾之處卻在于,對于“一邊倒”接受的記憶與警惕,妨礙著我國當代學界以足夠的耐心再度面對并重新審視同樣是自80年代中期起,日益顯示出原本面貌的俄羅斯文學。不知是一個接受俄國文學的最佳歷史機遇已然過去,還是一個更合適的接受氛圍尚未到來。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中俄兩國的文化交流不至于中斷,只要俄國文學本身依然是一種具有價值和特色的、不可忽視的文化存在,它就必將繼續得到中國廣大讀者的喜愛,繼續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意蘊充實與滋潤我國廣大讀者的心田。
文學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引導讀者輿論。在中國當代文學語境中,擺在我國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面前的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就是重新認識、描述和評價俄羅斯文學的歷史進程。延綿十個多世紀的俄國文學,究竟走過了什么樣的道路?俄國文學在其發展的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板塊、各個流派和各種潮流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相互關系?俄羅斯文化傳統、民族心理和精神訴求等,究竟怎樣制約著其文學的特質和演變趨勢,又怎樣表現于文學?俄國文學究竟為人類提供了哪些真正的經典,留下了哪些應當珍視的寶貴遺產?當代讀者是否還可以從俄羅斯文學中繼續獲取精神給養與審美愉悅?中國讀者顯然有理由希望通過研究者、評論者們的言說得到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但是,截至目前,國內學界尚未能滿足讀者的這一需求。我們至今甚至還沒有一部完整的俄國文學史著作。在國別文學史著述領域,已先后問世的有柳鳴九主編的三卷本《法國文學史》(1979、1981、1991),李賦寧、王佐良等主編的五卷本《英國文學史》(1994—2005),劉海平、王守仁主編的四卷本《新編美國文學史》(2000—2002),范大燦主編的五卷本《德國文學史》(2006),葉渭渠、唐月梅合著的四卷6冊《日本文學史》(2004)等。相比之下,我們還缺少由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多卷本《俄國文學史》,可以和“科學院版”《俄國文學史》相媲美。
“科學院版”這一概念,借用于俄羅斯—蘇聯學術界。在俄羅斯或蘇聯,代表某一學科領域在特定階段的國家水平的大型權威性著作,往往都是由俄羅斯科學院或蘇聯科學院組織實施,由“俄羅斯科學院出版社”(Издaтeльствo РAН)、“蘇聯科學院出版社”(Издaтeльствo AН СССР)等下屬出版社出版的。如十卷本《世界文學史》(1983—1994,已出版前8卷)、十卷本《俄國文學史》(1941—1956)、六卷本《蘇聯多民族文學史》(1970)等。“蘇聯科學院出版社”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改名為“科學出版社”(Издaтeльствo?Нayкa?),但仍隸屬于蘇聯科學院和后來的俄羅斯科學院,繼續出版許多大型的權威性學術著作,“科學院版”的提法也沿用至今。
圍繞編譯多卷本“科學院版”《俄國文學史》的問題,國內學者自20世紀90年代起就展開過多次討論。2015年年底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舉辦的“俄國文學史的多語種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之后,編譯宗旨與基本思路逐漸明朗,但時至2018年才開始正式啟動。在這一背景下,為一種學術緊迫感所驅使,我們決定選擇由蘇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所長、俄國文學史研究專家尼基塔·伊萬諾維奇·普魯茨科夫(Никитa Ивaнoвич Пpyцкoв,1910—1979)主編、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俄國文學史》(Истopия pyсскoй литepaтypы.В чeтыpёх тoмaх)(1980—1983),將其完整地翻譯為中文,并進行系統而細致的研究,以期全面呈現蘇聯時期一流學者所描述的從10世紀至十月革命前俄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展示這一千年間俄國文學的歷史演變、藝術成就、思想價值、文化蘊涵和美學特色;在和國內外同類著作的比照中,深入揭示這套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所體現的文學史觀念、主導思想和編撰原則,發現其結構方式、方法論特點和話語特征,探明文學史研究、文學理論建構和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關系,為我國學界和廣大讀者進一步全面認識俄國文學的成就、面貌和特色,為更新文學史觀念、優化文學史研究方法和推動文學史編寫水平的提升,為建構科學的、完善的文學史學、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話語體系提供有價值的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