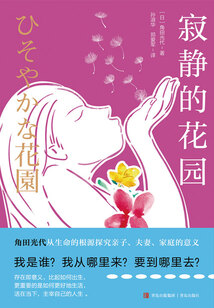
寂靜的花園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序 守護秘密花園
親愛的讀者朋友,在您開始閱讀之前,請先思考一下我提出的問題。如果您3歲到10歲這段天真無邪的孩提時代,每年夏天都在安靜舒適、色彩斑斕的夏令營中度過,那里有綿延不斷的群山,幽靜的道路,枝繁葉茂的行道樹,修剪整齊的草坪和院子,有很多房間的木屋,好玩的沼澤、森林和一處很大的廟宇;木屋的閣樓有天窗,躺在床上可以看著星星睡覺;食堂里有一張白木大桌子,很多人圍在一起共進晚餐;年齡相近的小朋友們一起無憂無慮地玩耍、交流。在這里,孩子們情同兄弟姐妹,可以一起干自己想干而平時不能干的事情,可以暢所欲言,沒有疏遠、嘲笑、無視和故意刁難,可以無須掩飾,可以隨心所欲地玩耍……這一孩子們的成長樂園簡直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但是,突然有一天,大人們擅自終止了這個夏日聚會,他們不但不告知其中的原因,還故意隱瞞實情,甚至隨著孩子們的逐漸淡忘,還矢口否認曾經去過那里,并嘲笑孩子們得了妄想癥。對此,您會怎么看待這件事情呢?
“懸疑小說”“推理小說”,脫口而出的是不是這樣的答案?沒錯,小說開頭就給讀者營造了懸疑的氛圍,我也是懷著忐忑的心情,被自己所臆想的恐怖真相吸引著看完的。結果,雖然不是懸疑故事,卻讓我們對“生”和“活”進行了深入思考。
小說講述了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出生的阿彈、樹里、波留、賢人、紀子、紗有美和雄一郎七人成長蛻變的故事。他們都是父母通過非配偶間人工授精,即都是用父親以外之人的精子誕生的孩子。故事從一次夏令營的回憶開始,這些孩子一到夏天就會去木屋露營。但突然有一天,露營被取消了。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在尋找答案。后來,孩子們重逢的過程也是了解父輩和自己身世的過程。
“等這孩子出生后,我們打算在充滿自然氣息的地方買房子,而不是在東京都內。讓孩子在那里打滾,聞著泥土的氣息玩耍……在院子里搭帳篷,捉蟲子。”正因為有了阿彈父母早坂夫婦這一計劃和夏天一起在那里度過的提議,才有了孩子們童年理想的烏托邦。這不僅為七個孩子提供了相識的場所和契機,使同齡的孩子們很快成了好朋友,而且也為以非正常方式受孕且內心忐忑不安的初為人父人母的大人們提供了交流的平臺。早坂夫婦真心希望能創造一個讓相同境遇的人可以隨時傾訴煩惱,互相扶持的社區。他們覺得以后一旦發生什么事情,只要有處境相似的家人在,大人和孩子們就會安心。
哲學家柏拉圖最早提出了世界公認的三大人生哲學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其實,角田光代的這部作品就很好地回答了這些哲學問題,即七個孩子是“如何出生,如何被養育,如何成長”的這些問題。
這七個孩子都是通過非配偶間人工授精的方式出生的。毋庸置疑,他們是超出常人的愛和希望的結晶,也可以說跟正常出生的孩子相比,他們的父母給予了他們更多的愛。早坂家是七對夫婦中最早接受治療的家庭,在接受治療前,小碧和真美雄就商量好了,并自始至終堅定自己的選擇和信念。即便他們經歷了三四次失敗,也毫不氣餒,繼續挑戰。小碧說:“我們并不關心捐精者是誰,從我們那么希望有個孩子時開始,這個孩子就已經是我們的孩子了。所以我們不打算把這件事告訴即將出生的孩子。不是要隱瞞,而是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是我們的孩子。”
在治療前,樹里的母親涼子與丈夫用盡了所有的時間和言語商量,捐精者也是他倆一起選擇的。他們想把自己沒有的優點給予孩子,因此盡量選擇比自己成績好、健康、漂亮、運動能力強、藝術才能出眾的供體。總之,對于即將到來的孩子,他們想給予孩子所有最好的東西。因此,夫婦倆選擇了看似完美的捐精者。
波留的父親因受外傷而客死他鄉。母親香苗斷然拒絕了雙方父母的勸說,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去了輕井澤的診所。她決定通過生孩子不再愛丈夫以外的男人,以單身母親的身份生活下去。跟其他父母不同的是,為了讓波留認同自己的身份,讓她不因為出身而胡思亂想,不懷疑自己的存在,香苗從小就積極引導波留,花了很長時間與她對話。波留是在十二歲時聽母親說自己是人工授精,而且是通過精子庫的精子受精出生的,之后她花了五年的時間,才學會了表述和理解。從第一次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開始,香苗就反復對波留說:“你是我和爸爸的孩子。我想要愛爸爸一輩子,所以才讓你來到媽媽身邊的。因此,你是爸爸在這個世界上最有力的證據。因為你既堅強又溫柔,這一點和爸爸一模一樣。”因為從小母親就這樣反復告訴波留,所以波留根本沒想過自己的父親會是在某個地方生活著的某個不認識的人。而且,母親對生物學上的父親也做了詳細說明。對波留來說,與在某個地方生活著的某個不認識的男人相比,被反復提及的“爸爸”當然更親近。所以,當她成年后知道這些時,心靈既沒有受到傷害,也沒有受到打擊,更沒有感到迷茫或者動搖。
恰如早坂夫妻所說的那樣,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充分溝通后才把孩子生下來的。有的人就是很簡單地想要個孩子,也有的夫妻之間并不怎么交流。不是每一對夫妻都是在真正想清楚后才做的決定,這恰恰是最現實的狀況。雄一郎的母親俊惠雖然沒有和丈夫多次溝通過自己的想法,但雙方都希望能這樣生下孩子,所以直到俊惠臨盆前,兩人都沒有任何疑問和不安。在眼看著就要生產時,俊惠才意識到自己那有別于“極為普通”的懷孕經歷,突然害怕起來了。
“我不能再做‘如果不生’的假設了,你也一定是這樣。沒有任何令人不安的事情。”從涼子開導俊惠的話語中可以看出,雄一郎的父母對很多事情都沒有想清楚。當雄一郎的父親在夏令營聽說去那里的父親都是不能生育的男人后,跟俊惠吵架并提出不再去時,俊惠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是事到如今,丈夫似乎還認為自己“不是父親”;二是她意識到自己沒有告訴丈夫去夏令營實情的嚴重性,自己沒有像涼子和小碧那樣,一口咬定“只有丈夫才是孩子的父親”。
紗有美說:“我媽媽好像太輕率,就說想要個孩子。雖然有男朋友,但又不想和那個人結婚……媽媽說反正要生孩子,就想找個更優秀的人的基因。像國公立大學畢業,大企業白領、醫生、學者什么的,或是通過體育保送進大學的現役職業運動員。她說如果不是這些人的孩子,就不想要了,因此,就去賣那種東西的地方買了。”
賢人的母親是人氣模特,以結婚為契機辭去了工作。雖然很可惜,但她想組建家庭,覺得自己馬上就能生孩子。但當她得知丈夫不育時,兩人商量后,決定接受非配偶間的人工授精。賢人的母親一直認為,這樣做是雙方都接受的,可隨著孩子不斷成長,她意識到想生、想要孩子的只有自己,是她一直在追求某種能代替模特這一工作的東西。
父母對這件事的態度,直接影響了他們后來對待孩子和孩子對生物學上的父親的認同態度。媽媽們的表現跟爸爸們的完全不同,用涼子的話說就是“無所畏懼”。盡管她們有的不被父母理解,甚至因此差點兒和父母斷絕子女關系,但都沒有影響和削弱她們無所畏懼的心情。
與生了孩子后無所畏懼的母親們相比,父親們的心理建設卻沒有那么強大。雖然當時無論如何都想要孩子,但是,當使用了別人的精子而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看到孩子遺傳了別人的優秀基因時,有的丈夫的心理開始變得復雜,對父親這一身份的認同困難,導致大多數家庭連婚姻都破裂了。孩子們知道了自己出生的真相后,心理也很復雜。
樹里的父親在發現去夏令營的父親全都是沒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后,沒能經受住每年一次的考驗,中途便放棄參加,甚至還離家出走了。離家出走的直接原因是樹里參加了畫畫比賽,成了年齡最小的銀獎得主。他在高興的同時,也下意識地想到這種才能是捐精者遺傳的,這讓他感到不寒而栗。他說:“從那以后,我便開始嫉妒,嫉妒那個比我優秀的人。明明是我自己那樣決定的,卻因為自己的選擇而備受折磨。”
雖然生賢人是夫妻雙方都接受的,但隨著孩子的成長,夫妻關系開始變得不融洽。父親的想法也與母親的出現了分歧。賢人的父親在分手時對賢人的母親說:“其實你不結婚也會過得很好,或者說能有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漂亮孩子也就心滿意足了。你斷送了別人的夢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你已經不需要我了吧。”透過這一段話,自卑、懦弱的男人形象躍然紙上。賢人也認為他是個懦弱的男人。小時候視若父親的男人,在離開時還對不認為是自己孩子的“兒子”狠狠大罵一頓,這刺激了賢人,讓他很自卑。
雄一郎和父親兩個人共進晚餐時,父親突然問他擅長什么科目,當知道他喜歡美工和算術時,父親說:“我啊,最討厭美工和算術了,我們一點兒都不像。”雄一郎注意到,雖然父親還面帶笑容,但卻讓人很不愉快,讓人捉摸不透。而且,從他父母的吵架中,也能窺見這個男人對這個問題還是很敏感的。不難看出樹里的父親、賢人的父親和雄一郎的父親還是很在乎自己不是孩子生物學上的父親這件事的,并顯示出了極度的自卑。
受原生家庭影響最嚴重的應該是雄一郎了。父母因關系不和,吵架便成了家常便飯,再加上后來母親經常加班到很晚,他連一頓像樣的晚餐都吃不上。父親的家庭暴力最終逼走了母親。他能理解母親,甚至想:如果自己有生活能力,也會逃走。但雄一郎認為這些并不是人生的分歧點,促使他自暴自棄走上人生岔路的是初中畢業那天,父親告訴他“那里的孩子,都是被父母遺棄在福利院的,所有的大人都是沒有孩子的養父母”。當然,母親原本就不應該把他丟給那個與他沒有血緣關系、沒有父親覺悟的“父親”。如果母親能再和父親好好商量商量,如果母親沒有逃避和父親無休止的爭吵,如果父親有做父親的覺悟,也許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雄一郎信以為真,從那天開始,他覺得一切都很愚蠢、毫無意義。自己想做點什么,想成為什么樣的人,等等,這些希望從那天開始莫名地消失了。一個人獨立生活后,他之所以要單純收留離家出走的女孩子過夜,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是被遺棄的孩子,不知道家庭的溫暖,而回家后能從樓下仰望自家窗口的橙色燈光,給他帶來了安全感。
隨著年齡的增長,紗有美覺得母親漸漸對自己漠不關心了,甚至有時還明顯表現出疏遠自己的態度。母親也總是把“因為有你”掛在嘴上。因為有你,我才不再婚;因為有你,我才這么拼命工作。在紗有美看來,“因為有你”聽起來更像是“如果沒有你”。如果沒有你,我可以再婚;如果沒有你,我就不用這么辛苦工作了。紗有美知道,那是只會說謊的母親沒有說出口的真話。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但一定是母親拜托人家,才把孩子生下來的,但生下來后卻沒了興趣。她認為是母親把她的人生搞得一團糟的。“我一直覺得自己很不幸。從未有過可以稱為朋友的人,也不認識自己的父親,母親說起自己的事情時總是心不在焉。我也從未想過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她從未覺得自己生下來是幸福的。
波留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家族病史,決定尋找生物學上的父親。可也有人并非如此。他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表現也各不相同。
阿彈說:“我也是在進入社會后才聽說的。不過,他們好像沒打算告訴我,是我自己調查了一番,然后才逼著父母說出了真相。”向父母詢問真相時,冷靜而聰明的母親沒有慌張或動搖,在和父親商量后,告訴了自己整個過程是怎么回事。阿彈認為母親的語氣中沒有一絲猶豫和困惑,充滿了自信,或許正因為如此,自己才沒有動搖吧。“我倒不覺得他們在騙人,但突然得知自己的父親是完全不認識的男人后,確實很為難。我也曾想過自己到底是什么,但中途厭倦了,厭倦了思考。不管怎么樣,自己已經在這里了,明天肯定會到來……曾想過自己會不會是被收養的孩子,這樣懷疑的時候,其實更痛苦。”受父母的影響,阿彈對這件事一直很淡定。以至于成年后第一次見面的賢人都產生了疑問。阿彈的這種不做作、坦率、表里如一的處事方法,以及因此而打動人心的本事,是在成長過程中養成的呢,還是與生俱來的素質呢?賢人覺得不可思議,阿彈這種無憂無慮是怎么做到的?雖然不能說是因為父母的坦白,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自己和阿彈的差別到底在哪里?
樹里分別去見了父親和母親。父親說:“我們真的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但是,只有一件事沒有談到,那就是孩子出生了該怎么辦……家庭也好,父親也好,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無法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要決定‘做’才能形成,而我還沒決定。給你取名字的時候,我還誤以為自己是你的父親呢。”見到父親后,說實話,樹里對父親感到很失望。他知道父親沒有說謊,并盡他最大的誠意來面對她了。但她曾經稱為爸爸的人不是父親,是“放棄”了當父親的人。母親說:“即使生下來的不是你,我也不會后悔,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和你爸爸在診所里看到各種各樣的信息時,就想選名校畢業……我深信這是對即將出生的孩子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可是,我們太天真了。能給即將出生的孩子幸福保證的,并不是這樣的‘條件’。因為年輕,我們沒有意識到,沒想到這件事后來會把我們逼上絕路……重要的不是那個,而是只有在孩子出生之后才能給予她的。因為那個孩子從一出生就和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你不知道在她的世界里什么是幸福的吧。”對母親的失望是即使托付給不認識的第三者,也想要孩子;即使與親生父母斷絕關系,也不改變決心;明知會傷害丈夫,卻優先考慮“為了孩子”。她覺得母親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她覺得自己做不到。因此,樹里經常自問:來到這個世界真好嗎?如果沒有我,爸爸媽媽還會漸行漸遠,甚至離婚嗎?因為無法找到自己生物學上的意義,所以連自己的存在是否有意義也會懷疑。
露營中止的那年的十一月,賢人的父母離婚了。第二年,“準爸爸”就搬到了公寓,而且當時母親已經懷上了妹妹。母親再婚時,賢人拒絕改姓,看似可以解釋為是出于對父親的愛和對母親擅自離婚的憤怒。其實,拒不改姓的原因是賢人害怕改姓后就永遠不能再見面了,就像跟參加露營的孩子們那樣。他覺得自己在那個家里是外人,就像混進別人家,感覺自己像個透明人一樣。從初二開始,他就沒斷過女朋友,十八歲之前一直在給別人添麻煩。讓兩個女孩子懷孕,還去看了心理醫生。接受心理治療時,賢人從母親那里知道了真相,他終于明白了自己為什么有時會有被空白吞噬的感覺。如果早一點兒告訴自己的話,也許會更好地處理自己的存在方式,不,應該說對待吞噬自己的空白的方式。他雖然知道“如果”沒有任何意義,但還是會這么想。“像這樣知道真相后痛苦不堪的人也有很多,但是為什么我從母親那里聽到真相后卻感覺一下子輕松了,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呢?大腦空無一片的感覺,不負責任的言行,每天事不關己的態度……但是,現在只是找到了過往這些表現的根源。我還是不認識自己的父親,也許一輩子都不知道,在這一點上我和一般人不同,所以我才覺得自己成了這樣也是毫無辦法的事,在一味地逃避。”賢人說自己從小就給人一種“輕浮”的感覺。在聽了母親的傾訴后,他的“輕浮”行為終于停止了,也不再隨便和女孩子扯上關系了。所以,當紀子告訴他她一個人帶孩子回了娘家時,他也沒能及時給予回應和關心。他現在和戀人過著“非常普通”的生活,但心里總有些愧疚:像我這樣的家伙,難道要裝模作樣地活在世上嗎?
了解真相,對孩子們來說,只是邁出的第一步。擺脫負疚感,確認自己不是一個人,覺得來到這個世界真好是更重要的課題。
紀子從小就害怕很多事情。她不想離開家,也不需要朋友,在幼兒園時緊張得連哭都不敢,一天就那樣等著父母來接自己。那是一個黑暗狹窄的地方。紀子覺得是從三歲的某一天,以及后來的幾個夏天,是賢人伸出手把自己從那里帶了出來,到了那個有陽光、鮮花、笑聲、香味和朋友的廣闊天地。從她們認識開始,紀子就經常在心里和賢人說話,每天像寫日記一樣給賢人寫信。紀子說雖然有父母,也有朋友,過著平凡而幸福的日子,但總覺得害怕,總是畏首畏尾。面對丈夫的冷暴力,她心里很失落,失去了思索能力,把自己封閉起來了。直到再次見到賢人,見到一起去露營的孩子們,她才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這種感覺就連懷孕時都未曾有過。于是她決然帶著孩子離開了自私自負的丈夫,雖然一無所有,但她打算重新找工作,獲得孩子的撫養權。她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因為自己不是一個人。
波留見到了曾經的捐精者,了解到他當年這么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報復社會。那個混蛋想在全世界散播自己的精子,想讓自己的子孫遍布全國,甚至海外。知道后,她深受打擊,因此決定放棄尋找。
面對非常想了解親生父親的真相的紗有美和雄一郎,波留理解他們迫切的心情。自己也一樣,生病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也不僅如此,她是想以更加不同的理由去了解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這個人。波留拼命思考如何保護他倆不受傷害,甚至都沒有注意到手里的香煙燒盡燙到指頭。于是她杜撰了下面的話說給他倆聽。
“他一直祈禱能生個好孩子,祈禱那個孩子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對他來說,捐獻精子就像向災區捐款一樣,有人遇到困難,恰好自己能提供,那就不能坐視不管了,只能盡自己所能吧。當時他就是這種心情。”“那個人覺得我幾乎不可能是他的孩子。雖然不是,但他還是很高興,很高興見到我。說我身體健康,已經長成這么優秀的大人,能接受自己的出身,不管什么理由,能來見他,他真的很高興。因為沒有一起生活過,所以我們并不是一家人,他也不是我的父親,但是,他會一直在遠方祈禱我們幸福,今后也一樣。”
為了讓大家實現身份認同,光太郎也用盡了所有的手段四處奔走,想要把下面的話語傳達給只是擦肩相識的孩子們。
“提供精子不等于做父親……很難想象沒見過的人的面孔和生活。突然出現的話,一定會嚇一跳。不是想見還是不想見的問題,不是如何出生的問題,而是如何活著的問題。說到底,不就是這個問題嗎?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到現在的,怎么生活的,那不就失去了自我嗎?”
樹里說:“你不覺得開始一件事很了不起嗎?當開始做某件事的時候,就覺得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如果我們的父母不想要孩子,不決定要孩子的話,我們就不會出現在這里了。如果阿彈你父母不想聚集在這里的話,我們根本就不會認識。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人在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決定后,接著實施,然后才開始改變的。總覺得非常了不起啊。”
這也和光太郎的比喻如出一轍。他說:“蘿卜泥和烤雞肉串一起吃,還是單獨當小菜吃,兩者有著微妙的不同,但都沒錯。也就是說,這個蘿卜泥有兩種命運。如果沒有你,蘿卜泥就沒有另一種命運。你看到的,接觸到的,品嘗到的,都和別人不一樣。”
開始做某件事后,帶來的不是結果,而是世界。如果沒有你,就沒有你看到的世界。比起如何出生,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如何活著,珍惜眼前所有,走屬于自己的人生。
就像波留在致辭中說的那樣:“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毫無畏懼地走出家門,并不是因為我們確信不會迷路,也不是因為我們確信不會發生令人困擾的事情,而是因為我們相信一定會遇到美好的人和事,在遇到困難時一定會有人幫助。只有這樣想,今天和明天才能走下去,夸張地說,才能活下去……如果一直待在那里,就會一直懼怕明天,懼怕世界。就不會有機會去見那些讓你不再害怕的美好事物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七個孩子都實現了身份認同,也發生了很大改變。雄一郎搬出了自己的公寓,開始了新生活。紗有美第一次覺得活在這個世界真好。紀子努力找工作,爭取孩子的撫養權。樹里打算再次嘗試不孕治療。他們對“生”和“活”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今后大家也會一直平等地擁有這片花園,作為隨時可以回去的秘密場所。
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佳作,譯文初稿完成時正值暑假,身為老師的我們的親戚朋友和孩子們有幸成為第一批讀者,大家感觸不盡相同,可謂受益良多。少年們對夏日樂園產生了共鳴,順便說一下,小學剛剛畢業的小外甥黃彥皓一口氣讀了兩三遍,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見,在此深表感謝。青年人為孩子們的努力重逢而感動,中年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行為和理念,老年人因光太郎、結城等人為了孩子們的成長而默默付出感到欣慰。
角田光代真實地寫出了非配偶間人工授精面臨的復雜問題,同時將七個孩子的溫柔、友情、困惑等感受融入日常生活,化為這部杰出的作品。這是一部告訴我們“生”和“活”這一深刻哲學道理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反映家庭教育的良作,更是一部關于家庭教育和自我成長完美結合的力作,值得推薦給面對出生、成長和育兒困惑的廣大讀者,相信大家一定會產生共鳴,收益頗多。
孫淑華 鄭愛軍
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