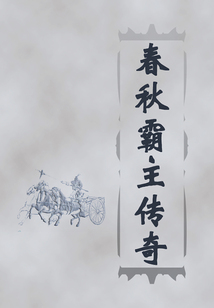
春秋霸主傳奇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春秋強君鄭莊公
鄭莊公是鄭武公之子,今河南鄭州市新鄭人,生于公元前757年。
鄭莊公是春秋初年的鄭國的有為國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他曾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亂,繼武公之后,為周平王的卿士。鄭莊公在位四十三年,將鄭國從弱小經(jīng)營得非常強大。
鄭莊公英雄一世,但也有兩個重要的政治失誤。一個重要失誤是生前沒有對太子忽(即鄭昭公)之位做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鄭國立即陷入無止休的奪權之爭。另一重要失誤是重用高渠彌,這為鄭國留下了嚴重后患。這兩個失誤,導致鄭莊公死后,鄭國迅速由盛轉衰。
第一節(jié) 鄭國交上了好運
鄭國的出現(xiàn)與壯大,離不開一連串的幸運事件。第一個幸運,就要追溯到鄭莊公的曾祖父周厲王的不幸。
周厲王是西周末期的一位國王,他極其專斷,鎮(zhèn)壓言論自由,導致百姓見面后連招呼都不敢打,生怕被誤認為議論朝政而喪命。壓迫的反作用力最終爆發(fā),公元前841年,鎬京的居民掀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暴動,周厲王被迫逃離王宮,越過黃河,躲到周朝邊境的彘(今山西霍縣東北)。14年后的公元前828年,周厲王在彘凄涼地去世。
周厲王逃走后,朝廷沒有國王,國家陷入混亂。公元前841年,太子姬靜登基,即周宣王。周宣王勵精圖治,為了擴大王室勢力,從家族中選拔能助其中興的人才,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姬友幸運地被看中了。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將姬友封到槿林(今陜西華縣東)為鄭伯,建立了鄭國。這是西周王朝最后一個分封的諸侯國。
姬友史稱鄭桓公,受封時已33歲。與其他諸侯相比,鄭桓公的封地面積較小,但由于周王室當時已經(jīng)非常衰微,能在有限的國土中獲得一塊封地,已是極大的幸運。雖然封地小,但總歸是個國王,有了做大做強的可能。
鄭桓公為人寬厚仁慈,對百姓關懷備至,因此深受民眾愛戴。消息傳到京都,周宣王已死,其子周幽王在位,將鄭桓公調入京都,封為司徒,協(xié)助處理國家事務。鄭桓公在新職位上盡心盡力,贏得了更多人的擁護。然而,周幽王因寵幸褒姒疏遠大臣,天下諸侯蠢蠢欲動,國家局勢岌岌可危。
鄭桓公預見到王室將面臨變故,便向周太史伯請教如何保全家族。太史伯分析后認為,成周(今洛陽)四方侯國都不適合鄭國,唯有洛邑以東、黃河和濟水交匯以南的地方最為安全。于是,鄭桓公請求舉族東遷,周幽王答應了。果然,不久后犬戎叛亂,周幽王被殺,西周滅亡。鄭桓公為保護幽王而戰(zhàn)死,雖然不幸,但也因此被譽為忠臣,給后代留下了光輝的名聲。
鄭桓公死后,其子掘突即位,史稱鄭武公。鄭武公在周幽王死后,與秦襄公、衛(wèi)武公等一起擁立太子宜臼繼位,并護駕東遷洛陽,史稱平王東遷。鄭武公趁機兼并了東虢和鄶?shù)兀w都于鄶,改名為新鄭,以滎陽為京城,在險要之地設關制卡,逐漸強大起來。鄭武公與衛(wèi)武公一同在朝中擔任卿士,衛(wèi)武公死后,鄭武公掌握了更多權力,專心建設鄭國,使其日益強盛。
這正是鄭國的幸運之處。鄭桓公和鄭武公都善于把握時機,而周幽王和周平王則是平庸之王,使得鄭國得以迅速壯大,為鄭莊公日后的稱霸中原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談論一個人的成功時,我們常提到“幸運”這個詞。確實,成功離不開汗水,但汗水不一定能換來成功。汗水需要一劑叫“幸運”的催化劑,才能產(chǎn)生成功。有些人認為幸運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但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鄭桓公被周宣王封為鄭伯,若非他才華出眾,怎能輪到他?鄭氏家族的東遷避難,若非鄭桓公有遠見,又怎能實現(xiàn)?因此,幸運與不幸往往是性格和能力的體現(xiàn)。
想成為幸運的人,首先要錘煉自己,擁有更好的性格和更強的本事。通過鄭桓公和鄭武公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需要明智的領導者,還需要他們能抓住機遇,順應時勢,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立于不敗之地。
在這些幸運與不幸交織的歷史事件中,鄭桓公和鄭武公展現(xiàn)了他們非凡的治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們的成功,正是鄭國崛起的關鍵所在。
第二節(jié) 史上最偏心的母親
鄭莊公名叫寤生,父親是鄭武公,母親武姜。武姜是申國人,鄭武公在執(zhí)政的第十年娶了申侯的女兒武姜為妻。武姜生下鄭莊公時,本應順利生產(chǎn),但莊公卻不按常規(guī),先伸出一條腿,另一條腿橫著卡住了,令初為人母的武姜疼痛難忍,幾乎要了她的命。
經(jīng)過一番折騰,鄭莊公終于出生,但武姜對這個差點要了她命的兒子心生不滿,給他起名“寤生”,意為倒著出生的家伙。相比之下,武姜的第二個兒子叔段順利出生,長大后濃眉大眼、唇紅齒白,是個標準的小帥哥,深受母親寵愛。武姜偏心地希望立叔段為繼承人,屢次慫恿鄭武公:“立老二當繼承人吧,老二更有能力!”
鄭武公對此不予理會。武姜很不高興,但也無計可施,只能拿寤生出氣,常常罵打他。然而,這個不受待見的寤生在母親的冷眼中頑強長大。到他十五歲時,鄭武公病重在床,眼看就要去世。武姜再次提出立叔段為繼承人的請求,稱贊叔段一表人才、力大善射、武藝超群。鄭武公聽后勃然大怒,召集大臣們宣布:“自古以來,長幼有序,不能亂立,更何況寤生無過,豈可廢長立幼?我的繼承人是寤生,不可更改。”
大臣們在繼承人問題上始終保持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紛紛表示:“主公英明,臣等一切聽主公的!”于是,鄭武公交代了后事,不久便薨逝(“公”死叫薨,“王”死叫崩,士大夫死叫卒,老百姓死就死了)。
鄭武公薨逝后,鄭莊公順利繼位,并代父作為周朝的卿士輔佐朝政。武姜見大兒子莊公活得滋潤,又找到他:“你繼承了你父親的位子,享有數(shù)百里的土地,可卻讓同胞兄弟只有那么一點地方,你于心何忍?”鄭武公在世時,被武姜纏得無奈,把小小的共城賜給了叔段,稱為共叔。
鄭莊公答道:“母親認為該如何處置呢?”
“讓他去制邑吧。”
鄭莊公說道:“制邑以險要聞名,先父有遺命,不準分封,除此之外的地方我都可以答應您。”制邑即虎牢關,是戰(zhàn)略要地,鄭莊公深知其重要性,不能輕易分封。
武姜接著說:“那就去京吧。”京位于今河南滎陽東南。
鄭莊公心想:母親真會挑地方,京城可是鄭國最大的城市,比都城新鄭還要大得多。他不愿意答應,但又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只好保持沉默。武姜見狀,臉色一沉道:“你如果不同意,那就把你的弟弟逐到別國,讓他受盡白眼,過著勉強糊口的日子吧!”
鄭莊公孝順,一見母親生氣,急忙說:“我同意,我同意。”于是,叔段便高高興興地赴任京城。
古語有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意為禍福相依,可以互相轉化。寤生的出生不幸,但最終幸運地活了下來。雖然出生有難產(chǎn)經(jīng)歷,不幸遭母親嫌棄,但由于父親堅持原則,他幸運地繼承了王位。而弟弟叔段在母親寵愛下,原本不屬于他的王位并未失去,還在哥哥繼位后得到了一座大城作為封地,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幸運兒。
然而,叔段的幸運中也隱藏著不幸。母親的偏心讓叔段心生不滿,逐漸滋生了野心。他覺得自己才是應該繼承王位的人,對哥哥的統(tǒng)治越來越不滿。叔段在京城安穩(wěn)了一段時間后,開始不滿足于現(xiàn)狀,他利用母親的偏愛和支持,暗中積蓄力量,圖謀更多的權力。
武姜對叔段的野心視而不見,甚至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相信叔段比寤生更有能力帶領鄭國走向輝煌。叔段利用這一點,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甚至開始在京城修筑城墻,建立自己的小朝廷,逐漸與鄭莊公分庭抗禮。
鄭莊公雖然心知肚明,但一直忍耐。他深知,一旦動手,將會引發(fā)一場兄弟相殘的血戰(zhàn)。為了國家的穩(wěn)定,他選擇了暫時忍耐,希望通過其他方式解決這一矛盾。然而,叔段的野心日益膨脹,最終走上了反叛之路。
歷史總是充滿了戲劇性。叔段的反叛,不僅讓鄭莊公陷入了困境,也使得武姜在內心深處倍感痛苦。她一直希望兩個兒子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但她的偏心和溺愛最終導致了兄弟之間的仇恨。鄭莊公被迫出兵鎮(zhèn)壓,叔段被徹底擊敗,這場兄弟之爭以叔段的失敗告終。
武姜的偏心不僅影響了她的兩個兒子,也對鄭國的未來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家族內部的矛盾與斗爭,對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偏心和溺愛,最終導致了兄弟相殘的悲劇。
鄭莊公在平定叔段的叛亂后,逐漸穩(wěn)固了自己的統(tǒng)治。他明白,要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以公正無私的態(tài)度治理國家,避免因偏心而引發(fā)內部紛爭。通過這一事件,他吸取了寶貴的教訓,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治國策略。
幸運和不幸往往相互交織,正是這些經(jīng)歷,塑造了鄭莊公的堅韌和智慧。他不僅成功地應對了內部的挑戰(zhàn),還在外部的對抗中展現(xiàn)了卓越的領導才能,為鄭國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過他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具備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善于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不斷完善自己的治國方略。
第三節(jié) 鄭莊公智敗共叔段
叔段到了自己的封地京城,心情十分愉快。對于一般人來說,擁有京這個大城,已足以心滿意足,享受榮華富貴。然而,叔段并不是一個滿足現(xiàn)狀的人,他喜歡折騰,尋求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首先,叔段一到任就修筑了超規(guī)格的城墻。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非國都的城邑,城墻的規(guī)模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國都的城墻為三百雉(約兩千一百米),而叔段的京城城墻遠遠超出了百雉(約七百米)的限制,幾乎相當于一所重點大學的面積。這一舉動立即引起了朝中大臣祭仲的憂慮。
祭仲對鄭莊公說:“草長得太高會不好收拾,何況是被您母親寵愛的弟弟?不趕緊采取措施,遲早會出大事。”鄭莊公淡然一笑:“多行不義必自斃,等著瞧吧!”
不久后,叔段果然更加放肆。他命令郊區(qū)的西鄙、北鄙之地的邑宰把土地和稅收歸他所有,并進行軍事演練,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叔段甚至占領了鄢城和廩延,這一行為引起了鄭莊公的注意。雖然鄭莊公聽了報告只是微笑不語,但朝中有位大臣公子呂激動地建議:“叔段可以誅殺了!”
鄭莊公卻說:“叔段是我母親的愛子,又是我的親弟,我寧愿失去土地,也不愿傷了兄弟之情。”公子呂反駁道:“如果您不盡快控制住他,恐怕國將不國!”鄭莊公沉思后表示會認真考慮。
散朝后,公子呂對正卿祭仲說:“主公忽略了國家大計,我對此十分憂慮。”他再次見鄭莊公,指出叔段和武姜可能內外勾結,危及鄭國。鄭莊公解釋說:“我主要是為了母親才一再遷就。”公子呂進一步勸道:“周公曾誅殺管蔡,‘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望主公三思。”
鄭莊公終于被說服,但他知道沒有確鑿的證據(jù),貿然動手會被母親和外界責難。于是,他決定以計策引出叔段的叛亂之心。公子呂獻計:“主公可聲稱去京都,叔段必以為國內空虛,乘機興兵犯鄭。臣預先埋伏在京城,待其兵到時夾擊,必能成功。”
鄭莊公同意此計,并秘密籌備。第二天早朝,他宣布去周輔政,由祭仲代管國內事務。武姜得知后大喜,急忙寫信約叔段在五月中旬襲擊鄭都。鄭莊公截獲信件,改動后送給叔段,并約定以五月初五為期,立白旗為接應暗號。鄭莊公看到叔段的回信,心中有數(shù),便出發(fā)前往廩延。
叔段接到信后欣喜若狂,立即行動。他假借奉命輔政之名,帶領滎陽和二鄙的軍士開往鄭都。公子呂派遣兵車四十乘,扮作商賈潛入京城。叔段的大軍出城后,城中放起了火光,公子呂帶兵攻入,不費吹灰之力便占領京城,并公布了叔段的罪行,百姓紛紛譴責叔段。
叔段聞訊大驚,急忙回軍,卻發(fā)現(xiàn)士兵已大半離去。原來,城中的家書使士兵們明白了真相,紛紛棄叔段而去。叔段見勢已去,逃到廩延,但鄭莊公和公子呂兩路大軍迅速攻破城門。叔段自知大勢已去,仰天長嘆:“母親誤我,我無顏見兄長!”遂拔劍自刎。
鄭莊公的計策得逞,叔段的反叛被平息。這一事件顯示了鄭莊公的智慧和深謀遠慮,也揭示了叔段過于輕率和缺乏遠見的致命弱點。叔段的悲劇告訴我們,做事需要有眼光和心機,謀定而后動,否則,幸運很快會耗盡,留下的只有不幸和悔恨。
這場兄弟相爭,既是權力斗爭的縮影,也是家族矛盾的極端表現(xiàn)。鄭莊公通過這次事件,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統(tǒng)治,也讓我們看到了歷史中權謀與親情的復雜交織。叔段的命運,讓人感嘆不已,既是幸運兒的悲哀,也是權力游戲中的一顆犧牲品。
第四節(jié) 鄭莊公的誓言與食言
在整理叔段遺物時,武姜的書信自然落入鄭莊公之手。他教人將這封書信與叔段的回信一并送給祭仲,并要求祭仲呈與母親武姜閱后,將母親送往潁地冷宮軟禁。鄭莊公對母親的行為極為憤怒,立下毒誓與母親武姜“不及黃泉無相見”,并讓祭仲將這個誓言傳達給母親。
武姜見了這兩封書信,羞愧無比,感到無顏見鄭莊公,于是離宮去了潁地。
然而,鄭莊公發(fā)過毒誓后,有一天卻后悔了。畢竟是自己的親生母親,血濃于水。鄭莊公突然想見自己的母親,這個念頭一旦冒出來,就在他的心里生根發(fā)芽,且日益生長。他無法忍受對母親的思念之苦,卻又不能違背誓言——這可怎么辦呢?
幸好,有個叫潁考叔的人幫鄭莊公想了一個辦法:“掘地及泉,隧而相見”。意思是挖掘一個很深的地下隧道,深至泉水奔涌,然后母子二人在那里相見,不就是黃泉相見了嗎?
這個辦法讓鄭莊公大喜過望。他立即派出數(shù)百名壯士在城外掘地,直至十余丈深方見泉水涌出。然后,鄭莊公和憔悴的母親武姜就在這個隧道里相會。不用說,母子相見,自然是重歸于好。他們各自作了一首“到此一游”的詩,兒子云:“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母親曰:“大隧之中,其樂也泄泄。”——后世的成語“融融泄泄”便誕生在這個黑暗的地下通道里。可見,黑暗與潮濕,也能帶來幸福、快樂與滿足。
因為一句話,鄭莊公不得不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掘地及泉”來彌補。把話說得太滿太絕的代價真是太大了。好在鄭莊公高居廟堂,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否則他真的除了食言,別無他法見到母親。
前事之師,后世之鑒。可惜時至今日,把話說得絕對的現(xiàn)象仍屢見不絕。諸如“這樣若成功,我就不姓X”或“除非……否則我絕不……”之類的句式,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xiàn)。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們無法預料其發(fā)展態(tài)勢,有的甚至不了解其發(fā)生背景,因此切不可輕易下斷言,不留余地,使自己無回旋空間。
話莫說絕,要留余地。言不至于極端,行方不會被逼絕境。《菜根譚》中有云:“天道忌盈,業(yè)不求滿。”意思是凡事要留有余地,如此則“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yè)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招外憂”。
在處理人際關系時也是如此。無論是家人、朋友,還是同事,我們都要謹慎言行,避免過于極端的表達。鄭莊公和武姜的故事,正是我們最好的教訓。鄭莊公雖然用聰明才智化解了誓言帶來的困境,但也讓我們看到,他在憤怒時立下的誓言,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麻煩和痛苦。
第五節(jié) 鄭國打敗衛(wèi)國
鄭莊公正沉浸在與母親團聚的幸福中,一個壞消息傳來:北邊的衛(wèi)國發(fā)生了宮廷政變。衛(wèi)國在鄭國北面一百公里,衛(wèi)國公子中的弟弟州吁驕奢好戰(zhàn),趁機殺了大哥衛(wèi)桓公,自立為君。
按說,鄰國的宮廷喋血與鄭國關系不大。但鄭莊公的眼光深遠,當衛(wèi)國使者送來訃告,鄭莊公得知公子州吁弒兄自立時,不禁嘆道:“我鄭國也將有兵事了!”群臣驚問原因,鄭莊公解釋:“州吁嗜好爭戰(zhàn),如今奪位,一定會窮兵黷武。鄭、衛(wèi)兩國有隔閡,衛(wèi)國若試鋒芒,必選我鄭國。我們要做好準備。”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衛(wèi)國公子州吁的背景。州吁的父親衛(wèi)莊公有個妃子戴媯,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完,一個叫晉。莊姜無子,但視戴媯之子如己出,鼓動莊公立完為太子。晚年,衛(wèi)莊公又納一妃,生下州吁。州吁頑皮暴烈,喜武不喜文,衛(wèi)莊公溺愛縱容。
大夫石碏曾勸衛(wèi)莊公:“若真愛州吁,應當好好教育他。若不立他為太子,就應抑制他,不讓他妄自稱大,否則會引發(fā)禍端。”然而,衛(wèi)莊公不聽勸告,石碏自己也有個問題兒子石厚,與州吁臭味相投,常在一起欺男霸女。
衛(wèi)莊公薨后,太子完繼位為桓公。桓公生性懦弱,石碏辭官還鄉(xiāng)。桓公對州吁肆無忌憚,不加管束。周平王崩,桓公要去吊唁賀新王。石厚對州吁說:“機會來了!明天設宴餞行,在西門埋伏五百刀斧手,酒至三巡,殺了他們,你就可以當王了!”
州吁大喜,命石厚帶領五百壯士埋伏在西門外。州吁親自駕車,迎接桓公到行館,擺好筵席。桓公毫無防備,酒至三巡,州吁一刀刺殺桓公,桓公至死不知是誰所為。桓公的臣子因畏懼州吁和石厚,只得投降。州吁謊稱桓公暴病身亡,回國篡位,并拜石厚為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至邢國避難。
州吁雖篡位,但百姓不認可,議論紛紛。州吁召來石厚商議,石厚建議:“找鄰國打仗,讓百姓知道我們的厲害。”州吁問:“打誰?”石厚答:“鄭國。鄭莊公滅了京城的叔段,叔段之子公孫滑在我們這避難,鄭莊公曾討伐我們,這是恥辱。現(xiàn)在打鄭國,名正言順。”
州吁擔心:“我們能打贏鄭國嗎?鄭莊公是個狠角色。”石厚說:“我們可以聯(lián)合宋、魯?shù)葒餐ム崱!敝萦跬猓彩骨蟊蓪庱从握f宋國。寧翊見宋殤公,說:“鄭國收留公子馮,圖謀伐宋。若聯(lián)合伐鄭,可除心腹之患。”宋殤公同意起兵,魯國公子翚受賄也出兵。陳、蔡兩國如期而至,組成五國聯(lián)軍,圍攻鄭國。
五國大軍如鐵桶般包圍鄭國。鄭莊公果然未雨綢繆,早已做好迎戰(zhàn)準備。這場大戰(zhàn)在即,鄭莊公將如何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大敵?讓我們拭目以待。
鄭國上下驚恐不安,但鄭莊公卻沉穩(wěn)應對。州吁弒兄自立時,鄭莊公就已預見到這場兵禍,早有準備。
鄭莊公對群臣說:“州吁弒君篡位,不得民心,因此借舊怨聯(lián)合四國來攻打我們,只是為了立威恐嚇百姓。魯國公子翚受賄發(fā)兵,不過是敷衍。陳、蔡與我們無仇,不必死戰(zhàn)。只有宋國忌憚公子馮,有意助戰(zhàn)。若送公子馮去長葛,宋兵必然轉移。再令公子呂帶兵五百出東門單挑衛(wèi)國,詐敗而走,給州吁一個勝利的名分,讓他滿足即可。”
群臣聽了,心服口服。鄭莊公的高瞻遠矚和未雨綢繆,使得他在眾人驚恐時,仍能看出機會。他立即派大夫瑕叔盈率兵護送公子馮去長葛,并遣使告知宋殤公:“公子馮已去長葛服罪。”宋殤公果然轉兵襲長葛。
蔡、陳、魯三國見宋兵轉移,有了班師之意。鄭國公子呂出東門挑戰(zhàn)衛(wèi)國,三國便做壁上觀。石厚率兵迎戰(zhàn)公子呂,未及數(shù)合,公子呂詐敗而逃。石厚追至東門,得勝而歸。
州吁問:“為何匆匆班師?”石厚說:“鄭兵強橫,莊公為王朝卿士,今勝一仗足以立威。主公剛上位,國事未定,久留恐生變。”州吁同意,魯、陳、蔡三國也賀勝班師。從出兵到解圍,不過五天。石厚令三軍齊唱凱歌,擁州吁回國。
鄭莊公早已預料到這一切,雖然鄭國損失不大,但無端被扁一頓,心中窩火。鄭莊公加緊操練兵士,準備報復。
衛(wèi)國內部也發(fā)生了變化。州吁凱旋后,百姓仍不服,在街頭唱道:“一雄斃,一雄興。歌舞變刀兵,何時見太平?恨無人兮訴洛京!”州吁問石厚:“百姓不服,該怎么辦?”石厚說:“請我父石碏,他位居上卿,百姓敬重他。”
州吁派人請石碏,石碏托病不出山。石厚親自請父,石碏建議:“應稟明周王室,請陳侯幫忙遞話。”州吁同意,由石厚護駕奔向陳國。
石碏寫血書給陳國大夫子咸,請求誅殺州吁和石厚。子咸和陳桓公認為衛(wèi)國的罪人也是陳國的罪人,州吁和石厚一入陳國就被捉了。石碏帶百官議罪,眾人認為州吁該殺,石厚是從犯可免死。石碏卻堅持大義滅親,命右宰丑和家臣儒羊肩一人殺一個。
鄭國派兵前來報復,燕衛(wèi)聯(lián)軍搶先攻入鄭國。鄭國采取避實擊虛策略,重點打擊燕國,最終擊潰燕軍,衛(wèi)國軍隊不敢對抗,逃回衛(wèi)國。
鄭莊公見衛(wèi)國服軟,轉而攻打宋國,攻破宋都外城,搶了大量財物。次年,鄭莊公準備報復陳國,陳國請和,結盟并聯(lián)姻,脫離宋、衛(wèi)同盟。
鄭莊公擊敗了衛(wèi)、宋、陳三國,東門之恥盡雪。翌年,在齊僖公調解下,鄭、宋、衛(wèi)三國重歸于好,盟于瓦屋。但不久,宋國挑釁,鄭莊公奉周平王旨意,聯(lián)合齊魯伐宋,攻下郜城、防城,將城邑送給魯國,魯國大喜。
宋國不滿,聯(lián)合衛(wèi)、蔡反攻鄭國,圍攻戴國。鄭莊公設計讓公子呂先救戴,自己混在兵卒中,奪取戴城,三國聯(lián)軍被擊敗。右宰丑陣亡,孔父嘉逃命,三國殘兵敗將多成俘虜。
鄭莊公展示了卓越的戰(zhàn)略眼光和軍事才能,成功化解內外危機,鞏固了鄭國的地位。
第六節(jié) 箭射周天子
鄭國在周平王東遷和組建東周政權上立下大功,因此鄭莊公和他的父親鄭武公都曾擔任周王室的卿士,掌握權力。然而,到了鄭莊公時期,兩者不斷發(fā)生沖突,主要因為鄭莊公權力過大,野心勃勃。
周平王為了限制鄭莊公的權力,起用虢公全權處理政務,但虢公不敢接受,回到本國。鄭莊公雖身在鄭國,但朝中事務都能及時傳達給他。得知周平王將政務分給虢公后,鄭莊公非常不滿,立即前往周都,當面質問平王,使平王難堪。為了平息鄭莊公的不滿,周平王將太子狐送到鄭國作為人質,而鄭莊公則將太子忽送到周王室。這種互為人質的做法在諸侯國間普遍,但在周王室與諸侯國之間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表明周王室已失去威嚴。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駕崩。鄭伯與周公黑肩共攝朝政,讓世子忽回鄭,迎太子狐繼位。太子狐因父王之死悲痛過度,不久也去世,兒子林繼位為周桓王。
周桓王因父親在鄭作人質而早逝,懷恨在心,削減鄭莊公的權力,將權力交給虢公。鄭莊公問計于大夫祭仲,祭仲建議以牙還牙,向溫大夫和洛大夫乞助,如周王遣使責備,就有理由對抗;如無表現(xiàn),再上朝不遲。
于是,鄭國給周桓王送了“厚禮”。祭仲率兵到溫界,要求借粟四千斗,溫大夫不肯,祭仲便帶士卒搶割田中麥稻。祭仲又在成周郊外偷割早稻,帶回鄭國。周桓王雖氣憤,但奈何不了鄭國。
周桓王八年,周王室與鄭國互換土地,周得鄭國四塊田地,鄭國卻得不到交換土地,心存恨意。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罷免鄭莊公的卿士職位,鄭莊公不再朝拜周桓王,兩國關系降至冰點。周桓王聯(lián)合衛(wèi)、蔡、陳三國討伐鄭國。周公黑肩勸阻無果,周桓王決定出兵。
按周朝軍制,天子擁有六軍,諸侯大國有三軍,小國有一兩軍。東遷后,周朝僅能動員三軍,每軍一萬余人。周桓王請衛(wèi)、陳、蔡三國助戰(zhàn)。公元前707年,周天子率多國部隊直抵鄭國長葛,鄭莊公嚴陣以待。這是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第一次對抗。
多國部隊中,中央軍實力強,兩翼衛(wèi)、陳、蔡軍隊較弱,鄭國公子突建議集中主力攻擊兩翼。鄭莊公采納,布置“魚麗陣”,戰(zhàn)車與步兵協(xié)同作戰(zhàn)。
鄭軍擊鼓進軍,從兩翼率先發(fā)起攻擊,兩翼蔡衛(wèi)聯(lián)軍和陳國聯(lián)軍很快陣腳大亂,紛紛逃竄。周桓王丟掉兩翼,只剩中央軍,鄭軍圍攻中央軍,周軍大敗。周桓王沉著應戰(zhàn),揮舞銅鉞鼓舞士氣,但被鄭將祝聃射傷。周桓王忍痛指揮撤退。
祝聃請求追擊,鄭莊公搖頭:“君子不逼人太甚,尤其是周天子。”當晚,鄭莊公派祭仲探望周桓王,以示禮儀。
鄭莊公戰(zhàn)后的善后工作做得很好,而周桓王既無由師出,又不自量力。此次戰(zhàn)役宣告了周桓王外強中干。此后,天子威望盡失,諸侯之間開始爭權,周天子不再受重視。
這場大戰(zhàn)中,鄭莊公展示了卓越的戰(zhàn)略眼光和軍事才能,成功化解內外危機,鞏固了鄭國的地位。而周桓王的失敗,則標志著周王室權威的徹底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