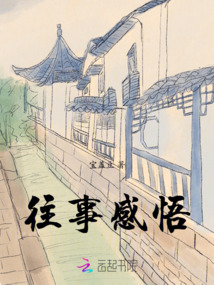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大河
我家門前有一條大河,但她又不是大河,在我小時候,她很大很大,現在的我看她,覺得很小很小。
她不像長江黃河那樣眾所周知,但她在我來到世界之前,甚至于我祖祖輩輩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她就存在了。
所以,它又是我的“母親河”。
成年后的我曾慢悠悠踱步去追尋過她的源頭,發現她發源自群山之巔,是從我們那里最高的山峰孕育而出。她由涓涓細流慢慢發展,彎曲婉轉流到我家門前的時候,已是一條四米寬三米深的小河了。
等我再長大一點的時候,因為求學原因沿著大河去到了市里,才知道大河已經“海納百河”,成了有十來米寬闊江面的平靜洶涌的“母親河”了。
再后來,我在地圖上拿著放大鏡看著上面的水網分布找尋她的終點,才發現她早已奔騰過萬江,由珠江口入海,匯入廣闊天地,去闖蕩更大的世界。
對大河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每周放的那半天假,在我難過、郁悶、孤獨和懷念家的時候,最喜歡的站在江邊,感受著江風吹拂,仿佛感受到了我家的感覺在對我低聲細語、撫摸留戀。
耳邊烈烈的江風呼嘯而過,大河似在耐心勸告我:孩子啊,不要往回看,眼睛長在前面,抬腳是要向前的,和我一起朝前看,奔涌向前!
我感受到大河的勸告,站著江邊憑欄眺望,或坐在石椅子上靜靜感受,看著它的平靜、無波、以及靜默的負重前行。
大江似她像她又不是她,我努力睜眼去窺探它身上所攜帶的關于我家鄉大河的最初模樣。
但我被奔騰的迷霧遮住了眼,什么都看不到。我知道,她身上有我家大河的樣子,但是我也知道,她不是我家那條大河。
對大河最初的記憶,來自于母親。
小孩子的腦袋天馬行空,往往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中華民族是個勤學好思的民族,這不,打小就顯現出來。
十個小孩里有五個小孩應該都問過自己家人,自己從哪來吧?
各地家長如何糊弄孩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聽到的回答就是:那年發大水,你在一個黑色木盆里,被棉被包裹著,在河上漂著,我拿一根長長的竹子,打撈上來,就有了你。
那會兒的我目不識丁,對數字長度絲毫沒有概念吧。所以往往說這的時候,媽媽還得把手臂用力打開,比劃著那根“撈”我的竹子有多長。
但是我看著,我媽這不像比劃竹子,她肉肉的體態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像她養的那些護崽的老母雞,在做準備戰斗姿態。
看我對長度沒有概念,媽媽神色無奈的看著我,深深呼了一口氣:“反正就是我拿根竹子,辛辛苦苦把你從河里撈起來的。”
媽媽錯誤了,我并沒有去深究竹子有多長、或者是發大水的河水有多湍急。
我低頭想了一會兒說道:“媽,那我漂來的那個木盆子在哪呢?那可是我第一個家,我得去看看。”
我媽眉毛聳了聳,眼珠子骨碌碌轉著,最后給了我一個“五糧子”(水果楊桃的家鄉叫法)。
但是此楊桃非水果楊桃,楊桃在我家鄉話中叫“五糧子”,因為果肉有五掰,向外延伸像梳子的牙齒。(讀書時意外得知,楊桃橫切還是五角星形狀呢。)
但是家鄉的“五糧子”,經過鄉土異化,重新賦予了新的含義。一般說“給個五糧子你。”的話,就是小孩說錯話,做錯事準備挨懲罰了。
所謂的“五糧子”,就是大拇指按著無名指和小拇指,然后食指和中指微微屈起,拿來當武器,敲不聽話小孩的腦勺。
武器不尖銳且安全,還可以熟練掌控力度,是屬于既趁手又力度剛剛好,疼痛不傷腦的好武器。
況且,只要不是先天性殘疾的話,人手均有兩個,屬于活到老用到老的武器。而且,這玩意兒不需要保養和保險,更不擔心損耗。
這玩意兒便宜又好用,是村里家長常用到的武器。每每看到我媽做勢給我個“五糧子”的話,我一般都會跑,然后亂竄去找救兵。
挨打的招數花樣百出,此處不一一而論,我們說回大河。
小時候被我媽洗腦多了,因此我對河里有嬰兒漂流的事兒,那是深信不疑。
因此每每發大水的時候,我都會跑到岸邊看,睜大著眼睛紋絲不動的看。但是為什么我就沒看到有孩子漂過來呢,我多想讓自己也有一回“河里撈娃”無痛當媽的經歷啊。
當然,河邊不止我自己去,我也會拉著媽媽去,因為小孩子一個人在河邊不安全。那會兒也是不懂,一個阿拉伯數字都認不全的小豆丁,怎么就那么惜命呢。
長大一點的時候,知道河里撈小孩是不切實際的了,慢慢的,我也就不在發大水的時候拉著爸爸媽媽去了。
而是一閑下來就去。
為什么呢,因為村子里夏日炎炎且悠長,小時候沒什么玩具,山水之間便是我們最大的玩具。
三歲小孩,正是貓狗都嫌的年紀。村里同齡一大群孩子,夏秋是屬于我們的快樂童年,也是撒丫子瘋跑的時節。
老家位于南方沿海城市,春夏秋冬的界限都不明顯。
一年四季倒是有三季與山水為伴。我的童年,留在了郁郁蔥蔥又井然有序的山林中,撒在了碧水瑩瑩,清涼沁人的大河中。
春天,悠悠流來的河水潤澤萬物,田里地里開耕的時候,我得跟隨大人一起去挑水灌溉,甚至于我還有一個專屬于我的小工具。(可能就是怕我在家搗蛋且無人看管,擔心發生意外吧。)
早晨,跟在媽媽身后,涉過比我還高的野菊花蒲公英以及比我還高的野矛草,等我穿過重重荊棘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露水已把我的褲子親吻了個遍,然后我就可以在一旁大樹下曬太陽了。
褲子一干,小孩子無限的精力就上來了,看到媽媽挑起桶的時候,我就會拿著我的小工具跟在身后。
“慢點走啊,別摔了。”
“這里有個坎兒,注意點。”
從菜園子到大河邊的距離,往往會響起母親那不安的叮嚀,但就算如此,她也沒有打擊我,或者恩威并施在原地呆著。
母親這一生的宗旨就是:孩子樂意試就讓她試唄,反正也沒啥損失,摔了吹吹就好,衣服臟了洗洗就好,走錯了再來一次就好……
有了這次經驗,下次就知道躲開了,這一摔,不虧。
好不容易走到河邊,岸邊泥土濕滑,媽媽擔心我一個踉蹌就會和大河來個親密接觸,因此早早讓我在三米外的地方守著。
我蹲在地上,無聊的拽著花花草草來玩,頭上戴著媽媽剛剛為了哄我而編織的花草冠,自己一個人和地上神色匆匆的螞蟻、漫無目的小蟲子聊天。
他們真可愛,他們是永遠也不嫌我煩的動物。
太陽熱辣辣的掛在空中,螞蟻顧著回家,蟲子也不知道去向何方了。
我抬起頭看向媽媽,只見媽媽健壯的雙臂把桶扔出去,甩出一道優美的弧線,但是卻讓桶整個睡在大河上面,讓桶隨波逐流,大河剛準備上當,想把桶沉入河底順便順走的時候,媽媽用力一拽繩子,往回一拉,順勢就提了滿滿一桶水起來。
抓起桶邊,倒了一點點混濁的河水進我的小桶里,上面還飄蕩著幾張竹葉,綠油油的,還漂著水旋,好看極了。
就這樣一小桶水,媽媽就把我打發了。讓我一個人,側著大半邊身子呼哧哈哧的拎著那桶異常“沉重”的水往回走。
但是一到地里,就顯示出我的微薄之力——辛辛苦苦搞來的水,僅夠澆三顆菜。
媽媽剛把水挑回來,看到我那懊惱的樣子,看了看這山山水水。忍住了笑意才說道:“我只女已經很棒了,等到時候這幾顆又大又甜的菜長好了,我專門摘了炒給你吃。”
經過這么一安慰,那點懊悔的心早已跑到十萬八千里外了,腦海里只想著到時候這個有多好吃多甜。
夏天白日冗長,莊稼人忙著水稻收割晾曬,忙著花生玉米番薯搶收,大河兩岸從日出到日落,都站滿了清洗工具、甩掉身上污泥的人,甚至連老牛游泳的地方都給霸占了。
農村的孩子早當家,這會兒的我們就沒空和大河親密接觸了,長輩不在,就得學著長輩的樣子撐起半邊天了。
一般早上起床,去田里幫做了一點小活兒,看看太陽掛到了哪,就該跑回家做飯了,做完飯再看看太陽,估摸著父母該回來了,就可以炒菜了,期間順帶還得看看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
為什么是看太陽不是看時鐘呢?
一是那會兒還沒讀書,不認識字;二是外面的空地以及房子的樓頂上,曬了家人付出幾個月光陰汗水的成果,得時刻注意天氣,淋著了可就得挨藤條燜豬肉了。
傍晚煮好飯,又匆匆跑去田里幫忙。
此時日落西下,夕陽像個金燦燦的圓滾磨盤一樣,雖已落幕,但仍散發著最后的悶熱,讓人渾身黏糊糊濕答答的,沒來由的燥熱生氣。
本來金燦燦彎著腰的稻谷,一日之間全被剝離了土地,只剩下秸稈散發著身上的水分,那份獨屬于夏日的氣味,多年之后的今日,我仍舊懷念。
在田里踩了半天泥巴,褲管子都是泥土,回程的路上,便自然而然去大河洗刷掉身上的泥土。
大河很是平靜,靜靜的接納、包容著我們臟兮兮的身體,無聲的沖刷掉了我們身上的泥點子,隨著平靜的流水流逝,曾在我身上短暫停留的泥土,不知沉淀在了哪里、奔涌去了何方。
看著父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著,身上的汗水把衣服淹漬濕透,又被烈烈太陽蒸發變干。到了黃昏的時候,就呈現出白色晶體了。
秋天,大河因為多雨時節的到來,顯得異常興奮,時常發出怒吼,農民仍埋頭在地里耕耘,一年兩季水稻,這可是關系著年末的口糧,因此就算刮風下雨,也得風雨無阻下地。
此時的雨水倒顯得有點多余了,父母早出晚歸去田里開隴排水,大河對于人們覺得多余的雨水,納入懷中不語,攜帶著濤濤水聲,一路奔騰向海。
豐沛的雨水匯入大河,滋養大地,隨著時間的變遷,我們也開始了秋季期的學習,成長年輪上的圈數漸漸多了起來。
放學到家,燥熱難耐,此時河中冰涼的河水,就是一臺農村孩子的免費空調。
小時候一到夏天秋天,一有空,人就泡在河水中,一大群孩子在岸邊上演著炸魚跳水憋氣,更有甚者還去逗弄在下游泡澡的、勞累了一天的老水牛。
大人在岸邊洗著農具,看著孩子在河里鬧騰,可能他們想的是,身上的泥點子在河里沖刷干凈了,晚上手搓衣服就不會那么累了。
冬天,天氣寒冷,終年辛勤勞作的農民在十二月初收了最后一批農作物之后,就進入了年節,生長了一年土地也得以休養生息,但是大河邊上,卻是愈發熱鬧了起來。
一年之計在于春,小年夜送灶神上天述職后,家家戶戶就開始忙著洗刷打掃了。
家里井水使用不便,河邊上臨過年那陣子站滿了大人小孩,在下游的人經常能見著河面上漂著一團團白色的泡沫在隨波逐流,由綿密變得稀疏,最終消散。
夢幻又唯美,弱柳扶風的,被北風一吹就不見蹤影了。
往日,這大河還提供了別的功能,河里水質良好,水草豐美,特產大小魚兒,承擔著家家戶戶魚肉以及貧乏時營養的供給,小孩夏季無事忙,拿個簸箕去撈魚撈蝦,在河邊玩鬧,在竹橋邊上伸腳去踩水,感受大河的緩慢柔美。
往日停水供給不上的時候,大河就承擔著兩岸居民生活用水的職責,隨手拿起兩個桶,接兩趟回來,沉淀掉可見物質,就解決了一天用水了。
在農村,習俗頗多,大河也見證著百年來,村子里的生命交替。
哪家如果有新嬰孩的誕生,月子里的尿布,初初幾天,長輩是會拿去河邊洗,也似在祈禱河神,今日我家有喜,請諸位大神高仙,保佑孩子健康和樂。
相比較于對新生命的精細祈愿;對逝去生命,人們對大河,則顯得敬重。
村里白事的時候,在下葬前往往和道公游街(家里土話叫下香)。
就是需要帶著逝去長者的遺照以及供養在靈前的香臺,由子孫牽引,同族人一起,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在附近走一圈,大概意思就是帶過世的老人再看一眼這個生養了他/她幾十年的故鄉。
往往這個時候,隊伍里就會有一個人挑著桶,其中一個桶里放著一把刀。
這個人往往就是長媳或者長女,隨隊伍前往河邊取水,道公先在河邊念叨著一些聽不懂的專業術語,然后往河里扔幾枚硬幣,就可以取水了,取回去的這個水的用途,就是拿來煮下葬前裝在那個隨葬的谷倉糧倉里(谷倉糧倉分別是兩個陶瓷罐子,類似家里腌咸菜的罐子)。
我想著,此行既是告訴河神這個消息:逝者往后在人間消了籍,同時也是希望河神能在逝者走黃泉路、過忘川河、上奈何橋、登望鄉臺時,給予一些助力,希望逝者能在六道輪回之際,望在鄉人份上,照看一二。
這一套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制度,便流傳到今了。
漢族自古以來就是個慎終追遠的民族,從清明重陽即可看出。
而與此同時,農村又是有別于城鎮化之外的。
在大眾的認知中,鄉人是木訥的,但同時又是良善的。他們以自身純樸,主動走進這滾滾發展的城鎮化當中,在外面是不足輕重的社會人員,但是在家里,卻是一家的頂梁柱。
鄉土人情將散未散,紅白喜事變成了維系這微弱關系的紐帶。而無論紅事白事,大河始終起著一個無足輕重又至關重要的位置,俗稱螺絲釘。
大河啊,我的母親河,人民受用于她,卻也敬畏于她。
河水無情,它曾吞噬過無數在這里生長的血脈與鮮活生命,夏秋之際多山洪暴雨,它也無情的浸泡著人民辛苦半年得來的作物,甚至于摧毀人民花費大半輩子心血建成的房子;
但同時,河水又是有情的,以其自身自巨大,之海納百川,滋養著這片貧瘠的土地,使其子孫后代,在這片土地生根發芽,生生不息。
而現如今,我在此回首看去,不知為何,很是心疼。
現今河岸兩旁仍是茂竹修長,竹子的生命力茂盛,扎根下來便開始擴張地盤。
腳下竹子的根部,遍布交纏、縱橫裸露在地表之上,枝丫之上還有枝丫,層層疊疊盤根錯節發展得猶如絮狀。城固身堅,永不低頭的氣節仿佛要與草地上的植物一爭高低。
而曾經河岸邊布滿稚童腳印的地方卻已荒草叢生。
是的,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外出打工是很多鄉土人家的選擇,靠天吃飯的容錯率太低了,況且一年到頭辛苦勞作,只能勉強溫飽。其中的得失,是個明眼人都看的出來。
由此帶來的鄉村人口流失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隨著科學技術革新以及信息傳播速度加快,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一家子幾個大人看著一個小孩,生命彌足寶貴,洶涌危險的大河,就更無人踏足了。
再往大河上一瞧,岸邊的蕨類植物以及雜木水草,在沒有了人類的干預之后,瘋狂生長擴張,早已越過岸邊地界,向河中央沖刺而去。
老舊卻粗壯的枝丫勾住上游飄蕩而來的垃圾,干枯的竹子橫亙在大河中央,攔截了樹葉以及一些飄蕩出來的雜草和廢棄的禾稈,層層疊疊,散發出令人不適的氣味,也遮掩住了大河的呼吸。
我曾在傍晚時分,在落日的相伴下尋找大河,溯河岸而上,企圖找到一點童年痕跡。
但很可惜,除了看見那群熟悉老水牛靜靜躺在水里休憩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一絲童年的痕跡。
可能是我的誤闖驚到了水牛,也可能是它生來就沒見過人與牛在大河里和諧相處(打鬧)的畫面,水牛大哥抬起那大大的、無辜的、靈靈的(可能是因為剛從水里抬起頭)眼睛看著我的時候,我也靜靜的看著它。
透過那眼睛,我明確的知道,那不是我少時見的那群水牛了,它的眼里多了一絲防備,而不是我少時見的那種安然自若。
是啊,經過時間變化發展,現在愜意躺在那里欣賞著我的,可能是年少時那群水牛的子孫后輩也說不定。
再往前走,發現原本寬闊的河面現在已被泥土掩埋了部分,那一大片我曾經游玩的平坦淺灘,那個堪堪末過小孩腳踝的戲水處,早幾年已被抽沙挖空,現如今變得深不可測,幽綠綠的不見底部,叫囂著她的危險,啜泣著她的無助。
而曾經可以挑來做生活用水,可以洗衣服以及洗農具的大河。在上游建造了一家養豬場之后,再也無人踏足。
偶爾隨河水漂流而來的動植物尸體,在不小心被岸邊枝丫勾住之后,村民還得罵罵咧咧拿著竹子去挑開,只能讓臭氣循河的蹤跡漂流而去,至此消失在大河內部。
她很多委屈,也在消化著人類對她的踐踏。
我駐足原地,呆呆的站著,站了很久,我企圖在這平靜的河面上找尋我曾經快樂的蹤跡。
但很可惜,上下遍尋而不得。
從我懂事起,那條大河就安靜不語,但又奔騰不息。
小時候的我看著它,覺得它老了,流的不急不躁慢悠悠的;現如今再看,我又覺得它十分年輕,轉眼之間,我卻準備老了。
歲月流轉之間,山河顏色未變,人間卻已道是滄桑。
大河與土地一樣,在祖輩未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長期的社會實踐生活中,摸索出一套與大河和諧相處的處世智慧來,如今,卻好似被拋棄了。
不知是大河拋棄了人們,還是人們在發展中遺棄了大河。
這一切,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