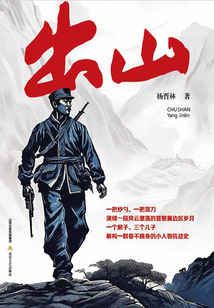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1
在東峪,閻來鎖的名頭很響,就像吊在閻家祠堂門口那棵老槐樹上的大鐵鐘。
比方說,大人只要一提閻來鎖,隨便一個(gè)吃奶的娃娃,也會(huì)在大人懷里使勁往外掙,一邊掙,一邊奶聲奶氣地說,吃肉肉吃肉肉。
可在村里,在閻家坪,他就火不了。
有一次,閻根有站在五道廟的滴水檐下,當(dāng)著幾個(gè)村人的面兒說,來鎖那兩把刷子,糊弄死人還差不多,伺候活人,他差遠(yuǎn)了。
閻根有說這話,下巴上的胡子如揚(yáng)場的木锨,不停地上下顛動(dòng)。
當(dāng)時(shí),幾個(gè)村人都愣住了,都站下,拿眼瞅閻根有,以為他喝醉酒了。
閻來鎖的手藝不咋地,大家早有共識(shí)。問題是,在閻根有之前,還從來沒有一個(gè)人,當(dāng)面站出來揭閻來鎖的老底兒,都給他留面子。
閻根有在五道廟的滴水檐下,口無遮攔說閻來鎖壞話時(shí),閻來鎖正在他家的院子里,調(diào)教他的大兒子閻守富。他一邊用拳頭巴掌感化守富,一邊還嘚吧嘚吧數(shù)落守富,顯得他打人多么講道理。
守富,你不要以為我打你心里痛快,我每抽你一巴掌,五根指頭起碼有四根,讓你的顴骨硌得生疼,你他娘的臉上怎么連點(diǎn)肉都沒有?你都吃我八年和子飯了,干的,稀的,甜的,咸的,那么多和子飯都入狗肚里去了?你個(gè)狗日的,到底不是我閻來鎖的種。
閻來鎖最后一句話總戳到閻守富的痛處。
只是這種交流方式,對(duì)父子倆來說同樣是把雙刃劍,閻來鎖揍完守富,總要用嘴吹那四根被守富的顴骨硌疼的指頭,一吹就是半天。
除閻根有討厭閻來鎖,好像村里人都喜歡圍著閻來鎖聽他吹牛。很多時(shí)候,閻來鎖如同一塊隆祥齋剛出爐的槽子糕一樣誘人,大家都喜歡往他家湊。
閻來鎖把裝有炊具的麻布褡褳,丁零哐啷往院當(dāng)中的石磨上一丟,把那件油膩膩的水裙從身上解下,用力抖一抖,踮腳掛在核桃樹的一截樹杈上,活像掛上去一塊令人垂涎的臘肉。
從山田里收工回來的村人,顧不上從豬圈挑兩擔(dān)豬糞,顧不上壘一壘塌下來的院墻,也顧不上幫女人往雞窩里轟一下夜不歸宿的雞,像貪戀某個(gè)蠱惑人心的狐貍精一樣癡迷,叼著旱煙袋,陸陸續(xù)續(xù)朝百丈崖下聚,圍著那棵兩人合抱不攏的核桃樹坐下,笑瞇瞇地聽蹲在石磨上的閻來鎖說事情。
間或,有人皺著鼻子,拔長脖頸,使勁在空中嗅一嗅,如同一只聞到肉味兒的狗。
來鎖,你給東家做豆腐包,過了幾遍油?
一遍。
一遍能行?
咋不行?豆腐包不是燒豆腐,油多了膩歪,再說他家也窮。
油大了好吃。
那也得看是做啥菜。
村人在百丈崖下不盡是聽閻來鎖一個(gè)人閑諞,更多的是一問一答。互動(dòng)環(huán)節(jié)的內(nèi)容很雜,村人想起什么問什么,當(dāng)然都是圍繞宴席的細(xì)節(jié)展開討論,討論的結(jié)果往往是大家不約而同咽下一大口口水,肚里咕嚕嚕滾過一陣腸鳴,狗剩婆姨在巷子里朝百丈崖方向吆喝自家男人,狗剩兒,吃飯啦。
好笑的是,閻來鎖不像閻根有那么能說會(huì)道,沒影兒的事兒能編出一本書來。笨嘴拙舌的閻來鎖,講著講著就講不下去了,上下兩片厚嘴唇,用力抖動(dòng)著,他想讓他并不精彩的話題延續(xù)下去,使勁咽一口唾沫,他看到七八個(gè)村人都沒有動(dòng),唯獨(dú)村長閻老實(shí)把屁股從核桃樹下的一塊捶布石上掀起,做出要走人的樣子。
回呀,回呀,不聽你廚子瞎咧咧了,還不如回家日老婆去。
有人蹲在地上,把草鞋丟在一邊,耐心地搓著腳指頭縫兒里的泥垢,張開黑洞洞的嘴,嘿嘿地發(fā)笑,眼睛卻意味深長地盯了趴在豬圈墻上喂豬的曲美英。
閻來鎖轉(zhuǎn)臉往街門口看,他的大兒閻守富正嬉皮笑臉地從二兒閻守財(cái)手里搶奪半個(gè)米窩窩。一股血唰地涌上臉,他咬著牙巴骨,從一直蹲著的磨盤上跳下。聽他閑嘮嗑的村人,以為他要去茅房撒尿,有人還打趣說,來鎖的尿泡沒有酒盅大,剛尿了又尿。誰都沒料到,廚子不是去尿尿,而是去打兒子,大家眼睜睜地看見閻來鎖伸出蒲扇似的巴掌,惡狠狠地抽在閻守富嘴巴上。
那時(shí)候,閻守富已經(jīng)成功地從二弟閻守財(cái)手里搶走了半個(gè)米窩窩,嗤嗤地笑著,還沒來得及把米窩窩塞進(jìn)嘴里,閻來鎖一巴掌抽在嘴上,米窩窩好似一只生了翅膀的麻雀,在七八雙眼睛的注視下,劃一道倉促的弧線,緊急降落在豬圈里了,把正在喂豬的曲美英嚇一大跳。
曲美英吃驚地看見她喂了大半年的大白豬,一口吞掉半個(gè)黃燦燦的米窩窩,就想,誰這么敗家的,好好的米窩窩不想吃,就隨手丟給豬了?然后,聽閻來鎖嘴里不干不凈罵道,也不撒泡尿照照,照照你那熊樣兒,就你那熊樣兒還吃米窩窩哩,你也配。
閻守富畢竟還是個(gè)孩子,細(xì)胳膊細(xì)腿不經(jīng)打,竟給他老子一巴掌打飛了,撞在寬不足五尺的街門上,吧唧一聲,又重重地摔在石頭門檻上。
大家啊呀叫起來。
有人吸著涼氣說,來鎖,你瘋了?守富是你兒。
不怪閻根有瞧不起閻來鎖,這個(gè)廚子的確是瘋了,他連娃娃們之間的小糾紛也要插手,而且還偏三向四的。
你們給我評(píng)評(píng)理,閻來鎖攤開兩手,上下抖動(dòng)著,人家是多子多福,我這小子,天生是給我添堵來了;人家的老大啥好吃的都緊讓著老二老三,我家這老大,他吃著碗里的,瞅著鍋里的;人家的娃娃都記打,我家這狗日的,記吃不記打。
閻來鎖這么罵罵咧咧地平息眾人的不滿,他總能找出各式各樣理由,佐證他打人的合理性。
閻來鎖不喜歡守富,閻家坪的村人都能看出。大家看出來也沒多大意思,閻守富是閻家老大,守富喊閻來鎖爹,又不管別人叫爹,打抱不平的村人只能背地里聲討幾句、譴責(zé)幾句、同情幾句而已,并不影響整個(gè)事件的走向。老子揍完兒子,照樣是兒子的老子,兒子被老子揍完,也照樣是老子的兒子,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無法用拳頭巴掌切割,仿佛切割村前流淌著的滹沱河一樣徒勞。
從地理學(xué)上看,滹沱河是流經(jīng)東峪的一條驅(qū)走風(fēng)塵的河流,如蠶食桑葉的河道,時(shí)緩時(shí)急的流水,還有岸邊一成不變的景物,身臨其境會(huì)讓人感受許多腐朽而原始的壓抑氣息。
閻家坪是散落在東峪半山腰上那無數(shù)個(gè)七高八低的村莊之一,閻來鎖是閻家坪土生土長的村人之一,區(qū)里征賦納糧,攤派官差,免不了叨擾這個(gè)土里土氣的名字。尋常,閻來鎖只是個(gè)耍手藝的廚子,只是個(gè)跑紅白事宴的廚子,整日煙熏火燎地被椒鹽麻油浸淫著。
東峪的廚子都是些土廚子,這樣的廚子基本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烹飪理論培訓(xùn),往往是家傳手藝,調(diào)涼菜,炒熱菜,燉燴菜,就那么固定的幾道,或十幾道。頂住天,也就能做出兩桌不重樣的大路菜,全然不像后來從某某烹飪學(xué)校或某某技校畢業(yè)的那些頭戴白色高帽子的職業(yè)廚師,他們把一棵其貌不揚(yáng)的大白菜,都能做出上百種新花樣。閻來鎖的廚藝擺不上大雅之堂,好比狗肉不上席一個(gè)道理。
閻來鎖的事業(yè)蒸蒸日上的那些年,東峪的大人小孩兒都喊得來他的名字,那是個(gè)象征酒肉白饃丸子油糕香噴噴的名字哦。你想啊,不管是窮人富人,不管是大戶小戶,哪家不做事宴?生老嫁娶都需要一種用豬油與蔥花烹飪出來的熱鬧且排場的儀式做鋪墊。但凡事宴就離不開鼓搗宴席的廚子,如此一來,長一雙瞇縫眼兒的閻來鎖并不缺東家。
這么一個(gè)很吃香的廚子,在閻家坪人眼里卻飽受非議。別的不說,就拿他打孩子這一條說吧,誰家都有孩子,誰家都有淘氣孩子,誰家大人氣急,都可能出手如電揍一頓自家孩子,就像吃飯不小心咬了舌頭邊兒一樣在所難免,可一般人打孩子都是雨露均沾,棍掃一大片,不管你是老大還是老二,不管你留光頭還是梳辮子,只要你喊我爹,喊我婆姨娘,自然免不了吃我一記老拳,而且出手的力道恰到好處,打人的解了氣,被打的長了記性。偏偏閻來鎖不按套路出牌,他家有三個(gè)男孩兒,他每一巴掌扇出去,都會(huì)落在固定的一張娃娃臉上,勢(shì)大力沉,不留情面。時(shí)間久了,那張娃娃臉往往要比一般孩子的臉大,估計(jì)是消腫沒有消徹底。這個(gè)臉大的孩子就是閻守富。
閻守富是被揍大的。
2
閻守富八歲那年,一個(gè)格外清爽的夏天,忽然被閻來鎖一巴掌扇壞心情。人這東西其實(shí)是個(gè)怪物,別看平常,什么罪什么苦都受得了,可就是不能糟踐心情,心情壞了,就會(huì)萬念俱灰。
那天,閻守富就是讓他爹把心情搞壞的,一時(shí)看倦滾滾紅塵,在村里失魂落魄四處尋找解脫的辦法,轉(zhuǎn)悠一陣子,在河堤上惶恐不安地觀望了一陣子,忽然看到一些男人魚貫而來,相跟著要出村,便悄悄尾隨其后。大人過河,他也過河,大人上山,他也上山,大人說話,他扎住嘴一聲不吭。
山越走越高,山下的村莊越來越小,最后變成火柴盒那么大。閻守富把手伸向那個(gè)火柴盒,用力一抓,緊緊握住,直到手里攥出水,覺得那個(gè)他并不喜歡的村子,連同他并不喜歡的閻來鎖,已被他揉作齏粉,松開手,朝手心吹一口氣,所有他不喜歡的東西,轉(zhuǎn)眼間消失在空氣里了。
他突然變得開心起來,跟隨村人做一次遠(yuǎn)行的態(tài)度也變得更加堅(jiān)決。
這伙人從頭至尾有七八個(gè),粗衣爛衫的,高綰了褲腿,肩上挎著繩子,后背上馱著木頭架子。這些人,守富有叫上名兒的,也有叫不上名兒的,叫上名兒的只有兩個(gè),一個(gè)是看祠堂的閻二本,一個(gè)是住在他們家前院的閻根有。
守富起初并不知道他們要去什么地方,要走多遠(yuǎn)的路,后來從他們或高或低的對(duì)話里聽出端倪,他們要去一個(gè)叫窯頭的炭廠馱炭。
路上除了零星的鳥鳴,剩下的就是刷刷的腳步聲。
閻二本走在隊(duì)伍最后。
閻二本朝前面喊,都走快點(diǎn),這么慢慢吞吞的,到了窯頭都過晌了,返回來更不好走,身子又重,又是上山,又是下山,還要過十八盤,趕不到落腳的客棧天就黑透了。
閻根有走在隊(duì)伍的最前頭,他還牽了一頭從閻緒家借來的花毛驢。他轉(zhuǎn)回頭說,二本,你急啥,這么著急,怎么不讓你娘早生你幾年?
閻二本說,我要讓我娘早生幾年,我成你爹了,你是我兒了,你馱炭就是替我馱呢,還用我遠(yuǎn)路風(fēng)塵做這苦力活兒?
閻守富也知道,馱炭是件苦力活兒,馱一回炭,脫一層皮,體質(zhì)差的,想都不敢想這事兒。
這些人都帶著繩子、麻袋和干糧,邊走邊大聲說笑。
從東峪到窯頭炭廠,除了上山就是下山,大家走得辛苦,吭哧吭哧的,不時(shí)要用袖子揩額上的汗。閻守富怕被人發(fā)現(xiàn),趕他回村,付出的心機(jī)和體力比大人更多,既要拿捏好不遠(yuǎn)不近的距離,又要手腳并用跟上去,以免掉隊(duì)。其實(shí)閻守富飄忽不定的身影,早引起閻二本的注意。閻二本一直以為有一條詭計(jì)多端的狼,把他們盯上了,便藏在一個(gè)石砬子后面,等閻守富走近,突然躍出,碗口粗的棒子幾乎砸向閻守富的腦瓜頂,這時(shí)才發(fā)現(xiàn)他襲擊的對(duì)象是個(gè)娃娃,而且是廚子閻來鎖家的大兒。閻二本硬生生地把棒子收住,破口就罵閻來鎖炒菜把心肝肺炒黑了,這么小的娃娃也敢放出來亂跑,不怕給狼吃了?
閻根有未卜先知說,不是怕給狼吃了,是遲早叫狼吃了。
路程遠(yuǎn)了,村人也不好把閻守富攆回去,只能當(dāng)累贅帶著。路上你一句我一句數(shù)落閻守富不懂事,數(shù)落閻來鎖不惜子,他們都不是瞎子,都看到閻守富頭上鼓起的大包了。
咿呀,閻根有故意一驚一乍,守富,你頭上怎么長包了?是你不小心自己碰的吧?
守富不說話。
村人從守富眼里涌動(dòng)的屈辱的淚光和不停顫動(dòng)的肩膀已經(jīng)看出,他們的猜測是正確的。他們異口同聲地罵閻來鎖不是人,是頭牲口。
一路無話,返程卻出了問題。也不是閻守富出了問題,而是經(jīng)過十八盤時(shí)趕上下暴雨,瓢潑似的雨水從天上直往地上倒。十八盤又是羊腸小路,一路都是下坡,左邊是山,右邊是澗,山高不可攀,澗深不見底,空手走路腿肚子都哆嗦,何況馱了那么多炭。
閻根有牽的毛驢是從閻緒家借的。這件事為什么要提第二遍?因?yàn)殚惛屑乙灿忻H,可閻根有告訴閻緒,他的毛驢不吃不喝光在驢圈里轉(zhuǎn)磨,估計(jì)活過今天,也活不過明天了。本來他不想借閻緒的驢,這也是沒辦法,閻二本非要約他去馱炭,他又不好意思拒絕,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
閻緒說,你小子想借驢就借吧,還扯這些?
村里人都知道閻根有會(huì)過日子,是那種借別人釘耙都想掰下兩股齒的人。這不,他想一次多馱點(diǎn)炭,讓驢馱子碼成了小山。
閻二本看到驢的四條腿都開始向外跐,忙提醒閻根有差不多就行了,它也是條命吶,小心回去閻緒跟你急。
閻根有不以為然,毛驢也就一畜生,開不得口,拉多拉少由不得它,你不說我不說守富不說,咱們一塊出來的伙計(jì)們都不說,閻緒知道個(gè)屌?
閻二本搖頭,我看你是想吃驢肉火燒了。
不過,閻根有也沒讓自己輕松多少,他背的炭塊比誰都重,走路像在砸夯,嗵嗵嗵的。他還把兩塊牛頭大的炭用繩子拴好,一前一后搭在閻守富肩膀上,說,你幫根有叔把這個(gè)背回去,我讓你嬸兒給你烙燒餅吃。
閻二本愛管閑事,看到后直嚷嚷,守富這么小,你想壓壞他呀?!
閻根有說,叫守富早點(diǎn)吃苦,免得大了找不到賺錢的門道,反正來鎖也不稀見他。
閻根有和驢在前邊走,驢屁股后面緊跟著閻二本,閻二本后面是閻守富。
老天爺在跟受苦人作對(duì),出炭廠時(shí)天氣還好好的,可一踏上十八盤,就開始下雨,而且雨勢(shì)漸猛。
閻二本發(fā)現(xiàn)前面的驢腿一個(gè)勁晃,像喝醉了酒,他擔(dān)心走著走著,咔嚓,驢腿折了。可驢腿沒折,驢卻一足不慎直往山澗滑去。閻根有還背著那塊炭,舍不得扔掉,撅著屁股死死拽住驢韁繩,撕心裂肺地喊閻二本快來搭把手。閻二本把身上的炭馱子往澗里一丟,忙去幫著拽韁繩,他看見韁繩套幾乎把驢脖子都拉長了,驢一邊在崖壁上胡亂蹬踹,一邊痛苦地哀號(hào)。
雨越下越大,空山水順著羊腸步道嘩啦啦淌下來,閻二本覺得腳底打滑,他擔(dān)心自己也滑下山崖。幸運(yùn)的是他沒滑下去,閻根有卻腳底一崴,打了個(gè)閃,閻二本眼疾手快,騰出一條胳膊去抓閻根有的衣領(lǐng)子,就聽嘣一聲,驢韁繩斷了,連同那頭毛驢連同雨水滾石,一股腦兒墜下煙雨蒙蒙的山澗……
閻根有沒死,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是閻二本抓住他的衣領(lǐng)子,他奮力掙扎著總算站穩(wěn)了腳跟。可是救了他一命的閻二本,卻呼天搶地地躺在馱炭的山道上,魚一樣打著堅(jiān)挺,他拽驢韁繩的那條胳膊,就像撕裂了一樣,軟塌塌地提不起來。閻二本哭爹喊娘的樣子,把后面背著兩塊牛頭大炭塊的閻守富嚇傻了,嚇得嗚嗚咽咽直哭。別人只顧照料閻二本,沒注意拖在末尾的閻守富哭成什么樣子,何況當(dāng)時(shí)還下著暴雨,雨水和淚水根本分不清。
回到閻家坪,不知是淋了苦雨,還是受了驚嚇,抑或是累壞了,反正閻守富病倒了,即使病倒,也沒吃上閻根有許諾的燒餅。不過也正是因?yàn)殚愂馗簧×耍悂礞i才饒他這次離家出走。這次,守富病得很重,高燒不退,幾乎快焐熟雞蛋了,嘴里說著胡話,眼睛一吊一吊的,白多黑少。曲美英一點(diǎn)辦法都沒有,眼睛哭腫了,腫成兩顆桃子,緊緊摟住渾身滾燙滾燙的守富,以為摟緊了,守富的魂魄就溜不走。也虧了嶺子底的郎中鄭雄黃,碰巧來看表姐曲美英,見外甥這副德行,也慌了神,又是扎針,又是灌藥,又用艾條熏,連續(xù)幾天療治,總算把閻守富從鬼門關(guān)上拽了回來。
3
廚子營生不因季節(jié)變化而分淡季旺季,婚喪嫁娶,定親滿月,慶壽周年,起房蓋屋,都按著事件的排序安頓事宴。有時(shí)營生趕上,擠一塊了,一家挨著一家,閻來鎖忙得陀螺似的連軸轉(zhuǎn),油勺子掂上掂下,快把胳膊都脫臼了。有時(shí)還有一天接兩家活兒的,比方白天是趙家莊做泥爐子的趙德萬娶媳婦,到了晚上,還有幾桌邊家?guī)X邊少貴替死去的老爺子送行的晚宴,東一單子,西一單子,宴席的豐歉各不相同,只有一個(gè)閻來鎖,總不能把他一劈兩半吧?偏偏這家伙胃口大,照接不誤,好在時(shí)辰寬裕,尚可調(diào)劑。
往年,或者更早以前,東峪有名的廚子并非只有一個(gè)閻來鎖。說起好廚子,掛在人們嘴頭上的是人家白玉溝的白拉柱、河南坪的郝二嘎、邊家?guī)X的陶麻子,閻來鎖算老幾?他頂多算個(gè)偷學(xué)手藝的半吊子貨。
這話不假,閻來鎖祖上以經(jīng)營石材為生,與廚子八竿子打不著一竿子。后來是閻來鎖眼饞鄰家喪宴上的五盔四盤,才翻著小眼對(duì)蹲在炕沿上抽煙的閻狗蛋說,爹呀,你讓我學(xué)個(gè)廚藝吧。
閻狗蛋一聽,愣一下,他端詳兒子在豆油燈里馬馬虎虎的模樣,說,你這娃倒精,知道大旱三年餓不死廚子。
話雖這么說,去哪里拜師學(xué)藝卻難為了石匠閻狗蛋。他知道東峪廚子的手藝一般不外傳,都是傳內(nèi)不傳外,傳子不傳女。但閻狗蛋不想冷了兒子一顆熱撲撲的事業(yè)心,先去白玉溝老白家,又去河南坪老郝家,后去邊家?guī)X老陶家,一共碰了三鼻子灰。閻狗蛋抹了抹臉上的汗,沒灰心,他對(duì)走得腿肚子直抽搐的閻來鎖說,當(dāng)初孫猴子拜菩提祖師學(xué)藝,也費(fèi)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學(xué)成的,鐵拐李不收,咱找呂洞賓去。閻狗蛋的大手牽著閻來鎖的小手饑腸轆轆返回閻家坪,爺倆吃飽喝足,又打算去一趟永興寺。走到半路,閻狗蛋讓兒子回去,他一個(gè)人去了寺院,他想找尖牛方丈求個(gè)簽,算算兒子的師傅大致在哪個(gè)方位,以方便接下來有的放矢。不想,尖牛方丈敲了一聲銅磬,說,施主不嫌路遠(yuǎn),去五臺(tái)山的顯通寺吧,我?guī)熜衷陲@通寺做住持,去了提我的法號(hào),準(zhǔn)行。這樣,閻狗蛋牽著閻來鎖一路北上,風(fēng)塵仆仆地走了兩百里山路,來到五臺(tái)山。在林立的寺廟群里找到顯通寺,找見住持把來意一說,住持讓人喚來當(dāng)家僧,又把尖牛方丈的話復(fù)述一遍,閻來鎖成了積香廚的一名俗家弟子,跟一個(gè)胖大和尚學(xué)手藝。
大和尚原本是不惜藝的,對(duì)初來乍到的閻來鎖也疼愛有加,但僅僅幾天,就把閻來鎖看扁了。閻來鎖不是默不作聲地幫他舀水生火洗碗涮鍋?zhàn)鲞@做那的,而是靠在廚房門板上,像主持春闈的主考一樣,問大和尚這菜叫什么,那菜叫什么,這菜怎么在滾水里煮一煮就成了,那菜怎么還下油鍋炒兩下?大和尚舌頭長,說話像含一枚煮熟的雞蛋,所以不大喜歡與人對(duì)話,而是喜歡用動(dòng)作教人怎么做菜,偏偏閻來鎖犯了這個(gè)忌諱。
大和尚狠狠地白他一眼,意思是要眼睛做什么?
閻來鎖眼小,沒看出大和尚白他一眼的意思,還那么煩人,除了問這問那,還喜歡磨嘰一些羊不上樹躥壟背跑的廢話,師傅呀,這是什么蘑菇,個(gè)頭怎么這么小?比我們東峪的蘑菇小了好幾倍,我娘說蘑菇燉肉好吃,你怎么不燉肉啊?我不愛吃羊肉,羊肉有膻味,我愛吃豬肉……
大和尚開始沒理他,后來憋不住了才說,出家人不動(dòng)葷腥。
閻來鎖說,葷腥是個(gè)啥玩意兒?
大和尚說,葷腥就是肉,肉就是葷腥。
閻來鎖把一個(gè)蘑菇掰開來給大和尚看,師傅師傅,這蘑菇里還有蟲子哩,蟲子也是肉吧?
大和尚一把奪過閻來鎖手里的臺(tái)蘑,丟進(jìn)簸箕。
閻來鎖沒有引以為戒,又說,這是黃花菜吧?我認(rèn)得黃花菜,過大年,我娘用它做供菜,是給天帝爺灶王爺還有財(cái)神爺吃的,前不巴年后不靠節(jié)的,師傅你做了給誰吃?
大和尚毒辣辣地又白了他一眼,心說這娃娃是個(gè)話癆。
又聽他說,師傅師傅,你們當(dāng)和尚的也吃甜苣菜啊?我跟我娘經(jīng)常去河灘挖甜苣菜,我娘不讓我插手,說我挖的都是苦苣,我分不清啥是甜苣啥是苦苣……
大和尚嘆口氣,惡狠狠地吐出一句話,你他媽的真煩人。
這樣,閻來鎖被大和尚打發(fā)去了離顯通寺不遠(yuǎn)的清水河畔,他不是去淘米的,也不是去濯菜的,而是在綠茵茵的野草叢里辨認(rèn)哪個(gè)是甜苣,哪個(gè)是苦苣。
認(rèn)了能有七八天,大和尚心說這娃娃該接受教訓(xùn)改邪歸正了,就讓他重新回到積香廚。可讓大和尚想不到的是,閻來鎖狗改不了吃屎,他不問大和尚齋飯的做法了,而是磨纏著大和尚給他講經(jīng)。偏偏這個(gè)積香廚的大和尚也是個(gè)半吊子和尚,除會(huì)炒一道金針菜,會(huì)燉一鍋山藥蛋臺(tái)蘑燴菜,會(huì)蒸一鍋發(fā)面饅頭外,經(jīng)文一概不會(huì)。閻來鎖不清楚這點(diǎn),只要看到大和尚蹲在大白塔前曬日頭,就非纏著大和尚給他講經(jīng)不可,他以為和尚念經(jīng)也是在講故事。
說一個(gè)嘛師傅,說一個(gè)嘛師傅,和尚哪有不會(huì)說經(jīng)的,我娘常給我說傻女婿相親,我爹一開口就是傻閨女鬧婆家,你也說一個(gè)嘛,說和尚娶媳婦也行。
娶你娘的頭,滾一邊兒去。大和尚生氣了。
閻來鎖分不清大和尚是真生氣還是假生氣,眨巴了半天小眼,又說,師傅,你是不是不會(huì)講經(jīng)啊?我從來沒聽你說過一句經(jīng)文。
大和尚這回不是煩了,不是惱了,不是生氣了,而是逼急了,厚嘴唇嘟嚕著說,你他娘還有完沒完了?誰說我不會(huì)念經(jīng)?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聽沒聽見你?你個(gè)小兔崽子。
很少有人知道,積香廚做飯的大和尚在沒出家之前,還做過一年半的陜西藍(lán)田知縣。后來不知怎么的,讓人把官帽摘了。摘了就摘了吧,小小知縣他也不怎么稀罕,干脆打了綁腿,渡黃河,跨汾河,涉過滹沱河,一路跋涉來到清水河畔的五臺(tái)山,清心寡欲做了一名廚僧。大和尚的確是看破紅塵了,只是無心也無力去擺弄那些刻在故紙堆里的經(jīng)文,閑來無事習(xí)慣蹲在大白塔下曬日頭。
大和尚平靜安逸的日子卻讓一個(gè)叫閻來鎖的小徒弟給打破了,他板著臉對(duì)長了一雙小瞇縫眼的閻來鎖說,你不該來顯通寺,你該去懸空寺當(dāng)?shù)朗砍狼槿ィ贿^你爹既然把你送來,總有他的道理,我不管你爹有什么道理,反正既吃僧家齋飯,就得替僧家做事,以后不要在廚房待著了,去后山打柴吧。
大和尚的話,閻來鎖不敢不聽,只好提溜一柄銹蝕的斧頭,背一圈麻繩,上山砍柴了。
春去秋來,閻來鎖把顯通寺通往后山的一條本來不是路的路也踩成了平路,總是空著身子出去,重著身子回來,巴掌磨厚了,肩膀磨平了,小小體格,健壯如牛。三年工夫,大和尚愣沒讓他沾過一回菜案。
有一次,閻狗蛋去顯通寺看兒子,在柴房里找到正在劈柴的閻來鎖,問他手藝學(xué)得怎么樣,啥時(shí)候能出師。
來鎖摸了半天后腦勺,支支吾吾說,我學(xué)會(huì)切土豆絲了,還知道大火小火了……
閻狗蛋一聽翻臉了,一巴掌扇過來,抽在他脖子窩里,狗日的,叫你好好跟人家大師傅學(xué),三年了,你學(xué)成個(gè)甚?切土豆絲,是個(gè)人就會(huì),還大火小火呢,火你個(gè)大板頭啊。
閻狗蛋揪著閻來鎖的耳朵出了積香廚,出了山門,連大和尚咬著舌頭喊他都不應(yīng),還不住嘴地罵,這鬼地方盡是糊弄人,啥出家人不打誑語,這幫禿驢沒一個(gè)實(shí)誠的。
4
臺(tái)城有個(gè)東冶鎮(zhèn),東冶鎮(zhèn)有個(gè)飯鋪叫慶春堂,掌柜是閻狗蛋姥姥門兒上的一個(gè)親戚。
閻狗蛋央告親戚讓兒子來當(dāng)學(xué)徒。親戚有點(diǎn)為難,又不好一口回絕,推脫說,學(xué)徒好當(dāng),就怕大師傅藏著捂著不讓來鎖學(xué),我雖是掌柜,可當(dāng)初跟大師傅談好了,只使喚人家的手藝,不授徒。
閻狗蛋不以為然,不授徒就不授徒,只要叫來鎖在邊兒上伺候大師傅就行,好好瞅,瞅多了,不會(huì)也就會(huì)了。
掌柜的不好再說別的,便點(diǎn)頭,行,叫來鎖給劉二當(dāng)下手吧。
劉二是五寨人,一年四季戴一頂小白帽,左眼大,右眼小,性子比較直。熟悉劉二的人,都知道他是個(gè)人精,一般炒菜倒是當(dāng)著閻來鎖的面兒做,可有幾樣拿手菜,比方龍鳳席上的叫花子雞、口水魚、臺(tái)蘑燉小雞之類,下鍋之前要清場,閻來鎖灰溜溜的像一只蒼蠅讓人一次又一次轟出灶屋,難免有些狠巴巴的心灰意懶。貓是老虎師傅,就是不教上樹。但是不要緊,有了在顯通寺的教訓(xùn),閻來鎖也多長了個(gè)心眼兒,不敢靠著門板一是一二是二地問話了,而是劉師傅長劉師傅短地哄劉二開心。劉二困了,把事先卷好的旱煙遞過去;劉二腿酸了,把一條板凳塞他屁股底下;劉二缺蔥了缺蒜了缺姜了,把早已預(yù)備好的蔥姜蒜遞過去。一來二去,劉二對(duì)這個(gè)打下手的小伙計(jì),也就另眼相看。
平常,閻來鎖準(zhǔn)備好幾頂高帽子給劉二戴,師傅,你知道外邊吃飯的都說你啥了?都夸你做的黑肉燴菜地道呢;師傅,你是這個(gè),閻來鎖蹺起大拇指說,我看東冶鎮(zhèn)再?zèng)]第二個(gè)大師傅能趕上師傅你了;我聽剛才出去的那個(gè)薄掌柜說你做的菜真香啊,香得都沒法說了……
劉二說,來鎖,不用你給我拍馬屁,不知道東家是咋想的,我是東家花錢雇來炒菜的,你是東家雇來做啥的?不會(huì)是專門哄我尋開心的吧?不過不是師傅跟你吹,不要說東冶,就是整個(gè)臺(tái)城,還真怕找不出第二個(gè)能做這道菜的大師傅呢,這是我爹手把手教給我的看家菜。
閻來鎖抽了抽鼻子,我娘不行,我娘炒的肥肉太膩,吃多了傷人。
劉二說,肉要在冷鍋里放,小火慢煎才能出凈油,肥肉不出凈油哪有不傷人的?等肉炒白,再加糖,再放蔥姜蒜……跟你個(gè)毛頭孩子說了,你也不懂,白費(fèi)我的唾沫。
閻來鎖一雙瞇縫眼彎成兩個(gè)小月牙,擺出一副真不懂的樣子,你們當(dāng)大師傅的真不簡單,一道菜有一道做法,料不一樣,火不一樣,順序也不一樣,哪記得住啊?單說這道菜吧,怎么在鍋里煸了還要上籠屜蒸啊?
劉二有時(shí)候答得細(xì),有時(shí)候答得粗,有時(shí)候答非所問,答得細(xì)是為了在閻來鎖面前顯擺,答得粗是他也道不出個(gè)所以然來,答非所問是故意把閻來鎖往岔路上引,以免手藝外流。但雙方交流的回合多了,劉二難免把前一次答粗的又答細(xì)了,把前幾次答錯(cuò)的又答對(duì)了,反反復(fù)復(fù),閻來鎖心里有了底兒。大師傅不在灶上,他就翻騰那些佐料罐兒,哪些常用,哪些不常用,哪些味重,哪些清淡,他都用心記下;大師傅的拿手菜出鍋后,他還會(huì)偷偷觀察罐里的佐料哪個(gè)少了,哪個(gè)沒動(dòng),然后湊近鼻子聞一聞菜的咸淡鮮陳寡濃,日子久了,也基本摸索出幾樣大菜的做法。可有一樣,眼高手低,閻來鎖沒辦法改變現(xiàn)狀,只有等待時(shí)機(jī)。
時(shí)機(jī)總是留給有準(zhǔn)備的人。到了某年秋天的一個(gè)落雨天,慶春堂的大師傅劉二沒來出工。掌柜的原以為劉二因漲工錢的事兒故意在房里跟他鬧別扭,便讓人去宿舍催,去催的人回來說大師傅病了,臉燒得像猴屁股,渾身篩糠似的抖,三床被子蓋上去都直呼冷。掌柜的知道劉二真病了,害傷寒了,忙吩咐人出門去請(qǐng)郎中。
郎中好請(qǐng),大師傅的空缺誰來頂?一般的,大師傅病了有二師傅,慶春堂原來也有二師傅,可二師傅跟大師傅合不來,斗了幾次嘴,還險(xiǎn)些掄菜刀釀成血案,出于對(duì)彼此生命的尊重,二師傅撂挑子不干了。眼看午時(shí)將近,食客要上門,掌柜的一下慌了神,搓著兩手在飯店的大堂里轉(zhuǎn)磨磨,這真叫過大年借籠屜,到哪兒找合適人呢?
這時(shí),少年閻來鎖主動(dòng)站出來救了慶春堂的急。閻來鎖像個(gè)小大人似的有板有眼說,實(shí)在找不到合適人兒,讓我試試得了,炒不好菜總比炒不出菜強(qiáng)吧?
也是急病亂投醫(yī),掌柜的沒法子,只好讓閻來鎖披掛上陣,卻不歇嘴地在一旁嘮叨,嘮叨的意思就是從本質(zhì)上否定這個(gè)初出茅廬的牛犢子,來鎖,你能行嗎?你連勺子都沒掂過能行?可不敢瞎逞能,甭把慶春堂的牌子給搞砸了,實(shí)在不行,干脆歇業(yè)一天得了。
閻來鎖小眼瞇虛成一條縫兒,故意說,大師傅這病怕一時(shí)半會(huì)兒好不了,這個(gè)得你拿主意,我也不敢給你打包票,你也知道大師傅手緊,從不讓人沾他的炒勺。
掌柜的死死盯住閻來鎖的臉,眼珠子一眨不眨,最后一跺腳,死馬當(dāng)活馬醫(yī)了,來鎖,抄家伙。
幾十年后的閻來鎖,已記不清他第一次越俎代庖替劉二掌勺的情景了,只記得掌柜的到了年底,額外給他十五塊現(xiàn)大洋,因?yàn)閯⒍]過幾天就痊愈了,閻來鎖該干嘛還干嘛。
閻來鎖是十四歲在東冶鎮(zhèn)慶春堂一炮打響的,當(dāng)然也不能說有多響,不就是做了幾天劉二的備胎嘛,但這樣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已足夠他日后馳騁廚場了。
轉(zhuǎn)年,二月二龍?zhí)ь^,閻狗蛋又找到慶春堂掌柜,說來鎖這狗日的不想干了,老給他捎口信,嚷嚷著要回去跑事宴呀,兒大不由爺,隨他去吧。
掌柜的本意是想留下閻來鎖,有朝一日大師傅撂挑子不干,一時(shí)又找不到合適的替補(bǔ),就拿來鎖頂杠子,可聽了閻狗蛋的話,掌柜的轉(zhuǎn)變了主意,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就拿眼瞅閻來鎖。
閻來鎖其實(shí)并不想走,蹲慣的茅坑不嫌臭,便瞪著小瞇縫眼問他爹,誰想跑事宴了,爹?誰給你捎口信了,爹?
閻狗蛋一巴掌扇過來,抽在閻來鎖的脖子窩里,好漢做事好漢當(dāng),說了的話還能收回去?瞧你那出息勁兒,能跑事宴么?誰家做事宴敢用你個(gè)榆木腦袋哩?
掌柜的也是明白人,忙說,不要打,來鎖沒錯(cuò),伺候人總不如伺候自個(gè)兒,十里長宴,總有散席的時(shí)候,回去吧,混好了,啥都不說了,混不下去的話,還來慶春堂。
閻狗蛋帶著閻來鎖回閻家坪。路上,閻狗蛋對(duì)兒子說,不要記恨你爹,爹也是為你好,師傅領(lǐng)進(jìn)門,修行在個(gè)人,往后呢,全靠你自個(gè)兒撲鬧了,別的忙,爹也幫不上。又說,天底下,誰不是自個(gè)兒為自個(gè)兒著想,哪有伺候別人一輩子的?
閻來鎖不領(lǐng)閻狗蛋的情,心說,你既然幫不上我,砸我的飯碗做什么?
5
萬事開頭難,這話不假。
閻來鎖初出道那陣兒,白玉溝的白拉柱、河南坪的郝二嘎、邊家?guī)X的陶麻子早就名滿江湖,有誰知道閻家坪還有個(gè)半路出家的小廚子叫閻來鎖?沒人敢把事宴交代給一個(gè)無名小輩來操持,不用說外村人了,連閻家坪人都不買他的賬,誰家有事宴,首先想到的是趕緊派人出村訂廚子,不管白廚子郝廚子陶廚子,只要是廚子就行,但閻廚子不行。閻來鎖不能主宰東家的意志,可豬朝前拱,雞往后刨,各有各的道道兒,他的道道兒就是黏人。
閻老實(shí)他爹閻緒就領(lǐng)教過閻來鎖的厲害。
那年,閻緒要給兒子閻老實(shí)娶媳婦。老實(shí)比來鎖年齡大幾歲,十八歲成家,娶的是長舒里老劉家的閨女。閻緒前些日子派人去白玉溝訂好了廚子白拉柱,臨近完婚的前幾天,閻來鎖才聽到風(fēng)聲。他去找閻緒,閻緒正在醋缸前用醋拐子攪和米醋。
閻來鎖說,緒伯伯,老實(shí)在不在家?
還沒等閻緒說在與不在,閻來鎖又說,老實(shí)的事宴訂好廚子沒?
閻緒用指頭蘸了一點(diǎn)醋在嘴里抿了抿,說,成了,挺酸的。又說,誤啥不誤啥,也不能把廚子落下,早訂下了,白玉溝的拉柱,臉上有白斑的那個(gè),菜丸子做得地道。
吃席又不是光吃一碗菜丸子。閻來鎖眨巴著小眼說,緒伯伯,你看我也出道了,我炒的菜不比誰差,我?guī)煾凳菛|冶鎮(zhèn)慶春堂的劉二,論起名望,東峪的廚子加起來都不夠我?guī)煾档闹讣咨w大。
閻緒把醋拐子擱在醋缸上,揮手驅(qū)趕著幾只綠頭蒼蠅,又用牛皮紙苫住缸口,咝了口氣,來鎖啊,前些日子是聽你爹提過這事兒,可你大娘說你狗日的還是個(gè)生手,怕把事宴做砸了,沒敢動(dòng)用你的貴手。
緒伯伯,我總得練手呀。閻來鎖說,一回生,兩回熟,你不賞我機(jī)會(huì),咋往熟里練呀?
吔,看你這話說的。
閻緒有點(diǎn)不高興,他準(zhǔn)備回屋里,卻扭轉(zhuǎn)身子對(duì)閻來鎖說,大侄子,聽你這口氣,我沒用你做事宴是我的錯(cuò)?你跟我家老實(shí)也是從小玩大的,總不能安啥壞心眼吧?給老實(shí)娶媳婦是件大事兒,一輩子說不定就這一回,我把一輩子攢下的辛苦錢都擱這兒了,總不能在廚子這塊兒讓狗日的你練手吧?做好了還成,做糊了,丟的是我閻緒的臉面,你賠我錢還是賠我丟了的臉面?再說,你就是賠,也賠不起……
閻緒說完,回屋了。
閻緒原以為閻來鎖經(jīng)他這一說,也就打了退堂鼓,哪想到,閻來鎖一直跟著他進(jìn)了北屋,還從他家的八仙桌上端起一碗茶,咕咕地喝了兩口,一抹嘴說,你咋知道我能做糊了?我要做好了咋整?
閻緒被閻來鎖噎得說不出話。半天,不尷不尬地笑了笑,笑出滿嘴黑乎乎的牙,狗日的,你小子是賴上你緒伯伯了,你咋好賴不分哩?你看我挺忙的,又得派人接老實(shí)他姥姥姥爺舅舅妗妗,又得接待親家送來的箱柜陪嫁,還得把大花餅讓人給親家送過去,老實(shí)的洞房也沒安頓好,我也顧不上支應(yīng)你,你想幫忙,等白拉柱來了,你給他打打下手吧。
依慣例,娶親前一天,廚子會(huì)出現(xiàn)在東家廚房里,準(zhǔn)備第二天的宴席。東峪的席面習(xí)慣五盔四盤,五盔四盤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需要充裕的時(shí)間,豬肉要紅燒,牛肉要紅燒,豆腐也要紅燒,蘿卜丸子的工序更加復(fù)雜,用板擦擦成蘿卜絲,入開水鍋煮爛,擰了水,剁成末兒,加入淀粉、肉末、調(diào)料,一顆一顆攥成球形,碼入籠屜中,蒸半個(gè)時(shí)辰出鍋。這樣的丸子才是個(gè)半成品,或入燴菜,或重新配湯料單另入碗,麻煩著呢。但有一樣,一個(gè)廚子一個(gè)味兒,一個(gè)廚子一做法,但哪個(gè)廚子都不是神仙手,都得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慢慢來。白拉柱的菜丸子在東峪廚子中間算是一絕,閻緒有一多半原因是奔著白拉柱的菜丸子去的,但白拉柱那天沒來閻家坪,倒是閻來鎖一早就像看門狗一樣圪蹴在閻緒家的街門外了,頂了一頭露水。
頭一天黃昏,有個(gè)閻家坪的老漢,去白玉溝找見白拉柱,給了白拉柱兩塊現(xiàn)洋,說閻家坪的事宴不做了,男方聽說女方有狐臭,臨時(shí)改變了主意,這兩塊錢是退事宴錢。白拉柱無話可說,人家親事都退了,要廚子有屁用。
閻緒即使捂上十床被子都?jí)舨灰娺@回事兒。他事先已經(jīng)按照白拉柱列出的食材單子,把需要用的蔬菜豬肉豬油佐料等等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準(zhǔn)備妥了,連白饃油糕都該上籠的上籠,該入缸的入缸,只等白拉柱一來,葷案素案、涼菜熱菜地細(xì)分了,可等到后半晌,還不見廚子過來張羅,閻緒跟他兒子閻老實(shí)說,白玉溝的廚子不能遇事。
事宴上的涼菜第二天可以現(xiàn)調(diào),有的熱菜也要現(xiàn)炒,可有的燒菜燉菜非好幾個(gè)時(shí)辰做不出。好在閻來鎖不用旁人招呼,自己動(dòng)手把該洗的洗了,把該擇的擇了,把該切的也切了,該蒸的燒的煮的也依次做了,然后,天黑了。閻來鎖揩凈炒勺炒瓢笊籬肉叉菜刀對(duì)陰沉了一張臉的閻緒說,緒伯伯,我回呀。
閻緒愣了一下,渾身一激靈,醒悟過來,卻有點(diǎn)過意不去,今兒可全虧大侄子了,明兒你一早就來,他白拉柱愛來不來,就是來了,也得有個(gè)說法才敢用他。
閻緒原想,白拉柱既是答應(yīng)下的事宴,就沒理由給他唱一出空城計(jì),即使真有事脫不開身,也該捎句話過來,不該讓東家望眼欲穿的。可到了第二天,娶親的隊(duì)伍快要出發(fā)了,起馬宴也該開席了,白拉柱還沒來。新郎、伴戚、娶親人、炮手都已更衣入席,他們吃的是閻來鎖做的五盔四盤,文火慢燉的紅燒豬肉紅燒牛肉格外香,除了蘿卜丸子,又加了一道生炸肉丸子,蒸肉碼出雙喜狀,清烹的蓮藕也擺出了笑臉的樣式,豆芽粉絲用北方人不大采用的辣椒煸了,淋了白醋,盤子四周又用幾葉青菜點(diǎn)綴了圖案,不管是坐席的,還是周圍觀看的,都在嘖嘖稱奇。
閻老實(shí)跟做伴戚的姐夫說,不用不知道,一用嚇一跳,來鎖這手藝不賴嘛,以前咱可看走眼了。
這樣的效果,讓閻緒一直懸在嗓子眼的心落了底,也說,多虧狗日的白拉柱沒來,他來了,鬼知道來鎖還能干了這個(gè)。
人說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其實(shí)不管好事壞事都能傳千里,閻來鎖的一桌起馬宴,讓東峪人稱贊許久,后來好多人都是慕名他的起馬宴才來訂他做廚子的。但沒有不透風(fēng)的墻,白拉柱還是拐彎抹角聽說了這件事,起先他真以為閻老實(shí)的親事黃了,后來聽人說閻老實(shí)還是那天娶的媳婦兒,只是廚子換了。白拉柱氣得直咬牙,他拿了那兩塊現(xiàn)洋專門跑了一趟長舒里,找到閻老實(shí)的老丈人,一五一十把那個(gè)老漢的原話翻騰給閻老實(shí)的老丈人,并把那兩塊現(xiàn)洋攤開給閻老實(shí)的老丈人看。老丈人聽罷,又看罷,半晌無語,突然咔咔地咳嗽起來,胡子拉碴的黑臉噘得紫紅,指著閻老實(shí)的丈母娘說,這就是你時(shí)常掛在嘴邊千好萬好的親家,你跟咱閨女說,他閻緒不把狐臭這事兒掰扯清楚,老子跟他老閻家沒完。
閻老實(shí)的丈母娘到底沒跟閨女講這事兒,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都嫁出去的閨女了,扯這些鬧心事做甚?以后閻老實(shí)每次去老丈人家,總覺得老丈人對(duì)他挺冷淡的,一副待理不理的樣子,忍不住問媳婦兒,媳婦兒也迷糊,說以前不這樣啊,以前一提你閻老實(shí)三個(gè)字,滿臉都是笑啊。又過了好久,直到閻老實(shí)當(dāng)上閻家坪村長,有一次老丈人來看望外甥女,喝了一壺二鍋頭,話匣子一開,數(shù)落起親家閻緒的不是。閻老實(shí)一聽,潑了一臉豬血,他當(dāng)然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結(jié)結(jié)巴巴說,爹,這事不能怨我爹,爹你冤枉我爹了。
老丈人聽不懂女婿的車轱轆話,吹胡子瞪眼,照你這么說,我們一家老小真有那韃靼人傳下的狐臭?
閻老實(shí)忙說,爹,我說的不是這個(gè),我是說,一準(zhǔn)是他狗日的閻來鎖背后搞的鬼,我爹壓根兒沒派人去辭退過人家白拉柱,那個(gè)傳話的老漢,十有八九是閻狗蛋,這倆狗日的,剝了皮都不對(duì)我的心事。
而那時(shí),不僅閻狗蛋下世了,另一個(gè)當(dāng)事人閻緒也久不在人世,倒是閻來鎖因一場事宴名聲大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