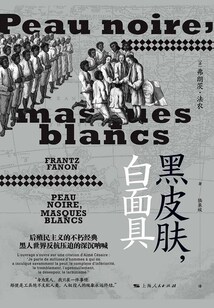
黑皮膚,白面具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
弗朗茨·法農(1925—1961)堪稱20世紀下半葉世界范圍內反殖民主義與黑人權利運動之中極具影響力的一位實踐者和思想家。在《黑皮膚,白面具》出版逾70年后,這本閃現著昂揚斗志和理性火花的著作,時至今日依然是研究后殖民主義和種族問題的學者們繞不開的一部經典。之所以說法農是一位行動的思想家,那是因為他的思想體系與他的生平、教育、行醫與革命經歷始終密不可分。
1925年7月6日,法農生于法屬馬提尼克島的首府法蘭西堡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海關檢查員,母親經營小商店。中學時代在老師艾梅·塞澤爾的熏陶下,法農就對殖民和種族問題格外關注。1943年,當自由法國部隊控制馬提尼克島后,法農志愿參軍趕赴歐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并因自己的英勇無畏被法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此后,他先后在巴黎和里昂接受教育成為一名精神病醫生。其間,身為黑人的法農切實深刻地感受到,作為法國公民的他雖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卻依然是白人眼中那個低等的、危險的、野蠻的“他者”。正是基于自身的這些經歷和感悟,法農在法國于1952年撰寫并出版了《黑皮膚,白面具》。
這本著作既是法農的處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這部激情澎湃、斗志昂揚的作品中,作者以汪洋恣肆的抒情文風,表達出深邃的思想,內容觸及了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多個層面。比如,語言與身份的關系、跨種族愛情與婚姻、黑人(及白人)的異化與表征、白人社會的多種神經癥等問題。此外,法農還與薩特(存在主義)、黑格爾(自我意識)、阿德勒(個體心理)等哲學家展開對話,駁斥了西方文化中以黑—白、主體—客體、自我—他者為基礎的二元對立,從而彰顯出黑人自我意識革命性的解構與重構的必要性。下面,我就從圍繞以上的主題,對《黑皮膚,白面具》進行扼要的梳理。
一、語言與身份
馬丁·海德格爾在他的文章《語言》(1950)中談到語言與存在和意識關系時,富有創見性地提出人在言說的同時,語言又在言說人。這種觀點一反常規提法,在極大地豐富語言基本功能的同時,更充分說明人類的語言也在切實地塑造著我們的意識和感知。無獨有偶,法農在這本書中也寫道:“說一種語言,便是宣揚一個世界、一種文化。”(p.30)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黑人文學經歷那種從標準英語向黑人英語的書寫轉變,不僅彰顯了作家的非裔身份,而且也創造了黑人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從而實現了對抗主流文化的政治使命和文學訴求。
然而,正如在本書中指出,奔赴巴黎求學的不少安的列斯青年返鄉之后,卻不再使用當地的方言克里奧爾語,而是熱烈擁抱殖民化他們、異化他們的法語,這充分表明這些黑人早已喪失艾梅·塞澤爾所言的“黑人性”(négritude)。不過,這肯定事出有因。白人社會強加的那種偏見,即黑人只會說蹩腳的法語,而且還總吞掉小舌音[r]。這種負面歧視強化了黑人對于法語的態度,有些黑人學生甚至使勁糾正自己的發音。法農書中批判的那些返鄉的安的列斯人,不講克里奧爾語方言卻刻意用法語抬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做法,并非表示一個人不能說出生地方言之外的語言,而在于他選擇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說的問題。
另外,對于白人刻意對黑人或阿拉伯人說蹩腳的法語,法農也是甚為惱火。正如法農寫道:“一個白人在向一個黑人說話時,舉止猶如一個成人應對一個兒童,他矯揉造作、輕聲細語、殷勤體貼、呵護備至。”(p.24)在作者看來,白人這樣的行為依然延續了殖民社會中主子的姿態,因為白人并未將對方作為平等的個體對待,而是以成人對待兒童的語氣在向異族發話。在我看來,法農對于語言的看法也值得外語學習者和使用者反思與借鑒;學習任何外語既不能將它們抬高到母語之上,也不能以犧牲自己的母語為代價,更不能以幾句蹩腳的外語四處顯擺和炫耀。
或許正是為了肯定自己的身份,法農的文字風格與很多法國本土作家迥然相異。為了凸顯作者的“黑人性”,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極少使用第一人稱單數形式“我”,相反卻大量使用人稱代詞“我們”來集體發聲,由此不僅強化了作者與整個黑人社會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且也在召喚黑人同胞要積極行動起來,投身黑人的去異化進程之中。此外,閱讀這本書還需要注意作者的兩大語言特點:一方面,曾經學醫的法農慣于使用醫學術語,比如“靜脈曲張”(p.69)、“切片機”(p.93)、“血液收縮壓”(p.178)等;另一方面,他會竭力借用很多新奇的意象或隱喻表達觀點,比如他在描寫個人作為客體被白人世界包圍那種天崩地裂的感覺時,就曾寫道:“上方的天空在撕扯它的肚臍,大地在我腳下嘎吱作響。”(p.92)這里值得提及,法農在語言層面這種異常顯著的陌生化處理,雖然會給閱讀造成不小的障礙,但確實會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二、跨種族愛情
真正的愛情是人與人之間最無私的利他主義奉獻。這樣的愛情定然是偉大的,它可以逾越膚色、年齡、地位等鴻溝。然而,婚姻是社會、文化、習俗的產物,跨種族婚姻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諸多問題。對于有色女人與白種男人的愛情,法農首先以本土作家馬約特·卡佩西亞的《我是馬提尼克女人》為例,批判了黑人女性對白色的盲目崇拜以及意欲從身體和思想上漂白自己的徒勞。另外,法農還以塞內加爾作家阿卜杜拉耶·薩吉的小說《妮妮》為例,分析了一心想嫁白人的混血女妮妮,在面對黑人男青年馬克塔的追求時的態度:“這個混血女子認為這封信是一種侮辱,簡直是對自己身為‘白人姑娘’名譽的冒犯。”(p.45)然而,當一個正宗的歐洲白人向一位混血姑娘迪迪求婚時,整個圣路易市竟然都為這個不脛而走的消息高興不已。由此看出,從種族主義已衍生出這種“白人>混血>黑人”的微妙等級高低次序,從而強化了黑人社會意欲漂白整個人種的觀念。不僅如此,法農也點明了黑人表現的這種類似神經癥的“情感亢奮”正是自卑感的體現,它同時又造就了白人病態的那種優越感。
除深入討論有色女人與白種男人的愛情之外,法農在第三章又將目光轉向有色男人與白種女人之間的關系。對此,法農以圭亞那作家勒內·馬朗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一個同其他人一樣的男人》為例,借助精神分析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作品中接受歐洲教育的黑人青年讓·韋納茲,在面對白人姑娘安德萊·馬里耶勒追求時那種陷入骨髓的自卑,因為這名黑人認為白人姑娘與“這個種族的任何人來往都有失身份”(p.53)。最后,小說主人公讓·韋納茲在白人朋友庫朗熱的一再勸慰下,在接受自己是個白人的前提下才勉強與安德萊開始交往。其實,在接受自己那種具有普遍性的白人身份的同時,表現出遺棄型神經癥性格特點的讓·韋納茲在貶損自己的價值,更在棄絕自己的黑人性,由此凸顯出這部小說的標題是何等荒謬,因為主人公顯然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和其他人一樣的男人。
在批判具有“消極—攻擊型人格”(p.59)的小說人物讓·韋納茲這種自我貶低、自我否定態度的同時,法農也剖析了另外一類人群。這類具有“積極—戀愛型人格”(同上)的有色男人,有些人趕赴法國的第一件事便是上紅燈區與白種妓女發生關系,有些則以愛之名娶白種女人,而支配他們行為的動機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報復心理。顯然,以上討論的有色男女,他們的主體性已經缺失,他們的意識已經異化。在法農看來,黑人社會只有通過積極的身份、意識和文化重構,真正擺脫自我貶低、自卑情結、情感亢奮等病態心理,跨越種族的愛情才能由神話變為現實。總之,世界上種族主義如果不徹底消亡(似乎也不會),那么基于平等之上的跨族婚姻也只能是個神話,它定然要比族內婚姻面對更多的問題、危機和沖突。
三、殖民種族主義
殖民種族主義不單是一些殖民者和探險家所為,在法農看來,它更是殖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的結果,也即它是歷經上百年不斷構建的產物。法農在第四章“被殖民者的所謂依附情結”一開始就切中要害,指出,馬諾尼在《殖民心理學》中將文明與野蠻對立起來、認為黑人自卑情結先于殖民主義存在的觀點錯誤至極。針對這種觀點,法農犀利地加以駁斥,聲稱殖民種族主義與其他任何種族主義一樣,而且“歐洲文明及其最具資格的代表對殖民種族主義負有責任”(p.72)。接著,法農也對馬諾尼認為與膚色相關的自卑情結只見于生活在另一膚色環境的少數個體身上的觀點予以回擊。毫無疑問,類似馬諾尼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歐洲在海外推行殖民主義的借口而已。
在將殖民主義視為一種文化構建時,法農借用薩特《關于猶太問題的反思》中的觀點“正是反猶太人主義者制造了猶太人”,平行地宣稱“正是種族主義者制造出有自卑感的人”(p.75)。誠然,殖民者的入侵給土著居民帶來的惡果,絕非只是心理層面的創傷,更有社會、經濟層面的破壞;這種破壞反過來又會強化心理上的創傷,從而對被殖民者造成更深層次的異化,讓他們喪失自己的主體性和自己的價值。換言之,土著居民的人性在殖民化過程中被剝奪了,于是喪失主體的“依附情結”便表現為心理上的所謂“自卑情結”。久而久之,這種自卑情結最終堂而皇之地進入被殖民者的無意識精神結構。以上社會化的構建,正是法農對于黑人自卑情結發生的精辟描述。
殖民種族主義不僅在無意識層面給黑人帶來精神創傷,而且通過文化手段(以教材、畫報、廣告、電影、電視為媒介)塑造出黑人刻板形象并不斷將其徹底固化。更為糟糕的是,安的列斯人在被動吸納這些主流文化時,竟然會自動和白人發生認同并接受對方的價值和觀念,故而讓種族主義變得更為復雜,由此形成一種虛假的由高到低的“白人>安的列斯人>非洲人”的等級次序。這里,法農以最早的一部有聲美國電影《人猿泰山》(1932)作為經典案例,進行了頗有卓識的精彩分析。不過,等遭受殖民的安的列斯人趕赴歐洲,這種假象瞬間坍塌,因為無論如何“他是個黑人。一到歐洲他就會發覺這一點,而且當人們談論黑人時,他就知道這同時涉及自己和塞內加爾人”(pp.120—121)。
四、黑人恐懼癥
對于膚色偏見,法農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它不外乎是一種對于他者的無意識仇恨和恐懼。對于西方大多數白人女性的“黑人恐懼癥”(négrophobie),不僅由于西方文化在表征黑人的過程中附加了很多負面色彩,而且在精神分析的層面,這種恐懼當中充斥著性欲、生殖的意味。對此,作者再次援用薩特有關反猶太主義的看法,對黑人恐懼癥進行了平行分析。正如西方文化再現猶太人時,因為畏懼對方的智力而將他們表征為視財如命的守財奴、貪婪自私的銀行家那樣,這種文化由于性欲受到壓抑,受“一種性無能或性自卑的情感支配”(p.129),而將黑人男子表征為只有生物屬性、定向于生殖和性欲的陽物,它反過來又導致了臨床上諸多白種女人的迫害妄想癥和黑人恐懼癥。由此,在性欲上受挫的白人男權社會,只能將他們帶有攻擊性的施虐狂定向于黑人身上,于是私刑、歧視、閹割、迫害在有黑人的國家全部上演。
在這本書中,法農自己創造了一個術語“文化強制”(p.154)來描述白人社會強加給黑人的各種價值觀念,這多少有點類似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在歐洲文化的表征之下,處于白人的凝視之下,非洲黑人的主體性存在早已千瘡百孔、支離破碎,轉化為真正的虛無。19世紀末興起的人種學、優生學更是披上科學的外衣來強化種族主義,這類“可恥”(p.97)的科學也為德國納粹大肆掀起的反猶太主義屠殺做好了鋪墊。正是這個原因,法農認為反猶太主義與種族主義在本質上并無二致,猶太人和黑人都不過是替罪羊而已。
在歐洲大眾文化中,黑人不僅意味著骯臟、丑陋、野蠻、愚昧,而且代表著魔鬼、色情、邪惡、妖怪。從哲學層面來看,這種西方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白—善、黑—惡等觀念的文化耦合,它其實凸顯的依然是歐洲思想體系中的二元對立。法農從中明銳地看到,白人社會通過“文化強制”給黑人帶來自我貶低、自卑情結、被動姿態、奴性屈服的同時,更從多個層面嚴重毒害了白人的自我意識和心理健康。簡而言之,黑人在被社會異化的同時,白人也遭到了同樣的異化,于是“愚弄者”成了“被愚弄者”,白人社會自身也遭到了反噬。由此,白人社會中常見的以黑人為主題的恐懼癥、妄想癥、施/受虐狂、譫妄等“病態”心理也都有了它們的根源所在。為了進一步佐證這種看法,法農從法國本土作家,比如喬治·穆南、埃米爾·德爾芒讓等人的回憶錄、雜志文章和作品中尋找答案,更對身為猶太人的米歇爾·薩洛蒙的作品當中散發的種族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五、黑人主體性
倘若黑人始終待在自己的故土,他的命運與白人小孩也相差無幾;但如果他要趕赴歐洲大陸,那就必然要考慮重構黑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存在的問題。面對膚色、性別和階級相互交織的殖民語境,法農首先從發展個體心理學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開始。在阿德勒看來,自我在發展過程中,始終會以他者為參照。然而,經歷過殖民化的安的列斯人所處的社會是一個神經質社會,法農由此認為,所有安的列斯黑人在選擇白人作為對照時,他們要么淪陷于自卑情結,要么采用“過度補償”(p.174)奮起反抗這種自卑,從而滋生出一種想成為白人的優越情結。對法農而言,要說黑人的個體發展存在問題,他們所處的“環境和社會”(p.175)得負很大的責任。
另外,對于黑人主體存在的問題,法農主要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入手。針對主體的存在,黑格爾認為“人的價值和現實就取決于他者以及對方的認可”(p.176)。這種看法有點類似世間全新物種的認可,一個物種在尚未得到分類學家發現和定名之前,它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顯然是個悖論。不過,法農從這種承認出發,并且往前更進一步指出,“為獲得自我的確定,就必須整合承認的概念。他者同樣在等待我們的承認,以便在普遍的自我意識中充分地發展”(p.176)。正如之前所見,法農其實已經將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相互性貫穿到異化、欺騙、承認等多個主題的討論,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對二元論的解構和重構,其中也凸顯出他的顛覆性和革命性,正如書中他援引費希特的那句話:“自我在對立中存在。”(p.200)
在法農看來,不論是阿德勒認為個體要參照他者產生自我意識的觀點,還是黑格爾所言的主體要得到他者承認才存在的看法,它們似乎都是一種寄生性的主體性理論,一種“令人詫異的騙術”(p.170)。必須要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去打破束縛在黑人身上的枷鎖,將受困于自卑情結、情感亢奮、過度補償的自我意識徹底解構,然后才能從社會和文化層面對黑人的身份和意識進行全新的重構。從這個角度來看,《黑皮膚,白面具》更像一部革命預言,因為在此書出版后不久,一場席卷非洲的反殖民斗爭和美國的黑人權利運動就轟轟烈烈地展開。
綜上所述,法農不僅是思想的勇士,更是革命的斗士。在這本黑人知識分子反抗殖民主義霸權的理性批判當中,法農在結語中指出,正如工人階級必須通過斗爭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處于殖民壓迫之下的人民也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消滅白人社會的壓迫。為此,很多學者尤其是歐美學者,認為法農的思想過于極端、激烈,認為他提倡的以革命手段終結殖民主義過于殘暴、血腥。這里試問在人類的斗爭歷史上,難道殖民者或壓迫者僅憑良心發現,就會給予被壓迫人民所有的權利和真正的平等嗎?恰似法農在書中揭示的那樣,美國黑人基本上沒有經歷過于殘酷的斗爭,南北戰爭期間林肯頒發的一紙《解放黑人奴隸宣言》就給了他們自由,然而昔日黑奴內心那種自卑、屈服、被動從未徹底消除。畢竟,他人給予的東西和自己爭取的東西,在主體的心理上絕對有著天壤之別。在這一點上,法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的暴力革命觀點與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末尾那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不謀而合,倆人對那種整天鉆入故紙堆當中、只知玩味文字的偽思想家都給予了最辛辣的嘲諷,并且充分肯定了實踐的重要意義和真正價值。
這里,我想再次回到本書作者尚未結束的生平介紹上來。在《黑皮膚,白面具》出版第二年,法農結束了自己的醫學訓練,隨即趕赴阿爾及利亞卜利達(Blida)精神病醫院擔任主治醫師。那時,當地民族解放陣線(FLN)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革命斗爭剛好拉開序幕。1956年,法農辭去了自己的醫生職務,成為民族解放陣線報紙主編,從而投身到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革命斗爭當中。在隨后的五年,法農先是被迫離開阿爾及利亞,而后又輾轉突尼斯和加納。在此期間,他的幾部著作和文章都圍繞非洲革命展開,比如《阿爾及利亞革命的第五年》(1959)和死后出版的《為了非洲革命》(1964)等。不幸的是,法農在加納確診患上了白血病,但依然堅持完成了《大地上受苦的人》(1961)。同年,法農先在莫斯科接受一段時間治療,后又轉到美國國立衛生院。1961年12月6日,法農病逝他鄉。
當今的世界格局和法農所處的時代早已不同。與時俱進的讀者細讀文本也不難發現,《黑皮膚,白面具》當中的個別觀點、有些例證也確實存在論述過簡、有失偏頗的地方。然而,這絲毫不會削弱本書傳達出來的那種與殖民種族主義決戰到底的豪邁之志。法農的生命是短暫的,但他傳遞的力量卻異常強大。他投身反殖民斗爭的事跡或許會被歷史所淡忘,但他留下的這些文字卻像一部不朽的經典,永遠以他澎湃的斗志和無畏的精神鼓舞著人們,去與任何形式的歧視、壓迫、剝削與暴政展開不屈不撓、毫不妥協的斗爭。只有世界人民真正贏得勝利的那一天,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寫道,人們才會看見“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陸泉枝
2022年夏初 于上海
參考文獻
Fanon,Frantz.Peau noire,masques blancs.édutions du Seuil,1952.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Faust.Verlag C.H.Beck,1986.
Heidegger,Martin.“Language,”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2nd ed.),edited by Vincent B.Leitch et al,W.W.Norton&Company,2010,pp.985—998.
Marx,Karl.“Theses On Feuer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