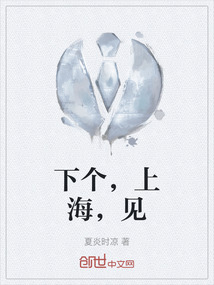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少年的風旅
邁入車門的那一刻,我承認,我開始舍不得了。下一個站點,是上海呢,我們在那兒見吧。
高二的最后一個暑假,我已被學業摧殘得,仿佛久旱大地上一條垂死掙扎的魚了。一個姍姍來遲的消息,卻讓我瞬間沐雨回春:我能去上海了。
父親因工作調動,從小城鎮調到了大都會,順帶把我也捎上了。就這么搖身一變,成了新上海人,美妙得就像在做夢一樣。
還有多久才能到?大城市是什么模樣?那兒會有屬于我的天空嗎?我在奔騰的高鐵上不住地幻想。
一晝與夜的灰森林
鄉巴佬進城,是什么樣的感覺?
寫字樓直聳入云,多米諾骨牌般地直插在一望無垠的地面;街道縱橫交錯,切豆腐似的劃分出不同區域;紅綠燈的號令下,人啊,車啊,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里川流不息;我像是螞蟻,跟隨著父親的腳步,鉆進鉆出在混凝土中生長出的樹里…所聞所見,都讓我感到熟悉又陌生。
入夜了。城市一改它白日里的單調肅穆,露出俏皮又妖艷的一面:霓虹燈亮起,高樓大廈披上了華裝,粉墨登場。蜿蜒曲折的街道燈火通明,承載著絡繹不絕的光點。隔江望去,對岸朦朧得仿若童話世界:東方明珠一枝獨秀,托舉著整片魔都的輝煌;其下,卻并未被其遙不可及的光環掩蓋,反倒流淌著萬千星光。夜上海的一切,都是那么地令人心馳神往。
小村莊里,夜意味著一天的結束。但在上海,生活才剛剛開始。
但我不能停留。我的棲身之所,不在這里。
二城鄉結合部的異鄉人
到了。我又一次覺得自己在做夢…
“城鄉結合部”——這是我對老閔行的第一印象。如果說黃浦代表了上海在商業上的精致,如盧浮宮里參展的油畫一般,那閔行,便是老上海工業厚重感的真實寫照——只能用狂野到不修邊幅的素描來形容。
鉛筆畫般的粗線條勾勒出房屋和街道,灰蒙蒙的,像烙著擦不干凈的鉛筆印子。較之于商業區這個光鮮亮麗的大小姐,他們成了廠里最樸實無華的工人,腳踏實地為這座城市創造財富;抬頭,天橋如長龍橫跨其中,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只留下一串串汽車的鳴笛;遠方,一只煙囪探出腦袋,它已不再呼吸。
朝著它的方向,我來到了這家廢棄的工廠。和無人問津的寶藏一道,埋藏在蔥蘢的綠意里。爬山虎漫步于不再無垢的墻,隔著門縫望去,雜草肆意地生長,早已不復當年模樣。鐵門銹跡斑斑,向我訴說著歲月的痕跡。靠著它,我聽見了它的心跳。
聽父親說,這里曾是全上海首屈一指的工業中心,享有“四大金剛”之一的美譽。只不過,隨著商業化轉型,逐漸跟不上趟了。
明明差了沒幾里,卻好像隔絕出了兩個世界。
這里不比市區的寸土寸金,但我們仍舊買不起房。只得寄人籬下了,就住在黃浦江邊上。房子最好依山傍水,看,我贏了一半呢。
我喜歡江邊吹來的風。這也是為數不多的,能讓人慢下來的地方。約是晚飯后,這兒便會熱鬧起來。大人牽著小孩,手挽手走在江畔的步道上。向前走,沒幾步就能撞見路演的青年人,通常伴著一把吉他,唱著青春,唱著感傷,唱著倔強。只可惜我囊中羞澀,象征性地給了二十塊。隔著護欄,總有頑皮的孩童拿著竹竿,伸塊五花肉下去吊螃蟹。他不吃,只是拿來把玩。都怪你,又讓我懷念起幼時逗螞蚱的時光。記得每次經過,都是一片黃發垂髫,怡然自樂的景象。江上時不時有船,我的思緒也容易被它載去遠方。
我喜歡這里的氛圍,使我心馳神往,飄飄然到差點忘了——忘了自己是外人這個事實了。
公寓樓里的生活氛圍很微妙。雖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彼此間卻并不熟悉。出門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連打招呼的工夫都省了。是啊,大家總是那么忙,大城市的生活,總是那么忙。
唯獨剩下周末的好時光。本地的熟人常相互邀約,或聚餐,或野營,或遠游,或相聚一堂……
而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人,怕是只有顧影自憐的份了。我不愿承認,每個周末就干脆躲進公園里。
不和陌生人互動,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遺憾的是,異鄉人“回家”的可能,也就這么被剝奪掉了。我也是頭一次感覺到,自己的天地,原來那么小……像什么?像籠子里的鳥吧。身體在這兒停留,心卻無處安放。
三地上巴士地下鐵
我十七歲的單車落在了老家那邊。出行基本只能靠公交。
我不是沒搭過地下鐵。但還是頭一回,擠進這么擁擠的人群。
人經常多到摩肩接踵的地步,卻連聲招呼都聽不見。大家都自顧自地,自娛自樂著。下一站,誰上來,誰下去,無人在意。畢竟快節奏的上海,就是一輛永馳的地鐵,沒有時間為他人停留。
但我還是喜歡搭地鐵,喜歡那種空間變換帶來的驚醒。就像鉆進愛麗絲的兔子洞里一樣,只消一會兒,就到達了另一片天地。尤其是從地鐵站出地面的一瞬間,追尋著出口的光點,頗有撥云見日的感覺。
相較之下,巴士就普通許多了。一般只有去補課會搭。等車,上車,投幣,下車,一路的平鋪直敘。除了我不曾留意的窗邊景致外,與那邊的巴士并無不同。
四悶棍、金魚和歪瓜裂棗
新的校園生活并沒有想象中那般精彩。這兒的學習氛圍比那邊輕松,此話不假。但躺著能上交大,那就真是扯淡了……走到哪兒,都還是得好好學習。
學習之余,才能省下交友的時間。來之前,媽媽總忽悠我,說大城市里漂亮女生多…或許是吧,但我們這兒,只是個“類城鄉結合部”啊…學生沒我老東家那么土,但也好不到哪去……
好在,比那群小區居民開放許多。初來乍到,就受到了一位歪瓜裂棗的歡迎。這么形容可能不太禮貌,但他確實是那個模樣和氣質…好在性格不錯,是我來這兒交到的第一個朋友。他是老閔行這邊土生土長的,一等一的地保。在他的帶路下,確實添了樂趣,省了麻煩。
漂亮的女生算珍稀動物。有個鵝蛋臉,波浪卷,扎著低馬尾的,我喊她“金魚”。因為馬尾絞出來的花紋很像。起初她還鼓起臉以示抗議,后面就習慣了:“再這么叫,就用我的魚尾巴甩死你哦?”她笑起來很漂亮。
上海是很國際化的,尤其體現在國際生這方面…記得那時,學校里嚴防死守抓早戀,當我正想為她以身試險時…她出國了……
還有個詩人一樣的角色。戴眼鏡,斜劉海,平時總鎖著憂郁的眉頭。一看就知道是文藝青年的那種。我叫他悶棍。沒事總想些復雜,又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我深受其害。
忘了說了,我們的教學樓是四四方方、長條狀的,四面環繞地圈起一座池塘。像客家圍樓一樣,只不過它們“圓”,我們“方”。里頭養了各色錦鯉,可能寓意著有朝一日,魚躍龍門吧。課間十分鐘,我們最常做的就是倚著欄桿看魚。
那天,如往常一樣,我們臨淵羨魚,談天說地。
“你有沒有想過…”
“嗯?”
“魚要是會說話,會怎么評價我們啊?”他指著一尾色白花青的錦鯉說道。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我搪塞。
“…總覺得,我們和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像沒聽見一樣,繼續自說自話著。
“從早到晚都困在這教學樓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所以它們一開口,大概會說…”
“笑什么笑?你們不也活在池子里嗎!”
壞了,他惹得我也開始思考人生了……
五海納百川
剛來那會兒,我總是以“異鄉人”自嘲。戶口落得很容易,也是托父親的福。但總感覺,自己不屬于這里。除開衣食住行上的不適應,還有心靈上的那種無所適從。
轉變是從哪里開始呢?大概,從我轉來后被新同學接納開始吧。那也是自抵達上海以來,第一次有“啊,我被人需要著”的感覺。
人啊,說到底還是群居動物。但在小區里,總是行色匆匆的,自顧自地活著。一個個的好像一座座孤島,并建起厚厚的墻壁,把心鎖在這里。唯獨在校園,有機會打破壁壘,建立聯系。就這么一來二往,上學反倒成了我最期待的事了。真是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俗話說,近朱者赤。跟他們處多了,我的舉手投足,也逐漸帶有上海人的調調了。
高中的時光還是蠻單純的,白的像梔子花一樣。學歷、人脈、家庭背景被統統棄之于地,交往全憑感情。連我這種不善交往的人,都能和他們打成一片。也是在那里,第一次展現了真實的自己。
老朋友偶爾也會來找我玩。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就樂呵呵地領著他們滿上海跑。外灘、五角場、上海中心、東方明珠…可以的話,也會去趟迪士尼……我盡可能地把一切考慮周全,自那時起,開始考慮禮數周到與否,開始揣度是否盡了“地主之誼”。
回想起來,從“拒斥”到“接受”,這個轉變過程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如春風化雨一般。多歸功于這座城市的文化特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好像沒有什么外來文化,是上海吸納不了的。一切“外來的,都能被它兼容并蓄成“自己的”,并推而廣之。海派文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上海還真是…不可思議啊。
我承認,開始喜歡上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