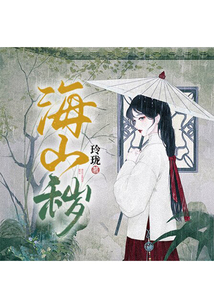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玲兒墜
定親方沒幾日,我的未婚夫沒了。
說是撞上仇家,當街被捅了刀子,連著當時同路商議婚事的我父母也沒放過。
同一天里,我成了孤女,也成了未亡人。
民國三年,驚蟄,宜納彩忌祈福。
農歷二月才開頭,北京城的冬還沒緩過來,煤市東街上,卻擠滿了人。
好大一支人畜招搖的隊伍,樟木妝奩、西洋穿衣鏡、四匹棗紅大馬、兩頭小黑驢,另有一兩人抬的大箱子跟在后面,喜洋洋美滋滋披紅掛綠好不喜慶。
縱是沒有嗩吶開道,也不妨人知曉這是一只送彩的隊伍。
最打眼的,還是隊伍頭上那個人,一個碗口粗的竹筒,上頂著托盤,下抵著腦瓜頂,既不抖也不晃,大搖大擺走在最前頭。那托盤里墊著紅布,紅布上金燦燦一根寸寬的金條。
能撐得起這場面的,莫說煤市東街,橫看半個南城,也只那一家……
彩禮送的上臉面,收禮的人家卻未見得喜。
“可不能啊,不能讓玲兒入洪家啊……當家的,可不能啊。”
“這有什么不能的?人家洪家二少爺是續弦,明媒正娶。”
“那是洪家……”
“廢話,就是洪家,才拒不得!”
“訥訥,誰家的東西?”清脆脆的聲兒斷了屋內爭執。
“這孩子,咋不知敲個門。”那福隆借責備掩飾尷尬,榮氏趁機扭頭抹了臉上的淚。
那玲兒歪著頭,水盈盈的杏眼眨了又眨,她一早就被父親支去了叔公家送東西,這會兒回來,才進胡同子就有人跟她道喜,再看這滿院子的東西,還有什么不明白的?
“瑪瑪剛才說什么洪家?”那玲兒又問。
那福隆回手拿過煙匣子,對著里面三兩個煙袋鍋左挑右選,又是填煙絲,又是對煙火,好半晌才鼓搗出個煙圈來,煙圈聚了又散,話卻沒一句。
“瑪瑪不吱聲算怎個回事?可是煤市東街的洪家?”末了還是那玲兒自己回了自己的話。
“你也17了,這么大的閨女算出閣晚的了,洪家……你也知道些,咱家關里跑山貨,來回的路子都靠洪家,跑山人沒有不過洪家的。你嫁過去,也算享福了。”那福隆鼓了口煙,圓眼珠半耷拉著眼皮,像一只沒什么精神的京巴狗。
“跑山人沒有不過洪家的……八大胡同里那些個掛粉紅燈籠的院子和海山賭坊呢?他們過不過洪家?”那玲兒盯著空中徐徐散去的煙氣,冷了一張俏臉。
這話把榮氏剛抹干的眼淚又引了出來。
“當家的,回了吧,那樣的人家……咱高攀不起啊!”榮氏哭著跪倒在那福隆腳邊,反倒把那福隆惹惱了。
“回什么回?這樣的婚回了,我那家關里的買賣還做不做?我這大個家業就為這毀了不成?你別一天哭唧唧的,這明媒正娶,你不樂意個什么勁兒?
要不是人家洪家想跟在旗的結親,你以為能輪著咱那家?要不是我從小把玲兒當小子養,又是請先生又是見世面的,你以為人家能瞧上咱?這是我那家幾輩子攢出來的緣分,行了,起來吧!”那福隆急吼吼地喊,好像自己這輩子嘔心瀝血培養她費盡了心思。
“那是您那時候沒小子,這會有小子了,姑娘就不當人了,往開妓院的人家送……”那玲兒最是聽不得這話,梗著脖子回嘴。
“啪”一巴掌抽在臉上,沒說完的話給憋了回去。
那福隆走了,他是氣的,莫說他在外面養個女人,就是娶進門來,又能怎么的?這丫頭真是自小給慣壞了!
“訥訥知道的吧?前兒我去店里,大人孩子都帶去了,伙計前后圍著喊小東家……”
那玲兒又氣又委屈,那孩子都五歲了,五歲……那玲兒自小做男孩打扮,十歲開始被那福隆帶著關里關外的跑山貨,到十二歲的時候,突然不讓她跟了,也不允她跟先生讀書,連店里也不讓來了。
只說世道不太平,正趕上各地鬧兵亂,訥訥也愿意她在家,這才恢復了女孩模樣。這會兒看,不過就是早年間沒兒子的時候,拿她當兒子養,真有兒子了,女兒也就不算什么了……
“男人嘛,外面有個把知冷熱的,常有的事。”榮氏性子軟,說的話也軟,眼圈卻是紅了的。
那玲兒咬著嘴唇福了福身子,走了,走得極快,斗篷兜帽上滾的貉子毛邊隨著步子搖晃,好像被那無端冷風打亂了的荒草。
二月十二,宜交易,忌會親友。
“瑪瑪、瑪瑪……訥訥……放我出去……”那玲兒連鬧了幾天,今兒更是一早給鎖在了屋里。
“小姐,別鬧了,老爺和夫人都出去了,胳膊擰不過大腿,陳媽瞧見了,洪家二少爺二十出頭,跟你年歲相當,長得那叫一個俊,聽說上頭那個少奶奶是病歿的,留下個幾歲的奶娃娃,從小帶,一樣親。
何況那二少爺是受家里器重的,上面大少爺腿有殘,這以后偌大的家不都得是小姐你當家……”嬤娘陳媽在門外絮絮叨叨,說著那福隆囑咐過的話。
“訥訥也出去了?去哪了?”那玲兒眉梢輕挑,停了捶門。
“洪家來請期,日子定了,二少爺請未來岳父岳母去吃烤鴨哩!”陳媽喜滋滋地說,她也得了未來姑爺的賞,大買賣人家禮數就是周到,傲是傲了些——那樣的人家,不傲才怪哩。
那玲兒倚著房門,冬要過去了,冷風從門縫擠進來,吹在耳邊依舊刺骨,冷風吹涼了身子,也吹涼了心思。那些舊年里奔騰的心思都給這冷風扼住了,什么家里的獨生女,什么關里關外,什么山貨生意,什么去看看新學堂……都給扼住了……
被扼住的那玲兒,又一次伸手推向房門,冰涼、冷硬的木門像被冷風凝住一般,動也不動,那玲兒的手就那么抵著,直到手指凍僵,才恍惚聽得門外一陣嘈雜。
亂糟糟腳步聲近前,早前怎么也推不動的門“咔噠”一聲開了,開得輕易又痛快。
陳媽半個身子栽進來,哭嚎悲凄:“小姐……我苦命的小姐啊……”。
越過陳媽,那玲兒看見了警察。
警察是客氣的,少見的客氣。可嘴里的話卻說得那玲兒渾身冰冷。
“節哀……”末了,眼見著為首的官爺嘴開了又合,她使勁地聽,卻也只聽見了一陣嗡鳴聲,聽不見、什么都聽不見。
“陳媽……”警察走了,陳媽還在哭,那玲兒抖著腕子扯住她,大聲問。
“他們說的啥?我……聽不清……”那玲兒只覺得自己耳朵里嗡嗡作響,響得心煩。
“小姐……小姐……怎么辦啊,怎么遇見這種事呢?好端端的三個人,怎么就沒了呢?說是有人尋仇,咋就尋到咱們頭上了啊,老爺和夫人都、都……咋這洪家二少爺他們也敢動手啊?這可如何是好啊……禮也過了,日子也定了……這是、這是……我苦命的小姐喲!”
陳媽說了一堆,那玲兒還是聽不清,可明明聽不清,眼淚卻落了下來。
哭了半晌,迎著冷風吹得渾身打哆嗦,陳媽苶呆呆杵在一旁,臉上亦是兩條淚溝,不算渾濁的眼滿目茫然。
“洪家來人了……”門房扯嗓子跑進來,慌的。這個時候的那家,沒有不慌的,人人都聽見了,人人都知道了,那福隆和榮氏在去飯館的路上被人捅了,就連洪家二少爺都沒躲過去。
四五個練家子從墻上跳下來,不問不喊直接甩刀子,誰能想到在自家地盤碰上茬子。
洪家二少爺一點準備沒有就讓人割了脖子,那福隆路邊撿了塊石頭還沒來得及扔,就讓人捅穿了肚子,榮氏嚇得直嚎,也給人捅個對穿……消息早就傳遍了,甚至比警察說的還仔細。
洪家送來了那福隆和榮氏的遺體,來人是個會辦事兒的,里里外外說得明白、說得得體。
“大少爺交代了,日后二少奶奶的事兒就是洪家的事兒,人生無常,遭逢如此變故,洪家日后就是二少奶奶的依靠……”那玲兒耳中還雜著嗡鳴,眼盯在已入了棺的二老身上。
棺是上等的杉木,那福隆身量不高,想來這棺木是臨時購置,對內里的人來說過于寬大了,榮氏的棺尚且合體,可內里的身子卻僵直得駭人,刻進面容的恐懼并不曾隨著生氣一起消散。
“辦喪有小的們,二少奶奶緩緩心神,莫壞了身子……”那人還在一樣樣交代,那玲兒卻只覺得冷,從心里往外的冒著寒。
這寒比那擠進門縫的冷風要命多了,這會兒子想來,那算什么冷呢?不過是自己矯情罷了,嫁人而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樂呵呵應了多好,何苦鬧那幾天,二老臨了也沒聽著句好話兒……這人,真就沒得這么輕易?她不信,她不能信!
“真是尋仇?洪家想怎么查?可能還逝者一個公道?”那玲兒盯著棺,含著淚,聲兒清冷得像數九寒冬里凍脆了的冰棱。
來人頓了頓才應:“回二少奶奶話,青天白日里的命案,自然都托給了警察署,署長那邊大少爺打點過了,二少奶奶緩緩心神,在家安心服喪,莫壞了規矩,外邊的事兒自有外邊的人操心。”
黑道兒尋仇的事兒托給警察署?這天底下的稀奇事兒還真都讓她碰見了?她不信!
那玲兒想說點什么,可她只覺得自己像冰天雪地里的一條魚,張著嘴,沒有聲兒,甩甩尾巴,尋不著水,拼了命的勁兒都使出去,沒得一點用。
說什么?憑著她?聽聽人家的話“外面的事兒自有外邊的人操心”,她這會兒子還能說個什么?
隱隱的猜測引出無端寒意,凍得嘴皮子發抖,肩膀隨著呼吸輕輕地顫,旁人眼里看來,是道不盡的悲。
那玲兒沒言語,洪家人沒言語,誰也沒言語。
待嫁的新婦,眨眼就成了孤零零的望門寡,克死未過門的丈夫,還克死父母,這樣的女子,這輩子,大抵就是如此了……
改朝換代的日子過得人心惶惶,越是沒味兒的日子,人就越愛看熱鬧,咂嘛咂嘛別人的熱鬧,自己的日子也就有味兒了。
有時候生怕熱鬧不夠味兒,還得自己再加上點佐料,佐料是咸的,每一次加料,都是在苦主傷口上撒鹽,可看熱鬧的人不在乎,他們在乎的只是這熱鬧好不好看。
那家的喪在看熱鬧的人眼里,倒是連鹽都不用加……
二月十三,宜交易,忌納喜。
那家從來沒這么熱鬧過,小院子里十幾個人忙忙活活唱喪,胡同里也支了喪棚,花圈白布掛了半個胡同,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往院里進,對著靈棚拜的涕淚橫流,左一句那公,又一句老親翁,那福隆這輩子都沒得到過這種禮遇。
那玲兒站在靈棚旁,一身重孝,頭盤髻,簪白絹。
頭一次盤發不是為喜,反是為喪,待嫁的姑娘轉天兒就成了守寡的婦,她大抵也算那家祖上頭一個了。
“小姐、小姐,那、那……那女人帶著小、小子來了,要歸宗……”陳媽慌張張跑進來,話跟燙嘴似的不知該怎么說。
那玲兒卻聽明白了,不光聽明白了,因著唱喪的聲停了,她還聽見了女人的哭聲兒。
一身孝的女人領著孩子一路哭喊,進了靈棚拉著孩子就要叩頭。
“我的老爺哎……我給您送行來了……你這走了,留下我們孤兒寡母……”女人嗓門大,哭得慘,竟沒人上去攔。
那玲兒氣得渾身發抖,回身掄起圓凳砸過去,人群這才亂起來,拉架的拉架,勸和的勸和,攆人的攆人。
陳媽扯著女人頭發往外拽,女人沖進靈棚抱著棺木不撒手,孩子淌著鼻涕哭嚎……好一通亂,亂得那玲兒心頭起火。
“你是個什么東西?你是過媒了還是下定了?跑我那家來認親了?這頭是你說磕就磕的?轟出去!”那玲兒一通喊,陳媽立馬下死手,女人滿腦袋白絹花掉了一地。
“虎子是那家的兒子,你不能轟出去,這一支就虎子一個根兒,列位宗族長輩給個公道啊!”女人倒也不是軟柿子,既然來了,自然也就沒做和和善善的準備。
族里來幫襯的兩個叔公,面有難色,那福隆外面養兒子的事兒,他們是知道的,那福隆準備今年把人抬進門的事兒,他們也是知道的,那是兒子,總不能扔外面,何況提前還收了女人遞的銀子……
“既然是那家的種……”到底有人開了口。
那玲兒扭轉頭昂起脖頸,舊日里水汪汪的杏眼冰刀一樣看過來,聲兒大得近乎破音:“我訥訥還沒入土吶!”
這一聲喊,讓開口的人虛了心,那福隆的生意是靠著榮氏家里起來的,不然哪里能這些年沒讓人進門。頭兩年那玲兒外祖沒了,榮氏又性子軟,那福隆才漸漸起了心思,可到底那家承著榮家的恩呢。
“我的老爺啊,那家不容人啊,我就和虎子去陪您吧……”女人見沒人幫襯,扯嗓子又是一聲嚎,貓起身子就往墻上撞。
女人是真下了狠,撞得使勁,“哎喲”一聲直挺挺翻倒在地,眼前一片白,半晌沒覺出疼。
她撞上的,是那玲兒拋過來的紙牛,人撲在紙牛上,壓碎了竹坯框,紙碎做的鬃毛落在冷風里嘩刷刷亂響。
“那家的喪,你見哪門子紅?”那玲兒氣得恨不能伸手扇她幾巴掌。
“娘……娘……”
“喲,洪家來人了!”
也不知道是小孩子扯嗓子的哭還是礙著門前的洪家人,那玲兒轉了話風兒。
“等喪辦完了,我給你句話,真是那家的孩子,也不能讓他流落外頭學那不三不四的,我家是行喪,不是絕戶,說話的人還跟這站著呢!”末這一句,是說給旁人聽的,在院里的,在院外的,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旁人。
那玲兒話說完,也不管紙活堆里趴著的女人,也不管那想開口又礙著洪家人的族叔,徑直往門前迎去。
洪家人是來磕頭的,來的是大少爺身邊的人。
哀樂再起,唱喪的聲兒又灌滿了那家院兒。
“貴客惜別……”知賓顫巍巍喊。
一應的禮作罷,洪家人沒走。
“二少奶奶節哀,大少爺有話兒,兩邊都是喪,二少奶奶先盡孝,自家這頭人多,忙得過來。等事兒了了,西邊臨山那頭有座庵,什么時候想清靜了,什么時候送您過去。”這話兒說的沒背人,聲兒倒是不大,可該聽見的都聽見了。
那家的熱鬧算是傳開了,停靈頭一天,外頭的女人帶孩子鬧喪,那家姑娘摔凳子砸人,洪家來人瞧見嫌沒規矩,要給送庵里去,那家的產業給族里人盯上了……
傳言就像預言,比那半仙掐卦還準。
接下來的日子里,族里那些一年到頭見不著幾回的三叔六公全來了,無一不是勸她把外面的孩子收回來,若是她看著礙眼,他們可以代養,到底姓那,總不能讓她瑪瑪九泉之下不安心……
那玲兒先是不言,后是怒罵,一個兩個惦記的都是那家那點家產,去大留小這種事都好意思拿來說,只差沒說等她去了庵里,他們就來接房子……
驚蟄雖過了,到底不是春,夜寒得襲人骨縫。
那家亂的得一塌糊涂,陳媽病了,門房日間累了,夜里睡得死,原本也不是什么大戶人家,除了白日里做飯的廚娘,也就一個短工,眼見那家出事兒,結了工錢走了,這會兒連個燃炭的人都沒有。
夜寒,不在開窗。心傷,不分晝夜。
那玲兒坐在榻上,裹著棉被,淚珠子一串串滾,除了淚,一聲也無。白日里說了太多話,罵了太多人,這會兒,除了哭,她什么也不想做,更不想睡,怕睡了再醒……又是白天……
夜,總會明。人,總要活。
好容易熬到出殯的日子,洪家是賞了面子的,胡同喪棚里紙活堆得小山似的,清一色的細坯泡紙,工精活細還好燒,送喪的隊伍更是排出一整條胡同,紙牛紙馬開路,喪樂震耳,哭聲連天。
不賞面子的,是那家自己人。
“你一個閨女家,打什么幡兒?又不是沒兒子!”
“你一個望門寡去給爹娘摔盆摔瓦?扯淡呢嘛!”
“有兒子就讓兒子來,你瑪瑪下去見了列祖列宗也有面兒!”
那玲兒舉著幡兒站在棺前,腦仁疼得直蹦。
屋漏自然還得趕上連夜雨,不知哪個王八蛋接了外面的女人和兒子過來,讓她鬧眼睛。
女人作勢要哭,那玲兒揮著幡兒沖過去,給死人引路的白幡兒碎遭遭戳在女人眼珠子前,忌諱的人忘了嚎。
“你兒子姓那,你可不姓,去大留小不是難事兒,這會兒給人當刀使,自己跟外面讓人抹了脖子,你哭都沒地兒哭!”趁著女人怔愣,轉又從腰間抽出一柄小刀來。
嵌八寶的小銀刀,那玲兒早年跟那福隆跑關外時候得的,一直喜歡的很,比巴掌大不多少,可戳破脖子還是夠的。
女人給嚇了一跳,扯著孩子往后退,刀卻架在了那玲兒自己頸子上。
“幡兒,閨女不讓打,還有遠房的子侄,輪不著旁的人,不行,今兒你們就再葬一個!”眼是紅的,聲兒是冷的,心底是厭煩的,那玲兒這些日子只覺出一個厭煩,這樣的日子,使人厭煩,要真能這么了了,也不是不行。
眾人又驚又怒,這當小子一樣養大的孩子竟沒規矩到這個份上,敢跟族里長輩叫停。
幾個老頭想上前,卻被門外人聲打斷。
“怎么著?那家能耐了?要逼死我洪家的媳婦兒?”聲不高,音色也是好聽的,卻沒人敢答話。
礙眼的人一個接一個讓開,只剩下舉著刀的那玲兒對上輪椅上的那雙眼。
眼深,色沉,深潭水一般。
滿院子的人,一聲也無,鬧哄了好些天的那家院兒里,頭回靜得連頭發絲兒落地都能聽見。
那玲兒長出口氣,安靜啊,真好啊,她覺得有些無力,卻只能使勁兒挺直脊梁,瘦弱的身子裹在棉袍里,一身重孝,讓她看起來像朵開在關外雪地扎根冰層下的冰凌花。
“給親家翁送行。”輪椅上的人開口。
“洪大少爺。”那玲兒收回刀見禮,不用人說,她能猜出來,除了洪家大少爺洪長年,還能是誰呢?相傳大少爺早年傷了腿,洪家的買賣才轉了一半到二少手里,為此兄弟倆還鬧了一陣子,傳言總歸是聽過的,更何況推輪椅的正是那日來傳話的人。
洪長年燃了三支香,合十做禮,他的身份,他的身體,縱使晚輩不行大禮,也是應當。
禮數盡了,洪長年才擺手道:“送老二那天,洪家來人接你。”聲音是溫潤的,人也長得周正,只是常年不良于行,略顯清瘦了些。
那玲兒盯著深潭一樣的眉目,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洪家人走了。
喪樂起,哭聲哀,沒有哪個遠房子侄敢接幡兒,白幡兒扛在了那玲兒肩頭,也再沒人敢多說一句。
從送去庵子里尋清凈到接進洪家送二少爺……洪家的態度,變了。
二月二十七,宜安葬,忌合婚。
那玲兒今兒的孝與早前不同,白麻斜襟襖子外三尺孝布圍腰,頭戴本白的“箍子”,發髻上的花倒是照舊。
天未亮便出門,不過七八日,人又瘦了幾分,越發顯得孝服寬大。洪宅門臉寬,偌大的正門,那玲兒輕飄飄的腳步邁進去,活像誰丟了的魂魄,生氣微渺。
卍字云紋的青磚影壁,門堂里闊得能停下人力車,這樣的人家哪里像個民宅?可它又的確是個民宅,普普通通的如意門,門簪小、門墩無,倒也不曾越制,可這門造得卻比廣亮大門還寬,內宅之大更是恨不能跨出半個胡同。就是這樣的宅子,偏生落在煤市東街這種地方,可這是洪家,也就不稀奇了。
那玲兒隨著管家媳婦往里走,直奔西苑靈堂,黑漆漆的夜,看不清洪家到底多大,只覺走了好半晌才到。
偌大的靈堂,跪了好些人,卻是一聲也無,沒有尋常人家的哭喪聲。
“二少奶奶今兒辛苦。”管家媳婦站定在棺旁,一旁的丫頭立馬捧來蒲團。
那玲兒跪坐下,盯著牌位上的名字——洪長生,這是她頭一回看見自己丈夫的名兒,也只有名兒。
那玲兒跪在那,看著牌位,挨著棺,身后守靈的人換了兩班,那玲兒沒動過,腿麻了,膝疼了,可她不想動,她現在一靜下來就不想動,靜啊,太難得了……
洪家也是真的靜,沒人理她,沒人看她,就好像沒她這么個人,那玲兒忍不住暗嘲自己一句“在哪兒都是不得待見的人”。
夜就這么過了,東方既白的時候,靈堂外隱隱起了動靜,靈堂里的人越發少了。
“該添油了。”那玲兒盯著牌位旁已開始炸花的長明燈輕聲道。
身后垂了半宿腦袋的丫頭立馬起身,動作利落地添油換蠟,末了還給那玲兒行了個禮。
那玲兒挺了挺腰,垂著的眼沒敢抬,怕露了怯。她本是嘀咕一句,沒想到真有人應,真有人動,還有人給她行禮,看來,在洪家倒比在自己家的人高看些。
大殮之禮,孝子賢孫扶棺送靈。
可洪家二少爺的孝子太小,扶不了棺,只著人背著,手里拿著幡兒。
那玲兒站在棺旁,看著那小娃,不過四五歲模樣,俏生生的眼紅得可憐。
“別哭了。”那玲兒忍不住拿帕子替他抹了抹淚。
“嗯嗯……你誰啊?”小娃卻不領情,揮手推她。
“我……叫那玲兒。”那玲兒不知該怎么介紹自己。
“你在這兒干啥的?”小娃抽抽搭搭地問。
“送你爹。”那玲兒如實答。
“送哪去啊?”小娃聽著了想知道的事兒,忘了哭。
“送去一個安靜的地方。”那玲兒歪頭。
“死人都去那嗎?”小娃這話問得不像個小娃。
“嗯,我爹娘前幾天送過去了,他們沒回來,想來是個好地方。”那玲兒抿嘴笑,笑著笑著,淚下來了。
“大大說了,人都是要死的,你哭啥呀?”小娃勸她。
那玲兒又笑了:“你知道的還挺多,那你眼珠子是為啥哭紅的?”
“哇……”這一聲問,算問到小娃的傷心處了。
“我想爹爹……”小娃哭得直抽,嚇壞了身底下背著他的人,慌張張把小人兒放下來,小人兒索性跑到那玲兒身邊兒要抱。
“我瞧你不錯,以后伺候孫少爺吧。”小娃邊哭邊把鼻涕抹在那玲兒的衣擺上,他就是孫少爺,大家都這么叫他,他也就這么叫自己。
那玲兒哭笑不得,抬眼間,有人推著輪椅進了院兒,小娃也重新又給背了上。
還是那張周正的臉,還是那雙深潭一樣的眼,沒說話,沒動作。
“不知他們兄弟是不是長相有似……”那玲兒如此想著,卻不曾扭頭看向身后棺木,她好像從沒想看過棺里的人。
陰陽先生起調兒門,喪樂聲里棺木起,如龍一樣的送葬隊伍出了洪家大門,那玲兒和一應女眷送到門口,飄灑灑紙錢落下,哭喪聲又起,有撕心裂肺的嚎,也有抽搭搭的哭,更有人踉踉蹌蹌奔出門跪地叩頭……
這才是喪,是家里有人的喪。
那福隆和榮氏走的時候,除了那玲兒,一聲真哭也無……
那家,沒人了……
三月初一,宜嫁娶,忌破土。
那家外面的女人又來了。
“頭七才過,你就這么急?”那玲兒沒有好臉色,她不是生氣,她是真的病,頭疼得挨不住。
“你總要給我句話……”女人原本是鼓著氣勢來的,可這會兒不知怎的,她有點怕那玲兒,真沒見過哪家未嫁的姑娘這么橫的,砸人打人還拿招魂幡指著生人,嘴里也利索,雖沒什么難聽的罵,可句句戳人脊梁骨。
那玲兒看著虎子,五歲的孩子,比洪家小娃大不多少,圓臉大眼,的確是像那福隆的。
“那家,你可以進……”那玲兒抬眼看向女人。
“這宅子你不能進,這是我訥訥住的地兒。”后面的話定住了女人半笑不笑的臉。
“山貨行,給你吧。”那玲兒這話說得輕巧,心里的悲涼卻恨不能縊死人。
“那咱明兒立個字據。”女人壓著翹開花的嘴角,忙不迭上前一步。
那玲兒狠壓眉心:“行,不傻,立吧,那家的東西給你兒子護住了,日后你們娘倆是升官發財還是餓死街邊,與我那玲兒無關……”話沒說完,女人跟想起什么似的,挑著眼又開口:“虎子到底是那家的兒子,這好歹是那家祖宅……”
“啪——”那玲兒手里的茶碗拍在桌幾上,女人的話給嚇了回去。
“祖什么宅?那家是什么大戶人家不成?還祖宅?這是我瑪瑪和訥訥早年間置辦的,那家祖上就是個包衣,你真以為在旗就是大戶人家了?大清亡了,滿族人不值錢,你也甭想著這宅里是不是有什么金銀財寶,有,我也不給你!”那玲兒騰地起身,女人嚇得扯著孩子就走,走得頭也不敢回。
那玲兒長出口氣,身子軟在椅上,清凈了,可怎么這么乏啊,才一個月不到,就跟過了半輩子似的。
三月初四,宜動土,忌遠行。
洪長生的頭七一過,洪家人就來了。
那玲兒看著罩了黑紗的人力車,耳邊是陳媽嗚咽咽的哭,半天才挪了一步,一步腿就軟了,每向前一步,就是靠近絕路一步,幾步遠的車,黑漆漆的紗被風吹得鼓起,紗后面不是座子,是再不能見光的人生……
“不、不去庵里。”那玲兒邁出去的腳往后撤,她本是打算認命的,山貨行都給出去了,她還有什么不肯認的呢?可這會兒看著那黑蒙蒙的車,她害怕了,后半輩子,就這么黑蒙蒙地過?不,她不想。
可沒人管她想不想。
“不去庵里,那小的就替洪家謝二少奶奶守貞。”話音未落,人群里上來個小子,托著三尺白綾。
“青天白日,你們要害人命不成?”那玲兒唇不見血色,自古寡婦兩條路,孤零零守貞的活,痛快快守貞的死。更何況,望門寡的媳婦喪期里自殺,官家是要賞烈女牌子的,洪家又有什么不敢呢?
“二少奶奶總要挑條路走……”洪家人垂首,態度是恭敬的,恭敬而冷漠。
那玲兒扭身要走,洪家人呼啦啦圍了滿院兒。
“二少奶奶是見過世面的,您這身份還這么住這兒,不合適。”洪家來的還是大少爺身邊的人,四十上下的中年漢子,身材壯碩,說話難聽,可態度柔和,柔和地勸人去死。
話沒說完,白綾小蛇一樣攀上脖頸,自縊,何須登高,有個人跟后面勒住了,兩手下壓,一扥,氣管就壓住了,再一扥,脖頸就折了……
冰涼涼的白綾,刀子一樣壓在咽喉上,吸進來的氣兒已開始不夠喘,喉骨壓向內里,針扎似的疼之后是鋪天蓋地地暈……
“好、不、不住、這兒……”掙扎著吐出幾個字,白綾松了氣力,冷氣涌進肺里,激起猛一陣咳。
“請二少奶奶上車。”話還是恭敬的。
那玲兒扯落白綾,咬牙看著地面:“我要進洪家,既然得你們稱一聲二少奶奶,那我就去看顧孫少爺,娘帶兒子,總合規矩吧?”清凌凌的聲兒落地,像折斷的冰棱,鋒利又清脆。
裹著黑紗的人力車走了,那玲兒透過黑紗看著夕陽余暉,雖不大清,到底還有光……
那玲兒這次進的,是洪家的側門,東側門。
輪椅咕嚕嚕壓過青石板,洪長年身上蓋著厚厚的大氅。
深潭似的眼盯著那玲兒。
那玲兒張了張嘴,突然笑了。
她原本想問不去庵里是不是就真要殺了她?她以為他是好人。然后她就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洪家怎么會有好人?
煤市東街的洪家,下九流里最說得上話的人家,八大胡同的掌旗人。逼良為娼、立賭做局、壓碼頭抽成、籠消息訛人、捅刀子茬架……這樣的人家,怎么會有好人?這樣的人家,是她巴巴上趕著要進的人家……
那玲兒笑了,笑得不甜,笑得不多,笑得像哭。
輪椅上的人鷹眉微蹙,洪長年沒想到她見了他是這個表情,就像他也沒想到她會拿椅子扔人,沒想到她真敢打幡兒,沒想到一個待嫁的姑娘竟一點不像個待嫁的姑娘……下邊人回的話兒里就已經給了他好幾個沒想到。
洪長年又笑了,眉頭展開,深潭一樣的眼映出微光,他真的笑了,縱是前邊那么多沒想到,可這會兒,她要來洪家,他卻是想到了的……畢竟,這是條活路啊……
夜,靜得能聽見風聲,沒有鳥叫,沒有蟲鳴,只有風聲,罕見的,洪長年覺得這吹過東苑的風除了涼點,聲兒還挺安人心。
“我愿進洪家看顧孫少爺。”那玲兒開了口。
洪長年沒應聲,也沒拒絕,一如那玲兒每次見他時的模樣,讓人看不明、猜不透。
“禮過了,孝也守了,洪家日后的規矩有一個算一個,我那玲兒都照著來……求大少爺,給條好活的路……”那玲兒福下身子,既然那家的女兒做不得了,她就做洪家的媳婦兒。
“呵。”輕笑出聲,深潭無波。
“送二少奶奶去西苑吧。”洪大少爺給了條活路,那玲兒跪地欲拜,卻被攔了住。
“進洪家,好活不好活的,不好說啊。”洪長年話說得柔和,像一句良言,良言難勸該死鬼的良言。
嬌小的人兒給送走,洪長年微抬手,廳外暗處閃出人來。
“盯著點,有什么不該有的動作……先報……看看這那家丫頭還能搞出什么想不到的事兒來,要真為了那家老頭的死來的,也算我沒白高看她一眼……呵。”洪長年溫和的語調一如既往,輕笑聲里周正的臉上滿目坦然,坦然得像個君子,正人君子。
輪椅壓著青石板咕嚕嚕走了,穿過風聲的洪長年,眉是蹙的,這會兒,他又覺得這風聲不安心了。
但,有意思……洪家,除了藏污納垢之外,很久都沒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