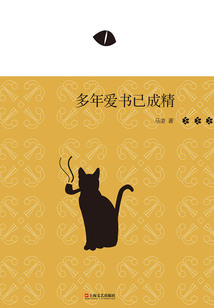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20章 代后記:多年愛書已成精
- 第19章 女神的朋友圈:成就她的有朋友,還有那個物欲橫流的世界
- 第18章 瘋狂與神性
- 第17章 劍橋往事:天真 八卦與毒舌
- 第16章 冰人夏洛特在無所之地的中央打開一只康奈爾盒子
- 第15章 另一個米開朗琪羅
第1章 書蟲指南:三只名牌蜜蜂
書蟲分四種。最多的是甲蟲,飛到哪里算哪里,東啃一點西啃一點,不講究,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更專業的是蜜蜂,往往只認一片領域,槐花啊椴花啊,所得端賴勤勞辛苦,還有蜂群的組織分工,它們有刺,蜇人是痛的。最有境界的是蝴蝶,本是花叢中來,一度作繭自縛,終能變成另外一種樣子,輕盈飛過了滄海。令人唏噓的大約是蚯蚓了,打了許多洞,發現各種聯系,走不出,或者壓根兒就不想走出,在盲目中癡迷,而且緘默無語。
言及“書蟲”,讀書人聯想到的恐怕是《爾雅》里的“覃魚”,是陸游的“吾生如蠹魚”,由“書蠹”而化“脈望”,是舊時讀書人的自況和期許。而當代世界,“讀書”與“讀者”都變得復雜起來,此處的“四種書蟲”,乃是指“四種讀者”——作為甲蟲的一般讀者,作為蜜蜂的專業讀者,作為蝴蝶的創作型讀者,以及作為蚯蚓的癡迷型讀者。同為書迷,四種讀者在態度、方法、收獲上大異其趣,但在一樁事情上相當一致:那些關于讀書的書,總是區分書蟲與非書蟲的“誘捕劑”,也總是專業讀者給一般讀者的“指南針”。長夏無事,在文學花海里拈出三只名牌蜜蜂,來一窺究竟吧。
(一)一只飛了很遠的工蜂
世界上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匱乏的悲劇,另一種是豐裕的悲劇。每一個教授“世界文學”課程的大學老師,必定對后一種體會尤深。從現存最早的史詩——兩河流域的《吉爾伽美什》開始,人類寫就的文本浩浩湯湯,雖歷經蟲蠹之災、水火之厄、政治整頓、宗教清除……留存下來的經典之作也足以填塞圖書館的一半空間。
18世紀,歌德意識到文學正在前所未有地擴展,更多人可以讀到來自更多時代和更多地方的更多文學作品,原本局限于特定地方和特定傳統的文學,正在變成一個融合的整體,于是他莊重宣布:“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時代即將到來,每個人都必須為推進它做出貢獻”。
19世紀,另外兩個德國人也認識到,受工業化和全球貿易的驅動,“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自己寫作的《共產黨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于世”,未來的國際不僅共享物質財富,也共享精神財富。20世紀,“世界語”雖然沒有通行,但“文字共同體”不再局限于民族語言,經由翻譯、出版、特別是互聯網這樣的新媒介,每個人都可以漫游在這個文字寫就的世界。當代的問題不在于經典不夠多,而在于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重新篩選、確立經典的過程,總是伴隨著意識形態與文學傳統、保守與激進、替換與增補的各種權衡。
哈佛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開設了哈佛慕課“世界文學經典”,他主編過厚重逾6000頁的《諾頓世界文學選集》(第三版和第四版),要從中挑揀出16次課、32學時的材料,就像硬要從一大片花田里挑選出16朵花,那種掙扎、不舍和不安,難以盡述。憑借高明的技巧,普克納出版了用作通識課教材的《文字的力量》,以“講故事”和“文字技術”一明一暗兩條線索,高度概括了世界文學的歷史:“這一文學的民主化過程得益于從字母和莎草紙到紙和印刷術等技術手段的幫助,這些技術降低了文字世界的門檻,讓它向更多的人開放,而這些人接著又發明了新的形式,即小說、報紙和宣言,同時也確立了古老經典文本的重要地位。”文學的歷史必然包含文字的歷史、媒介的歷史、作者的歷史、讀者的歷史,特別是思想觀念的歷史。普克納展現的是文字共和國日益自由民主的過程。所以,一本21世紀的“世界文學導讀”,始于航天飛船上的宇航員朗讀《創世紀》,終于《哈利·波特》的中世紀傳奇大雜燴,不會令人驚訝。
普克納的宏大文學史觀很是時髦,暗自融合了書籍史、閱讀史、媒介史、思想史,也符合從“作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闡釋學轉向。他的本行是戲劇研究,懂得如何在大視野中營造戲劇性,讀這部《文字的力量》,猶如一部大型交響樂在伴奏,使人激動如大海。更重要的是,普克納的編寫方法非常之“政治正確”。一方面,平民百姓地位凸顯,“文字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專業作者們。實際上,我邂逅了一群出乎意料的人物,從美索不達米亞的記賬員和不識字的西班牙士兵,到中世紀巴格達的一名律師、南墨西哥的一個瑪雅叛亂者,以及墨西哥灣的海盜們。”另一方面,他小心維持著地域、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平衡,在書中,東西方最早的史詩都在——《吉爾伽美什》和《伊利亞特》;東西方最早的小說也在——《源氏物語》和《堂吉訶德》;“教師”們包括佛陀、蘇格拉底、孔子和耶穌;在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旁邊,有瑪雅的《波波爾·烏》和非洲的《桑介塔史詩》;既有《共產黨宣言》傳播史,也有阿赫瑪托娃和索爾仁尼琴遭禁史;為了讓“后殖民文學”不缺席,加勒比海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都有專章……平衡、妥帖、全面。盡管印度教師不能設想沒有《羅摩衍那》、中國教師會對沒有《紅樓夢》耿耿于懷,可是說到全面而簡潔,似乎不能要求更多。如果普克納是一只蜜蜂,他是那種超級工蜂,其勤勞、眼界和技巧,學院派蜜蜂們都是首肯的。唯一的問題在于,西方教師們一定會質疑:莎士比亞安在?
(二)一只負責的偵察蜂
普克納的《文字的力量》首版在2019年,同年10月,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去世。布魯姆應該沒有看過此書,不然定會攥緊拳頭做獅子吼:怎么可以少了莎士比亞!只因在布魯姆這里,莎士比亞就是“經典”的代名詞。深深不屑于當代的批評模式和教育風氣,他自嘲說:“我是一只恐龍,歡樂地自稱:‘布魯姆·崇拜莎士比亞·雷龍’”。“莎士比亞可以代表最高文學造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地理解了,它能夠治愈每個社會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布魯姆儼然一位“莎翁原教旨主義者”,沒有一部莎士比亞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有,就再來一部。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布魯姆將莎士比亞置于經典的“正中心”,在他看來,莎翁將“影響”的陰影投向殿堂的四面八方,而在對此“影響”的“焦慮”中,一些作家在抵抗和變異中確立了個人風格,從而在殿堂里獲得一席之地。這批經典作家,包括歌德、華茲華斯、奧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爾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卡夫卡、博爾赫斯、聶魯達、佩索阿、貝克特……。按照另一位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對《西方正典》的解讀,“莎士比亞永遠大于我們,永遠藏在我們背后,永遠是在我們頭頂。莎士比亞是生活‘強大的先驅’,他的作品在我們還沒開始對其做任何評價之前就已經改變了我們。”布魯姆認為是莎士比亞“發明”了現代的讀者,乃至作者,因為莎士比亞的影響早已成為傳統,無遠弗屆、無處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大量閱讀、引用、“誤引”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成為弗洛伊德隱秘的、精神上的“父親”,正是在此意義上,布魯姆拋出擲地有聲的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亞去解讀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來解釋莎士比亞。”
布魯姆的確像雷龍一樣龐大,一生寫了五十多部著作,一千余篇導論,被譽為“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有原創性和最有煽動性的一位文學批評家”。在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任教的身份,使得他牢牢掌握話語權,從極端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視角,勉力維護著文學經典的地位與聲譽。如果說普克納小心翼翼地平衡著“階級、性別、族裔”這“左翼的神圣三位一體”,布魯姆簡直就是“精英保守白人男性”的代名詞,對于“政治正確”不屑一顧,他感慨說,由于被女性主義者指責,勞倫斯被徹底驅逐出英語國家的高等教育,“學生從而不再閱讀20世紀的一位大作家、一個獨特的小說家、講故事的人、詩人、批評家、先知。”憤懣之情溢于言表。
不得不說的是,布魯姆曾經參加一個“幫派”,學院里稱為“耶魯學派”,更具街頭風格的綽號則是“闡釋學黑手黨”或“耶魯四人幫”。除了布魯姆,另外三位是保羅·德·曼(Paul de Man)、喬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希爾斯·米勒(Hills Miller)。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他們均在耶魯大學任教,同時又活躍于文學批評領域。“黑手黨”,自然是顛覆性的、危險的、霸道專橫的。他們不是不講理,只不過講得不是平常的理。在后現代主義半革命半游戲的氛圍中,他們贏得了英文系青年教師和學生們的熱情追隨。他們的反對者認為,他們在經典文本里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干的是天理不容的黑道勾當。而“黑手黨們”擺出無政府主義者的姿態,縱容自己的愛欲情仇,把文本剖析得血淋淋的卻又講究程式和技藝,各顯其能分庭抗禮,享受著道中人的特殊光榮。這里面,作為“教父”的德曼留下座右銘:“一切閱讀都是誤讀”。既然如此,私人的趣味、個人的眼光就具有了合法性。是以,布魯姆等人縱然是學院派,卻也不再是利維斯那樣的學院派。寫有《偉大的傳統》的利維斯,要求文學必須有道德價值,必須促進社會的健康,而在布魯姆這里,只認可三大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達到標準的,是為“經典的崇高”。
布魯姆的著作國內已經翻譯出版了16部,特別是譯林出版社的“哈羅德·布魯姆文學批評集”,皇皇巨著,略略讓人敬而遠之。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還是他古稀之年的性情小書《如何讀,為什么讀》較為“趁手”,不妨視作他個人的文學公開課。在這里,學院派布魯姆做出了反學院派姿態,他對于高深的工具反感,對于“憤怒的”文化研究反感,對于刻板的意識形態化解讀尤其反感。他說:“專業讀書的可悲之處在于,你難以再倡導你青少年時代所體驗的那種閱讀樂趣,那種哈茲里特式的滋味。我們現在如何讀,部分地取決于我們能否遠離大學,不管是內心方面的遠離還是外部方面的遠離,因為大學里閱讀幾乎不被當成一種樂趣來教——任何具有較深刻美學意義的樂趣。”威廉·哈茲里特是19世紀評論家,寫有《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反對權威、習俗和狹隘見解,有自由風骨和人文趣味。布魯姆所倡導的“哈茲里特式的滋味”、老派的“閱讀的樂趣”,也就是回到鑒賞式解讀,融合分析與評估,一言而蔽之:虔誠地讀、單純地讀、大聲地讀、反復地讀。整部《如何讀,為什么讀》滿腔熱忱、如數家珍,只有看到閱讀之中的這種癡迷,才會恍然大悟:布魯姆是蜜蜂中的偵察蜂啊,雖然略有聒噪,但他長于發現、他指路、他手舞足蹈,他也有點甜。
(三)一只蜇人的大黃蜂
當前炙手可熱的批評家非詹姆斯·伍德莫屬。他比布魯姆小三十五歲,從《衛報》首席文學評論員到哈佛大學文學批評實踐教授,從第一部書《破格》(1999)到最近一部精選集《嚴肅注意》(2020),二十年間他活躍于《倫敦書評》《新共和》和《紐約客》這樣的頂級期刊,受邀于牛津、劍橋和哈佛這樣的頂級名校,用英國人的機靈、幽默、毒舌,把文學蜜蜂的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伍德曾經同時使用兩個筆名,James Wood和Douglas Graham,前者有學院派的智性、精致和犀利,后者則更加魯莽、任性、刻薄。如果說早年文章更多學院派炫技,是“伍德教授風”,隨著年齒漸增,越發隨心所欲,是“格拉漢姆媒體風”。
對于“哈佛前輩”布魯姆,伍德評價說,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化的布魯姆”,有缺陷,但這缺陷是創造性的缺陷,“是自成一格的口吃”。受勢不可擋的天賦大能驅動,“有時候看上去好像他綁架了整個英語文學,再用一生時間釋放人質,一個接一個,全憑自己喜好。”實際上,伍德的野心更大,他不僅綁架英語文學,他綁架西方文學,他不釋放人質,他“肢解”了他們。在第一部批評集《破格》里,他縱論文學與信仰,從藝術角度抨擊了品欽、德里羅、厄普代克、羅斯、莫里森、巴恩斯,對長者布魯姆頗有微詞,對敵手喬治·斯坦納極盡挖苦之能事——“喬治·斯坦納的文章非同小可,那是一座汗水的豐碑。讀他文章的人會很熟悉其不精確和夸張;其成群結隊的形容詞;其以教堂般的寧靜包圍那些偉大作品。”第二部《不負責任的自我》里有更多“受害者”:弗蘭岑、拉什迪、庫切、托馬斯·沃爾夫,以及被稱為“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們。這個名單不斷延伸,當紅作家很難逃脫,比如奈保爾、麥克尤恩和保羅·奧斯特……
伍德不諱言文學批評夾帶個人“私貨”的性質,時時將個人經歷穿插其間,但是顯然,他懂得一個重要道理:“評論只有在自身也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后,才能流傳于世”,他的確使評論成為了文學的一部分,無他,他熟悉所有的文體奧秘和敘述技巧,那些文學之為文學的東西。在小說批評領域,他認為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自有經典地位,“但是讀來已欠精彩”;昆德拉談論小說藝術的三本書也很出色,只不過,“有時我們希望他的手指能再多染些文本的油墨”。他頗為欣賞的20世紀小說批評家是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法國形式主義者羅蘭·巴特,因為“他們像作家一樣思考”,關心風格、詞語、形式、比喻和意象,只是遺憾啊,他們是寫給其他專業人士看的,架勢十足毫不指望普通讀者看得懂。既然如此,好了,伍德只好挺身而出了,他“以評論家立場提問,從作家角度回答”,寫了一本給普通讀者的指南書:《小說機杼》。
如果說普克納的歷史是恢弘的,布魯姆的經典是中觀的,伍德的批評則是具體而微的。如果說普克納的關鍵詞是“政治正確”,布魯姆的關鍵詞是“影響的焦慮”,伍德的關鍵詞則是“自由”。他“發明”了術語“自由間接文體”(Free Indirect Style),這是一種徘徊于敘事主體和虛構人物之間的視角,在一些時候,作者的全知全能視角與人物的限制視角之間出現了“走神”,比如“泰德透過愚蠢的淚水看管弦樂隊演奏”,“愚蠢”就是這個自由間接體,這個詞來自泰德自己還是作者?抑或兩者皆可?伍德說:“多虧了自由間接體,我們可以通過人物的眼睛和語言來看世界,同時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語言。我們同時占據著全知和偏見。作者和角色之間打開了一道間隙——而自由間接體本身就是一座橋,它在貫通間隔的同時,又引我們注意兩者之間存在的距離。”在伍德看來,自由間接體和文學本身一樣古老,在庸人中規中矩地寫作之時,大師們已經用這樣的魔法間接獲得自由。與此類似,在莎士比亞、福樓拜等大師筆下,常現有趣而冗余的細節,它們旁逸斜出,意識與思想也跟著浪游,“不負責任的自我”所帶來的意外和驚喜,是文學神髓所在。
學院派的蜜蜂嗡嗡飛著,貌似一團亂麻,實則各有分工,也各有特色。一只蚯蚓看得入神,看到了外部與中心平分秋色,看到了整體與細節各有千秋,很多種路線,很多種聯系,一時興起,打破緘默,電腦前敲下五千字,是為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