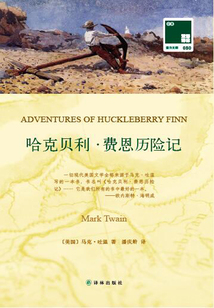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雙語譯林)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序
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誰能比奧德修斯更像希臘人?比浮士德更像德國人?比堂·吉訶德更像西班牙人?比哈克貝利·費恩更像美國人?”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美文學大師 T.S.艾略特
“現代美國文學,全都來源于馬克·吐溫寫的一本書,書名叫作《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它是我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書。[1]在這以前沒有過,打它以后也沒有這么好。”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美國小說家 海明威
在美國文學史上,能榮膺世界大師級文化巨人的頭銜,當然首推塞繆爾·蘭霍恩·克萊門斯(1835—1910)。他的筆名馬克·吐溫,原意“兩英尋深”,是密西西比河上專測水深的員工的術語,也意味著他的整個一生跟密西西比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996年問世的美國牛津版《馬克·吐溫全集》(共二十九卷)主編,得克薩斯大學英文教授雪莉·費·費什金撰文指出,馬克·吐溫曾被譽為“美國的塞萬提斯”“美國的荷馬”“美國的托爾斯泰”“美國的莎士比亞”“美國的拉伯雷”。[2]1933年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一詞,就是從馬克·吐溫小說《亞瑟王朝廷上的美國佬》一書中移用過來的。[3]馬克·吐溫另一部長篇小說書名《鍍金時代》[4],已給整整一個時代命了名定了性。馬克·吐溫率先將民間幽默與嚴肅文學融為一體,使草根百姓、俚俗細民成為文學中的主人公,還讓方言土話甚至俚語行話登上了藝術殿堂。馬克·吐溫開創了富有濃郁特色的美國本土氣息的一代文學新風,因建功奇偉而獨步文壇,譽滿全球。當時美國文壇主將豪威爾斯[5]曾稱他為“我們文學中的林肯”。著名評論家門肯[6]尊奉他是“我們民族文學的真正始祖”。英美現代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T.S.艾略特[7]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在英美兩國開創了新文風,是英語的新發現。哈克的形象是永恒的,堪與奧德賽、浮士德、堂·吉訶德、堂·璜,以及哈姆雷特等舉世馳名的文學典型相媲美。他甚至還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指控蓄奴制度,要遠比《湯姆叔叔的小屋》[8]更加令人信服。當時美國小說似乎還沒有得到英國文學界認同。但是,英國大文豪蕭伯納[9]給馬克·吐溫的信中卻這樣寫道:“未來的美國歷史學家會認為你的作品對他必不可缺,就如同法國歷史學家認為伏爾泰的政論文對他必不可缺一樣。”后來,歐洲人對馬克·吐溫的評價之高,甚至超過了他本國的人,他們認為,馬克·吐溫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馬克·吐溫的生平與創作,對我國讀者來說恐怕不算太陌生。可是,馬克·吐溫在美國與世界上無遠弗屆的影響,也許鮮為人知。因此,本人不揣冒昧,在此稍作介紹。
當今美國,在密蘇里州圣路易斯有一家馬克·吐溫銀行,紐約杰克遜高地有一家馬克·吐溫小餐廳,佛羅里達州萊克蘭有一家馬克·吐溫煙鋪。在西雅圖等四個城市,各有一所馬克·吐溫小學。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有一家馬克·吐溫書店。馬克·吐溫的慈祥形象,居然還出現在田納西州某煤氣公司、首都華盛頓某家旅館、加利福尼亞州某座公墓,乃至于銷售巴斯名酒(作家最愛喝蘇格蘭威士忌酒)的偌大廣告牌上。
馬克·吐溫的崇高聲望和音容笑貌,盡管是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但是,他斷斷乎不會成為僵化了的偶像。恰好相反,馬克·吐溫至今依然活在人間。《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在當今美國,“從初中起一直到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各高等學府里,乃是教得最多的一部小說,教得最多的一部長篇小說,教得最多的一部美國文學作品”。有的圖書出版公司將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及其有關評論、背景材料輯成匯編本,贈給各大學教授作為教學參考書籍。好幾個馬克·吐溫扮演者,頻頻出現在美國各地影劇院、新片試映室與購物中心。我在美國各地書店親眼看到,單是《馬克·吐溫全集》,就有三套(牛津版、蘭登版、加州大學版)同時陳列在書架上,這在美國作家中間恐怕也是絕無僅有。馬克·吐溫的作品早已走向世界,在那不勒斯、利雅得、貝爾法斯特[10]和北京等地學校課堂上,都被指定為學生閱讀作業內容;而且,自20世紀以來,從阿根廷到尼日利亞到日本,地域幾乎遍及全球的作家群,也一直受到馬克·吐溫的積極影響。時至今日信息化時代,馬克·吐溫又成為網絡上人們日常交談的時髦主題。世界各地傳媒記者,幾乎每天都覺得理所當然地要從馬克·吐溫的經典作品中援引一些名言雋語。美國不少電視連續劇(比方說,《星際旅行:下一代》[11]等)里,還常常讓馬克·吐溫擔綱出任主演。好萊塢劇作家也都要從他的作品里汲取滋養與靈感,不時推出一些影片來。甚至許多撰寫神秘小說與科幻小說的作者,還會不斷地把馬克·吐溫編進他們的故事情節中去。挺有意思的是,哈克還有幸成為影視屏幕上的一顆明星。至少有六位美國電影導演,曾經請哈克登上銀幕,同時,俄文版的哈克影片也有四部之多。我在美國各城鎮公共圖書館以及各音帶出租公司,就看見過各種不同版本的錄像帶,相當走俏。好幾套電視節目曾將《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向全球觀眾播映。耐人尋味的是,在1955年一檔節目里頭不知怎的將吉姆這個關鍵性人物完全抹掉了。另外,還有不知凡幾的連環漫畫冊,一部片名為《馬克·吐溫歷險記》的動畫片,這全說明《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部故事在美國早已家喻戶曉,盡人皆知。一百多年以來,哈克和他的小說,早已根深蒂固地進入了美國人的民族意識中去。幾乎可以這么說,每個美國人的血脈里或多或少地會帶有哈克的基因。
不論在20世紀還是21世紀,人們對《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都情有獨鐘。有的美國評論家甚至還這樣預言說:只要我們這個星球上依然存在著貧困、仇恨、種族主義、溺愛兒童、獸行、暴力、偽善、壓迫、苦工,以及還有奴役——不言而喻,人們還得一遍又一遍地仔細捧讀《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馬克·吐溫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正當他創作旺盛的年代,即在1876年—1883年,[12]在這期間,他寫過兩部重要作品《海外浪跡》與《王子與貧兒》,將《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擴充成為《密西西比河上》,同時還把一些短篇作品收入了三個集子。不過,那個時期他創作的重點,乃是醞釀已久的另一部小說,當時書名是《湯姆·索亞的伙伴》,場景:密西西比河谷。時間:19世紀40至50年代以前。作者打算利用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和《湯姆·索亞歷險記》里寫過有關漢尼拔和密西西比河的素材,在后來定名為《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中得到充分展開,最后達到登峰造極的頂巔。
馬克·吐溫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真可以說是獨辟蹊徑,博采眾長。他將先前幽默作家在他們的短小趣聞軼事中包含的真知灼見兼容并蓄,納入一個規模較大的框架里去。后來,他的這一寫作設想果然卓有成效,不消說,這是跟他從題材中不斷開挖、不斷發現新含義分不開的。他那豐富的想象力經常使他的創作才智熠熠生輝,而方法上的不斷創新,反過來又給他的想象開拓了新的視野;這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辯證關系,在其他作家的成長過程中也屢見不鮮。
這種辯證的過程,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構思中,也是特別令人矚目的。他在先前一些作品里經常表露出自己的立場觀點,不消說,極其顯眼;此次寫作手法上有了創新,讓哈克采用了第一人稱來敘事狀物,作者自然用不著直接闖入故事敘述中去,所以,原先他寫作上的這一不足之處,也就不復存在。可是,故事一轉到以哈克為主的時候,運用民間俗語進行文學創作,明擺著具有很大的潛力,特別是運用方言也可以表達嚴肅的主旨,而且還可以讓運用方言的敘述者從區區第一人稱轉變為一個深悟人性的典型,凡此等等都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顯然,這也是小說創作上一場嚴峻的挑戰。由于馬克·吐溫出色地回應了挑戰,結果使《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成為他所寫的書里頭最偉大的一部書,同時又是美國文學中僅有的兩三部得到公認的杰作之一。不過,毋庸諱言,這一驚人的成就隨之也產生了他寫作上一個尚待解決的新問題:原來馬克·吐溫這部小說是以帶有喜劇色彩的故事啟端,隨后按照故事情節逐漸發展,漸漸開始具有跟喜劇前提相悖的悲劇含意。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從內容上說,包含著三個組成部分。其中,哈克與吉姆冒險出逃、向往自由的故事,不消說,最惹人矚目。吉姆拼死要逃離的是當時的奴隸生涯。哈克竭力逃避的乃是他醉鬼父親的暴虐,沃森老小姐和道格拉斯寡婦善意的、所謂文明的管教,以及當時美國社會習俗上數見不鮮的繁文縟節和清規戒律。馬克·吐溫把他的熱情和他最熟悉的生活底蘊,少年時代河上小鎮和那條河上的生涯,全部傾注在小說的篇章中。狄更斯在他的《旅美見聞記》中認為密西西比河是一條“流著泥漿”的濁流,“除了每天夜里有無害的閃電向漆黑的天空閃耀以外,沒有一點兒愉快的東西”。可是,對馬克·吐溫來說,不論在他的童年還是在他的回憶里,密西西比河不啻是整個生命。在他那生花的妙筆底下,密西西比河已被寫成人生旅程的象征。小說中第二個組成部分,內容特別豐贍,是作者亦莊亦諧地針對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城鎮所做出的社會諷刺。這種諷刺一方面令人忍俊不禁,特別是描述潑皮痞子“國王”和“公爵”的那些插曲,一方面也揭露了令人發指的暴行,比方說,格蘭杰福特與謝潑德遜兩家為了世代族仇互相廝殺,以及舍伯恩上校殘殺孤苦伶仃的老好人博格斯。小說最末組成部分,是著重塑造哈克這個人物性格逐漸豐滿、臻于完美的過程。有的評論家指出,《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除了小說結尾處湯姆·索亞式的營救吉姆那一段以外,都是十全十美的,堪稱一幅令人難忘的美國邊疆少年的圖畫[13]。在當時充滿暴力、偽善、冷酷、貧困的現實社會里,哈克貝利因敢于叛逆,倒是不失為自由的,外部環境想要把他“管教”成一個文明人,可他到頭來仍然是一個沒有讓外部環境扭曲、讓外部環境敗壞的淳樸的人。馬克·吐溫對哈克的描寫,清新、活潑、逼真,好似神來之筆,特別是有一些經典段落,讀起來令人回腸蕩氣,真可以說是這部小說中的華彩樂章。
以上這三個基本組成部分,馬克·吐溫一開始動筆,想必就時時刻刻浮現在他腦際,因為正如美國評論家所說,這部小說的偉大,主要就在于它的連貫性,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相互聯系。不過,多年來美國評論家對這部小說進行潛心研究——沃爾特·布萊爾教授甚至還給它制訂出創作年表——都已表明:馬克·吐溫為了探索一種結構,能夠落實自己對主題和人物的構想,確實經歷過好幾個階段,而不是一蹴而就。他剛開始寫作的時候,雖然未必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筆觸究竟會指點到哪里,但是我們讀者似乎一目了然地看到作者無論在創作意圖上還是手法上,始終處在不斷有新發現、新創意、新亮點的過程之中。
小說從開頭這幾章歷險紀事,漸次轉入中間那些長篇大段的社會諷刺章節時,促使故事情節得以全面深入地展開,并由此發展到第三十一章著名道德危機中對哈克這個人物最后做出的心理透析。不言而喻,這種道德危機是由哈克驚悉自己拯救吉姆歸于失敗而引起,因此也就標志著探索自由的真正結局。至于發生在費爾普斯種植園里令人困惑的最后插曲,建議讀者最好不妨把它看成是馬克·吐溫要把剛剛露頭的悲劇復歸到故事原先規定好以喜劇告終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種花招罷了。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1884年在英國倫敦查托·溫多斯圖書出版公司問世后,頗受英國與歐洲大陸讀者歡迎,但在美國反而遭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說它“純屬垃圾”“極端粗俚”“不堪卒讀”,甚至被麻省康科德公共圖書館列為禁書。盡管這樣,翌年《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在美國再版以后,在文學界卻好評如潮。T.S.艾略特就贊不絕口地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馬克·吐溫許多書里頭唯一稱得上杰作的一部書。”“馬克·吐溫寫了一部遠比他自己所能感悟到的更為偉大的書。”T.S.艾略特在肯定馬克·吐溫所塑造的哈克這個不朽的美國人典型時,一迭連聲贊美道:“誰能比奧德修斯更像希臘人?比浮士德更像德國人?比堂·吉訶德更像西班牙人?比哈克貝利·費恩更像美國人?”另一位美國著名詩人奧登(1907—1973)則一錘定音地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乃是了解美國的一把鑰匙。”迄今一百多年以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始終以它永恒的藝術魅力,吸引著全世界數以億計的不同年齡和不同知識層次的讀者,遲至1982年還被《紐約時報》譽為“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十多年前,沃爾特·布萊爾教授根據一項精確的統計資料,估算出已印造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總冊數在十億以上,不消說,遠遠地超過任何其他美國文學作品。特別是近五十年來,美國文學評論界曾就哈克與吉姆河上漂流的象征意義,密西西比河與岸的象征,小說最后結尾的成敗得失,乃至于莫非哈克是個黑孩子諸問題,一直進行探討,迄今還是見仁見智,爭論不休;據說每年還要推出好幾百篇頗有分量的論著。不久前,我在哈佛大學最大的衛登納圖書館[14]書庫里,見到所收藏的馬克·吐溫各種版本原著以及有關長篇評論書籍,竟然多達六百余種;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美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勝古跡“馬克·吐溫故居”及其珍本收藏處,毗鄰的三一學院沃金森圖書館里,同樣是汗牛充棟,簡直令人望“書”興嘆。顯而易見,在美國,圍繞著馬克·吐溫小說,從學術界、文學出版界、影視娛樂圈,乃至于尋常百姓家里,似乎掀起了一股久興未艾的“哈克熱”。
作為譯者來說,總的感受是,馬克·吐溫在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里筆觸所指,已涉及南北戰爭以后美國現實、社會、種族、宗教、風俗、歷史、傳統、女權的各個方面,簡直可以說包羅萬象,涵蓋了一切,所以說它是始于19世紀中葉、一直延續至今的美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我認為也不算太過分。難怪我不止一次地閱讀它,理解它,感悟它,還是感到很吃力。動筆開譯前看過不少有關評論著述,譯時大大小小譯注總共做了一百七八十條,反正在我迄至今日譯過的八大部美國文學長篇名著中,就數它注釋上花的功夫最大。即使這樣,拙文仍不敢對小說妄加置評。相信我國讀者閱后自有真知灼見。
要說我跟《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部小說,似乎也有那么一點“書緣”,前前后后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
記得我是在國立浙江大學慈湖畔大學圖書館[15]里才頭一次讀到《西風之神》[16]叢書版《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部傳奇小說,當時手邊還在翻看的,碰巧又是塞萬提斯的英文版《堂·吉訶德》(不過,恕我直言,我只讀了它的前半部,底下就沒耐心讀下去了)。當然,那時我并不知道美國評論家盛贊《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書,曾將馬克·吐溫與塞萬提斯相提并論;同時又指出,先是湯姆與哈克(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一書中),后來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湯姆一角淡出,哈克易位,變成了主人公,于是,哈克與吉姆這一對搭檔,竟跟吉訶德與桑丘·潘扎那一對主仆人物有頗多相似之處。當然,我更不知道門肯贊美小說時這樣說過:“我相信《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世界上偉大的杰作之一,完全可跟《堂·吉訶德》媲美……而且遠遠地勝過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17]……(馬克·吐溫)就是屬于一切時代的偉大藝術家里頭的一個。”門肯在這里說馬克·吐溫乃是“屬于一切時代”的藝術大師,這一文壇典故源自17、18世紀英國大作家本·瓊森對莎士比亞的最高評價[18],自此以后傳為美談,幾百年來一直被認作衡量一位藝術家的幾乎不可企及的圭臬。當時讀后將我深深地吸引住的是小說跌宕起伏的情節,引人入勝的故事,鞭辟入里的諷刺,還有小說中對瞬息萬變的大自然景象的生動描繪(諸如江河島岬、日月星辰、風雨云霧等等),無不充滿了詩情畫意,令人嘆為觀止;于是,自然而然,我就萌生了迻譯的念頭,借以填補一下美國文學在我國的空白[19]。無奈新中國成立初期,當務之急斷乎不是譯介美國文學,二十多個寒暑端的是彈指一揮間。迨至改革開放的80年代初,我才如愿以償,連續譯出了一些美國文學長篇名著,其中包括本人情有獨鐘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我特別感謝老友、詩人、資深翻譯家吳鈞陶先生,由于他竭誠邀約與高情雅意,拙譯《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有幸列入《馬克·吐溫十九卷集》第十卷(吳鈞陶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精裝本.2002年版),頗受專家、讀者厚愛。
英國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說過:“到一個外國的文學領域中去漫游,跟我們到國外去旅游極其相似。”[20]說來也真湊巧,1995年夏至1997年春,我偕同夫人張許訪問美國期間,也許是置身于異域文化氛圍之中,耳濡目染,似乎平添了幾許真實感受,跟書中主人公好像更容易引起共鳴;夫人有時不覺技癢,就不聲不響,斷斷續續譯過一些片斷,聊以自娛。沒承望“無心插柳柳成蔭”,眼前這個譯本倒成了慶賀她今歲六秩生日的禮物,又算是圓了我半個世紀前的“夢”,哪怕是拙譯也許還遠沒有盡善盡美地傳達出地地道道屬于塞繆爾·克萊門斯所獨有的韻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以來,英、美、澳文學界出版界及著名媒體《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讀者文摘》,通過不同方式評選出最受作家、文學家與廣大讀者喜愛的“世界十大文學名著”,美國僅有一本入選,即《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理由是這本書是“美國最偉大的小說”。
潘慶舲
1998年春識于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3年元旦補識于圣約翰名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