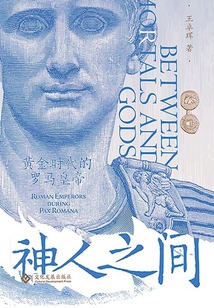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20章 后記
- 第19章 黃金時代的羅馬皇帝
- 第18章 康茂德:放權又自大的角斗士皇帝
- 第17章 馬可·奧勒留:哲學家皇帝
- 第16章 安敦尼·庇護:不識甲兵的賢君
- 第15章 哈德良:云游四方的守業皇帝
第1章 前言
作為一個還在成長中的西方古典歷史學子,我一直對當今人們看待羅馬帝國的視角與觀點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因為在西方的羅馬帝國時期,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也有著繁榮昌盛的漢帝國,難免讓人想要將兩者拎出來對比。不過有時會有一些人太過執著于尋找羅馬帝國與中國古王朝在制度、文化、軍事、經濟上的相似之處,而忽略了羅馬文明本身的特色。當涉及“共和國”“帝國”“皇帝”“行省”等概念時,也難免代入我們自身的現代觀念與我們自身對中國歷史和皇帝的認識。這對于看待羅馬帝制與皇帝而言,難免有失公允。于是我想嘗試著從大家熟悉的一些概念出發,站在羅馬人的立場和角度,來介紹他們眼中的羅馬歷史。
我想在讀者正式走進這本書之前,先在前言里聊一聊我完稿之后對這本書的看法,我在寫書時所考慮的立場和角度,以及這本書采用的敘事手法所固有的盲點與缺陷。這本書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我希望能從羅馬人的角度來敘事,講述羅馬人眼中的羅馬皇帝,并對皇帝在帝制中的角色定位進行進一步探討。
首先要澄清一下,這里所謂的羅馬人,指的是擁有羅馬公民權,擁有羅馬或希臘家族姓氏,生活在帝國中前期并且把羅馬城看作帝國中心的人。符合這三點的人,才是前文中所稱呼的“羅馬人”。之所以在這本書的格局內強調“羅馬人”身份的原因主要來自材料的局限性。本書中所引用的大部分歷史材料都來自羅馬史學家和生活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希臘史學家。這也就導致他們所提供的觀點從一開始就代表了當時羅馬人與希臘人對羅馬皇帝的看法。那么此書自然也難免與材料一樣有著相似的局限性。
在此書中,我采用的敘事手法更傾向于為讀者呈現一手史料內的皇帝。我傾向從文獻史料出發,還原當時人們眼中的羅馬皇帝,而非一味地追求還原一個更客觀真實的羅馬皇帝。這并不代表這一手法徹底放棄了論證,只是在二者之間,我會有選擇地展示當代人們眼中的皇帝。舉個例子,當我引用蘇埃托尼烏斯、塔西佗、維克多等史學家時,我并不會每次都從語言學與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去分析他們記載的真實性,而是會把他們原文的內容呈現給讀者。這樣既能減少我主觀上對材料篩選的程度,又可以讓讀者更直觀地認識史料內的皇帝。
這一敘事手法的優點在于,讀者可以把這些一手史料看作了解羅馬皇帝的一扇窗戶,通過這扇窗戶,今天的我們所看到的光景將在一定程度上與兩千年前羅馬人眼中的光景重合。不過缺點也是明顯的,畢竟直接呈現出的一手史料內容與經過學者反復推敲考究過的內容還是會有一些出入。不過為了更好地表達皇帝的個性,也為了能更直觀地表達羅馬人的價值觀,我認為這種敘事手法是值得的。
這本書采用的敘事手法也有一些固有的盲點與缺陷。首先便是本書中的大部分材料都是源于文本,但是文本只是古典歷史研究中的一部分。一手史料固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現如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是基于非文本材料,如古錢幣、紙莎草、碑文、建筑遺址等。我個人作為一個古典經濟史學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傾注于把古錢幣、碑文與文本研究相結合上。物質遺產與文獻所帶來的信息與講述的故事自然天差地別。因本書基于一手文獻,便忽略了其他材料所帶來的信息。不過考慮到本書的初衷,即講述羅馬人眼中的皇帝,以文本為基礎更容易構建敘事的框架。
這個敘事手法所帶來的另一個盲點便是省略了行省人民眼中的羅馬皇帝。如同我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中所說,每個皇帝在不同的行省人民的眼中都不太一樣,這也就導致了如果我從行省人民的角度出發,那么敘事的結構將不停地在各個行省之間來回切換,這樣并不有利于本書線性的敘事結構。不過日后如果有機會,我也會考慮從各個行省人民的立場出發,來講述他們眼中的羅馬皇帝。
本書的目的也不僅僅是想單純地向大家呈現羅馬人眼中的世界與皇權,同時也是對羅馬帝制以及皇權本身的探討。“羅馬皇帝”這一稱呼從屋大維建立帝制開始便一直很難落實到一個單一的頭銜,有的人會認為“勝利的將軍”(Imperator)代表“皇帝”(Emperor),但是“勝利的將軍”這一頭銜在共和國時期便一直存在,并用于稱呼那些為共和國擊敗外敵的執政官們。
亦有人會認為“奧古斯都”(Augustus)代表皇帝,因為自屋大維被元老院授予這一頭銜之后,歷任羅馬皇帝都會被元老院授予“奧古斯都”這一頭銜。也有人認為“愷撒”(Caesar)這一頭銜代表皇帝,因為自屋大維改名為“愷撒”之后,歷任皇帝都以“愷撒”自居。還有人認為皇帝頭銜中那些象征著實權與榮譽的頭銜才代表皇帝,如“保民官之權”(Tribunicia Potestas),“行省行政權”(Proconsul),“元老院元首”(Princeps),“共和國之父”(Pater Patriae)與“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等。
但事實上,無論是從對皇權的認識角度出發,還是從皇帝本身的角色出發,這些所有的頭銜都可以被看作是皇帝,但是單獨拎出來,卻也都不是皇帝。“皇帝”作為一個專屬名詞在拉丁語中并不存在,類似的頭銜只有:“王”(Rex)、“暴君”(Tyrannus),和拉丁語化的希臘詞匯“國王”(Basileus)。而這些詞匯對于經歷過王治的羅馬人來說,都是殘暴與壓迫的象征。在共和國建立之初,元老院的議員們在推翻最后一任國王塔奎尼烏斯(Tarquinius)時,曾立下誓言“羅馬將永遠沒有國王。”[1]這一誓言在屋大維建立帝國之初依然存留在羅馬人的自我認識中,所以羅馬的皇帝,注定無法擁有一個與“國王”同義的稱呼。
這些頭銜對于了解羅馬皇權而言,絕不是咬文嚼字的形式主義。羅馬帝國在元首制期間,皇權的邊界與定義一直都十分模糊,甚至都沒有任何一個體制內的帝國官僚團體直接隸屬于皇帝。帝國的運轉在圍繞皇帝的同時,也圍繞著元老院。在元首制時期,對于羅馬人來說,共和國的體制與制度,客觀上依然存在,這也就導致這一時期所謂的“羅馬帝國”其實一直存在于“共和國”的表象之下。元老院依然掌握著大量的政治資源與財富,依然具備與皇權制衡的資本。這也是為什么從屋大維開始直至戴克里先之前的這一時期被稱為“元首制”,顧名思義,即“元老院之首制度”,皇帝也依然被認作是“元老院之首”。
最初的羅馬帝制就是這樣在許多獨特的羅馬文化下形成,進而導致了每一位羅馬皇帝都在試探皇帝一“職”的各種邊界。有皇帝挑戰權力的邊界,欲大權獨攬,與元老院勢不兩立;有皇帝挑戰人與神的邊界,欲自封為神,享受萬世供奉;亦有皇帝挑戰社會的邊界,為了追逐個人喜好,不惜淪為世人眼中的小丑。而這些對邊界的試探無一不在共和國與帝制的雙重框架之下。對于羅馬人來說,元首制時期的皇帝是元老院的議員,亦是超乎議員的存在。也正是在皇帝與元首這兩種身份的融合與分裂之間,一代又一代的皇帝尋求著權力、理想與責任的平衡。而這本書的初衷,便是為了與讀者朋友們分享與探討這些有趣的皇帝,以及屬于他們的時代。
王卓琿
2022年5月19日
于芝加哥大學
注釋
[1]Livy.Ab Urbe Condita.拉丁語原文:Omnium primum avidum novae libertatis populum,ne postmodum flecti precibus aut donis regiis posset,iure iurando adegit neminem Romae passuros regn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