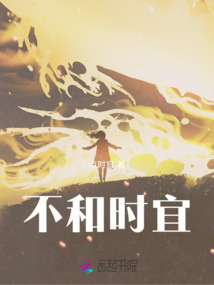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712連鎖反應:半陌生人
“只要陽光燦爛的一天代替陰雨連綿的一天,所有的事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世界的面貌就會發生變化。”——題記(取自《變色龍才是政治的徽章》)
有些時候,我覺得生活是灰暗的,至少在這件事情發生的過程中是這樣,也懷疑是所謂的主觀能動性在不斷讓自己的命運變得多舛。馮某讓我貸款轉賬時我的腦子里分明閃回過父親早年間清晰的勸阻聲“不要隨便網貸”以及母親對我軟性子的急迫擔憂“凡是讓你轉錢的事情多留個心眼”,但我還是鬼使神差地選擇相信了他所說的話,甚至摒棄了自己原先具有的認知。我開始質問自己,是什么讓我愿意去相信一個在網上認識了不到半個月且從未謀面的“半陌生人”,想來想去,是我在這之前總在內心里覺得“他是我的老師,是一個平時會認真負責監督我”的“老師”。這對我有幾分甜味的“好”,源自于從小到大這份對老師的“敬畏”。半陌生人也曾透露與我說,他是2012年教育管理畢業的本科生,這份教育經歷讓我自動替他安上了一層“有經驗、高素質”的濾鏡。
在事情發生以后,我意識到自己要么被詐騙了,要么見證了隱晦的疑似違法行為,所以心里頗不寧靜,難以入睡。但最讓我難過的,是這份“信任感”的缺失,以及信任度并未同等的背棄感。除此之外,我為我在整個事件中表現出來的迷糊行為表示汗顏,并且對這份在利益面前所產生的“動搖”感到羞恥和難以接受,因為,我是一個不得不相信“唯對錯論”的人。我總會在潛意識里認為我犯了錯,犯了原則性錯誤。
我向來不喜歡把一切罪責都怪到“原生家庭”四個字上,先天的教養雖然重要,后天的自我價值尋找、自我修煉才應該占主導地位,但許多來源于父母的價值觀的塑造卻在我這里根深蒂固。我有一位“細節控”母親,在她的詞典里,細節最能反映一個人的全部,“一件衣服都晾不好,這輩子你就完了”“這點小事都做不好”“你連端個盤子都端不好你有什么用”此類的話語總能充滿在我的回憶里。在我的回憶里,我永遠是那個“什么事都做不好的女兒”,而她永遠是那個“能干的母親”。她對我要求嚴格不僅反映在細節把握方面,還反映在“做錯事了就該受到懲罰”這幾個字上面。做錯了題,就該挨打;對父母有了情緒,就該罰跪(但往往“罰跪”這兩個字總是用來恐嚇我們的)。父母是權威,如果挑戰權威,就該受到相應的處罰。他們似乎做出了重要決策,找準了時機,在孩子們尚能拿捏的童年建立起一個等級森嚴的家庭制度,而我的母親似乎就站在制度的頂端。但一枚硬幣總有兩面,“唯對錯論”的價值觀雖然給我帶來許多情緒上的痛苦,讓我持續長久地沉迷于一件又一件已經發生的過失里,但總能讓我在失敗當中有所成長,成為具有“完美主義”傾向的“唯對錯論”者。這樣,別人在問我想要吃什么水果的時候,我總會先想:在這個場合,面對這些人,我選擇吃什么水果才是對的?如果因為在餐廳上吃菠蘿顯得異類,我會感到不安,也會長久難以釋懷這份羞恥。
而童年記憶里,父親這個角色似乎成為了一團像霧一樣的陰影,邊界模糊不清,甚至留給我的印象還不如母親的深刻。他總能在母親實施那套準則開始推行道德教育或價值觀教育的時候唱白臉,勸誡母親別說了,或是以一種與母親截然不同的態度來安慰小孩,似乎想以此類“溫柔”突出他與母親的區別,給小孩留下好的印象。有時候,他對于小孩的錯誤也許會置之不理。但我可以說他的存在感似乎微乎其微了,他在我的童年里唯一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便是在我追問“為什么你只喜歡妹妹不喜歡我”的時候,留下了一句“誰說的”。可事實上,妹妹出生以后,他只會抱妹妹,再也沒有抱過我,而我卻從未在母親那里看到這種改變。他總會替我謀劃各種各樣的出路,關心我的前程,是我人生一位很重要的“導師”,但也只限于導師。
來自父母的溫情,我似乎在大學以后才能學著體會到。當然,作為一個天生對情感就不太敏感的人來說,即使父母如何如何地釋放他們對我的愛意,我想我也不會多么感受到的吧!隨著我的年齡增長,父母對我的關愛也慢慢從我的學業和事業上剝離,轉向心理健康和生活健康。
絕對的“對錯論”讓我在這件事情上出現了和往常碰壁時候一樣的內疚、自責、悔恨、悲傷感,因為我總覺得我犯錯了,而且是一個不小的錯誤。所以,即使在打電話之前我沒有徹底醒悟,在打電話得知母親不同意這件事以后,我感受到了一絲恐慌,因為我總以為母親是對的。在嘗試要回錢款,回到原先既定狀態后,半陌生人不愿意退款給我以后,我的世界好像突然就變成灰色了。無數災難在我的世界里預演:“我貸款了,等發工資還……如果沒還上,爸媽知道了這件事情怎么辦?承諾他們的三千塊錢怎么還給他們?如果還了我的生活費又有什么著落……”一方面,我覺得我蠢,做出了一件令人不恥的事情,與我一直以來自詡的“清高”人設相撞;另一方面,我非常自責,不敢想象這樣一筆錢不見了,如果是爸媽知道了他們會怎么樣罵我(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他們掙錢那么不容易,我卻這樣胡亂揮霍)。
我想起來書里引用的一句話:“我們應該在危難來臨之前做好應對它的準備,或者勇敢迎接它,而不是先把自己消耗殆盡。”我也以為我可以做到勇敢,但現實并非如此,莫名其妙的恐懼總是不斷滋生。我總是不斷想起來貸款的問題,總覺得我欠了很多。我能想到唯一的辦法便是祈求早一點發工資(正常安排是八月中旬發八月以前三個月的工資)。如果是已成定局,那我似乎只有力氣哀嚎。而在首發三個月工資以后,這筆工資的絕大部分錢需要用來還貸款。
我以為苦難會伴隨暴雨,暴雨會伴隨洪澇,卻沒想到也會迎來太陽。相識已久,相知卻淺,我從來沒想到會有人愿意借錢助我周轉。更出乎意料的是,對方道出的理由——從情緒低谷、收入中斷到生活質量受困——切中了我未能言明的困境。我很震驚,也感覺到了那么一絲輕松。或許對于我來說,欠債的壓力不會消失,但那一刻,凝滯的世界好像重新流淌起了色彩。或許是因為這份信任。
2025/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