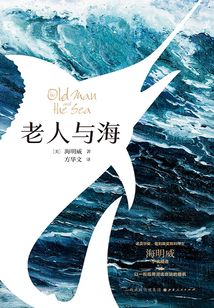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序
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世界文壇最為著名、最有個性的巨擘之一。他的父親是名醫生,酷愛打獵、釣魚等戶外活動,他的母親喜愛文學,這一切都對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學畢業后,海明威曾在堪薩斯的《星報》當了六個月的實習記者。這家報社要求新聞報道簡捷明快,海明威深受其益,形成了洗練的文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加入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奔赴意大利戰場,曾多次負傷。大戰結束后,他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軍功獎章”“銀質獎章”“勇敢獎章”。此后,他作為記者常駐巴黎,一面寫新聞報道,一面寫小說。
在寫作風格方面,正如英國作家赫·歐·貝茨所說,海明威那簡約有力的文體引起了一場“文學革命”,在許多歐美作家身上留下了痕跡。海明威尊奉美國建筑師羅德維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趨于精練,縮短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并提出了“冰山原則”,只表現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實、含蓄、耐人尋味。海明威的寫作態度極其嚴肅,十分重視作品的修改。據說他每天開始寫作時,要先把前一天寫的文稿讀一遍,讀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書寫完后從頭到尾改一遍;草稿請人打字謄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樣出來再改一遍。他認為這樣的三次大修改是寫好一本書的必要條件。他主張“去掉廢話”,在修改時把一切華而不實的詞句刪去,每一句、每一段都達到“精益求精”。還有人說,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膝蓋被子彈打碎,海明威必須站著寫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永遠站著”的“強硬”風格,字句也異常簡練。自殺前,他留下遺言,要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恕我再也不能站起來了”。不管原因如何,反正他惜墨如金,字字句句都是詳細推敲的結晶。雖然沒有開創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卻是一位開了一代文風的語言藝術大師。1929年,《永別了,武器》問世,以后又發表了《有的和沒有的》(1937)、《喪鐘為誰而鳴》(1940)和《過河入林》(1950)等幾部長篇小說。但真正使他留名世界文學史的是中篇小說《老人與海》。《老人與海》于1952年出版,翌年便榮獲普利策獎,1954年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雖然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說思想性強,令人回味無窮,贏得了成千上萬的讀者。美國著名史學家威德勒·索普曾在《20世紀美國文學》中寫道:“盡管海明威的小說要隔很長時間才出版一本,但是在一本新小說出版之前的幾個月就已經引起了人們的爭論,并且這種爭論在小說出版后的幾個月還在繼續進行。”海明威的作品大受歡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其中充溢著美國人所喜歡的“陽剛之氣”。他以高超的藝術手段塑造了一個個敢作敢為的英雄好漢。
正如我國學者于冬云在評論文章中所言:“所謂海明威的文體風格,即赫·歐·貝茨所稱道的簡潔、干凈、含蓄、凝練。這是一種‘絕不矯飾、平易粗放、街頭硬漢般的文風’,他尤其擅長用‘那種公牛般的、出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語言’來陳述他故事中的那些獵人、漁夫、斗牛士、士兵、拳擊者的思想和行為。福柯認為,影響和控制話語運動的最根本因素是權力。西方現代社會語言學研究有一種觀點認為男性語體和女性語體是有區別的,并把男性語體歸為一種有力語體,把女性語體歸為一種無力語體。以此標準來重新審視貝茨一再稱頌的海明威的文體風格,便不難發現在這種簡潔粗硬的文風下掩蓋的男性權力特征……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海明威的敘事文體是一種典型的男性話語方式。”獲獎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種疾病,身心遭受了極大的痛苦,沒能再創作出很有影響力的作品,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極悲觀的情緒。1961年7月2日,蜚聲文壇的海明威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整個世界都為此震驚,人們紛紛嘆息這位巨人的悲劇。美國人民更是悲悼這顆美國文壇巨星的隕落。在這個總統死了都不會舉國哀痛的國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國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憑他獨特的作品,就憑他那硬漢精神!
海明威逝世已六十余年,而他的作品仍煥發著強大的生命力——海明威不死!如何翻譯他的作品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們堅決反對“對號入座”式的字對字翻譯,因為這樣的譯文完全是西語結構,甚至會出現文理不通的現象——每個字讀者都是認識的,但就是不知道這些字連在一起表達的是什么意思,瞿秋白稱其為“非驢非馬的騾子文”。這樣的譯文恐怕連小學生的作文也不如,只能算作“信手涂鴉”,乍一看倒是做到了“移形”,卻忽略了“傳神”。看鼻子、眼睛和裝束與原作并無差異,只是少了原作的精氣神,像是原作的“木乃伊”,失去了活力。我們建議重視和采用錢鍾書的“化境”理論。所謂“化境”,不僅要求譯者“移形”,還要“移意”和“移味”,也就是說應該做到“形神兼備”,讓原作“投胎轉世”,從“譯出語”徹底融入“譯入語”。其中最難的恐怕要算“移味”,也就是用譯文反映原作者的審美情趣、藝術風格以及人生觀等重大卻又微妙的因素。還有一種傾向也應該警惕,那就是“借景生情”“借題發揮”,只是一味展現自己的文采,全然不顧原作的內容,翻譯出的作品只有“張三李四”的味,卻缺少了海明威的味。魯迅曾戲稱這樣的譯文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與原作“風馬牛不相及”的譯作。瞿秋白當年批評這種不負責任的譯者:“……是和城隍廟里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是欺侮讀者,信口開河地亂講海外奇談。”[1]翻譯本身就是很難的,翻譯海明威的作品更難。翻譯得不好,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就沒有了“英雄味”,而會變成一個個沒精打采、胡言亂語的“小癟三”——這樣的情景是誰也不愿看到的。我就是懷著這份忐忑、警惕之心著手翻譯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說的……
方華文
2021年9月1日
作于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