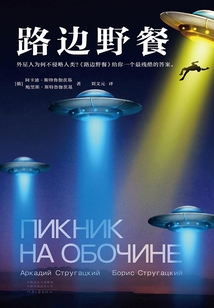
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序
厄休拉·勒古恩
這篇序言的一部分摘自我在1977年為《路邊野餐》撰寫的一篇評論,那年這本書的英語版本首次發行[1]。我想把那個時代讀者的一些反應記錄下來。當時,蘇聯最糟糕的日子依然歷歷在目,而蘇聯小說在智慧和道德上仍舊趣味盎然,散發著勇于冒險的魅力。同樣是在那時,對蘇聯科幻作品的正面評價在美國還很少見,基本上都是關于它們的政治聲明,因為美國科幻界那些參與冷戰的人士認為,生活在鐵幕[2]之后的每一位作家都是敵方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為了保持道德的純潔性,這些保守派拒絕閱讀(保守派們向來如此),這樣他們就不必注意到這個事實:多年來,蘇聯作家一直在用科幻的形式書寫相對不那么受其現實影響的作品。
無論何種現狀,科幻小說都很容易運用想象力加以顛覆。那些官僚和政客不懂得如何培養自己的想象力,往往認為里面不過就是些射線槍和胡說八道的玩意兒,只適合給孩子看。作家可能只有像扎米亞金在《我們》中那樣對烏托邦公然批判,才會招致審查機關的鎮壓。斯特魯伽茨基兄弟既沒有公然批判烏托邦,也從未(據我所知)直接批判他們政府的政策。他們所做的無非就是寫得仿佛對意識形態完全不感興趣,我當年覺得這是最令人欽佩之處,現在仍然這樣認為,而我們許多西方國家的作家都很難做到這一點。這二位就像自由之人一樣寫作。
《路邊野餐》講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第一類接觸”類的故事。外星人造訪地球,隨后便離開了,在地球上留下幾個著陸區(現在被稱為“造訪區”),里面到處都是他們丟下的垃圾。野餐的外星人已經走了,馱鼠一樣的人類雖然高度警惕,但同時也充滿好奇,他們靠近皺巴巴的玻璃紙、啤酒罐上閃閃發光的拉環,試圖將其馱回自己的洞穴。
大部分垃圾碎片都令人費解,且極度危險。其中一些被證明很有用(比如為汽車提供動力的永續電池),但科學家們始終都不確定,他們對這些裝備的應用方式是否恰當,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把蓋革計數器當作手斧,把電子元件當作鼻環。他們搞不懂這些造物的工作原理及其背后的科學問題。一家國際研究所資助了這方面的研究。交易垃圾的黑市繁榮起來。“潛行者”潛入禁區,冒著各種駭人的致殘或死亡風險,偷取外星人的垃圾,把東西帶出來,然后賣掉,有時甚至還會賣給研究所。
在傳統的“第一類接觸”類的故事中,溝通一般是由英勇無畏、富有獻身精神的太空人完成的,緊接著,雙方會進行知識交流、軍事較量或做一筆大買賣。但在《路邊野餐》里,那些來自太空的造訪者即便注意到了我們的存在,對溝通也顯然毫無興趣。也許在他們看來,我們就是野蠻人,或者與馱鼠無異。他們不予交流,我們無從了解。
可是,人類需要了解。那些造訪區影響著每一個與之相關的人。對造訪區的探索滋生了腐敗和犯罪;逃離造訪區的人,災難如影隨形地跟著他;潛行者的后代基因發生變異,變得不像人。
雖然基于這一晦暗設定,作者卻將故事寫得真實生動,走向令人難以預測。故事地點好像位于北美,也許是加拿大,但人物并無特別的民族特征。但是,他們每個人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討人喜歡。那個老奸巨猾的潛行者——倒賣商渾身散發著一種既令人反感、又招人喜愛的活力。作品中的人物都很真實可信,沒有什么才智超群的角色,都是平凡之人。核心人物雷德就是個普通人,他脾氣暴躁,冷酷無情。大部分角色都吃苦耐勞,過著毫無尊嚴、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既不多愁善感,也不憤世嫉俗。人性沒有被過分美化,但也沒被丑化。作者對筆下的人物充滿憐憫,同時也沒有掩藏他們各自的弱點。
在本書問世的年代,以普通人作為主要人物的科幻小說是極為罕見的。即便是現在,這種文學類型也很容易落入精英主義的窠臼,主人公都是些才智超群、舉世無雙的天才,是船長而非船員,是手握大權者而非工薪階層。那些想讓這一文學類型保持專業化——更確切地說是“晦澀難懂”——的人,傾向于精英主義的風格。而那些單純把科幻小說當成一種寫作方式的人,則更喜歡托爾斯泰式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從將軍的角度,還通過家庭婦女、囚犯和16歲男孩的視角來描述戰爭。《路邊野餐》即是如此,不僅通過知識淵博的科學家來描述外星人的造訪,而且重點講到了它對普通人的影響。
人類目前或將來能否理解我們從宇宙中接收到的任何乃至全部信息?對于這個問題,大多數從科學至上主義大潮中誕生的科幻小說通常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能”。波蘭小說家斯塔尼斯瓦夫·萊姆稱之為“人類認知普遍主義的荒誕”。《索拉里斯星》是他關于這個主題的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在該書中,人類因無法理解外星生命體發出的信息或非自然物體而遭遇挫敗,他們最終沒能通過考驗。
認為“更高等”的生物可能對人類完全不感興趣的想法,會很容易受到公然嘲諷,但兩位作者卻用一種諷刺、滑稽且富于同情心的基調表達了這個觀點。在小說后半部分,一位科學家和一名心灰意冷的研究所員工,就外星人造訪的影響和意義展開了一番精彩絕倫的辯論,作者在倫理道德和智慧上的超高修養由此躍然紙上。不過,個體命運才是故事的核心。一般而言,點子文學的主人公都是提線木偶,但雷德卻是個有血有肉之人。我們關心他的命運,因為他的生存和救贖都處在危急關頭。畢竟,這是一部俄國小說。
斯特魯伽茨基兄弟把萊姆關于“人類理解論”的討論做了進一步的升級。如果“人類處理外星人遺留物品的方式”是一種考驗,或者,如果雷德在最后那可怕的一幕中經受了殘酷考驗,那么,考驗實際上是什么呢?我們怎么知道到底通過了沒有?究竟何謂“理解”呢?
最后的許愿“希望每個人都幸福、自由”,無疑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不過,這部小說絕不僅是關于蘇聯解體,或者基于科學的“普遍認知論”之美夢破滅的寓言。在書中,雷德的最后一句話是對上帝說的,也可能是對我們說的,那句話是:“我從未將靈魂出賣給任何人!它完全屬于我,還有未泯滅的人性!你自己搞清楚我想要什么吧,因為我知道,我的愿望不可能是邪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