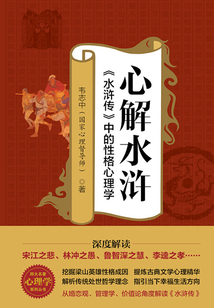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20章 李逵的天真與無知
- 第19章 巾幗不讓須眉,解讀水滸女英雄
- 第18章 存天理滅人欲?太天真
- 第17章 從《水滸傳》看婚姻關系
- 第16章 難成大事的梁山團隊
- 第15章 表面智多星,實則真“無用”
第1章 前言
編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解讀心理學的智慧,為我們今天的生活、工作做指引,給我們的現實生活帶來啟發,為我們遇到的具體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有一個成語叫作古為今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一直以來是心理學人,也是其他學科的專家一直在做的。這話最早是毛澤東提出的,毛澤東也喜歡讀經典,而且他不但讀,還評《三國》、評《水滸》,自己也經常引經據典。也就是說,為什么名人、偉人能在講話中提起經典?是因為他們不但讀,還會加以拓展。我之前到山東孟府孟廟講學的時候,看到有一個走廊,展板上面累計著習近平歷次講話中提到孟子的次數。孟府孟廟里展出的習近平講稿當中,也提到過孟子的學說、孟子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過很多經典。比如他也講過《左傳》《資治通鑒》里面的內容。記得他去韓國訪問的時候,談到關于交朋友的問題,他提到: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這也是傳統經典里的內容。
這不是在“抖書袋”,也不是通過引經據典來體現自己的高大上。不論毛澤東也好、習近平也好,他們都從傳統的經典中獲得了深刻的感悟。在古代,是不分學科的,沒有數學、化學這些學科,也不分文科理科,更沒有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哲學,基本上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導。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先生,他的前輩陸九淵就是研究心學,研究人的精神、意志世界。孔子則研究倫理學,但是又不完全是倫理學。梁肅民先生解讀儒家經典《論語》,他說《論語》不是哲學,因為哲學是西方人的思想體系;也不是教育學;也不是倫理學。那它到底是什么學呢?他說這叫作“自己學”,是研究自己的一門學問。自己在成長中發現的規律,針對這些規律進行研究和探討,總結出來,就變成了《論語》,這就是“自己學”。
過去的經典都包含了什么?涵蓋面非常廣,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包括兵家、法家、道家、農家等。比如農家講究種地,提出了二十四節氣,現在二十四節氣已經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了。我們也出版過關于二十四節氣的書。在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涉及人的生活發展、人類文明進步、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內容。就好比中醫,它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是道,是一門綜合性的醫學。西方并沒有真正認識中醫,而等到西醫的不足之處漸漸顯露的時候,中醫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為什么?因為它是一個綜合的整體。這就是為什么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因為它的內涵相互連接、貫穿縱橫。
作為一名心理學工作者,我們要學習如何在傳統文化和經典中發掘精華。如果我們能夠發掘這些精華,并且加以利用轉換,那就不得了了。對傳統文化的發掘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發掘整理,第二個層面是詮釋轉換,第三個層面是技術應用。
發掘整理由理論家來完成,他們在浩瀚的文化經典寶庫中,一點一點地提煉出里面的精華,將它們編排出來。就像考古工作者,要慢慢用刷子、用小鏟子把土剝開,再把文物一件一件碼好,編好號,甚至把土層也分類標記,這就是發掘整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理論家需要有很充足的經驗,需要很大的能力。很多時候注重應用的心理學人看不起發掘理論的過程,但若是沒有這樣的發掘整理、理論的加工,我們今天就不可能有應用背后的理論依據。
詮釋轉換,就是把經典著作本身的內容和其內涵重新進行詮釋,也就是解讀和詮釋經典。詮釋轉換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經典注我,另一個是我注經典。前者是我們依據經典原來的樣子,想盡一切辦法去還原。比如經典的原文,有16種文獻解釋不一樣,有多種角度的解釋,那我們在詮釋的時候,就把這16種以前的詮釋全部展開,拿出來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一個最終的結論,提出新的詮釋,或者去論證那16種詮釋中自己最支持的一種。詮釋轉換也是一種有著應用思維和視角的理論家工作。從事這類工作的往往就是學院派,或是在科研院所里的實踐派理論家,是以應用為主的。可是這個時候大家發現,詮釋轉換還不能夠為我們所用。比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個句子過去有人這樣解釋,說學習是快樂的;也有人那樣解釋,說實踐是快樂的;還有人認為這句話是在說,沉浸在學習的海洋里是快樂的。一句話能有許多種解釋,那么我們就可以把所有解讀展開進行詮釋。有人會問,別人怎么解釋跟我有什么關系?提出新的詮釋之后我又要怎么用?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學老師,是教書的,我怎么能夠讓我的學生快樂呢?有了詮釋而不知如何應用,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有第三個層面——技術應用。
發掘整理和詮釋轉換都完成后,我們就要落地。什么叫落地?落地又要做什么呢?落地其實就是指做出一個具體的心理教育技術。學而時習之,我們帶著學生學習一遍之后,讓他們來表達他們在學習當中的體會。體會過程中,讓他們去親手操作,操作完之后讓他們分享。我們把這個過程變成一個科學流程,然后就可以發展為一個心理教育的技術了。這樣一來,學生們就可以感受到應用技術前后學習體驗的差異。學生以前是對著書本使勁念、使勁記,學得既不舒服也不快樂,很悶。而現在,老師把自己教的知識轉化為具體的技術,使用了新的教學技術,這樣的效果和傳統的教學是不一樣的。在解讀經典當中,一種方向是由上自下,另一種是由下自上。
在說這個之前,我要把剛才說的“經典注我,我注經典”解釋完全。剛才我只說了一半,即“我注經典”,就是由我們去還原經典的真實含義,尊重真實,不能有任何主觀性的猜測,不能憑借自己的感覺、用自己的假設去做文章。另一種就是陸九淵提出來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進行新的以需求為導向的轉換和詮釋。這就是古為今用的另一個方向了。
如果我們只是還原經典的真實面貌,那它對于我們的價值就大打折扣,雖然我們繼承了,但是我們沒有發揚。習近平主席在歷次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講話中都提到,我們要繼承,還要發揚。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什么是去其糟粕?有一個詞叫不合時宜,有人認為去其糟粕就是拋棄不合時宜的內容。當時的那種理論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好的,但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到了現在這個背景下就不再適用了,我們要與時俱進。可是我的觀點不同,我認為兩種都要保留,古代背景下產生的那樣的一種觀念,一種理論,一種思想,一種方法,我們還是可以保留下來作為參考和借鑒,但這不意味著我們要去應用。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去掉,不能把它從教科書上刪去,因為刪去了就沒有參照物了。
我重新解讀陸九淵,提出了“經典注我,我注經典”的觀點。發掘整理,就好比去一個墓穴進行考古工作,這個是誰的墓葬,里邊有什么寶貝,是什么時期的墓葬,當時的工藝水平如何,這都是客觀事實,容不得主觀臆斷。一上去就猜測,只粗略地觀察就得出結論是行不通的。未經驗證的猜測是不能作為結論的,這就是以理論為主導的工作。但若是以應用為主導,那應該怎么做?以解決實際的問題為導向,那就可以從“我注經典”的角度來工作了。“我注經典”是指我們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注經典。如果說一個應用者,一個實踐家,也遵循理論家的“經典注我”,那“我”就沒有立身之地了。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重復理論家的“之乎者也”,那我們早就餓死了。
像我們這種在社會上做心理學研究的人,自稱為民間智庫。智庫有三種,國家智庫、大學智庫和民間智庫。目前中國社會學科領域,國家智庫是非常強大的,資源是最豐富的。至于大學智庫,各個大學也有各種研究所,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上的各種研究所、研究院一年發表的論文數量也是非常龐大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豐富的。而民間智庫的成就基本上為零。作為我們研究院的院長,我認為我們至少要有一些作品,做出一些實際的研究。我們作為民間智庫,要著重于以應用為導向的研究。這就涉及由下至上和由上至下的視角。
由下至上是我們在實踐中發現了一個問題,然后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這種角度就叫作由下至上。下就是下游,下游就是實用的、應用的,具體需要的,而上游則是源頭。
我們既要站在下游看源頭,又要站在源頭看下游,也就是說除了由下至上,還要由上至下。有了這種整體思維才可以站在經典的世界里解讀經典,不然你就只能片面地學習,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什么學什么。要有上游的思維,要有科學的、整體的思維,有了發掘整理理論的能力,你才不會亂來。這就是由上至下的重要性。要根據大眾的需求,從理論出發,生產技術和應用,然后再從應用中總結經驗,提煉為新的理論。專業的心理學人要有科學和整體的思維。
這是很重要的觀點,為什么?因為我們在學界有來自學院派的批評,學院派的人認為專注于研究應用的人不夠科學。而研究應用的人也往往容易過度自卑或自大,用這種過度的自我否定或肯定來進行自我保護。學院派的人認為應用派的技術只是個游戲、一種不科學的小把戲。這兩個流派之間總是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但大家要理解的是,由下至上的應用派、由上至下的學院派,都是有自己的科學依據的。并不是說著重于應用和實踐探索不科學,也不能說搞科學研究、發掘整理就沒有實際意義。這兩者都是有用的,有用則無用,無用之大用,這是莊子的思想里面早就講過的,此一時彼一時,此時無用,他時有用。一塊木頭不會因為不能被用來做板凳而變得無用,它可能放在路邊,一個過路人碰巧鞋上有泥,在木頭上面把泥蹭去,你說它有沒有用呢?如果用板凳去蹭鞋上的泥,反倒不合適,因為要把腳抬得老高,還未必能擦干凈,但是用一塊粗糙的木頭,就能很輕易地蹭干凈鞋上的泥。有用還是無用不是絕對的,我們要以道家的思想去辯證地看待。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解讀經典的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從實際需求出發,自下而上地去解讀和應用經典,這個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和原則。
第二,我們要區分在經典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無用的。并不是說一部經典越著名就越有用,有用的經典要契合當下的環境與需求。作為學習心理學的人士,我們要從經典里吸收對我們有用的內容。
第三,我們不可斷章取義。對于經典的解讀非常多,但是人們會發現以往的解讀里有很多斷章取義的部分,會摻雜作者自己的思想,沒有站在比較全面和足夠客觀的角度去思考。所以在我們的解讀中,要以更全面的視角,而不是斷章取義地解讀。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無論是積極的,還是一些已經跟時代脫節的觀念,都是符合我們民族傳統的心理歷程的。這些歷程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能夠為我們的生活服務什么,這都是我們在學習經典的過程中需要思考的。
每一個人都從自我需要、自我感受為出發點去學習的。不同的人學習了同樣的東西,他們所接收到的信息,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樣的。這本書的第一章主要討論了如何解讀經典、解讀經典的方法、解讀經典的原則、解讀經典的態度和解讀經典時的注意事項。這樣就可以使資歷尚淺的人,對文化心理學,對理論心理學,對文藝、美育心理學沒有太多了解的人,對這個領域產生初步的了解。但我要在這里強調,我們這本書對經典的解讀是主觀而不是客觀的,為什么?因為我們是自下而上的,是從人們的需求出發,從心理學的角度去解讀經典,這必然會導致一些不客觀、不完全符合經典原意的情況。我們站在心理學的角度,以心理學的需要去解讀傳統的經典,是無法完全還原經典的。
這就涉及既要避免自己的主觀意識,又要站在自己主觀的立場考慮自身之需求的辯證思路。既然是心理學的視角,就和其他的視角不一樣。而心理學也有多個視角,這個就是主觀中的客觀。比如,在《向〈西游記〉取育兒經》一書中,《西游記》是我主要的解讀對象。而這一次我們主要解讀《水滸傳》。《水滸傳》和《西游記》同屬四大名著,我解讀《西游記》的時候,是以成長的視角來解讀。孫悟空從石頭縫里蹦出來,到成佛的過程,這是他的成長過程。一講到成長,就涉及心理學領域了。而成長和發展不可能和人格沒有關系。所以對《西游記》的解讀,就是把發展心理學里的內容,把人的發展過程和孫悟空從猴到佛的發展過程對應起來,找到其中的規律,再結合現代心理科學的研究原理,最后轉換成為具體的指導思想、理念和方法。這便是《向〈西游記〉取育兒經》一書的由來。
我未來還計劃撰寫另一本書,和《向〈西游記〉取育兒經》是姊妹篇——《向〈西游記〉取心理成長經》,講述的是唐僧而不是孫悟空的成長。孫悟空的成長是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而唐僧是一個修行者,是想要讓這個社會、讓更多的人因佛法而受益的一個有追求的佛門弟子。那么他們的成長經歷必然是有不同的。同樣是講成長,一個是通過孫悟空談青少年兒童心理的成長和發展,一個是通過唐僧談成人世界的心理成長,那么我們就可以針對一本《西游記》,以兩種不同的視角來做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