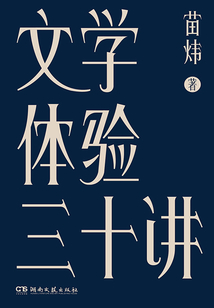
文學體驗三十講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為什么他在“賢者時間”吃一塊西瓜呢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忽然取消了年夜飯,大年初一的一個聚會也取消了,那個晚上有點兒霧霾,街上靜悄悄的,不見人影,我開始動筆寫這部書稿。后來的世界發生了很多事,但寫起來倒也很順暢,兩個月也就寫完了。從文學青年當到文學中年,這樣整理自己讀過的小說還是第一次。
文學這東西是啥呢?不過就是表達一下情感,大家交流一下情感,體會一下活著是什么滋味。小貓豎起尾巴,是它高興了;狗見面叫兩聲,也是在表達自己的心情;人比貓狗復雜一點兒,要用文學和藝術來傳達活著是一種什么滋味。
魯迅先生有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這段話很冷漠。
魯迅先生還有一句話,非常有詩意。他是這么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他老人家前面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也許,他寫這段話的時候很健康,病了以后想法就不一樣了。
一九三六年他生病了,有一天覺得病情有點兒緩和,夜里讓許廣平給他倒點兒水喝,打開燈,讓他四下看看。許廣平給他端來茶,喝了兩口,但沒給他開燈,說,為什么開燈?魯迅說:“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么?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去地看一下。”許廣平還是沒給他開燈。魯迅躺在床上,看見什么了呢?他說:“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
《“這也是生活”》這篇文章,寫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沒過多久,魯迅先生就去世了。
不同的人生狀態,可能有不同的人生感受。但有時,我們可能會有互相矛盾的感受:一方面覺得,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一方面又覺得,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過去的兩三個月,和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可能都會有一些復雜的感受。
怕死嗎?當然。覺得自己孤獨嗎?從來都有點兒孤獨。有一點兒抓狂嗎?還好。以后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呢?不確定。為什么我的想法和別人不一樣呢?我能安靜一點兒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為好呢?世上那么多人,真的和我有關嗎?我們真正關心的人有幾個呢?我該同情什么,我又能憐憫誰呢?我是不是就有點兒可憐呢?愛是什么呢?
文學提供不了答案。文學沒什么用,大家不靠想象生活。但在很少的時候,文學幫我們逃避。
也可能不止逃避。文學總是有點兒“喪”,有點兒優柔寡斷,總是會帶來很多負面情緒,但它也會幫你處理很多負面情緒。文學還關心失敗者,但文學較少關心“時代的一粒灰”,更多關心一個人面對的那座山,關心個人的困境,關心那些歷史褶皺中的人,幫他抖落開細碎的、不為人知的感受,幫他獲得安慰,幫他獲得一種“心靈之鏈”,讓他有一點點穩定感。
美國有個文學評論家叫哈羅德·布魯姆,他說,我們都害怕孤獨、發瘋、死亡,莎士比亞和惠特曼也無法讓我們不怕,但他們帶來了光和火。
這光和火是什么呢?安慰、同情和理解,洞察更復雜的人性。
是的,我獲得了這些。
但我覺得,還有點兒別的東西。
不一樣的人——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在國外看見猶太人的感覺,他們穿著黑色的袍子,戴著小帽,發型也怪怪的,在他們的街區上散步。原來這就是猶太人,是不一樣啊。我琢磨自己為什么會有那樣強烈的異樣感?從小到大,我接觸的都是差不多的人,總有人向我強調“集體”,總有人擔心“不一樣”,即便是現在我們到了一個所謂“價值多元”的時代,大家也對“異己”這東西有排斥。我們只跟自己相處,只跟同時代的自己相處,這種駭人的孤陋寡聞總讓人覺得貧瘠。
簡單和復雜——
我還記得第一次讀到《西西弗神話》里,神懲罰西西弗,讓他每天推一塊石頭上山,推到山頂,石頭就落下來,西西弗要回到山腳下繼續推,周而復始。神為啥要這樣做呢?以前我看的故事是“愚公移山”啊,一個老頭兒帶著家人要把門前的大山挖走,他們鼓足干勁兒,子子孫孫無窮盡,打算祖祖輩輩干下去,可沒過些日子,神就出現了,幫著愚公移走了大山。
會有一個神幫我解決眼前的困境嗎?還是他會把我安排在一個類似西西弗的困境中?我總覺得,后一種情況出現的概率更大。我們的想法還是不要像愚公的那樣天真簡單。
我們現在是不是變得簡單了呢?比如說用“三觀正”來要求文藝作品,誰的三觀算正呢?D. H.勞倫斯正嗎?尼采正嗎?不能“踩一捧一”?可文化產品需要判定優劣啊!什么事情都以“我懂不懂”“我喜歡不喜歡”來衡量嗎?政治正確?這又是哪兒來的標準?我們對更復雜的敘述沒耐心了嗎?我們是不是看了太多(可能也寫了太多)情緒化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只停留在第一次的反應上呢,對文章的評價就是解氣、痛快、憋屈、放屁、胡說八道、真好?我們會想得再深一點兒嗎?
思想總是晚來一步,誠實的糊涂卻從不遲到;理解總是稍顯滯后,正義而混亂的憤怒卻一馬當先;想法總是姍姍來遲,幼稚的道德說教卻捷足先登。
——萊昂內爾·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職責》
對現成說法的質疑——
還是一段個人經歷。有一次沙龍,有個讀者提問,說他是個大學生,該怎么應對碎片時間的學習?我有點兒糊涂的是,學生不應該有大把的時間學習嗎?誰把他的時間切成了碎片?現在這個時代真的是碎片化了嗎?收音機里的外語講座從來是二十五分鐘一節課,新概念英語一篇課文的錄音一直都是兩三分鐘啊。難道你不應該花力氣凝固自己的時間嗎?還是接受一個現成的說法,說現在是“碎片時代”,然后就任由自己碎片化?這兩種做法哪一個更輕松,哪一個對你更好呢?
文學的一個功用是反對套話,許多現成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文學還會反對庸俗。我們不愿承認自己庸俗,但面對高級文化總有點兒抗拒。古典音樂,聽不懂吧?俄羅斯小說?人名太長了,記不住。面對凝聚心智的東西,我們總有一個低級的抗拒的理由。
好,以上這些問題,這本書能提供答案嗎?怎么做到更寬容?怎么變得更復雜一點兒?
提供不了答案。
但我試著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讀這本書,能對文學有一個系統的了解嗎?
好像也不能。我覺得,這本書更像是講故事。我們年幼時,都是聽故事以獲得經驗,然后學習專業知識,獲得專業經驗。這本書可能重回講故事的狀態,陪伴你度過一段孤獨的時光,讓你能有所安慰。
讀小說有什么用呢?
可能會有點兒用,比如逃避一下現實。我們賴以獲取經驗的閱讀應該更廣泛,讀科學,讀歷史,都比讀小說重要。
會推薦書嗎?
我擔心我推薦了,你也沒時間讀,我會提到很多書,如果對哪一本書感興趣,你可以找來看看。閱讀是一件私人的事,讀小說更是個人化的體驗。
到底啥叫文學體驗呢?
契訶夫有一篇小說《帶小狗的女人》,里面寫一對偷情的男女,兩人上床之后,男人吃了一塊西瓜。文學史課會講契訶夫短篇小說的成就,文學評論會講這個細節呈現出一種真實性。文學體驗可能會關注那個西瓜:為什么他在“賢者時間”吃一塊西瓜呢?他就不能吃點兒橘子啥的?西瓜那么多汁兒,滴在手指上多黏啊——可能偷情也是這樣黏糊糊的吧。
文學體驗其實就是講我的感受,這些體驗大多跟生活中的一些困境有關。但愿你有所收獲,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生活,看看人的處境,感受細膩一點兒,心靈豐富一點兒。
好吧,先說到這兒。
第一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