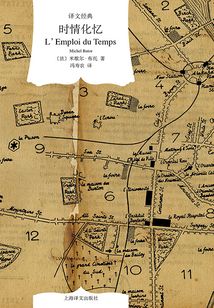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序[1]
柳鳴九先生在主編“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第四輯時向我約稿——翻譯法國著名的新小說派作家米歇爾·布托(Michel Butor,1926—)的《時情化憶》。這部小說遠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那種“無情節、無主要人物”的新小說派小說,它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既穿插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又摻有撲朔迷離的謀殺疑案。但它有別于傳統小說的是其新穎獨特的形式,這些小說形式象征性強,寓意深刻,容量大,能多層次、多側面地反映現實。總之,布托以其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技巧表現他所謂的“先進的現實主義”[2]。由于作品形式別具一格,作者遣詞造句獨具匠心,翻譯這部小說是一場艱辛的勞作。翻譯完畢,譯者欲就此書的獨特形式、翻譯上的技術處理和作品的象征意蘊淺談些芻蕘之言,并略作評論。
首先,譯者想談談這部小說的題目的翻譯。原著作品題目是“L' Emploi du Temps”,直譯為“時間的使用”,顧名思義,時間是小說的重要因素,作者獨辟蹊徑,巧妙地搭配時間,使時間的安排成為這部小說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我將小說題目意譯為“時情化憶”,似乎使其更有了一點文學味、一點美感。“時情化憶”與漢語“詩情畫意”諧音,這部小說的“詩情畫意”表現在:“詩”指布托的小說的確像一首蘭波式的長長散文詩,里面的許多重復就像詩歌的“疊句”一樣回旋跌宕,布托本身就是詩人,他的小說就像散文詩一樣美;“情”指敘述人雅克對阿妮的“愛情”,在全書最關鍵的第四章“姐妹倆”中,敘述人如泣如訴地表達對阿妮姐妹倆情深意切的愛,一個個長句像他心田的涓涓細流在向阿妮哀訴衷情,他說:這部回憶錄也可以說是他寫給阿妮的一封情書;至于“畫意”,小說用大量篇幅介紹“舊教堂里的一塊彩色玻璃上的畫”以及博物館里18幅掛毯畫,前者是描繪該隱誅弟的《圣經》故事,而后者是描繪忒修斯王子闖迷宮探險的希臘神話,希臘神話和《圣經》中的這兩個故事是這部小說的基石,這些畫的寓意非常深刻,要理解它們的“畫意”是解碼文本的關鍵。“詩情畫意”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層意思。
由此,我根據“詩情畫意”的諧音改為《時情化憶》,其實許多法國作家也喜歡做文字游戲,首先是因為“時間”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形式,作家刻意在故事時間和敘述時間上進行精心的安排和實驗,新小說的創新就是在“時間”這個形式上表現出很高的詩學價值,翻譯這部小說的題目離不開“時間”或“時”,因此,我借“詩情”改為“時情”,從諧音角度突出“時”這個主題,“時”隱含著“詩”意;而這個“情”仍然保留,表現敘述者對兩個姐妹的深切愛意;“畫意”為什么改成“化憶”呢?因為這是一本日記體的回憶錄,布托的回憶有點像普魯斯特的“追憶”那樣追蹤失去的時間;“化”是變化之意,如:梁祝的“化蝶”,春風化雨的“化”之意,小說里的時間和愛情通過布托的藝術手法“化”作一串串的回憶,經過作家的精心安排,組成一曲交響樂般的回憶錄。
一
評論首先應從文本的表象入手,尋找表象的獨特性。憑著經驗和直觀,可以發覺文本表層的語言的“陌生化”或風格的“偏離”,以及主題的反復出現等異常現象,它們就是獨特的表象,是作者的匠心所運或者潛意識的投射。這些獨特的表象往往蘊含著作品的象征意義,從這些表象可逐步深入到作品的深層結構。
如果說米歇爾·布托的《時情化憶》的表象富有獨特性,那么首先是小說的長句子。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除普魯斯特外,可能其次就是布托用句最長。倘若以一個句號算為一個句子,在《時情化憶》里,通常是一個自然段為一個長句,最長的句子達十多段,占三四面紙,約有兩千多個單詞。長句有的像峰回路轉、連綿不斷的溪流,有的像重重疊疊、枝繁葉茂的樹,更像一把散開伸長的扇,就連法國讀者見到這些長句也會咋舌,翻譯之艱辛在于先要不厭其煩地把長句拆散、捋清、梳理,然后才能用相應的中文加以表達。但這些自出機杼的長句卻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隱含著深邃的象征意義。敘述者自我坦露:“長長的句子猶如細繩一樣繞在這個墩上,又把我連在5月1日這個日子上;那天我開始編結這條細繩,這條句子細繩是一條阿里阿德涅的線,因為我處在迷宮之中,因為我埋頭寫回憶錄以便重新處在迷宮里,所有這些線都是我給已識別的路線上標記的路標,我在布勒斯頓度過的日子的迷宮比起克里特島迷宮要復雜得多,因為我越往前走,迷宮就越在擴大;我越想探索它,它就越是變形。”(7月28日星期一日記)。《時情化憶》這部小說敘述了法國青年雅克·雷維爾來到英國布勒斯頓一家公司實習一年,進城后,布勒斯頓的煙塵、瘴霧、寒冬、無聊、骯臟似乎要吞沒他,這個城好像魔鬼在施魔法,使他疲怠不堪、意志消沉、麻木不仁,他覺得自己在漸漸地遺忘過去。雅克仇恨這個城市,他不屈服于城市的壓抑,要奮起反抗,要像希臘神話的英雄忒修斯一樣進迷宮探險,殺死怪物彌諾陶洛斯。雅克在進城七個月后,即5月1日開始以寫回憶錄的形式來探索這座布勒斯頓城迷宮:“我決定寫回憶錄,以便我重新回到過去,治愈自己的病,以便弄清我在這個充滿仇恨的城市中經歷過的那些事,以便抵御城市的迷惑,使自己從麻木的狀態中蘇醒過來……為了不使布勒斯頓的污垢染黑我的血、我的骨、我的眼睛,我決定在我的周圍筑起一道城墻,它是用一行行回憶錄來構筑的……”(8月5日星期三日記),而這一行行回憶錄的長句象征著一條阿里阿德涅線。
雅克初來布勒斯頓,邂逅一位秀雅明麗的姑娘阿妮,兩人心心相印,在雅克最孤單無聊的日子里,阿妮日日陪他共進午餐,成為雅克心靈里的一片綠洲。阿妮就像希臘神話中的阿里阿德涅公主一樣給他溫暖和柔愛。阿妮是文具店的售貨員,賣給雅克一張城市地圖,使他認清城里街道、建筑物的布局,后來阿妮又賣給他一大刀白紙,他就是在這些稿紙上開始寫回憶錄。這張地圖和這刀稿紙象征著阿妮給他一個線團。不久之后,阿妮的胞妹來此度假,羅絲更加嬌媚可愛。雅克如同希臘神話里忒修斯王子背叛阿里阿德涅一樣,疏遠了阿妮,企圖親近羅絲。羅絲也像希臘神話里的費德拉公主一樣妖艷,但雅克生性膽怯,沒有抓住時機向她求愛。當他獲悉羅絲和同胞呂西安訂婚時,黯然神傷,發現自己真正愛的人是阿妮,轉回來再找阿妮,想向她吐露衷情,卻為時太晚,被冷落的阿妮另有所愛,雅克痛不欲生。從某種角度看,這部回憶錄也可以說是雅克寫給阿妮的一封情書,一個個長句也像一條雅克心田中涓涓流出的長長細流在向阿妮哀訴衷情。由此可見,布托的長句隱含著象征意義,是他情感的投射。在翻譯時,譯者企圖保持原著的這種長句風格,但漢語的句子一旦太長,讀起來免不了佶屈聱牙,因此,在漢語表達上用的是通常句子,但在標點符號上像原著一樣,采取“一逗(號)到底”的方法,一段一個句號,原著中長句有多長,譯文上也相應有多長。但法語邏輯性強,分句與分句之間都用連詞或關系詞連接,因此,在漢語表達時也適當配些關聯詞,這樣盡量保持“形似”,以展現長句的風格。
布勒斯頓博物館里掛著十八條掛毯,上面畫著希臘神話忒修斯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整部小說的縮影,《時情化憶》的故事情節和主要人物可以說是從這個神話引發出的,布托就是在忒修斯探迷宮這一隱跡紙本上再現雅克探布勒斯頓城,以及雅克與阿妮、羅絲的愛情瓜葛。這就是法國現代小說中偶爾見到的“小說套小說”(la mise en abyme)的創作技巧。正如中國的《紅樓夢》,曹雪芹在開頭和第五回設計了兩個神話,一是“女媧補天”,二是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整個《紅樓夢》的故事和主要人物是由這兩個神話引申出的。
平心而論,雅克與阿妮、羅絲的愛情故事只不過是小說的一段插曲,一條副線而已,小說的主線是敘述者“我”(即雅克)與布勒斯頓城的對立。愛情這條副線是為主線服務的,雅克把愛情的失敗歸咎于布勒斯頓城對他的戲弄和懲罰,是它把兩位美麗的姑娘從他身邊奪走,愛情這條副線加深了“我”與這座城市的對立。布勒斯頓城是一座神秘的迷宮,它像牛頭人身的怪物彌諾陶洛斯一樣兇狠,也像七頭蛇一樣變幻無常。敘述者說“從一開始,這個城市就與我對立,令人不快,使我陷入困境……它加緊控制;我目前失去航向,開始健忘,從而對它深刻的仇恨也在暗暗滋長”。布勒斯頓城使用詭計消耗雅克的精力,遏制他的勇氣,麻痹他的意志。但雅克以寫日記的形式要從這種“渾渾噩噩的混渾中解脫出來,從悶悶不樂的心魔中解脫出來”。在小說里,不僅僅“我”與城對立,而且雅克的黑人朋友——霍勒斯·巴克也是勇敢的斗士,他是非洲移民,在城里做苦工,他與這座城市格格不入,生活在社會邊緣和底層,被視為局外人,他詛咒這座城市;還有偵探小說家伯頓也是布勒斯頓的叛逆者,他以筆名J·C·漢密爾頓出版了一部偵探小說《布勒斯頓的謀殺》,寓意極深,他在書中揭發布勒斯頓的殘忍,咒罵新教堂,不僅僅他們三人,全城居民都受到這座城市的壓抑、鉗制、扼殺,全城人都在詛咒這座城市,要布勒斯頓城毀滅。由此看來,雅克、伯頓和黑人霍勒斯同處于反抗人物的聚合軸上。因此,整部小說貫穿著一個“人與城”的二元對立結構。
布托不僅僅把布勒斯頓當作一個空間、一個迷宮加以描寫,而且把它當作一個主動出擊的怪物或人物。作者用怪物彌諾陶洛斯、妖仙喀耳刻、章魚、烏龜、蒼蠅、七頭蛇等希臘神話中的一系列妖怪和動物的形象來形容城市;作者還用擬人化的手法,在作品下半部讓布勒斯頓像人一樣和敘述者對話,其實,這是敘述者內心的“潛對話”。在小說中,布勒斯頓城的化身應該是詹姆斯·詹金母子,他們倆象征著布勒斯頓的傳統文化,詹姆斯的母親長得極像新教堂的藝術神雕像,而詹姆斯是布勒斯頓土生土長的青年,從來沒有走出過這座城,他對黑人霍勒斯十分反感,表現出一種城市排外欺生的態度。伯頓在《布勒斯頓的謀殺》一書中對新教堂的誣蔑咒罵暗暗觸怒了詹姆斯母子。伯頓遭遇車禍后,詹姆斯坦白他做了一個噩夢,夢中他開著車,向一個行人沖去,這人長得既像伯頓又像黑人霍勒斯。實際上,這并非一場噩夢,卻是活生生的一場慘劇。詹姆斯在潛意識里埋下了對城市反抗者的仇恨,他成為布勒斯頓的捍衛者和執刑者。布托在創作中往往喜歡把城市和人物連在一起,在小說《變》里,塞西爾“代表著羅馬的面貌、羅馬的聲音和羅馬的邀請”;同樣,在《時情化憶》中,詹姆斯代表著布勒斯頓城。從表面上看他是雅克的同事,殷勤熱情,但實際上,他企圖用車輾死伯頓,又從雅克那里奪走阿妮。在人物深層結構中詹姆斯處于二元對立結構的另一極。在這一極的人物聚合軸上有布勒斯頓城、詹姆斯母子。在作品中布勒斯頓城仿佛是一個活生生的主要人物,它似乎知道雅克在反抗,利用雅克的虛榮和疏忽,讓雅克將《布勒斯頓的謀殺》一書的真正作者泄露出去,導致伯頓受害;它奪走阿妮,借此懲罰了雅克(“我們償清了”),和雅克打了個平手。
“人與城”的對立體現人對城的反抗和城對人的扼殺。反抗這一主題具體表現在“火”這一子題的象征意義上,城市經常發生火災,游樂園的小火車鐵軌被燒,霍勒斯在游樂室打氣槍,故意丟下煙蒂,導致火災,連中國餐館也起火關門……火災意味著城里人希望布勒斯頓城毀滅。雅克于4月30日晚把布勒斯頓地圖燒掉了,這種無意識的燒毀實際上是他發自潛意識地對城市的報復。四處的火災似乎是從他這一火種燃起。但火災使中國餐館關門停業,雅克與阿妮吃了個閉門羹,幽會不成,導致愛情失敗,雅克認為這是城市故意把火球彈回傷害他。總之,作者把城市作為一個狡獪的人物加以描寫。
城市如何會扼殺人呢?這正是敘述者在《時情化憶》中努力要探索的問題。如果說博物館里的掛毯上所描繪的忒修斯探迷宮是小說的縮影,那么舊教堂的彩畫玻璃上所描繪的該隱誅弟的《圣經》故事則是解開這個問題的密碼,是小說的關鍵所在。希臘神話和《圣經》中的這兩個故事是這部小說的基座,整部小說的大廈就是建立在這個基座上。伯頓在《布勒斯頓的謀殺》中指出:布勒斯頓城最著名的建筑物算是舊教堂的一塊描繪兇殺的彩畫玻璃。《圣經》故事該隱誅弟說明了人類始祖就互相殘殺。兇殺是《時情化憶》的重要主題之一,小說敘述了三個層次的兇殺:一是彩畫玻璃上的該隱殺害其弟亞伯的慘劇;二是伯頓的《布勒斯頓的謀殺》中板球運動員約翰尼·溫被其兄殺死在新教堂的祭廊上;三是《時情化憶》的中心事件詹姆斯·詹金企圖用車撞死伯頓。作者巧妙地把三個慘劇重疊在一起,恰似一個級差嵌套的中國魔匣。一層層打開了隱藏在匣里的秘密,揭示人類的內在悲劇。該隱誅弟是魔匣的最內層,暗示著兇殺是人類的本能。這三個故事橫貫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人類文明史,從人類始祖到現在人類就在不間斷地互相殘殺,該隱是城市的締造者,城市能有幾多和平?在敘述者眼里,布勒斯頓的圍墻上似乎都寫著“兇殺”兩個大字,城里隨時都在發生兇殺、謀殺、車禍等事故。這一切都可以從這塊彩畫玻璃上得到解釋,敘述者經過艱苦的探索,雖沒有言明,但我們可以由此解碼,得出結論:該隱誅弟乃是布勒斯頓城罪惡的本源,是城扼殺人的淵源。
二
上文我們從長句這一外在形式的象征意義出發,探索小說深層的迷宮結構——二元對立結構,我們現在試把抽象出的這一結構從深層又回到表層加以檢驗,看這一結構是否準確,是否站得住腳。
小說深層的二元對立結構投射在時間的使用上表現為“兩重時間對位”。布托在創作中借用音樂的對位法,在音樂里,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聲部在和諧的織體中結合,兩個聲部可以互換位置,如高聲部變成低聲部,低聲部變成高聲部,這就叫轉換對位,或稱二重對位,三個聲部也可以互換位置,四個或更多的轉位聲部也是如此。布托說:“平行對比、倒回過去、循環反復——這一切都是我們時間意識的基本要素,并已為音樂藝術的分析所證實。”[3]在《時情化憶》里,作者對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的處理就是采取平行對比、倒回過去、循環反復這三種手法。
《時情化憶》的主人公雅克·雷維爾在英國一年的實習已經過去一半多的時候開始寫回憶錄,寫作時間(即敘述時間)從5月初到9月底,回憶前一年10月以來經歷的事(故事時間),因此存在兩重時間: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兩個層次時而互相平行,時而互相纏繞,但敘述時間并非靜態不動,而是處于運動狀態,故事時間影響著敘述時間,敘述者眼前接二連三發生事件,他有時既要敘述眼前發生的事情,又要倒回追憶過去,從一個敘事層轉向另一個敘事層,組成雙重甚至多重的時間對位結構,這些層次的相互纏繞正是思維過程的關鍵所在,人的思維過程包含有極其復雜的層次結構,如上面一個層次是靠底下的層次來支持的,但是又反過來影響和控制底層的活動。
布托在談到他的小說時說過:“它不僅是一座空間的迷宮,也是一座時間的迷宮。”敘述者與其說在探索布勒斯頓城這座迷宮,倒不如說他穿梭于時間的隧道,在探索時間的迷宮。請看下列圖表,便一目了然。
章目 題目 日記篇數 敘述時間 故事時間:現在進行時 故事時間:最近過去時 故事時間:愈過去時 故事時間:復合過去時
第一章 進城 20篇 5月 - - - 10月
第二章 前兆 21篇 6月 6月 - - 11月
第三章 “車禍” 20篇 7月 7月 5月 - 12月
第四章 姐妹倆 21篇 8月 8月 6月 4月 1月
第五章 永別 20篇 9月 9月 7月、8月 3月 2月
←時間的隧道(7個月)→
這部日記體小說全書分五章,敘述時間從5月到9月共五個月,每個月的日記結集成一章;每章又分五節,一個月有四周半,每周(除周末外)寫的日記約二至五篇不等結集成一節;每章五節有20篇或21篇日記,全書共102篇。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書日記的中間,也就是第51篇,正好是7月中旬寫的那篇敘述偵探小說作家伯頓被車撞傷的日記,從小說的形式看,這一事件是整部小說的中心,從內容上看,它也是關鍵所在,是情節發展的高潮。敘述時間從5月1日開始,首先回憶前一年剛進城時的光景,中間間隔七個月,在這兩重時間之間便產生一個“容積”,或者說一個心理上的“深度”。自始至終,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復合過去時)平行推進,保持雙重時間對位。但由于作者仍身居城中寫回憶錄,隨著敘述時間的不斷推進,眼前的事件也在連續發生,作者又得記述正在進行中的、發展中的事情,我們暫借法語語法的時態術語加以稱呼,這叫做現在進行時故事時間,如在第二章中,作者時而敘述眼前6月發生的事,時而倒回過去敘述七個月前的事。從第三章開始為了解釋現在進行中的事態,又得回憶近一兩個月經歷過的事,這稱為最近過去時故事時間,到了最后兩章又得深入到記憶的中層,回憶四月、三月發生的事,這暫且稱為愈過去時故事時間,而始終與敘述時間平行間隔七個月的故事時間稱為復合過去時。這些故事時間和敘述時間形成一條有深度的時間隧道,作者調動自己的記憶在這條隧道中探尋,“只有通過許多其他變幻不定的日子,才能相繼給我們喚回往昔的日子,每一事件喚起前一事件的共鳴,前者卻是后者的根源,前者可以解釋后者,或者兩者互相對應”(9月24日星期三日記)。在這卷回憶的膠片上,有的地方相當清晰,有的地方相當模糊,但前者喚起后者,后者牽出前者,這樣相互補充,彌補遺漏,多次倒回追憶,在時間的隧道里穿梭往返,最后使這卷回憶的膠片光亮清晰,投射出一幅幅清楚的圖像來。
作者時間運用的第三種手法是循環反復,例如敘述者不厭其煩地回憶他多次去看舊教堂那塊著名的描繪兇殺的彩繪玻璃和博物館珍藏的十八條描繪忒修斯故事的掛毯畫,每次觀賞體會都不一樣,都有新的發現,他的認識每次都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這種循環反復目的在于突出主題,加深認識。人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是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每一次的觀賞帶來的新發現都是對前一次認識的補充和完備。循環反復相互補充,以期日臻完善。時間的兩重對位或多重對位也是一種互補關系,從認識論看,布托運用的時間技巧正符合物理學家玻爾提出的互補原理,根據玻爾的理論,描述同一微觀現象,可用很不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圖像來描述,例如波動圖像和粒子圖像,但兩者卻相互補充,缺一不可。擺弄這兩種圖像,從一種圖像轉到另一種圖像,然后又從另一種圖像轉回到原來的圖像,我們就能最終得到隱藏在實驗后面的實在的正確印象。布托在《時情化憶》中正是遵循人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來支配時間,來把握和反映世界。
這七個月組成的時間隧道雖然復雜,但終究是微觀的、短暫的、明顯的,然而細心觀察,在作品中還存在一條宏觀的、漫長的、隱蔽的時間隧道。布托說過:“我們將不得不逆時間之流而前進,越來越深地沉沒在過去之中,就像考古學家或地質學家,發掘時先在較晚期的地層進行,然后逐漸深入到古代地層中去。”[4]布托的確像考古學家一樣探索時間的迷宮,追根溯源到人類的創世之初。
這條宏觀的時間隧道隱沒在布勒斯頓城的地理空間上的各個老建筑物上。我們先看看原著扉頁上的一幅城市地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城市分為十二個區,從一區至十二區的路線呈多重“之”字形串聯排列,就像三彎九轉的迷宮路線,城市的中心區是六、七、八三個行政區,與敘述者在6、7、8月里所寫的最關鍵的三章巧合,尤其是第七區,是城市的心臟,而小說敘述的車禍也正是7月中旬發生,有趣的是雅克在布勒斯頓實習十二個月,與十二個行政區不也是巧合?這也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布托所說的“內在的象征關系”。[5]那些流動的集市像走馬燈一樣圍著城中心在四周轉動。最有象征意味的是在第七區,新舊教堂和博物館三座古老的建筑物鼎足而立,與附近的高層百貨大樓相映成趣。從現代化的百貨大樓到十九世紀建造的新教堂,再到十六世紀建造的舊教堂,由此追溯到羅馬時代的布勒斯頓城(當時稱為“戰爭之城”),以及古希臘雅典時代的影響,直至《圣經》中人類始祖的該隱,形成一條漫長的時間長廊,我們似乎看到布勒斯頓的滄桑變化,看清了布勒斯頓的本源。從某種角度看,布勒斯頓城是一個四維空間的迷宮,其中橫貫著一個時間的第四坐標。
三
布托在《時情化憶》里采用的時間對位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的啟發。他在其重要論文《巴爾扎克和現實》中這樣寫道:“巴爾扎克在寫作《人間喜劇》時,完全沒有遵照編年史的順序,他一點一點地發掘展現在他眼皮下面的一種現實的各個方面,他經常要回憶過去。”[6]在布托看來,巴爾扎克的小說也是采用敘述眼前事件和回憶過去兩重時間交叉進行。布托的時間對位法既繼承巴爾扎克的創作手法,又吸取音樂原理,作出了更大的創新。往往有人妄下定義:法國的新小說是“反傳統,反巴爾扎克的”,但米歇爾·布托的作品并非如此,他非常推崇巴爾扎克,他曾激烈抨擊有些人只讀《人間喜劇》中的幾部小說就斷章取義大談特談巴爾扎克,這是滑稽可笑的。而他通讀了《人間喜劇》的所有小說,對巴爾扎克深有研究。他強調要“把握住巴爾扎克作品的整體”[7],“如果從整體上來研究巴爾扎克的作品,我們就會發現直到今天,它的豐富和膽識還遠遠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的教益”。[8]藝術的創新離不開傳統這個肥沃的土壤,沒有傳統就沒有創新,否則創新就成為“空中樓閣”。布托認為“小說形式的創新……是更為先進的現實主義所不可缺少的條件”。[9]
布托所謂“先進的現實主義”的最大特點是用象征的手法揭示現實。《時情化憶》處處布下象征的陷阱,隱喻暗示,寓意極深。舊教堂彩繪玻璃上的該隱誅弟的故事表明了該隱在人類的創世之初就創造了城邦,由這個兇犯締造的城邦隱伏著殺機;博物館掛毯上的忒修斯的故事揭示古雅典是一切城市文明的發源地,主人公又從新聞劇院放映的風光片里看到羅馬帝國的盛衰,羅馬帝國這個觀念籠罩著布勒斯頓城;古希臘雅典時代的強大和羅馬帝國的強盛像一道道回聲從歷史遙遠的深處向現在的布勒斯頓城回蕩來。布勒斯頓城——古稱“戰爭之城”——與該隱、古雅典、古羅馬、克里特島等都有歷史文化上的血緣關系。城市象征著兇殺、暴力和戰爭。城市之所以扼殺人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雖然布勒斯頓城是作者虛構的城市,但它卻代表著現代城市,敘述者說:“我知道布勒斯頓不是唯一的此類城市,曼徹斯特或利茲,紐卡斯爾或設菲爾德、利物浦等城市似乎也都有一個新建的、有趣的教堂,大概還有那些美國城市——匹茲堡或底特律等都可能對我產生同樣的影響,但我感到布勒斯頓,它集中體現了這些城市的特點,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這類城市中,它的魔法最陰險、最厲害。”這句話說明“城壓人”是現代城市的普遍現象,不僅僅在英國,美國,甚至全世界的都市都存在這個現象,布托試圖通過藝術創作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實質,認識西方文明的衰敗。在布勒斯頓城,教堂和博物館象征著傳統文化,新建百貨大樓象征商業經濟,市政大樓象征著政治權力,在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社會集合體中,人生存在一個“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惡劣環境之中,人與城的對立實際上也是人與物、人與環境的對立。戈爾德曼認為“新小說是有深度的現實主義創作,因為它創造了一種與馬克思、盧卡契指出的社會現象——物化現象相一致的文學形式”。[10]羅伯—格里耶也說過:“新小說關心的是人和人在世界中的處境。”《時情化憶》采取象征的方式,通過對城市的探索,觸及人與環境這一課題,更具有進步意義的是,小說中的人物面對強大的環境不甘沉淪,敢于反抗,像忒修斯那樣不屈不撓地探索,努力從困境中掙脫,爭得自由,這種人生態度值得倡導。
布托說:“從一定的高度來看,小說的現實主義、形式主義和象征性好似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刈的整體。”《時情化憶》是一部試驗性的作品,作者把這三者有機地結合,盡管有些不夠協調,仍有不足之處,但白璧微瑕,仍不失為一部獨特、成功的作品。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