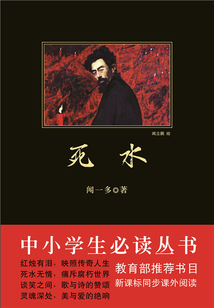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5評論第1章 藝以美弘道(1)
建設的美術
世界本是一間天然的美術館。人類在這個美術館中間住著,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術品,同造物爭妍斗巧。所以凡屬人類所有東西,例如文字、音樂、戲劇、雕刻、圖畫、建筑、工藝,都是美感的結晶,本不用講,就是政治、實業、教育、宗教,也都含著幾層美術的意味。所以世界文明的進步同美術的進步,成一個正比例。
文明分思想的同物質的兩種。美術也分兩種,有具體的美術,有抽象的美術。抽象的美術影響于思想的文明。具體的美術影響于物質的文明。我們中國對于抽象的美術,從前倒很講究,所以為東方舊文化的代表。對于具體的美術,不獨不提倡,反而竭力摧殘,因此我們的工藝腐敗到了極點。
歐戰完了。地球上從前那層腐朽的外殼已經脫去了。往日所夢想不到的些希望,現在也不知不覺的達到了。其中有一種反抗陋劣的生活的運動,也漸漸的萌芽了。歐美各國的人天天都在那里大聲疾呼的鼓吹一種什么叫做國家美術(National Art)。他們都說無論哪一個國家,在現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時代--科學進步、美術發達的時代,都不應該甘心享受那種陋劣的、沒有美術觀念的生活,因為人的所以為人,全在有這點美術的觀念。提倡美術就是尊重人格。照這樣看來,只因為限于世界的潮流,我們中國從前那種頑固不通的、輕視美術的思想,已經應該破除殆盡了。況且從國內情形看起來,像中國這樣腐敗的工藝,這樣腐敗的教育,非講求美術決不能挽救的。現在把怎么挽救這兩樣東西的方法,同為什么要挽救它們的道理,稍微講一講,可見得美術不是空洞的,是有切實的建設力的。
納斯根(John Ruskin)說:“生命無實業是罪孽,實業無美術是獸性。”(Life without industry is guilt,industry without art is brutality.)我們中國當宋明清富強的時期,美術最發達,各種工藝例如建筑、陶瓷、染織、刺繡、髹漆、同金玉雕刻,也很有成績。只到清朝咸、同以后,美術凋零了,工藝也凋零了。社會的生活呈一種萎靡不振的病氣。建房屋的、制家具的、造器皿的都是潦草塞責,完全失了他們從前做手藝的趣味。所制造出來的東西都是粗陋呆蠢到萬分,令人看著,幾幾乎要不相信這種工藝界從前還會有那一段光明的歷史。所以現在要整頓工藝,當然不能不先講求美術。
在沒有討論美術應該如何講求的方法以前,我們先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我們要振興工藝,是抱定一個什么目的。一國的工藝出產品,假設盡仗著國內的銷行,是不中用的。最要緊是在出口的多才好。所以我們要講振興工藝,就得使我們的貨在國外能夠銷行得多。這本是商學的定理,不待細講。
我們從來沒看見一個外國人不喜歡我們舊時的瓷器、陶器、銅錫器、絲織物、刺繡品、髹漆器、同金玉器的。質而言之,只要是純粹的中國的工藝美術品,決沒有不受外國人的歡迎的。自然在我們自己的眼光看起來,這些東西都是很平常,總沒有舶來品的新鮮。我們的工商界因此就以為中國貨果然是不如外國貨。于是拼命的仿效外國。把頂好的瓷品上涂了一點不中不西的薔薇花,或是一雙五色旗,就算是改良的了。一般絕無美術知識的人,居然就買它的,因為它很像洋式。哪曉得叫外國人看著,真要笑死了啊!我們常聽見外國人講,要買真正的中國東西。我們又常碰著外國人勸我們學我們自己的畫,不要學西洋畫。所以我們現在不想發達瓷業則已,要想發達瓷業,為什么不趕快恢復從前的宣霽、雍霽、乾霽、康熙美人霽種種的色釉,同從前所行的純粹中國式的花彩--圖案畫或景物畫,以便去迎合外國人的心理呢?只要我們的景德、醴陵、宜興等窯的出產都能銷到外國去,我們的利權就保住了。那時候,我們自己喜歡用東西洋瓷的只管去買真正的東西洋貨,還要那些不中不外的假洋貨干什么呢?這里所講的不過挑瓷器一樁做個例,其余各種工藝,可以類推。
上邊所講的中國工藝美術的價值,恐怕有人還不相信。其實照美術學理上分析起來,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中國畫重印象,不重寫實,所以透視、光線都不講。看起來是平坦的,是鳥眼的視景(Bird’s eye view),是一幅圖,不是畫。但是印象的精神很足,所以美觀還是存在。這種美觀不是直接的天然的美,是間接的天然的美,因為美術家取天然的美,經他的腦筋制造一過,再表現出來。原形雖然失了,但是美的精神還在。這是中國美術的特點。裝飾美術(Decorative Art)最合這種性質。所以中國從前的工藝很發達,也就是這種美術的結果。
我們近來喜歡講保存國粹畫,可不知道怎樣保存的法子。“保存”兩字不能看死了。凡是一件東西沒有用處,就可以不必存在。假設國粹畫是真好,我們就應當利用它。與其保存國粹不如利用國粹。利用是最妙的保存的方法。中國的美術要借工藝保存。中國的工藝要借美術發達。
中國人的美術知識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藐視圖案畫。裝飾美術里邊最要緊的一大部分就是圖案畫。我方才講過了,中國美術最宜于裝飾。中國圖案畫實在是特別的富于美觀。但是圖案畫的一個名詞,在中國畫史上是沒有的。我們所有的這種美術,全是尋常技師自出的心裁,沒有經過學理的研究。我們尋常只知道六朝三大家同吳裝的人物,南北兩宗的山水,沒骨體勾勒體的花鳥,同蘇趙諸家的墨戲,就是中國的美術。哪里知道中國最有價值的美術家,還有歷代造陶、瓷器、商嵌、七寶燒、景泰藍的那些技師?更有誰知道什么制雜花夾纈的柳婕妤妹,制蜀錦的竇師綸,制神絲繡被的繡工上海顧氏,同漆工張成、楊茂?我們中國人既然有天賦的美術技能,再加上學理的研究,將來工藝的前途,誰能料定?可惜我們自暴自棄,只知道一味的學洋人,學又學不到家,弄得烏七八糟,豈不是笑話嗎?日本人學西洋人,總算比我們學西洋人學得高明。但是他們現在也明白了他們自己的美術的價值,竭力提倡保存他們的國粹。我們中國的美術,比日本是怎么樣?再不學乖,真是傻了。
(原載1919年11月《清華學報》第5卷第1期)
電影是不是藝術
電影是不是藝術?為什么要發這個疑問?因為電影是現在最通行、最有勢力的娛樂品,但是正當的、適合的娛樂品必出于藝術;電影若是藝術,便沒有問題,若不是,老實講,便當請它讓賢引退,將娛樂底職權交給藝術執行。
許多人以為娛樂便是娛樂,可樂的東西,我們便可取以自娛,何必“吹毛求疵”,自尋韁鎖呢?快樂生于自由;假若處處都是約束,“投鼠忌器”,那還有什么快樂呢?這種哲學只有一個毛病,就是盡照這樣講來,那“章臺走馬,陌巷尋花”也可以饜我們的獸欲,給我們一點最普通可是最下等的快樂呢。
我不反對求快樂,其實我深信生活底唯一目的只是快樂。但求快樂底方法不同,禽獸底快樂同人底快樂不一樣,野蠻人或原始人底快樂同開化人底快樂不一樣。在一個人身上,口鼻底快樂不如耳目底快樂,耳目底快樂又不如心靈底快樂。藝術底快樂雖以耳目為作用,但是心靈的快樂,是最高的快樂,人類獨有的快樂。
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我們一舉一動,不能同我們的同類沒有關系。所以我們講快樂,不能不顧及這個快樂是否有害別人--同時的或后裔。這種顧慮,常人謂為約束,實在就是我們的未來的快樂底保險器。比如盜賊奸淫,未嘗不是做者本人底快樂,但同時又是別人的痛苦;這種快樂因為它們是利一害百的,所以有國家底法綱、社會底裁制同良心底譴責隨其后。這樣,“今日盜賊奸淫之快感預為明日刑罰裁制之苦感所打消矣”,所以就沒有快樂了。但是藝術是精神的快樂;肉體與肉體才有沖突,精神與精神萬無沖突,所以藝術底快樂是不會起沖突的,即不會妨害別人的快樂的,所以是真實的、永久的快樂。
我們研究電影是不是藝術底本旨,就是要知道它所供給的是哪一種的快樂,真實的或虛偽的,永久的或暫時的。抱“得過且過”底主義的人往往被虛偽的、暫時的快樂所欺騙,而反笑深察遠慮的人為多事,這是很不幸的事。社會學家頡德(Kidd)講現在服從將來是文明進化底原理。我們求快樂不應抱“得過且過”底主義,正因它有礙文明底進化,有人疑我們受了“非禮勿視”底道學底毒,才攻擊電影,恐怕太淺見了罷?
電影到底是不是藝術?普通一般人都說是的。他們大概是惑于電影底類似藝術之點,那就是戲劇的原質同圖畫的原質。電影底演習底過程很近啞戲(Pantomine),但以它的空間的原質論,又是許多的攝影,攝影又很像圖畫。這便是它的“魚目混珠”底可能性。許多人沒有剖析它的內容底真相,竟錯認它為藝術,便是托爾斯泰(Tolstoy)、林賽(Vachel Lindsay)、侯勾(Hugo)、彌恩斯特伯(Müinsterberg)那樣有學問的人,也不免這種謬誤。我們切不可因為他們的聲望,瞎著眼附和。
我們有三層理由可以證明電影決不是藝術:一、機械的基礎,二、營業的目的,三、非藝術的組織。
我們知道藝術與機械是像冰炭一樣的,所以藝術最忌的是機械的原質。電影起于攝影的機械底發明,它的出身就是機械,它永久脫離不了機械底管轄。編戲的得服從機械底條件去編戲,演戲的得想怎樣做去才能照出好影片來,布景的也得將就照相器底能率,沒有一部分能夠自由地發揮他的技能同理想。電影已經被機械收為奴隸了,它自身沒有自由,它屢次想跳出它的監牢,歸服藝術界,但是屢次失敗。可憐的卜拉帝(William A.Brady,美國全國電影營業公會會長)已經正式宣布了電影底改良只能依靠照相器底進步,不能企望戲劇底大著作家或演習家。
電影底營業的目的是人人公認的。營業的人只有求利底欲望,哪能顧到什么理想?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迎合底心理--這個心理是于社會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他們管不著。兇猛的野獸練得分外地兇猛,耍把戲的耍出比尋常十倍地危險的把戲,火車故意叫它們碰頭、出軌,摩托車讓它們對崖墻撞,烈馬不要命地往水里鉆,--這些驚心怵目的,豢養人類底占有的沖動的千奇百怪是干什么的?無緣無故地一個妖艷的少婦跳上屏風來,皺著眉頭嘆氣、掉眼淚,一回兒又捧著腮兒望你丟眼角,忽然又張嘴大笑,丑態百出,鬧了一大頓,是為什么的?這種結構有什么用意?這種做派是怎樣地高妙?它們除了激起你的一種劇烈的驚駭,或挑動你的一種無謂的、浪漫的興趣,還能引起什么美感嗎?唉!這些無非是騙錢的手段罷了。藝術假若是可以做買賣的,藝術也太沒有價值了。
前面已講過電影有兩個類似藝術之點,就是戲劇的原質同圖畫的原質。要證明它是假冒的戲劇而非真戲劇,需從三處下手:一、結構,二、演習,三、臺裝。關于結構的非藝術之點有六:
一、過度的寫實性。現代藝術底趨勢漸就象征而避寫實。自從攝影術發達了,就產生了具形藝術界底未來派、立方派同前印象派,于是藝術界漸漸發覺了真精神底所在,而藝術底位置也漸漸顯得超絕一切,高不可攀了。戲劇與電影正同繪畫與攝影一樣的。電影發明了,越加把戲劇底地位抬高了。電影底本領只在寫實,而寫實主義正是現代的藝術所唾棄的。現代的藝術底精神在提示,在象征。“把幾千人馬露在戰場上或在一個地震、災荒底擾亂之中,電影以為它得了寫實底原質,不曉得群眾已失了那提示底玄秘的意味。理想的戲劇底妙處就是那借提示所引起的感情的幻想。一個從提示里變出的理想比從逼真的事實里顯出的總是更深入些。在這人物紛紜的一幅景里,我們看著的只有個個的人形罷了,至于那作者底理想完全是領會不到的,因為許多的印象擠在我們腦筋里,已經把我們的思想弄亂了。”這便是過分的寫實底毛病,而電影反以為得意,真是不值識者一笑。
二、過度的客觀性。客觀與寫實本有連帶的關系,藝術家過求寫實,就顧不到自己的理想,沒有理想就失了個性,而個性是藝術底神髓,沒有個性就沒有藝術。“圖畫戲(指電影)講到表現客觀的生命,它的位置本很高,但照它現在的情形推測,永遠不能走進靈魂底主觀的世界。客觀的同主觀的世界是一樣地真實,但對于戲劇不是一樣地重要。戲劇,偉大的戲劇底唯一的要素是‘沖突中的人類的個性’。靈魂底競爭怎能用啞戲描寫得完備呢。感情,或者深摯的肉體的感情能用面貌、姿勢表現出來,但是講到描寫沖突,言語同它的豐富的提示底幫助是不可少的。”電影完全缺少語言底質素,當然于主觀的個性底沖突無法描寫了。
三、過分的長度。科倫比亞大學影戲部主講福利伯博士(Dr.Victor Freeburg)講:“理想的影戲應該從三卷到十卷長。為什么我們必定五千尺為我們一切的影片底正當的長度?影片底長度應該依它的故事底內部的價值為標準。譬如,我們要叫裴圖芬(Beethoven)一個月做一闋琴樂,并且每闋限定二十一頁長,或是請一個詩家作詩每首要七十九行,那不是一個笑話嗎?但是我們現在對于電影便是這樣的。”很多片子若僅有它的一段倒是很好的情節,但不知道為什么要故意把它壓扁了,拉長了,再不夠,又硬添上許多段數,反弄到它的結果又平淡、又冗長、又不連貫,一點精彩也沒有?我們這里演過的Brass Bullet、Hooded Terror等都屬這類的。
四、過分的速度。這層一半是它的機械的原質底關系,一半是腳本底結構底關系。卜拉帝講因為它的(電影底)深度不夠,“它的動作只能表現作者原有的感情底一半,要把這個缺點遮蓋起來,使觀者忘卻它們所見的只是人世底一個模糊影像的表現,就不得不把許多的事實快快地堆積起來。”我們看電影里往往一個主角底一生塞滿了情緒的或肉體的千磨萬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若想象我們的生命如果也是如此,恐怕我們要活不長了。“理想的感情底條件與自然底無形的情緒而并長。”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一株樹忽然從一粒種子里跳出來,我們也從來沒有看見太陽在它的軌道上繞著地球轉底二十四點鐘底速度。一切的藝術必須合乎自然底規律,才能動人。
大概長于量就不能精于質,顧了速度就只有面積沒有深度。質既不能精,又不能深,如何能夠感人呢?葛司武西(John Galsworthy)關于這點講得最愷切詳明,“影片在很短的時間里包羅了很廣的生命底面積;但是它的方法是平的,并且是沒有血的,照我的經驗,在藝術里不論多少面積同量從來不能彌補深度同質底缺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