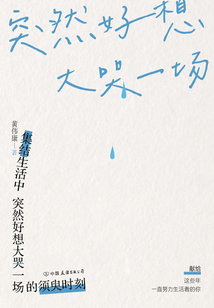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紅心兆赫
“據英國媒體報道,2010年5月8日,一頭灰色鯨魚在以色列沿海突然出現,海洋生物學家對此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種鯨魚的家在數千英里外的太平洋。它究竟是如何輾轉千里,最后成為地中海這片陌生海域的隱士呢?”
一個安靜的雨天,阿慧來到了這個家。
透明雨傘收起來,沿著地面一路滴水,最終與阿慧的雨靴一起被擱在房間外。我蹲在木頭柜前問阿慧:“想要吃曲奇餅干還是巧克力呢?”阿慧沒有吱聲,我拿過餅干,回頭看見阿慧專注地坐在我溫習功課的書桌前。她探著頭,在仔細地翻看一本圖集。然后,掰著指頭在草稿紙上涂鴉。
圖集上是一只灰色鯨魚。這是我搜集到的資料,我正在為學校的廣播社寫最后的一次主題稿。稿子內容大概是關于一只孤獨的鯨魚因為氣候關系游過了一段驚人的距離,來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生存而備受人類關注,由此推導出地球氣候正在惡化這一不愿聽到的聲音。
沒錯,廣播社的節目主題就叫作《最不愿聽到的聲音》。這是滲透我很多心血的一檔廣播,原先的定義是搜集和披露人們生活中的一些壞行為,從而呼吁文明與關愛,讓大家投入公益行動。起初,廣播內容無外乎是類似“陳同學消息,在英語角通往教學樓的樹梢上掛著早餐遺留的豆奶”這種話題,直到前陣子由新生主持的一期中,宣讀了投稿中披露學校領導的一則事項,廣播社被下了停播令。
廣播社大概就要完蛋了吧。
阿慧是我的外甥女,此時她仿佛在跟那只灰頭灰臉的鯨魚交流,全神貫注。我把她抱在懷里,指著圖集上那只露出海面的鯨魚,用手指戳了戳它問:“阿慧喜歡鯨魚嗎?”她側起頭,用水靈靈的眼睛盯著我,微笑地點頭。“阿慧是鯨魚嗎?”瞥見阿慧涂鴉里的鯨魚多了兩只腳和一個領結,我逗她。阿慧還是用大眼睛看著我,扯著自己的領結靦腆地笑起來,仍然是點頭。
“原來阿慧是鯨魚呀。”我笑起來,親吻她的額頭。
就在這個時候,隔壁房間又傳來了重重的敲擊聲,嘭嘭嘭——那是安田發出的聲音。安田是體育生,性格剛烈又冷酷,愛好拳擊。因為力道兇猛,房間里的沙包時常會失去控制撞到墻壁上。
而另外一個房間住的是一名柔弱又平凡的女生,身材嬌小,可是看上去卻有著無窮盡的力氣——因為患有潔癖,所以總是在干活。我正回頭盯著那堵無辜的墻,忽然又隱隱約約聽見房間外有水桶與地板摩擦的聲響。
糟糕,阿慧的雨傘和雨靴應該晾干凈再帶進家來!
我頓覺不好意思,朝房門大喊:“夢澤,對不起……把地板弄臟了哦。”
“沒事,我擦擦就好呢。”隔著房門悶悶的聲音。
這時,阿慧拉了拉我的手。我重新探過頭,發現涂鴉上的鯨魚多了一雙丑丑的翅膀。“哈哈,飛出海面的鯨魚嗎?”
……多么奇怪的一只鯨魚呀。
我想。
高考失敗后,我便從家里搬到學校附近的一幢公寓。十八歲的我,愛好畫畫和寫作。因為藝術生的日常開支較高,何況爸爸也不讓自己當藝術生,所以不能再繼續畫下去。業余愛好就只剩下寫作,一直在為學校的廣播社供稿。廣播社是高二那年由我與小一屆的艾略特一起向學校申請組建而成的,如今被學校下了停播令,還剩最后一次機會向大家告知“停播是我們‘最不愿聽到的聲音’”。而艾略特呢,艾略特是我的女朋友,有著非常性感的睫毛,但是很愛哭,特別是到了高三被迫分開的時候她哭得最兇。
一切都像是一部壞掉的機器,停止了運作,便再也沒有繼續運作下去的意志。
為了便宜,我住的是合租房。分到的是朝南的一個小房間,只有窗戶沒有陽臺。剛搬進來的時候,碰面的人是隔壁房間的安田,他正在組裝一臺買來的健身器材,表情冷漠。后來發現多半時候的午休,另外一個室友夢澤都會在客廳里拖地板。直到有一天,頂著兩塊碩大胸肌的安田來我房間借書,我帶著愧疚說“需不需要去幫夢澤的忙”時,安田冷冷地說:“不用理她,正好有人天天打掃衛生,有潔癖的人哪幫得完呢。”那時,我才得知夢澤患有強迫癥。
于是,安田每天都在運動,夢澤每天都在打掃衛生,我每天都在六點起床,然后六點半開始早讀,接著八點開始一天的課程。因為離開了家,所以每天吃的幾乎都是一樣的食物,走的都是一樣的路,讀的都是背過的書籍,看著是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著,實際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日子過得渾渾噩噩,毫無生氣——
我覺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我什么都不會。
“早在十八世紀,灰鯨就已在北大西洋地區滅絕,此后,再也沒人在這個區域見過它。而這頭身長約十米的龐然大物第一次被目擊到,是在以色列中部的荷茲利亞,至于它是如何到達這里的,科學家也不得而知。”
有一天我接到了姐姐的電話。因為外婆的忌日將到,家人打算回母親老家探親,加上處理各種瑣碎事項,需為期一個月。所以,正在讀幼兒園的外甥女暫時由我來帶。阿慧便來到了這個家。
我與姐姐的年齡相差甚大,阿慧出生那年我還在讀初三,幫忙帶過阿慧,與她一起被迫地感受過照顧別人的那種酸楚與責任。可以說,阿慧成長的一點一滴都印在我的眼底。我愛阿慧。但是這次不一樣了,這次是我獨自一人去試著照顧一個需要榜樣的孩子,而且是在我把生活過得最意志消沉的時候。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雨天,我打開門看見阿慧撐著一把小雨傘,站在姐姐旁邊沖我笑。我蹲下來,阿慧便過來熟絡地親吻我的臉頰,然后沖我大叫。我抱住她,微笑地把手指抵在她的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太大聲。然后我問:“阿慧做好跟舅舅一起生活的準備了嗎?”阿慧用她水靈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良久,笑著朝我點頭。
于是,除了讀書和發呆,生活的重心似乎開始有了著落。
阿慧的幼兒園離家并不遠,每天清晨幫阿慧刷牙洗臉然后準備早餐;在阿慧早餐的空隙將她的書包裝進一壺白開水,幫她穿好革皮鞋,最后牽阿慧去幼兒園;中午領阿慧回家,午飯過后送她回幼兒園午睡,自己再去上學。每次見到我,阿慧都會開心地放聲大喊,十分快樂的模樣。
傍晚也是一樣,見到我的阿慧那期盼的眼里閃著光,高興地沖過來被我牽回家。晚上為阿慧洗完澡,多半的時候是我在房間里復習功課,阿慧在床上自己玩布娃娃。阿慧很乖。
日子看上去好像也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只是重復做的事情又多了一件罷了。如果寫成日記,大概又可以一周寫一次總結了吧。但是,很多個午后,當我趴在數學課的課桌上時,我就會想:“阿慧現在在做什么呢?”
在做什么呢?
世界上的人們是否都在做著自己有所計劃的事兒,是否都是每天做著同樣的事情,把我們的人生定下了課程表、工作表、時間表,循規蹈矩而又精力充沛地去進行著呢。如果是這樣,別人為什么不會迷失自我,又是如何做到這般甘心?
這個年齡的我,永遠都不可能明白。
“阿慧到吃甜點的時間了吧?”單單這樣的想法,便讓我期待時間過得快一點。快一點便能去接阿慧回家,看到她開心無憂的臉龐,然后溫暖我。
“以色列海洋哺乳動物研究與援救中心負責人哈那·舍伊寧博士對這只灰鯨做了鑒定,他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有人把它形容為最重要的鯨魚目擊事件之一。’
更新奇的是,這只灰鯨被人們稱為‘52赫茲’。
‘52赫茲’的名字取自于它唱歌的頻率,它與同類有所不同。一般的須鯨亞目都是以較低的頻率約15至25赫茲在唱歌,可是它卻是用頻率高出許多的52赫茲,就這樣唱著只有自己聽得見的歌,至今仍無法找到伴侶,成為世界上最寂寞的一只鯨魚。”
最近回家的路上,阿慧突然悶不作聲了。
連續幾天,她既沒有踩著小步搖晃著我的手臂,對身邊經過的小攤販的氣球也提不起興趣。我蹲下來問阿慧,她表情木訥,只是搖頭。我一邊對小孩子也有心事而感到好笑,一邊又為之感到擔憂頭疼。之前很乖的阿慧,此刻顯得十分倔強。
今天阿慧的心情看上去糟糕透了,她走路索性連頭都懶得抬,對我遞給她的糖果擰在手里擰出了一手汗,也懶得吃。問她,她也不開口。
這個時候,前女友艾略特給我發來了短信,她說希望與我見一面,想跟我談談。末了,她又補發了一條:“關于廣播社的事,無關感情。”
我回了:“好。”阿慧感覺到我停下來,拉了拉我的衣角。我看著她那直愣愣的眼神,只想快點把她帶回家。
我馬上給阿慧洗澡,察看她身上是否有被處罰的瘀青,未果。這個晚上我都在試圖讓阿慧開心起來,偶爾會逗得她咯咯笑。阿慧的心思我似乎可以摸透,因為阿慧一直都交不到朋友,難道是這個原因困擾阿慧嗎?
第二天。
課間操過后,天空下起了雨。雨水敲在窗戶和樹葉上,教室像一個封閉的容器,沙沙作響。我兩眼空空地盯著一道閱讀理解題出神,無法靜心,趁第三節課的鈴聲還沒打響,便逃出了校園。
我決定去趟幼兒園窺探下情況。一路上,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直到我撐著雨傘突兀地停在幼兒園的門口。
雨還在細細地下著,我從鐵欄桿往里窺看,里頭非常嘈雜,有幾對孩子排列整齊地在走步子,有幾個則在嬉笑著跑來跑去。我再掃一眼便認出阿慧,她站在又踢腿又旋轉的兩個孩子旁邊,模仿她們的樣子,把腿笨拙地舉得老高,像在學一支舞蹈。明顯,那兩個孩子不愿意讓她加入,沒一會兒便朝她說著什么推開她。
早就應該料到。
在其他人的眼里,阿慧是個怪孩子。今年已經五歲的阿慧還不會說話,性格孤僻,不吵不鬧,但高興的時候就會扯著喉嚨大喊大叫。沒有特別喜歡吃的食物,也不貪吃。唯獨喜歡漂亮的裙子還有跳舞。
跟她玩的孩子們都嘲笑她是啞巴,久而久之阿慧受到排擠,沒有朋友。久而久之,為了保護阿慧,我寧愿不讓她跟其他孩子在一起玩耍。而實際上,阿慧是聽不見聲音。因為耳朵聽不見所以永遠學不了說話,被大家誤以為天生是啞巴。
家人多渴望能聽到阿慧甜甜地叫我們“爸媽”和“舅舅”,這種感覺有多少人能理解呢。多半的時候,是我們自顧自地跟阿慧說話,而阿慧只能看著我們的比劃,點頭或者搖頭,高興就大叫,委屈就大哭。
這是我們的心事。曾幾何時,阿慧連最正常的生理權利都被上天剝奪。為了保護阿慧,我們操碎了心。
我收起雨傘走進去,蹲下去抱住阿慧,撫摸她的頭。她看見我露出驚喜的表情,喉嚨里咯咯地喊著聽不懂的話。我輕輕比劃著,用柔軟的眼神看著她,安慰她說:“不要。”
“唉。”
“不要。”
“欸哎。”
“不要,不要。”
我也不知道我在要求阿慧不要做什么,是不要學,還是不要跟她們玩,但我相信阿慧明白我模糊的意思。阿慧的世界能接受所有模糊的信息。
我捏著她的小手,環繞四周看到黑板上貼著一張海報——“省幼兒第四屆育苗杯舞蹈比賽通知”。這時老師看到我,我道明來意,并被邀進辦公室。我告訴帶班老師阿慧最近的情況,最終詢問到原來是幼兒園正在準備舞蹈比賽,而阿慧無法參加。
“阿慧聽不到音樂,你知道,本來孩子就難教。所以在孩子們練習期間她只能在一旁玩耍……我們有安排其他老師看護她。”
腦海里立即浮現一群排成隊伍的孩子在學習舞蹈動作,而阿慧在一旁站著張望的畫面。我的心臟瞬間被揪住,疼并且越跳越快。
“但是,”我接過話,仿佛跟阿慧一起被那席話賦予了羞恥感,“為什么不讓她加入學習排練,她不去參加比賽只要參與過程,讓她不被孤立不好嗎?她還是個孩子……就算她是個孩子,她已經會察覺到異同并且會沮喪。”
“我也感到頭疼,阿慧聽不見,她跟別人不一樣。起初想讓她加入排練,可是有些隊形是已經安排好的,她硬要插入或者嚷著我把她安排進隊形,有時真的會耽誤進程。跟她講她又聽不見,又倔。音樂又聽不到,其他人老會笑她。阿慧跟其他孩子真的不一樣。”
我的臉刷地紅起來:“既然讓她來幼兒園就是為了讓老師教的呀,您耐心點跟她比劃下我相信她會乖的。”
“明知道做不了的事還硬去做就是傻瓜,怎么可以呢?這次比賽很重要,去年拿了二等獎。本來當初不愿接受阿慧入學的,因為她的情況比較……”
不同,不一樣,不正常。
“不要再強調她跟別人不一樣!我知道了。”我的眼神銳利起來,一團火焰陡然在我身體里騰燒,我沉住氣,心想大人們永遠都是這么自以為是。不愿意我當藝術生的大人,說我高考失敗是因為不認真學習的大人,擅自決定解散廣播社的大人,還有此刻在我面前強調阿慧跟別人不一樣的大人。你們懂什么呢!
在我看來,阿慧跟其他孩子一個樣。有喜有悲需要正常的生活,需要人疼也需要別人保護!我站起來準備離開,走出去看到阿慧還在那里糾纏,便擋在阿慧與那兩個孩子中間,拍打阿慧模仿她們而抬起的腿,兇猛地拉起阿慧的手,使勁地指劃并再次跟她說:“不準學她們!”
有什么了不起!我心想。為了保護阿慧,不讓阿慧再遭受這些嘲笑,我決定不讓阿慧參加比賽,不讓阿慧學習跳舞,不讓她跟那些天真的孩子玩。
我扳過阿慧的身體,在阿慧咿咿呀呀抗議的聲音中,扯著她的手把她帶回了家。
我終于知道,小時候家境不好,我賴在那家昂貴的玩具店門口不肯走時爸爸為什么會那么生氣,還打我。是無能為力,你卻一定要得到。是無法抵達,你卻一定要飛翔。是心疼,卻又無法滿足你。
這是我第一次對阿慧發脾氣,不知道是在氣阿慧的“不爭氣”還是氣我的“不爭氣”——
明知道做不了的事情還硬去做,就是傻瓜。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數十年來都在追蹤海底的一個聲音,它聽起來像是鬼魂的嚎叫,也像是低音號的鳴奏。這個神秘的聲音便是來自這只名為‘52赫茲’的鯨魚。
有的科學家和鯨魚生物學家猜測,‘52赫茲’是一只未知的鯨魚。它可能是一個殘缺兒,或者也可能是一個稀有的‘混血兒’,才會發出與眾不同的聲音。但無論怎樣解釋,這頭‘52赫茲’沒有朋友,獨自歌唱,卻是獨一無二的。”
我坐在床邊喘著粗氣,胸腔劇烈起伏著,良久,豆大的汗珠便從額頭滲了出來。阿慧一聲不吭地伏抱著我,她抬起頭直勾勾地望著我,然后又抿起嘴用手撫摸我的臉,一下又一下。我看她的眼睛,她撇嘴勉強笑笑,然后搖頭,再搖頭。
阿慧在叫我不要生氣。
我雙手托住阿慧的臉頰,慨然嘆了一口氣。為了阿慧,很多小事都讓我們心力交瘁,我對她說:“沒關系,總有一天阿慧會跟大家一樣呢。”
是希冀嗎?還是自欺欺人呢?
我們有多少個充滿幻想的、不可預料的、會變好的“有一天”呢。在我與阿慧之間,好像只有一個月的期限。而那之后的幾天,生活狀態似乎還是那樣,總是戰戰兢兢地擔心起阿慧——
有一天,我在自習課跑來看阿慧,在鐵柵欄外看著阿慧獨自一人坐在一只木馬上,看著另外一邊排著隊形的孩子在排練舞蹈。她看得非常認真,雙手握在膝蓋上,一動不動的背影朝著我。我盯著她那小小的背,用盡全身的力氣隱藏住那快要迸發出來的情緒。
有一天,我來接阿慧。還沒被家長接走的幾個孩子在繞著圈,把她困在中間。他們大聲喊叫“啞巴啞巴”,阿慧開心地笑著,以為大家在跟她玩游戲。我沖過去,孩子們一哄而散,我擰住其中一個孩子的衣領,他害怕得哇地叫了一聲。阿慧跺著腳使勁地拍打我的手,試圖讓我放手,咿咿呀呀地抗議我欺負她的朋友。
而今天放學后,我看到阿慧在那群孩子中又開始笨拙地模仿著那些動作,因為已經到排練后期,跟著音樂,阿慧更吃力又別扭地動著。有個女孩朝她做鬼臉,笑聲中還夾雜著“笨蛋”。這次,我想跑過去拎起那名女孩,把她嚇哭,可是我沒有。“阿慧!”我吼阿慧,我對她感到失望。我既為有人欺負她而生氣,又為她的重蹈覆轍而感到失望。
“你以為大家在跟你玩?大家都在笑你,你知道嗎!”我尖銳地喊著,直沖沖地跑向她。阿慧大聲喊叫,咿咿呀呀,眼神既驚恐又不知所措,仿佛還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錯。
我扯過阿慧的手臂,想讓她離開練舞的群體。她跺腳,蹲下去不肯走。我把她拉起來,使勁再扯,阿慧亂彈著腿,賴在地上。她漲紅了整張臉,雙手放在眼前,瞬間哇地哭了出來。
“嗚嗚嗚嗚嗚……”
阿慧非常大聲地哭喊著,那音調不明的哭聲還有擰在一起的五官戳中了我的心臟。我索性抱起阿慧,就往幼兒園外躥。
她的腳一路亂蹬,直到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才把阿慧放下來。
“我一開始就在校門口喊你,不過你好像有心事一直沒有聽見,我就跟過來了。”跟著我的人是艾略特。
“不好意思。”夾雜著阿慧的哭聲。
“我剛看到啦,你很強硬,為什么不讓她跳舞?”
“嗯,外甥女,耳朵聽不見所以別人會笑她。”
“這樣,對不起,但我看出她非常喜歡咧。”
我低頭看向哭個不停的阿慧:“嗯……找我有事情嗎?”
“廣播社的事,之前說是暫停,前些天來消息,說直接停播了。”
“意料到了,之前跟負責老師談過,一直沒給我音訊。停了就停了吧。”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們下面的學弟學妹可以負責,廣播社的存在是他們的愿望,你是社長只有你能出面呀。”艾略特語氣強硬起來。
“已經沒有辦法的事能怎么辦呢。”
“你怎么變得這么冷漠?”艾略特跟以前一樣,看上去還是非常容易哭的樣子,“你怎么能這么自私?你對寫作和廣播社的熱情被狗吃了嗎?”
“正因為這樣我才要用這種方式去保護它們。”我看向阿慧,無奈地勸她,“不要哭了,靜下來。”
此刻只剩下阿慧的哭聲,良久,艾略特撫摸著阿慧的頭說:“保護,說得好聽。到最后,我們沒有在一起,廣播社停了,你也無暇畫畫寫字,這就是你所謂的保護?就跟你對她一樣,看上去是保護,明明就是自私的表現。阻止她就是保護嗎?”
我自私嗎?我為了不讓阿慧被人嘲笑,我是自私嗎?我擅自為阿慧作決定了嗎?我阻止了阿慧想做的事情了嗎?是這樣嗎?
直到艾略特的身影走遠,把阿慧送回房間后,腦海里還在回蕩著她那冷冷的話。我踱到洗手間,準備洗把臉冷靜下來,推開門卻意外地看見室友夢澤蹲在馬桶旁邊,蜷在一起的身子劇烈地抖動著。她在哭。
我愣住了,錯愕地退了回去。“夢澤?”我試圖靠近,緩慢地走過去,輕輕喚她。
“夢澤你沒事吧?”
夢澤嗚嗚咽咽地哭泣著,看上去十分傷心。身邊干凈的地板淌著水,在燈光下反著光。我蹲在她身旁,試探性地安慰她:“為什么哭?”
狹小的洗手間把夢澤喉嚨里哽咽著的話,逐漸地放大開來——
“為什么……有些事情別人想做卻不能做,為什么有些事情我不想做,可就是控制不住地去做,好像自己很樂意去做一樣。我已經很努力在控制了呀,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呀,可就是沒有辦法。”
這席話讓我呆若木雞,潛意識里的目光集中在夢澤反過來的手掌,我瞪大眼睛被嚇了一跳。
那是一雙皮膚極薄,泡得起皺并且還有傷口往外流著血的手掌。
“雖然喜愛鯨魚的人們會為這頭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而傷感嘆息,然而盡管她孤零零的,但是我們的‘52赫茲’看來健康得很。”
昨晚的阿慧早早地睡去,到現在都還沒有起床。我背著英語單詞,看到安田做完運動回來,在客廳里來回走動。起身去準備早餐,推開門便看見安田正在把他房間里的沙包往外拖。他抬頭看我,難得地喊了聲“早”。
“早,沙包壞了嗎?”
“不是,拿去扔掉。房間東西太多,而且得認命看書了,看它礙眼。”
“我以為沙包一直是你發泄的工具,怎么還會礙事呀。”我打趣道。
“哪有,體育生最懂,真正的發泄是沒有聲音的呀。”
安田把沙包拖出客廳,然后下了樓道,留我傻站在原地。
我洗了把臉,淘米下鍋,當我推開房間的門,目睹了阿慧在做的事。醒來的阿慧背對著我,沒有發現我正在看著她。她雙手舉成一個圈,合在頭頂,然后踮起腳尖,左站右站。繼而,左右腳開始踢起來,像那些排練的孩子一樣,盡管沒有拍子但卻在偷偷努力地踢著步。
我的心瞬間沉了下來,側身倚在房門看她跳舞……
良久,阿慧一個笨拙的轉身便看見我。她急促地停下來,有點驚慌地抿起嘴,把手藏在身后,仿佛等著我過去責罰她。我盯著她,吸了一下鼻子,搖搖頭。她漸漸放松下來,舉起手拍拍身邊的地板,召喚我過去。阿慧笑著拉起我的手,左右搖晃,她在教我跳舞,要我跟她一起跳。
瞬間,我蹲下去抱住阿慧……我緊緊地攬著她的身子,紅了眼眶,我憐惜地摸她的臉,朝她說:“阿慧去比賽好不好?”
讓阿慧去比賽吧!
我像失了魂地撥打帶班老師的電話,提出了我的懇求。討論許久,對方還是那句“這次比賽很重要,每天孩子們都很辛苦地排練著……”
“請您一定要讓阿慧參加!我會幫阿慧完成排練,她會很努力。”我堅定。
“可是……”
“拜托了!”我聽出我的聲音有點異樣,不知道為什么,我在想著的事情是,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我什么都不會。難道連阿慧的愿望也無法幫忙完成嗎。
“明明她就是有困難,為什么一定要讓阿慧參加呢?”
不是為了榮譽,但是這次活動如果完成,卻是阿慧一生的勛章。
我把手搭在阿慧的身上,摩挲她那小小的身板,良久終于艱難地擠出那么一句,語氣癱軟下來的一句:“因為……因為我是她舅舅……還有,阿慧喜歡跳舞。”
“盡管如此,這頭鯨魚的適應力同時也鼓舞著每一顆孤獨的心。”
我到幼兒園把一整套的舞蹈記下來,并試圖用最簡易的方法教給阿慧。阿慧很聰明,動作學得很快,并且很熟悉,可是聽不到的阿慧無論如何都拿捏不到節奏。只能在排練的時候陪伴阿慧,教她跳舞過程盡量盯住其他人,學著別人的節奏。
就這樣,每天都與阿慧一起努力著。很快,很多天連續的練習過后,比賽的日子到來了。
當天我在臺下緊緊地鎖定阿慧的一舉一動,為她拍照。輪到阿慧這一組時,我的心臟開始猛烈地跳動起來。阿慧謹慎地站好在自己的位置上,臉蛋被撲上紅紅的粉,十分可愛。
音樂響起來,阿慧遲緩地跳起來,動作總是比別人慢。我揪心地凝視著,盡管阿慧不能非常準確地跟上節奏,但目前還沒有出現錯誤。
開始變換隊形,阿慧站在前面了,我的心就要被擰到了嗓門口。我用盡氣力祈禱阿慧能夠順利完成這支舞蹈。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突然,音響發出啪啦啪啦的嘈雜聲,最終啪嗒一聲,音樂停止了——
心臟漏跳了一拍。
貌似是機器故障,音響出現了問題,全場一片嘩然。舞臺上的其他孩子都停下了腳下的舞步,可是阿慧全然不知發生了什么,不知道音樂停止的阿慧卻還在繼續賣力地跳著,于群體中突兀地顯現出來。
我目瞪口呆,高高地大搖著手臂在心里喊“不要不要”!阿慧見到我開心地笑起來,仍歡樂地舞動著她的小胳膊。
“咦,那孩子怎么回事呢?”
阿慧踮起腳尖,身體還在十分認真地左右搖晃著。
“好好笑喲。”
臺上的孩子也在后面捂著嘴,只有阿慧還不知道停止——
我揮動著手臂,艱難地懇求阿慧:“不要不要!”
我的時間被凍結了。
2秒,4秒,6秒,8秒。阿慧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跳,我的心里也在數著時間。
周遭的笑聲像此刻緊繃又輕松的氣氛,瞬間就彌漫開來。此刻的討論還有笑聲,都關于阿慧。是嘲笑嗎?是嘲笑吧?是嘲笑吧!我像被釘在原地,無法動彈,心臟一直漏著拍子地加速再加速。
我相信我們有很多很多種時候,在別人的目光下行走,在別人的眼里我們被嘲笑,被說成傻瓜,但是我們渾然不知,因為我們做了其他人不會做的事,我們做了別人不允許做的事。
看著渾然不知的阿慧,我心急如焚。這種心急就跟目睹阿慧當初生病時一樣,在阿慧出生還沒有兩個月的時候,阿慧得了黃疸癥。心急的我們看著阿慧的腦部被按著插進一支針管強行注射,或許就是那一次,阿慧的聽覺神經受損,阿慧注定聽不見,我們注定一輩子為阿慧感到可惜。
……不要嘲笑她好嗎?她聽不見,她無法聽見,她喜歡跳舞喜歡交朋友,可是她無法聽見。不要嘲笑她好嗎,她是聾子,你知道嗎?我的外甥女是聾子,是殘疾人,你知道嗎?你懂這種感覺和希望嗎?
我不知道為什么在心里對自己這樣說,我感到難受。
15秒過去了,40秒,60秒過去了,我第一次發覺時間過得如此地慢。當阿慧跳完了那支舞蹈,察覺臺下的笑臉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傻傻地站在臺上時,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我哭了。
“盡管它唱響的二十年都是無應答的吶喊,沒同伴聽懂的赫茲只是在冰冷的北太平洋里回蕩著,它卻一直唱下去。”
70秒!
現場奇跡般地響起了雷動的掌聲,為音樂停止還繼續跳著的五歲的阿慧。我被吸走了魂魄般瞪大了我的眼睛,淚水還無法止住,卻情不自禁地又涌了出來。
當我終于理解到現場的那些笑聲都是對阿慧的一種肯定與鼓勵而不是嘲笑之后,那一刻,淚水早溢滿我的眼睛。模糊中是阿慧那張由驚慌變得無邪的笑臉,一直循環在我的腦海里。
阿慧幼兒園的舞蹈得了第一名,這是永遠屬于阿慧的勛章。并且,一個月的時間即將過去,可我與阿慧的這件小事將永遠留在我的心里。
幾天后,安田作為體育生去到了省城培訓,臨走前有來向我簡單地告別。而夢澤,我陪她去見了一趟心理醫生,目前正在積極地與強迫癥斗爭著。艾略特在這個月的月考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績,我為她感到開心,我們偶爾會一起出來吃個飯,然后各自在校園里努力著。我覺得這樣也挺好。我的寫作也還在繼續哦,一直到后來,我還開始為我夢寐的雜志投出了我的第一篇稿,希望寫出我眼里生活的意義。
讓其他人感到意外的事情是,廣播社在前天重開,廣播在昨天倉促地重新播出了。
阿慧的比賽過后,我把阿慧暫時托付給艾略特,然后我睡了整整一天。接著我又去學校活動部的主任辦公室外站了一個下午,我懇求他接受我的意見,并寫了一套解決方案給他。我決定把廣播社的節目主題改為《最想聽到的聲音》,換一種方式播出,從此聽到的便是無關教誨的聲音,都是正面的消息。
于是,主題為“傾聽你的心聲,跟著你心里的聲音去生活”,名稱為“紅心兆赫”的第一期廣播開播了:
“它叫Alice,它1989年被發現,從1992年開始被追蹤錄音。在其他鯨魚眼里,Alice就像是個啞巴。它這么多年來沒有一個親屬或朋友,唱歌的時候沒有人聽見,難過的時候也沒有人理睬。原因是這只孤獨鯨的頻率有52赫茲,而正常鯨的頻率只有15~25赫茲,它的頻率一直是錯的。”
我知道,阿慧的心聲將代替很多生活中的“鯨魚”說話,步行在我們失意而雷同的生活里。
一個晴朗的早晨,阿慧離開了這個家。
而我的新生活才剛剛開始。
(此文給我的外甥女方銘慧,希望她健康成長。)
很多人相信一見鐘情,卻不相信我對你的這種愛。
不過。
也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