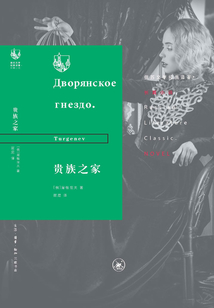
貴族之家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小引
一八五八年夏日,屠格涅夫從國外歸來,在他的田莊斯帕斯科伊過了勤勞的四個月。到了冬天,當他回到彼得堡,來到他的朋友們面前的時候,他帶來了一部小說的原稿,這就是“使得整個俄羅斯為之流淚”的那部小說——《貴族之家》。
小說發表于次年一月號的《當代》雜志,立刻為它的作者確立了第一流小說家的名譽。雜志的批評欄給它奉獻了巨大的篇幅,女主人公麗莎的名字成了流行的用語,青年作者們把他們的作品羞愧地捧呈于這位作家之前,即便是一向只把屠格涅夫認為是隨筆作家的岡察洛夫,這時也不能不把他當作小說家而對他側目了。總之,如果屠格涅夫的其他大部分作品從讀者那里所喚起的毀譽往往難得一致,至少對于這部作品,則無論他的友人和敵人,無不異口同聲地稱贊。《貴族之家》的時代快過去了,新的人漸漸在俄國生長起來,而屠格涅夫的作品卻對于那夕陽似的時代給予了無限詩意的描畫,這,當然是會感動每一個讀者的心靈的。在一八五五年所寫的《羅亭》里(在那時,屠格涅夫還不曾給他的無行動力的英雄安排一個光榮的死),作者已經對他的青年時代——理想主義的四十年代——做出了同情的然而同時是譴責的告別,而在這一部里,作者更以一個踏入了人生中年的人的溫情,回顧了已經過去的青年時代的危機,那調子,也就更其親切,而尤其更為惆悵了。
然而,這小說,也并不僅僅給那將要過去的時代以最后的凝視和傷悼。在這里,正如在作者的另外的長篇里一樣,也表現著一個特定時代的思潮和其特殊的氣息。拉夫列茨基不再是羅亭式的人物了,卻是一個更有根基的人。拉夫列茨基,在不幸的打擊之后,卻還有堅強的氣力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這不是一個純然的徒托空言者,不是一個羅亭式的沒有根的、無家的俄國漂流者,他不僅耕種了土地,而且也該有自滿的權利,因為,“他也盡可能地為著他的農民們圖謀了并且保證了生活的利益”。
屠格涅夫自己,原是一個“頑固的西歐派”,所擁護的,不是信仰,卻是理性,不是民族主義,卻是人類主義,不是東方的正教,卻是西方的文明,然而,為了使他的小說更忠實于時代的思想,他不惜借著拉夫列茨基的口宣說著自己所不能同意的斯拉夫主義,而使他所憎惡的潘辛將自己所擁護的西歐主義的思潮變成歪曲。[1]西歐主義者的羅亭,在這里墮落為潘辛一流的俗吏,而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卻出現在勝利的光影里,成為改革農民生活的實行者了。當然,羅亭是不能變成潘辛的:羅亭所有的崇高的理想,在潘辛,一個俗吏,卻絕不能有;而同時,斯拉夫主義者的拉夫列茨基,也絕不能成為“到民間去”的運動的先鋒。
可是,忠實的藝術家而兼深刻的思想家的屠格涅夫對于這一歷史的矛盾,卻給予了一種極其光輝的解決:唯有對于人民生活有著真實的了解,才能說到西歐主義,不然,上焉者,會變成徒托空言而當與現實接觸之際就只能逃避的羅亭式的英雄,下焉者,則簡直變成潘辛式的俗吏;而在另一方面,對于斯拉夫主義者,也唯有在犧牲自己而圖謀萬人的福利之下,這才能夠發現俄羅斯的獨特的命運和使命。在這種意義上,屠格涅夫對于那永遠懷著熱情的米哈萊維奇,也許是寄托著深大的希望的。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屠格涅夫寫出了一個過渡時代的英雄的命運。而在麗莎身上,他則創造了在那個時代俄羅斯的土地上所生長出來的最完美的女性的典型:誠實、虔敬、純潔、崇高,有著善良的、溫厚的心田和堅強的、不可屈的意志。不十分美,然而卻自然地可愛,不秉有特大的天賦,然而,卻有著自己的思想。她不是一個愛國者,然而,她卻愛著俄國的人民。麗莎在小說里的自我犧牲,就保證著未來的俄羅斯女性的一切更積極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論及普希金的《愛瑾·奧涅琴》里的女英雄泰狄亞娜之時,曾經說道:“像這樣美的、積極的俄羅斯女性的典型,在我們的文學中,是一直不曾被創造過的。”[2]然而,將屠格涅夫的麗莎當作了唯一的例外。在泰狄亞娜,是以自我犧牲、義務感而完成了她的美和積極性;在麗莎,也是。在這里,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藝術家已經預言了新的女性的到來。而這種女性,在他的次一部小說《前夜》里,就果真到來了。
不幸的婚姻、幻滅的戀愛、詩和哀愁的調子,當然是使這小說得到最普遍的申訴的原因,然而,全體看來,以這作品本身的完美和諧,也就可以博得極大的稱贊。不像在《羅亭》里,作者與主角的同情和譴責有時不能得到適當的調協,也不像在《前夜》里作者對于行動的英雄缺少表現,亦不像在《父與子》里,虛無主義者有時變成了可笑的人物,更不像在《處女地》里,作者的藝術的直覺彌補不了他與現實情形的隔閡……以一貫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細、平靜的流水似的場景和動作,還有多半是自傳式的實感和親切,《貴族之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的藝術杰作。在這里,我們難得找出一個極其細微的錯誤的音符,也更難發現一個極小的不必要的場面。[3]
每一個人物,從被稱為“俄羅斯的格麗卿”的女主人公麗莎起,以至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牝獅型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堅強而爽直的姑姑,懶惰而且自私的母親,俗物潘辛和年老的、不幸的音樂家倫蒙,莫不出現于神奇的、藝術的光影里。不僅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個仆婢,甚至每一個動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讀者的心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短短的家族史的插曲,給我們復活了農奴解放前的俄羅斯的歷史,在那對于“好的往昔”的回憶里,我們看見了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斯制下的地主世界,那些只會說空話的老新黨們是怎樣脆弱,怎樣在現實生活之中露出了原形。而這么相形之下,四十年代的英雄們就到底顯現著無限的優越性了。小說中的每一段對話、每一處背景,也無不精美絕倫,奇妙地增加著一般的效果,并且適宜地遂行著特定的任務。俄羅斯的風景、荒廢的地主的邸宅和莊園、沉靜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溫柔的私語和神奇的音樂……所有這些,只要和屠格涅夫的筆一經結合起來,就不知怎樣產生出了不可思議的魅力。至于那有名的“尾聲”,則是除了應用音樂的術語以外,在文字中再找不出恰當的贊美的。
在《羅亭》里,正如赫爾岑所說,“屠格涅夫是以上帝造人為榜樣,依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羅亭”。《貴族之家》也可以算得屠格涅夫底自傳成分極濃的小說之一例。拉夫列茨基,多半就是作者自己的寫照。那平靜的莊園生活,與屠格涅夫自己在斯帕斯科伊的羈囚之日是頗相類似的;西歐的倦游,使他想念著故國,有如拉夫列茨基底回到俄國來耕種土地;對于費雅度夫人的無望的戀情,使他在他的小說里不自主地露出了凄惻;而女主人公麗莎的原型,則據說正是他的一門遠親,而且日后也正如麗莎一樣進了修道院的一個少女。當拉夫列茨基在小說的尾聲里向他的后輩們告別的時候,他曾經說道:“未來是屬于你們的……雖然有著悲哀,卻并無嫉妒。”這,也正象征著屠格涅夫自己的心情:在當時,新的人已經上前來了,如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這些青年人們才是真正的歷史推動者,屠格涅夫在心情上雖然不能同他們調協,然而,在思想上卻是不能不和他們諧鳴的。他已經到了中年,他惆悵于自己的青春已經失去,然而,他也正和拉夫列茨基一樣可以自滿,因為他不獨不曾失去“善良的信仰、堅強的意志和活動的欲望”,并且也不曾停止他自己的進展:在他的緊接著《貴族之家》而出現的《前夜》和《父與子》里,他所寫的就不再是他自己的回憶,卻是當前的青年的典型了。
屠格涅夫的文章承繼著普希金的詩和明潔、果戈理的諷刺和豐富,加上他自己的抒情主義和憂郁,他將兩位偉大的創業者所遺留下來的文學語言變成更純熟、更洗練,而且更詩化。因此,這里的譯文——尤其因為不是從原文直接譯出之故——如果漏走了屠格涅夫,而只是用另外的語言講了一個屠格涅夫所曾講過的故事,那在譯者自己,是不會覺得十分意外的。可是,譯文雖然粗劣,譯者卻盡了他最大的慎重和努力,這是敢于向讀者擔保的。如能因為這點慎重和努力,和對于原作的熱愛,或在某些方面的共鳴,使這譯本還能勉強可讀,使讀者在讀過之后還能略略窺見原作的面目,那就是譯者最大的幸福。
譯文所根據的是英譯,一共有四種不同的本子:(一)拉耳斯頓譯(W.R.S.Ralston: Liza )萬人叢書本;(二)伊莎伯爾·哈勃葛德譯(Isabel F.Hapgood: A Nobleman's Nest)全集本;(三)康斯坦士·迦奈特譯(Constance Garnett: A House of Gentle Folks)全集本;(四)達維斯譯(F.D.Davis: A Nest of Hereditary Legislators)。除了最后一種間有脫落外,其他三種都是早有定評的好譯本。就中,拉耳斯頓所譯,既忠實且多神采,因為是作者的友人,所以根據的原文也是經過作者親手訂定過的,和他本間有出入,同時,長句和長段也多改成了短的;哈勃葛德的譯本是以絕對忠實著稱的;迦奈特也是有名的忠實譯者。在譯這書的時候,我的主要根據是拉耳斯頓譯本,標點和段落,多依哈勃葛德,最后的校對,則對照迦奈特。如有三本各不相同的地方,那就參看第四種譯本,采取較近似的一種。有時,也參照熊澤復六的日譯。
我不能忘記許多年來我每一次閱讀這書的時候所得到的喜悅和感動。九年以前,我曾以幼稚的熱情將這書譯過一次,但是,幸而那草率的譯稿不曾得到出版的機會,而且終于也不見了蹤影。近年來,忠實而負責的譯者漸漸增多了。把名著還它一個名著,不獨是讀者的企望,并且,也成了多數翻譯者所努力的目標。至于我自己,雖然極愿在優異的譯者們的后面做一個拙劣的追隨者,但這目前的成績卻是不足道的。然而,我希望著我以后能有進步。
這一次的譯文,動手于去年夏季,及至校印完畢,已到今年的初春了。全稿譯成之后,得友人陸蠡先生對照法譯,陸少懿先生對照日譯,柳野青先生對照英譯,逐字校讀,荒煤先生校讀最后的排印稿樣,或提出各種譯文間的參差,或對我自己的譯文給予修辭上的指正,花費了他們許多寶貴的時間,是當特別感謝的;書中間雜的法語,在翻譯之際,多就正于吳金堤先生;音樂術語,則多由賀綠汀、呂驥和張汀石三位先生給以鑒定,一并致謝。
最后,對于俄國的人名組織和稱呼習慣,為了便于初讀俄國作品的讀者,在這里也略加解說。俄國人名,普遍由三部分組成,如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第一部分,費多爾,是自己的名,即教名;第二部分,是父名,伊凡諾維奇即指父親名叫伊凡,而后面的語尾則意云“其子”;第三部分是姓。“費多爾·伊凡諾維奇·拉夫列茨基”就是說這人姓拉夫列茨基,名費多爾,為伊凡的兒子。女性的名字也同樣有這樣的三個部分,不過父名的語尾則意云“其女”,如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即是這姑娘自己名叫麗莎維大,姓加里丁,是米哈伊爾的女兒。除這之外,也還有昵稱,如費多爾被稱成費狄亞或費狄烏其嘉,麗莎維大被稱成麗莎、麗賽大或者麗索其嘉。在稱呼上,一般地,上對下,僅稱其教名,或昵稱;教名連父名,則表示客氣,行于下對上,平輩間有交情者或僅僅相識者。所以,當拉夫列茨基稱麗莎為“麗莎維大·米哈伊洛夫娜”的時候,瑪爾法·提摩費埃夫娜就說道:“米哈伊洛夫娜怎么到你的頭上來的?”以拉夫列茨基對麗莎的身份,僅稱“麗莎”就行,原可不必這么客氣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 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