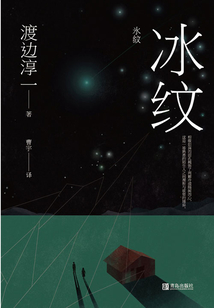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回想
“昨天晚上,我碰見了久坂。”
吃完早飯,丈夫敬之將這一消息告訴有己子。
今年上小學的獨生女真紀已經去了學校,只有丈夫敬之和妻子有己子兩人在飯廳里。
“久坂?”
最近稍稍發福的敬之,早晨只吃蔬菜沙拉和一片烤面包。敬之剛吃完沙拉,看著桌上的報紙,點點頭。
“在什么地方碰到的?”
“他來醫院了。”
有己子從側面看著讀報的丈夫,揣測他突然提及該事的用意。
“他回札幌了?”
“不,不是的。”
“那么是來玩?”
“不……”
敬之點上煙,又看起報紙。
對丈夫欲言又止的態度,有己子稍感煩躁。
敬之的說話方式一貫如此,自己挑起話頭,卻又不爽快地回答。回答時,眼睛不是看著電視機就是看著報紙。
但他并非對談話不感興趣。他雖然眼觀別處,似乎無聊地應答著,實際上卻敏感地關注著談話的對象。現在,有己子感覺他就是如此。
“為了工作上的事情?”
有己子克制住焦灼的心情,盡量平靜地詢問。
“或許他就要回札幌了。”
“就要……”有己子在嘴里嘟囔著。
在有己子才二十二歲的時候,久坂利輔離開札幌的大學附屬醫院,前往日本海的海濱城市天鹽町的醫院工作。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七年了。
“那么,他要回來了?”
“不是。”
敬之放下報紙,要喝咖啡。有己子失去了繼續追問的勇氣。站在水槽邊。
當壺里燒開的咖啡飄出香味時,敬之又接著說:“昨天下午,他突然來醫療部了。”
敬之坐在餐廳椅子上,欣賞著窗外飄落的雪花。有己子扭過頭看了他一眼,問道:“一個人?”
“對。”
有己子倒了兩杯咖啡,把其中一杯遞給了敬之。她和丈夫隔著餐桌,相對而坐。
“當時,他說想回來?”
“不,那家伙還是什么都沒說……”
“那,為什么……”
“在那種鄉下城市待了七年,都待傻了吧。”
說完,敬之嘬了最后一口熱咖啡。
久坂回札幌的事情還沒確定,丈夫似乎只是揣摩到了久坂的心境。
“久坂常來札幌嗎?”
“據說這次來之前,有兩年沒來過了。”
“那他還是有什么事才來的,對吧?”
“他媽媽好像死了。”
“他媽媽……”
有己子吃驚地抬起頭。
敬之和久坂是札幌大學醫學系的同屆生,大學畢業后,兩人一起進入第一外科醫療部。雖然之后一人留在大學,一人去了地方醫院,但同屆同門的情誼并沒割斷。朋友的母親過世,朋友從鄉下趕回來,而丈夫直到現在才說,有己子不知他內心是怎么想的。
“什么病?”
“聽說是心絞痛。”
“突然去世的……”
“好像是的。”
“剛剛新年……”
有己子嘆息著,敬之又看起報紙。
“久坂的媽媽一直在札幌嗎?”
“好像在手稻,和他妹妹一起生活。”
從札幌向西驅車三十分鐘就可以到達手稻,那是臨近大海的郊外。
“那你要去吧?”
“今天晚上是守靈夜,我要去一下。”
“穿西裝?”
“要黑色的,再戴上黑袖標就可以了。”
“守靈從幾點開始?”
“六點。”
敬之似乎本來就打算說這件事。他拐彎抹角地說,大概是有含義的。有己子警惕地看著丈夫。
“送錢嗎?”
“醫療部會出的,不用準備吧。”
“但那是醫療部出的,個人還是要出的吧?”
“是嗎?”
“對呀,你們是同屆的,而且受到他不少關照。”
“不對,我不記得他給過我什么關照。”
“怎么……”
有己子再次吞聲不語。
這個人究竟在想什么?
久坂是否關照過敬之,那是男人世界的事情,有己子無從知曉。但不管怎樣,至少是同屆生,多少應該表示點心意。
“包個五千日元,如何?”
敬之似乎同意了,站起身,面朝衣柜門上的鏡子。
“醫療部有裝錢的紙袋吧?”
“有吧。”
敬之在鏡子前系著領帶,點點頭。
他是大學副教授,從事著刻板的職業。也許是這個緣故,敬之總是穿白襯衫,配上昂貴卻又讓人感覺樸素的領帶。
“我走了。”敬之系好領帶說道。
有己子趕緊從衣柜抽屜里取出新手帕,然后將桌上的香煙和打火機遞過去,接著又跑到玄關擦皮鞋。
敬之似乎喜歡有己子聽到自己突然說“走了”后忙不迭的樣子。他現在也馬上拿著公文包,站在玄關處,低頭看著擦拭皮鞋的有己子。
“晚飯不回來吃。藥商在‘濱茄’請我吃飯。晚上可能要晚點回家。”
敬之穿上藏青地、黑條紋的大衣,然后深深地戴上呢帽。
坐電車去大學有三站路。夏天敬之幾乎每次都步行上班,下雪則多乘電車。雖說是副教授,但因為每天早晨醫療部九點有協調會,所以八點半就要離家。
“走了。”
“走好。”
有己子在門口伏地行禮。這雖是老套禮節,但在送行時不可或缺。
新婚半個月后,敬之曾鄭重其事地對有己子說過這樣的話:“從我小時候開始,在我父親出門時,我母親必定是伏地行禮送行。父親死后,母親則對我這樣。也許你會認為那是陳腐的東西,但如果你那樣做,我一天都會神清氣爽。因此請你要遵守這一禮節。”
敬之的父親是書法家,敬之是父親的小兒子,上面有兩個姐姐。從小開始,他作為男人的權威性就被充分認可。他讓妻子伏地行禮,送迎自己上下班,從而獲得滿足,這或許就是他對往日的一種留戀吧。
起初,有己子覺得那很夸張,有點難為情,但習慣后就沒什么特別的感覺了。
她妹妹理惠有次來玩,吃驚不已:“姐姐,你像在侍奉陛下。”
有己子只能苦笑。
“只要做個形式,那人就滿足了。”有己子非常明白——如果只做那一件事,就能讓丈夫有個好心情,又何嘗不可呢?
有己子和敬之是七年前完婚的,那一年敬之三十歲,有己子二十二歲。那時有己子的父親氏家伸太郎是札幌S大學醫學系第一外科的教授,敬之是她父親主管的第一外科的屬下,在伸太郎的指導下,他拿到學位,取得了助教資格。即便在才俊云集的第一外科,敬之也算出類拔萃,那時就有傳言說他是未來的教授候選人。
當然,伸太郎也認可敬之的才華,他會讓敬之帶領大家收集學會所需的數據。有己子大學畢業時,和敬之定下了婚約。
有些屬下認為迎娶主任教授的千金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會惹人妒忌,招來流言蜚語,在單位的處境會變得困窘。但抱有那種觀點的人實際上也是出于對被選中的人的嫉妒,換了自己,又有幾個人會斷然拒絕呢?
伸太郎直接對敬之提及結婚事宜,敬之當即允諾:“很高興您的女兒能嫁給我。”
的確,當時的有己子即便沒有教授千金的身份,也是位很有魅力的女性。
提到結婚事宜時,她還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她就讀的大學是只招收女生的教會學校,札幌的大家閨秀大都集聚于此。
光聽聞有己子的經歷,有人會把她想象成古語所說的“深閨千金”,其實不然。她夏天打網球,冬天玩滑雪、溜冰,還會駕駛,擅長體育運動,算是個瘋丫頭。她小巧玲瓏,青春洋溢,又是個大家閨秀,這不能不引起伸太郎年輕屬下的好奇心。
當伸太郎建議她和敬之結婚時,有己子沒有格外起勁兒,也沒有反對。
有己子當時才二十一歲,從未把一個男子當作結婚對象考慮過。
“女孩子最好早點結婚。那個男人沒錯。”
“你一畢業,五月份就舉辦婚禮,怎么樣?”
“等等!”
“怎么,對諸岡有不滿?”
諸岡是敬之的姓。
“也不是……”
新年或者學會有需緊急磋商的事宜時,諸岡敬之曾來過幾次,有己子知道這個人。他看起來沒有顯著特征,但在某些時候,他那透過眼鏡的視線敏銳而冷靜,似乎能證明其青年才俊的傳聞。
在談婚論嫁前,有己子沒有特別在意敬之。只是在一年前的元旦,第一外科的職員們在家中聚會時,在伸太郎的要求下,敬之唱了家鄉越中地區的民謠。當時,有己子覺得他聲音齊整,但沒有感情。對于敬之的記憶,不過如此而已。
就像有己子對敬之不關心一般,敬之看上去對有己子也沒有興趣。對于教授的千金,其他屬下會說奉承話,投以傾慕的眼神,只有敬之毫無興趣,熱衷于說一些晦澀難懂的話。
不過,他能如此痛快地應承伸太郎的提議,可見其內心對有己子也抱有好感。
“對方說行,你也要答復吧?”
“為什么那么急呀?”
“因為你爸還有一年就要退休了。他想在此之前讓你出嫁。”
通過媽媽的話,有己子知道了父母的打算。在爸爸在位時出嫁對有己子有利無害。
但是如果可能,有己子想再玩玩;如果可能,她想談一次真正的戀愛,享受青春后再步入婚姻生活。她覺得如果就這樣和敬之結婚,生活雖然穩定,但會作為平凡的妻子,慢慢地陷入家族生活之中。
“怎么樣?”
“難道你有其他意中人?”
被父母逼問時,一個男人的面容出乎意料地在有己子的腦海中閃過。
那是同屬第一外科,與敬之同期的久坂。
沒有任何關聯,只不過在伸太郎發問后,久坂突然浮現在有己子的腦海中。當時,想到這個人,有己子意外地惶恐不安。
為什么那個人會……
有己子沉默不語,回味著一瞬間的念頭。
元旦時,下屬們聚在一起,來伸太郎家拜訪。那時,不知為何,久坂總是蜷縮著瘦長的身軀坐在末席。下屬們入座時,順序大體遵循畢業時間,按照學長到新人的順序,依次往下。當時,敬之已經坐到前排,即便他再優秀,與他同期的久坂也應該坐在比他靠后兩三個位置的地方,再不濟也該坐在中間——至少從屬下們歷來的排序來說應該是這樣。
但是久坂坐在靠近末席的地方,夾雜在剛進入部門工作兩三年的年輕醫生中。有時,晚到的年歲大一點的下屬,也就坐在下方,而久坂就算和大家一起到,也坐在下方,似乎那是被規定好的位置。
不可思議的是,對此,久坂本人也罷,周圍的人也罷,都沒有覺得奇怪。
有己子幾次想問爸爸這件事,但沒敢開口。因為爸爸可能會呵斥她:“單位里的事情,你不用知道。”
或許是排序奇怪,或許是正月里當大家觥籌交錯時,他沒有興奮地唱歌,而是獨自沉默的緣故,有己子反倒對他留有印象,上菜時會觀察久坂的神態。
久坂的面部和背部一樣細長,臉色總是有點蒼白,眼窩深陷。酒量似乎很大,只要給他倒酒,他就喝。但是,就算全場的人都興奮了,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視對面的墻壁,專注地聆聽眾人的歌聲。一曲唱罷,他和大家一起拍手。
乍看上去,他似乎融入了熱鬧的宴席氛圍,但仔細觀察,便能發現那只是表象,他的心在別處,表面上和眾人步調一致,其實心不在焉。
“怎么樣,有意中人嗎?”
“沒有。”
有己子拋卻那一瞬間浮現在腦海中的久坂的身影,重新坐好,面對母親。
現階段,能否說自己就是喜歡,有己子毫無頭緒。即便自己說“喜歡”,他是否接受也無從得知。
醫療部的職員中,有一種人會主動向有己子示好,而另一種人則是故作無心狀,而且后者多是有意識地裝作不關心。但只有一個人,就是久坂,似乎不是這兩種類型的人。只有他,不管有己子如何,他一直不關心。
自己不是喜歡,而是在意那個人。
有己子決定忘記久坂的身影。
與敬之的婚約商定后,在結婚前的半年中,有己子和敬之有過多次約會。只要見面,敬之總是文質彬彬、舉止瀟灑,就連那些為爭奪有己子而相互提防的醫療部職員們,對于他們的婚約也沒有表現出驚訝。或許他們覺得敬之得到有己子純屬正常,畢竟敬之的優秀和受伸太郎的器重,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可是,即便周圍所有人都認可敬之,有己子的腦海中依然會時時出現久坂的身影。
久坂只在一年一次的元旦出現,此外的情況,有己子無法得知。偶然來訪的醫療部職員在與父親的談話中,也沒有提及久坂的名字。
可是,對于未知的事情,有己子更加在意。
在婚前的一個月的九月初,有己子不經意地向敬之問到了他。
“和你同期的久坂先生在嗎?”
“你認識他?”
“他來過我家。”
“對了,是新年的時候吧。他怎么了?”
“也是在……”
敬之欲言又止,點上煙。
“從下個月開始,他就要去天鹽了。”
“天鹽……”
“你去過那里?”
天鹽臨近北海道北部的稚內,是個面臨日本海的小城。兩年前大學放暑假的時候,有己子和朋友想去北部的利尻島和禮文島,她在地圖上發現,在那兩個島的對面有個叫天鹽的小城。
“他為何要去那種鄉下地方?”
“因為許多事情。”
敬之欲言又止,有己子反倒被勾起了好奇心。
“事情?什么事情?”
“他本來就不會長期留在大學,本來就預定要去小地方。他在醫療部能待到今天,是因為你爸爸的憐憫。”
“爸爸的憐憫?究竟是怎么回事?”
“沒,也沒什么……”
“怎么回事?請告訴我。”
“好,那我說,但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當然不會說。”
“他曾經惹過事端。”
“事端?”
“是的。”
“怎么回事?”
“簡單說,就是殺人。”
“殺人……”
說完,有己子趕緊捂住嘴巴。
因為有兩個人坐在他們的斜前方,其中的男子回頭看了看他們。
“但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證據。”
“那為什么……”
“據說,他進入醫療部的第二年,去地方醫院時,認識了一個已婚女子,那女子有個身患重癥殘疾的孩子。他過于同情那個女子,就有意識地殺害了那個孩子。”
“真的嗎?”
“那孩子當時十個月大,天生手腳彎曲,連媽媽的臉都無法識別,是個嚴重的殘疾兒,如果做手術,恐怕體力不支。”
“可憐!”
對于即將結婚的有己子而言,那并非毫無關系的事情。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但他倒霉,被手術室的護士告密,讓那個女子的丈夫知道了。”
“但手術不是那個女子要求做的嗎?”
“我覺得也是。但久坂什么都沒說。”
“那不是沒有證據嗎?”
“雖然沒有,但護士告發了。”
“護士為什么要……”
“好像是那個護士喜歡久坂,但是久坂和那個已婚女子親近。”
“那是中傷?”
“也不能這么說,好像孩子的爸爸反對那個手術。”
“結果呢?”
“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那件事最終糊里糊涂過去了,作為醫療事故和解。當地醫院和我們的醫療部應該付了一些錢,當然他本人也出了。”
敬之嘬了一口有點涼的咖啡。
有己子調整心情,盯著旁邊的墻壁,然后像猛然想起來什么事一樣問道:“但即便那樣,他是否也是為了孩子的將來著想而做的呢?”
“或許有那種考量,但對方是一個無法自我表達的嬰兒,所以沒有安樂死這一說。而且,在現代醫學中,安樂死還沒有被正式認可。”
“但久坂先生沒有惡意吧?”
“大體上是的。但是因為有他和那個已婚女子的傳聞,所以事情就麻煩了。”
“那種事是真的嗎?”
“久坂本人什么都沒說,但無風不起浪嘛。”
雖然都是醫生,還是同屆,但敬之的話讓人覺得他似乎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那個已婚女子后來怎么樣了?”
“不知道詳情,好像被迫離婚了。”
“然后呢?”
“有人說她跟隨久坂了……”
“但他不是單身嗎?”
“是的……”
“告密的護士呢?”
“好像辭去了醫院的工作。因為那件事,久坂先生回到醫療部……出了那種事情,無法待在當地,所以他就返回醫療部,直到事態平息。從那以后,他就不拿手術刀了。”
“為什么?”
“好像失去自信了。”
“……”
“本來是個優秀的家伙,和已婚女子弄出那種事,真是個呆子。”
眾人聚會時,總是默默無聲地坐在末席的久坂的身影出現在有己子的腦海里。那身影雖在人群中,實則脫離了人群。
“從前出了那種事,是要被開除的。你爸爸說如果那樣處罰,只會讓他痛苦,于是格外開恩了。”
“那他這次去的醫院是什么樣的?”
“那里只有一個內科醫生。當年的事件已經風平浪靜了,所以他可以去鄉下從頭再來了。”
說完,敬之干咳一聲,說了句“呆子”,微微一笑。
三天后,有己子見到了久坂。
現在想起來,連自己都不明白當時怎么會那么大膽。
她打電話到醫療部,自報家門,說是伸太郎的女兒,讓久坂下班后出來。久坂順從地在約定的時間出現在公園飯店的大廳。
起初,有己子本打算詢問他的那件往事。“聽聞當年出了那件事,想知道原委,就約你出來了。”有己子覺得這樣說比較自然。
但當她見到久坂時,便失去了詢問的勇氣。事實上,只要見面就足夠了,沒必要再問那件他本人避諱的事情。
不知為何,久坂沒有詢問有己子約自己的原因。雖然他應該知道有己子和敬之訂婚的事情,當時也沒有涉及那一話題。
兩人去了飯店十一層的酒吧,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以及旅行等事情。當兩人并排坐在酒吧柜臺前,有己子產生了一種錯覺,感覺自己像是早就和久坂在一起了。但他是怎么想的呢?有己子無法從寡言少語的久坂的神態上估摸出來。
也許是那種焦灼讓她大膽,最后是有己子請求久坂帶她到賓館去的,就連有己子本人也不是很明白自己怎么能說出那樣的話。只在那一瞬間,久坂直勾勾地看著有己子,很快便無聲地站起來。隨后他將有己子帶到賓館,占有了她還未曾交給任何人的處女之身,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得到有己子時,他卻令人不可思議地面無表情,淡然不迫。
兩小時后,當他們離開賓館分別時,有己子雖然失去了處女之身,卻既沒有后悔,也沒有悲傷。不知為何,她反倒覺得這樣一來,就可以安心和敬之結婚了。
一個月后,敬之和有己子如期舉辦了婚禮。久坂因為有急事,沒有參加婚宴。
以后,久坂沒有再聯系自己,有己子覺得他和有夫之婦斷絕聯系也是理所應當的。盡管如此,有己子心中仍有點不滿。
有己子曾經兩三次問敬之久坂怎么樣了,他只是說“在天鹽”,沒有特別疑心的樣子。
伸太郎在有己子結婚后的第二年如期退休,而敬之依舊留在大學,從助教升為講師,三年前成為副教授。他像所有人預料的那樣,順利地出人頭地。
在這七年中,有己子成為一個孩子的母親,副教授的夫人,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會時常想起久坂。
那天晚上,敬之十一點多才回家。
以前不怎么喝酒的敬之最近經常受到制藥公司私人診所的接待,好像能喝一點了。即便這樣,他的酒量也就是兩合清酒,五六杯威士忌加水。
敬之的臉相當紅,可能在飯店吃完,又去了酒吧。
有己子聽到玄關處門鈴的響聲,急忙從客廳趕過去,伏地行禮迎接。
“回來了。”
“嗯。”
敬之看著低頭的有己子,顯得很滿意,將包遞過去。
在結婚的第四年,有次玄關的門鈴響了,有己子卻沒有出去,因為當時她在烤肉,加上女兒真紀看電視的聲音太大,沒聽到門鈴響。
敬之在玄關等了一陣,因為有己子沒出來,便暫時進家,走進玄關旁邊的廁所,一直等到有己子出來。
有己子說他是個怪人,讓人捉摸不定,還很較真,無論什么事情,與實質相比,他更加注重形式,這就是敬之的思維模式。不過,當他外出或回家時讓妻子伏地行禮,未必只是形式主義,或許他是想通過這樣來滿足那種讓恩師女兒服從自己的虛榮心。
“包里有飯店給的小禮品。”
“什么呀?”
“店里特制的壽司。”
說完,敬之去了書房,看完桌子上的今天的信件,回到日式房間,脫下西裝,換上和服,然后來到客廳,坐在桌前。
他們的房子不是很大,磚混結構,很牢固,樓下的三個房間采取集中供暖,即便在北方也感覺不到寒冷。敬之成為副教授后,把老屋進行了翻新,有己子的娘家出了一半的錢。
有己子疊好敬之脫下的西裝,回到客廳時,敬之正在桌前看晚報。女兒真紀一小時前睡覺了。
電視里正在播放十一點開始的時裝秀節目。
有己子倒好茶,遞到敬之面前。敬之和平時一樣,眼睛看著報紙,手拿茶杯喝起來。桌子上放著有己子為真紀編織了一半的帽子。
剛才敬之回來的時候,有己子從玄關看見外面小雪飄飛,但在集中供暖的房間里絲毫感受不到寒冷。
有己子給自己也倒了杯茶,嘬了一口,看了看敬之。
敬之還在看同一張晚報,上面有什么內容讓他看那么久?敬之戴著眼鏡,相貌端正,但面無表情。雖然相貌端正,但沒有讓人留戀的地方。
又嘬了一口茶,有己子按捺不住,說起話來。
“久坂家的守靈夜怎么樣?”
“嗯。”
敬之這才放下報紙,看著有己子。
“去了許多人吧?”
“沒有,只是家里人罷了。”
“久坂的母親一個人住在札幌嗎?”
“好像和他妹妹一家住。這次也是死在他妹妹家。”
“他爸爸原來是干什么的?”
“以前在小樽好像是個水產品的大批發商,戰后生意失敗,很快就死了。”
“那么他們家只有久坂和他妹妹了?”
“好像還有個弟弟。”
敬之拿出煙,點上火。等他抽了一口后,有己子繼續問起來。
“久坂是長子,不照顧媽媽嗎?”
“他就是個隨便的人。”
丈夫說得很激動,一瞬間,讓有己子有些吃驚。
“惹出事端,和來歷不明的女人待在一起,他媽媽應該為他操了不少心。”
“他媽媽健在的時候,你見過?”
“曾去過他家一次。”
有己子關掉電視。
“久坂傷心吧?”
“沒有,他還是平時那樣,面無表情。”
敬之吐了一口煙,煙霧拖著一條細線,飄散開去。就男人而言,他的嘴唇過于紅潤了。
“好像他媽臨終時,他也沒有趕上。”
有己子想象著久坂在妹妹家的樣子。也許在那里,久坂雖然是喪主,但仍像個外人一樣,無聲地坐在角落里。
有己子想和他見面。
見面也未必會怎樣,只是見面,聊聊這七年的歲月就足夠了。現在有己子已經沒有往昔的大膽和自信,而且身份也不同了。
七年的歲月給久坂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
就像有己子已經為人妻,成了一個孩子的母親一般,久坂應該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吧。久坂給有己子的印象是看上去沒有女人緣,但身邊總有女人圍繞,或許對于有己子的事情,他只是把它當作小情事而忘卻了。
無聊……
有己子獨自想著久坂,突然覺得那很愚蠢。即便結婚是個枷鎖,這七年,有己子一直守護著丈夫一人。賢淑貞潔的只有有己子,而久坂或許有許多女人。而且久坂可能還像以前那樣,默默無聲地占有了她們。
有己子決定不去想久坂,即便想也不能怎樣,只會徒然生氣,雖然她這么想,但內心中又有一種天真的念頭——久坂也許還想著我。對于給他處女之身的有己子,久坂未動聲色,對于其他女人,他也不會動心的。說不定,久坂的心境和往昔相同。如果見面,他或許會用那能看透一切的眼神,微微默認。
最終,七年間發生在兩人之間的難道只有衰老嗎?有己子覺得如果那樣就太揪心了。
“久坂說問你好。”
敬之像突然想起來一樣。
“問我好……”
敬之這次從正面盯著有己子看。有己子覺得像被責備了一樣,低下了眼睛。
“明天十點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你去嗎?”
“我去守靈夜了,明天就算了。”
“但醫療部一個人都不去……”
“算了。”
“……”
“要不然你去?”
“我?”
敬之那茶色的眼睛微微動了一下。
“算是代表我去。”
“那怎么行,那反倒會失禮的。”
很快,敬之默默地站起身。
客廳往里走是臥房。真紀一個人睡在右邊,旁邊隔著一點距離,鋪著兩個地鋪。
敬之對于晚上的夫妻生活不積極。剛結婚的時候,他頻繁主動地提出要求,最近則斷斷續續。他常在地鋪上看書,有時看累了,會突然提出要求。
有己子有時剛想睡,有時已經睡著了卻被弄醒,因此對房事也不太起勁兒。
那天晚上也是敬之先上床,有己子關好門窗、煤氣,將燈光調暗后才上床。敬之本來像往常一樣,借著臺燈看書,有己子一躺下,他便將腳伸過來——這是敬之向妻子求歡時的習慣。
有己子沒有回應,借著臺燈的光亮,看著天花板。
丈夫的腳逐漸放肆起來。在他的動作下,有己子發覺在聽到久坂消息的晚上和丈夫做愛,是讓人難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