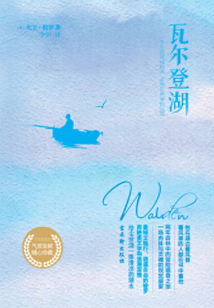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我居于何處,我為何生活
我在這里住下來,或者一個鐘頭,
一個夏天,或者整整一個冬季。
在這里我看到時光飛馳,冰雪消融,春天將至。
在生命的某個時期,我們會自然地考察每一個我們可能會安家的地方。因此,我對我周邊數十英里之內的土地都詳加探查。在我心里,我已經持續不斷地將所有的田地一一買下,因為每一寸田園我都要買,并且我也了解了它們的價格。我與每一個農夫交談,品嘗他們的水果,與他們探討田間的稼穡,用他們心目中的價格或者付出更高的價格,然后再抵押給他——我買下了所有,沒有紙質契約,他們的話語就是契約。因為我本來就熱衷于閑談——耕耘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耕耘著他的心田。在得到了我的所有享受之后,我便揮手離去,而將土地依然留給他自己。這段經歷讓很多朋友誤認為我是土地經紀人。其實我無論在哪里坐下,都可能在那里生活,周圍的景色則以我為中心向四周蔓延開去。房屋,只是一個座席而已。如果在鄉村,那當然就更好了。我看到了很多適合這個座席的位置,只是沒有那么容易就準備妥當。或許有人認為這離村鎮太遠了,但在我,應該是村鎮離這里太遠了。然后,我就告訴自己,就在這里住下好了。然后,我在這里住下來,或者一個鐘頭,一個夏天,或者整整一個冬季。在這里我看到時光飛馳,冰雪消融,春天將至。這片土地未來的居民,不管他們的房子建在哪里,都可以肯定這里已經被人占了先機。搭建一個小屋的時間,就足以將土地變成果園、樹林或者牧場,然后決定在門前保留哪些漂亮的橡樹和松樹,或者將哪些砍伐的樹木如何派上更好的用場。然后,我將這些全部放下,就如同讓土地休息一樣,一個人能夠放下的事情越多,他越是富有。
我的想象如此之遠,以至于一些土地不能進入我的法眼——這種抗拒正合我意——我從來不會因為真實的占有而傷害我的一根手指。有一次差一點成功的經歷就是,在霍樂威爾,我買下了一塊土地,然后我選好了種子,準備好了木料來打造一輛手推車。然而,就在原來的土地主與我簽訂合同之前,他的妻子——每個男人都會有這樣的妻子——反悔了,她希望能夠保留他們的田產,并且付給我十美元作為違約金。說實話,當時的我周身上下只有十美分。然而,我究竟擁有十美分、一塊地,還是十美元,或者兼而有之?這對我的數學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戰。我最后還是讓霍樂威爾收回了土地,也沒有接受他們的十美元。因為就這塊地來說,我已經獲得了很多,準確地說,是我很慷慨地用我付出的成本又將土地賣給了他,事實上他也不寬裕,所以,我又額外送給他了十美元。然而我還是保留了我的十美分,還有準備做推車的材料。我已經覺得自己是個富有的人了,并且我得以保留了那一片風景。
我勘察所有,如同君王,我的權威,無人違抗。【28】
我常常看到一個詩人,他總是在享受完田園中美景的精髓之后,飄然而去。那些愚昧的農夫認為他只是帶走了幾枚野果而已。農夫們不知道的是,多少年之后,他們的田園被詩人寫進了他的詩篇中。那令人艷羨卻又無形的籬笆已經將他們區分開來。
霍樂威爾田園的真正魅力,在我看來就在于那幽靜和深邃。它距離附近的村子大約有兩英里,離最近的鄰居也有半英里,而且還有一方廣闊的田地將公路與它隔開,另一面則依傍著河流。據它的前任主人說,這條河上的霧氣能讓春天的田園免于霜凍。不過這并不在我的考慮范圍之內。房屋和棚屋顯得灰暗而破敗,還有那零落的籬笆,恰好將我與之前的主人隔開適當的距離。那些蘋果樹,布滿苔蘚,上面依稀有一些野兔的咬嚙痕跡,也昭示了我有著怎樣的一些鄰居。此外最重要的是還有這樣的一段回憶,早些年我在這條河上泛舟而上,看到過火紅的楓林掩映下的這些房屋,還偶爾會聽到幾聲犬吠。我急于得到這塊田園,等不及業主將那些巖石搬走,砍掉那棵枯死的蘋果樹,將草地上剛剛破土而出的赤楊樹苗鏟除……總而言之,在主人還沒有收拾妥當的情況下,我已經要搬進來了。為了得到前面所說的那些好處,我打算不再改動,如同阿特拉斯一樣,用雙劍扛起世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阿特拉斯有獲得任何回報——我愿意如此,沒有任何的動機和借口,只待付清款項之后便可以不受別人侵擾地享受這田園。因為我一直都知道,只要我讓其自然發展,就能夠得到我想要的那些完美的收獲。
因此,我所說的從事大規模的農活(至今我依然有自己培育的一塊土地),就當時來說僅僅是準備好了種子。很多人告訴我,種子的改良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我從不懷疑時間能夠辨別優劣。到最后播種的時候,我想我絕對不會讓自己失望。然而,我要跟我的伙伴們說的是,僅此一次的就是盡量讓自己遠離束縛,獲得自由自在,如果將自己與一塊土地捆綁在一起,與關進政府的監獄沒有任何區別。
老卡托的《農村》是我的啟蒙教材,它曾經這樣說過——可惜我唯一見到的譯本將原書弄得了無趣味——“當你想要買下一片田地的時候,寧愿讓腦子里面多想它,也不要貪婪地真的購買下它,也不要怕麻煩而疏于照看,不要認為一周去看上一次繞上一周就已經足夠了。如果這片土地真的很好,那去得越多也就越能感受到快樂。”我是不會貪心到要去購買的,但是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持續不斷地去照看它,即使我死了,也要埋在那里,這樣會讓我在人生的盡頭還能夠感受到更多的樂趣。
我現在要描寫的,是我這樣類型的試驗中的另外一次,我準備更加詳細地描寫。為了方便起見,我將兩年的經歷縮減為一年。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一樣,我無意去描寫沮喪的詩篇,而是如在清晨報曉的金雞一樣,昂首啼鳴,以喚醒我的那些鄰人。
我第一次居住在林間,換句話說,白天和黑夜都居住在那里,剛好是獨立日,那是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那個時候,我的房子還沒有完全建好,也就只能算是一個可以避雨的棚架。房屋既沒有粉刷,也沒有裝好煙囪,墻壁是那些飽經風雨的破舊的木板,到處都是寬大的縫隙,所以晚上會覺得有些寒冷。墻壁之間樹立的白色柱子以及那些剛剛刨得光滑的門窗,給房子增加了一絲亮色,特別是早晨。木板上面浸滿了露水,讓我總是覺得在中午的時候就會滲出芬芳的樹膠。在我的心中,這個房子整天都會發出陽光的瑰麗,這讓我想起前一年在山中偶然到訪的一座房屋。那也是一座未曾粉刷、墻壁漏風的小屋,非常適合過路的神仙落腳歇息。那里也適合于仙女到訪,裙擺搖曳,扶搖而過。清風拂過屋頂,如同掠過山脊一樣清爽和煦,那時斷時續的曲調,有如天籟之音。晨風一直沒有停歇,曲調也從未間斷,卻沒有能夠聆聽的耳朵。對于世人來說,靈山永遠在天地之外。
如果不把一艘小船計算在內的話,在那之前我唯一擁有的凡物就是一頂帳篷。而且,這頂帳篷也只是在夏天出外郊游時偶爾一用,現在已經被卷起來放置在我的閣樓之上。至于那艘小船,則早已在幾次轉手之后,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之中。此刻,我擁有了更加堅固的可以遮風避雨的房屋,已經向著活在人間的目標又前進了幾步。這座房屋雖然簡陋,卻好像將我置身于某種結晶之中,賦予我一定的色彩。在這里我根本不需要跑出屋子來吸取新鮮空氣,因為屋子里面的空氣和外面一樣清新。說是在房間之內,不如是在門后面更加貼切。《哈利凡薩》【29】中說:“缺乏鳥鳴的房子就如同是沒有調料的肉食。”我的房子不是這樣的,因為我忽然發現我的身邊就是鳥兒,但我并不是捕捉鳥兒,而是把我自己放置在它們周圍。我不僅僅和那些常常來到果園和花圃的鳥兒十分親近,也與那些密林中充滿野性、令人激動的歌手十分親近。畫眉、唐納雀、野麻雀、怪鴟、北美夜鶯以及其它鳥類等等,它們幾乎沒有,或者很少會給村鎮的人唱出迷人的小夜曲。
我住在一個小湖邊,距離康科德村子的南面大約一英里半,地勢較康科德略微高出一些,在康科德與林肯之間的山林掩映之中,就是這片湖泊。在此以北兩英里的地方,就是當年的康科德戰場。由于我所在的地方地勢較低,周圍被山林遮蔽,所以我的視野最遠就到達半英里之外的湖泊對岸。第一個星期,不管我怎么向窗外看去,總是覺得這湖泊在山的上面,它的湖底要高出其它湖泊很多。在太陽升起的時候,我看到湖面褪去夜色的霧衣,慢慢地露出它粼粼的漣漪以及平靜的湖面,而湖面的薄霧,則如同幽靈無聲無息地隱匿在山野之中,就好像是夜間湖面的一個秘密聚會結束一樣。在山中,露水常常會在樹枝上面掛很久,直到第二天還沒有完全消散。
一過八月,一陣輕柔的細雨之后,這小小的湖泊就成為了我最為珍惜的鄰居。此時,湖面和空氣極為平靜,天空則滿布濃云,雖然只是午后不久,卻有著如同夜晚般的沉靜。樹林里的畫眉在高歌,到處充斥著歡快的聲音。湖面上面的空氣在烏云的映襯之下顯得有些暗淡,湖中則是一片光明,處處皆是倒影。從近處山頂上一處剛剛被砍伐過樹木的缺口望去,在湖的對岸,有一處美妙的風景一直向南延展。小山頂上留下了一處大的開闊地,其入口就是湖泊,在兩岸的山坡包夾之下,在樹林與溝壑環抱之中,那湖水宛如一條山澗在山間游走,那里實則是沒有流水過境的。我的眼光越過小山樹林的蒼翠,跨過巍巍的山巔,在那視野盡頭,有無數的小山,呈現出優美的藍色,好像這都是天國刻意營造的。另外,也可以略微看到康科德村莊的一角。從另外的方向望去則沒有什么特別的,因為我在叢林包圍之中,視野有限。周圍有水真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它給大地提供了漂浮的動力,讓其能夠游弋。當洪水暴發的時候,我越過湖面向薩德伯利草原遠眺,似乎看到整個山谷都上升了一樣,或許是因為沸騰的山谷出現了海市蜃樓的景象吧,那山谷如同是一枚被放置在山谷中的錢幣。湖面上的大地,如同一塊被隔絕的表皮,在一片水面上漂浮,于是我明白了,我所居住的地方,只是一塊干涸的陸地。
雖然我門前的視野并不十分開闊,但是這絲毫不會讓我感到局促和束縛,那里有足夠的草場讓我的思維能夠縱橫馳騁。湖對岸橡樹叢生的地勢一直向西延展,穿過大草原,一直朝向當年韃靼縱橫的北亞高地,提供給游牧民族以足夠的放牧空間。達莫達拉【30】需要大片開闊的牛羊放牧場所的時候,他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除了享受開闊的視野再無其它。”
時間和空間都已發生了變化,我生活在這宇宙的遙遠的角落,如同天文學家每每在暗夜中觀測的遙遠的夜空一樣,這里距離我最向往的歷史不再遙遠。我總是在描繪著這樣的一個地方,那里幾無塵埃,被快樂彌漫,沒有熙攘或喧囂,這樣的地方或許只在九霄之外,比仙女座還要遙遠。在我看來,我的小屋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悠遠而僻靜,永遠潔凈如初,永遠保持新鮮。如果說居住在昴宿星、畢星團、牽牛星或天鷹星這樣的地方更加有意義,那我也會不顧一切地去追尋,至少我可以如同這些遙遠的星宿一樣,遠離我鄰人們的那些生活方式。這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
曾經,有位牧羊人,
他的思想有如高山般崇高,
他所飼養的羊群星羅密布地點綴在高山之上。
如果他的羊群一直不斷地攀爬,總是在比他的思想還要高的牧場上,那么他的生活會是怎樣呢?
每一個早晨對我來說都是讓人愉悅的邀約,讓我能夠簡樸、真誠地生活。我每天對著曙光膜拜,如同虔誠的希臘人,然后在湖中沐浴。這項看似頗具宗教信仰的活動,也是在我看來最有意義的活動之一。據說,盛湯的浴盆上有這樣的文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也依稀明白了其中的涵義,黎明能夠讓英雄時代再現。清晨,當我推開房門和窗戶,在房中靜坐的時候,一只飛蟲在我的房中徘徊,那不可名狀的飛行軌跡以及難以捕捉的鳴叫聲音深深觸動我的心弦,似乎我是在聆聽著那傳揚美名的號角一般。這是荷馬的一曲挽歌,這是空中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蘊藏著自身的憤懣不安和居無定所。這其中頗有宇宙本體之感,宣告著宇宙的永恒活力和生生不息。黎明啊!一天之中最讓人懷念和珍惜的時間,這是一段讓世間萬物獲得重生的美好時段。人們能夠在這段時間內保持足夠的清醒,至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人體機能能夠從黑夜的沉睡中得到復蘇。如果每個早晨喚醒自己的不是自己的自省,而是仆人的肘頭,如果喚醒我們自己的不是自己的靈感和內心,而是工廠的鈴聲,那么這樣的生活是多么的了無生趣。如果我們醒來,卻并沒有比睡前擁有更加崇高的思想,那么這樣的一個白天,也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白天。如果一個人不相信在一天中總有那么一個小時,比他褻瀆的每一個時辰都更加神圣,那就說明他對人生已經陷入絕望,他的生活已經向黑暗中墮落。經過一夜的休整,人的感官,甚至靈魂都會重新煥發生機,將會嘗試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甚至可以這樣說,人的一生中所有重大的值得銘記的轉折,都是在黎明的氛圍中出現的。《吠陀經》【31】說:“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詩歌、藝術,人類一切最純潔、最智慧的行為,都是這個時刻孕育出來的;所有偉大的詩人和英雄,都如同曼依一樣,是曙光之神的寵兒,在黎明時分,迎著旭日初升,奏響那最美妙的樂章。那些總是充滿希望、富有思想的人們,他們總是在不斷追趕著太陽的腳步,所有的時光就有如永恒的黎明一般。這是不同于時鐘所示的時間,也差別于世人的勞動和作息觀念。在我看來,只要思維清醒,只要能夠獲得領悟,一切時光皆是黎明。精神的修煉就在于摒棄渾渾噩噩的睡眠。如果人們不是在昏睡中虛度光陰,為什么他們對于自己的時間只能給出如此可憐的詮釋?并非是他們不夠聰明。如果不是因為在沉睡中虛度,他們本應當有所成就。數以百萬的人從睡夢中蘇醒,然后從事體力勞作,幾百萬分之一的人能夠保持清醒以獲得有效的心智,但是只有億分之一的人能夠真正的蘇醒以感知生活的詩意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至少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真正清醒的人,如果遇到了,我將怎樣去面對那張面孔?
我們要學會從沉睡中蘇醒,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讓自己保持清醒免于陷入沉睡。但是不能只是使用機械的手段,而是應當基于對黎明的向往;即使我們在深度睡眠中,對于黎明的憧憬也不應當失去。能夠通過繪畫或者雕刻,來完成藝術品的創作固然十分美妙,但更加值得夸耀的事情是能夠塑造出美好的氛圍和媒介,讓人們能夠有所啟示。能夠升華生命的價值,才是最為高尚的藝術形式。蕓蕓眾生都有著讓自己的生命更具價值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夠拋棄世間的瑣碎,上天就會明示我們應當何去何從。
我來到這片叢林的目的是要讓自己的生活更加符合我的思想,是為了探究生命的本質。只有如此,我才能夠在離開這世界的時候,不會因為失去了真正的生活而悔恨。我從未想過要虛度光陰,那是對美好的生命的褻瀆;我也從未想過要順從上天的安排,除非那實在是避無可避。我希望我能夠體會到生命更加深層次的精髓,如同斯巴達人那樣勇敢堅毅地生活,讓生命那些非本質的因素得以篩除,積極進取地開辟新的人生之路。讓生命煥發出輝煌的光彩,然后將這生命的本質廣為傳播。如果生命注定卑微,那么應當如何才能夠讓那些劣根得以過濾,并公之于眾?如果生命本為尊貴,那么也需要用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加以驗證,從而能夠讓這高貴的生命在我接下來的生活中得到顯示。在我看來,世間大多數人都不清楚究竟他們的生活是屬于上帝,還是屬于魔鬼,然而他們又會草率地輕下判斷,將他們的人生歸結為“上帝賜予他們一切,他們彰顯上帝的榮耀”。
我們依然如同螻蟻一樣卑微地生活,盡管神話早已明示我們已經完成了向人類的進化。一個簡單的人,除了運用十個手指之外,不需要更大的數字,頂多在一些特殊狀況下把腳趾也算上就可以了。至于更多的部分,就簡而言之就好了。簡單,簡單,還是簡單。我跟你說,人生之事只有三兩件就好了,而不是那成百上千,更遑論那數以百萬,你的指甲蓋足以記錄這些事情。在當今這個波濤洶涌的文明社會里,一個人要時刻面對暴風、海浪、流沙的沖擊,除非你縱身一躍,沉入海底。那些能夠通過縝密的計算安然抵達港口的成功者們,他們需要多強的計算能力啊。簡單一些,簡單一些,再簡單一些!一日三餐大可不必,一餐足矣;不需要杯碟滿桌,三兩個足矣;每件事情都可以更加簡單。
國家總是在做很多的改進,很多所謂的內在化改進,但實際上都是流于表面的,頂多也就是在一個笨重臃腫的組織里,就像擺放家具一樣,被浪費和揮霍敗壞,就像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家庭一樣。面對這樣的狀況,僅有的解決方案就是嚴苛地實施節約,一種甚至比斯巴達人的生活更加簡樸的節約,讓我們的生活目標更加高遠。人們將一個國家的商業狀況、冰塊的出口能力、電報的使用狀況等的重要性無限放大,卻忽略了他們是否是真的需要。然而我們究竟應當像人一般生活,還是如同狒狒一樣沒有明確的判斷?如果我們不先鋪好枕木,不日日夜夜地建設,又如何能夠準時到達天堂呢?可是,如果我們總是把精力放在我們自己的事情上,總是在自己的家里,又怎么會需要鐵路呢?實際上,不是我們在利用鐵路,而是我們背負著鐵路。你是否思考過在那鐵軌下面的枕木究竟是什么?是一個個男人,不是愛爾蘭人,就是美國人,他們被掩埋在黃沙中,鐵軌就架設在他們的脊背上,火車在他們的身軀上疾馳。所以說,一些人通過鐵軌獲得了人生的幸福,必然有另外的一些人陷入不幸。
為什么我們的生活總是要匆匆忙忙?俗話說:一針及時,可省九針。于是,我們現在就開始縫上一千針,只是為了節約那未來的九千針。我們都得上了多動癥,導致連腦袋都沒辦法停下來保持穩定。如果教堂著了火,當我將教堂的鐘繩拉動報警之后,不等那繩子復位,村落農莊上的男人們,盡管他們早上還在以自己事務繁忙而推諉,各個地方的婦女、孩子們,我敢說,都會放下工作循著鈴聲而趕到這里。他們的到來,恕我直言,不是為了挽救燃燒中的財產,更主要的是來欣賞燃燒的場面,反正火已經燒起來了。而我們(當然,火不是我們放的)是來看看這火是如何被撲滅的。如果不麻煩的話,我們也可以順便救救火。就是這樣,即使燃燒的就是這個教區的教堂。午飯后小睡半個小時,醒來總會先問:“有什么新鮮事?”似乎別人都應當是他身邊的衛兵。他告知別人要每半個小時叫醒他,其實并沒有別的目的,作為回報,他會將他的夢境告訴對方。一夜睡眠之后,那些新鮮事就似乎像早餐一樣不可或缺,“麻煩你告訴我世界上什么地方什么人發生了什么新鮮事。”于是,他一邊吃著面包,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看著報紙,然后他知道在這個清晨的瓦奇多河上,一個人被挖掉了眼睛。然而他卻絲毫沒有在意,他生活的這個世界,如同一個深邃而神秘的黑洞,而生活在其中的他自己,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眼睛。
對我來說,沒有郵局我一樣能夠很好地生活。我很少用到郵遞,準確地說,我這一生所收寄的郵件能夠對得起那份郵資的不過一兩封而已,這句話我在幾年前也說過。一便士的郵資制度,其本來目的是你利用一個便士能夠獲得別人的思想,但事實是通常你只能夠得到一個玩笑。我敢說,我從來就沒有從報紙上面獲得過真正有價值的新聞。如果我們只是從報紙上看到一個人被搶了,一個人被殺了,或者一棟樓房著火了,一艘輪船沉沒或者爆炸了,或者一頭母牛被西部鐵路上的火車撞死了,一只瘋狗死了,或者一群蝗蟲在冬天出現了,諸如此類,我們不需要重復多次,只需要看一次就夠了。如果你明白了其中的原理,又怎么需要再花費時間去看那數以千萬的實證呢?在一個哲學家的眼睛里,所有的新聞都只是流言蜚語,那些編輯們就像喜歡搬弄是非的老太太,然而對這些流言著迷的卻大有人在。我聽說最近有一天,為了盡快知道一則國際新聞,人們如同洪流一樣涌到報社之外,幾面大的玻璃窗都被這洪流沖碎。然而我覺得,這新聞只要是有點頭腦的人,在十二個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都能夠寫出來,而且準確無誤。再比如,說到西班牙,你只需要將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羅,塞維利亞和格拉納達這些名詞恰當地放進去——與我讀報的時代相比,或許有些改變吧——然后,如果需要一些新鮮的消息,那就將斗牛放進去好了,這就構成了真實的新聞,就能夠告訴人們西班牙的現狀或者災難等消息。至于英國,距現在最近的有價值的新聞大概就是一六四九年的革命吧,如果你時刻關注那里的糧食產量的增長,其實也毫無必要,除非你是為了要做一些投機的生意。對于一個難得看到報紙的人來說,這些年國外實在是沒有什么新鮮的事情,就算是法國大革命,也不例外。
什么是新聞?只有那些永不過時的事情,才更有意義。虛偽和欺騙被人們奉為至理名言,現實有些讓人不可理喻。如果我們都只是謹守真實,而不被虛無縹緲所干擾,那么用我們常見的來作比喻,我們的生活就好像《天方夜譚》這樣的童話一樣。如果我們總是對那些已經存在的東西心存敬意,詩歌與音樂將會在大街小巷出現。如果我們不再慌亂而且足夠睿智,我們就能夠知道只有崇高而美好的東西才會永恒,那些虛妄的快樂和卑微的膽怯都只是人們心中的過眼煙云。人們總是在半夢半醒之中,透過蒙眬的雙眼,被瑰麗的幻影所迷惑,來抉擇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且切實奉行,謹守規則,然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幻想和泡沫的基礎上的。那些還在自由嬉戲的孩童,他們反而更能夠明白生活。而那些看似什么都了解,看似閱歷豐富,看似充滿經驗和智慧的成年人,他們的生活則毫無意義。
我曾經從一本印度古書中看到這么一個故事:曾經,有個王子,在小時候被迫離開了古國,流落到民間,被一個農民收養。他一直在這種環境之下生活長大,他的性情也被深深地打上了這個環境的印記。直到一位大臣發現了他,將他的身世告知了他,他也因此認識到自己王子的身份,他的性格也因此被還原。這個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印度哲人,他說:“靈魂被所在的環境迷失,進而影響了性格表象,直到有仙師幫他獲悉真相,他才知道自己本來就應該是婆羅門【32】。”在我看來,我們這些新英格蘭人如此卑微生活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總是不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人們真實信奉的真理,總是在宇宙之外,在那遙遠的星辰之間,在亞當出現之前,在世界最后一個人死亡之后。然而,這所有的地方和時代,都是此時此地的。上帝最為神圣的就是此刻,時光的流失不會讓他更加偉大,我們只有感受周圍的真實,才能夠更加體會到他的崇高。上天常常會順從我們的意識,不管我們是步伐迅捷,還是緩步前行,都會為我們鋪好道路。讓我們用畢生之力來感知吧,詩人和藝術家們并不能夠總是有那么完美和諧的創意,但是,他們的后來者會不斷地讓美趨于極致。
讓我們就如同大自然一樣從容度過每一天吧,不要因為硬果殼或者是一只蚊蟲的翅膀而改變軌跡。迎著黎明,早早起床,吃或者不吃早餐,自然而然而無絲毫局促;不管人來人往,任由鐘聲響起,哪怕孩子哭鬧,也認真地思考要過好每一個日子。為什么我們要放棄自我,隨波逐流呢?我們不要停留在淺灘,以免被卷入旋渦或激流。只要經過了這些艱難險阻,前面將會是一路坦途。不要讓你的膽氣消弭,煥發你的精神吧,向著希望不斷前進,就像尤利西斯被縛在桅桿上遠航一樣。如果火車的汽笛響起,那就讓它聲嘶力竭吧;如果車站的鐘聲響起,為什么我們要開始奔跑呢?我們還要分析這是什么音樂?我們要冷靜下來,謹慎行動,讓我們的雙腳踏遍那片布滿偏見、傳統、謬誤的土地,穿越巴黎、倫敦、紐約、波士頓、康科德,從詩歌、哲學到宗教,直到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堅實的根基,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現實。然后我們可以肯定,就是這里了,沒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我們能夠在洪水、冰霜和火焰下面,開始建造我們的城池或者國家,或者堅固地豎起一個燈塔,立起一個標桿,這個標桿不是尼羅河上的水面標尺,而是衡量真實世界的標桿。這樣,后來者就明白了,那些虛妄和幻想如同洪流的淤積,究竟有多深?如果你直面真實,你會感受到太陽的閃耀,如同一柄彎彎的東方短刀。我們都為了真實,如果我們即將死亡,在彌留之際,最好能夠聽到喉嚨的響聲,能夠感受到大限到來的寒意;如果我們活著,那就讓我們專注于我們的事情吧。
時間是一條小溪,我在其中垂釣,也喝溪中之水。在我喝水的時候,我發現那溪的沙底是那么淺,然而,流水過后,留下的卻是永恒。我想在更深的地方取水,我想到天空中垂釣。我常常感慨,自己早已經喪失了出生時期的睿智。智力就好像是一柄快刀,能夠剖析一些秘密,從紛繁蕪雜中開辟出道路。我再也不希望我的雙手終日無效地忙碌,我的大腦就是我的手足,在我看來,最好的感官都在其中。我的直覺跟我說,我的頭腦可以掘洞,如同那些動物利用爪子或者尖嘴一樣,我可以憑借我的大腦在山間探尋掘出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