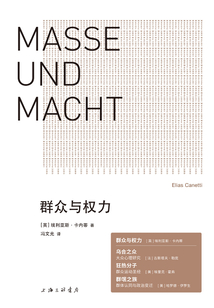
群眾與權(quán)力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首版譯序:論“距離”
卡內(nèi)蒂的《群眾與權(quán)力》從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結(jié)合上剖析、闡述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本書涉及人類學、生物學、社會學方面的知識,與此相應(yīng),作者使用的范疇、概念的范圍也很廣。我想就本書中的一個概念即距離發(fā)表一點看法。
一切生命個體都要同另外的個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最直接的原因是為了求生。肉食動物想縮短與捕獲對象之間的距離,以便最終抓住它,吃掉它;被捕獵對象則力求擴大與捕獵者之間的距離,以便保持自己的生命。人類在捕獵野獸時僅靠個體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人類在原始時期必須加強個體之間的緊密性,縮小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距離,這樣才能對付力量和速度都要比人大得多的野獸,這是為了滿足吃的需要。同樣,為了安全的需要,原始人也必須縮短個體之間的距離,提高緊密性和集體性,只有這樣才能在自然力量面前保證自身的安全。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主要談兩個原因:一個是生物性的原因。人首先也是一種動物,而動物對外界總是有一種天生的警惕情緒,任何直接的觸摸、抓碰都會引起動物的恐懼。人也是如此,在被觸碰時也會有一種恐懼感。人的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嚴的需要都要求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作者在他的著作《獲救之舌》中說:“人類有一種天生的特性,易向恐懼投降。恐懼不可能消失……萬事萬物大概以恐懼最不容易改變。我回溯早年的生活,最早認識的便是恐懼,其根源是無窮無盡的。”面對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和兇猛的野獸,面對死亡,人們充滿了恐懼,他們克服這種恐懼的辦法就是加強緊密性,縮短距離。書中描寫了一個部落的成員臨死時,部落中的許多成員撲向這個將死之人,把他壓在底下,上面的人越堆越多,越堆越緊,他們這樣做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減少將死之人在死亡前的恐懼,也是為了消除他們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可以說,這一類恐懼是人類天性中的一個永恒的因素。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貧富分化、階層和階級,這些社會原因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擴大了。由人的社會性原因造成的距離容易發(fā)生變化。人出生時屬于某一個階層或階級,屬于富人階層或貧民階層,但這種狀況是會變化的,或者由于社會變革而發(fā)生變化,或者由于個人的努力而發(fā)生變化。本書作者對社會原因所造成的因門第不同、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人的傲氣,很為反感。他在《被拯救的舌頭》一書中寫道:“對于出身高貴而洋洋自得的人,我的反感很深。”門第、財富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會變化的。有一種距離卻比較持久,這就是統(tǒng)治者與群眾的距離。不管統(tǒng)治者是代表奴隸主、封建主還是資本家,統(tǒng)治者與群眾的距離總是存在的,不過距離的大小不一樣。從資本主義發(fā)展以前的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這種距離總的來說是趨向擴大的。
群眾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的發(fā)展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原始部落中,人們是怎樣選出自己的領(lǐng)袖呢?在有些部落中最初是根據(jù)力量,人們在選擇部落的領(lǐng)導人時采用的標準是誰的力量大。誰力量大,誰在角逐中取得勝利,誰就成為領(lǐng)導者。人們崇拜力量,崇拜權(quán)力,力量與權(quán)力是相通的。部落成員選出領(lǐng)導者,領(lǐng)導者代表權(quán)力,因而也可以決定群眾的一切。本書中講到的蘇薩人就是這樣:酋長下令蘇薩人毀掉谷物和儲備,殺掉牛群,他們就照辦,以致他們在一次大饑荒中幾乎死盡滅絕。其實他們知道這樣做會毀滅自己,但是這是酋長下的命令,他們只好服從。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權(quán)力的代表者不僅靠力量,而且還要靠財富和地位。這時,群眾與權(quán)力化身之間的距離要比原始部落中群眾與權(quán)力化身之間的距離大得多。在一定范圍內(nèi),距離和權(quán)力是一起擴大的。權(quán)力的代表者懂得,在一定范圍內(nèi),與群眾保持一定的距離,群眾就會敬畏權(quán)力,就容易被控制。
從群眾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的內(nèi)容來看,主要起作用的是群眾的特性。本書的作者認為,群眾有如下一些特性:一、群眾要永遠增長(人數(shù)增多);二、群眾內(nèi)部平等占統(tǒng)治地位;三、群眾喜歡緊密地聚在一起;四、群眾需要導向;五、在群眾內(nèi)部,公共目標會淹沒私人目標,只要還沒有達到目標,群眾就會繼續(xù)存在。從這些特性來看,群眾是天生具有追求平等、抹殺個性的傾向的。本書中提到,有些部落對獨食者持鄙視態(tài)度,對狩獵和分配中有不規(guī)行為的人,往往采取逐出部落的懲罰措施,逐出部落比處死刑還要殘酷。從歷史上看,凡是權(quán)力的代表者能較好地利用群眾的上述特性的,都能取得較好的效果。只要迎合群眾喜歡聚集在一起、不斷增長的特性,提出奮斗目標,實行平等的措施,就可以掌握群眾的心理。
在掌握和利用群眾的特性方面,宗教做得比較成功。宗教讓群眾相信遙遠的美好的未來,誰對宗教持虔誠態(tài)度,誰就能在彼岸獲得幸福。群眾在他們共同信仰的偶像面前是平等的。另外,宗教提出的幸福只有在彼岸才能實現(xiàn),因此總是一個有待實現(xiàn)的目標。有些宗教還要求教徒在宗教儀式上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交頭接耳,不能喧嘩。如果允許教徒在宗教儀式上交頭接耳,互相議論,那么他們就不會對偶像保持敬畏的心情,偶像的威望就會大打折扣。
當然,群眾的這些特性也會隨著群眾的變化而改變。現(xiàn)代文明開始發(fā)展之后,等價交換原則貫穿于一切領(lǐng)域,個性的發(fā)展有了廣闊的基礎(chǔ),彼岸的幸福只是滿足一種心理的需要,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奉行的是利益原則,群眾內(nèi)部的平等也只留下一個形式,實際上不平等的成分越來越大。群眾越是發(fā)展,群眾在宗教儀式上表現(xiàn)出來的信仰、平等就越是一種形式,這時,宗教想激起教徒的狂熱就很困難。群眾越不發(fā)展,就越有可能出現(xiàn)宗教狂熱;群眾越不發(fā)展,就越有可能出現(xiàn)凌駕于群眾之上的權(quán)力。隨著人的個性的發(fā)展,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擴大了,但科技的發(fā)展卻間接地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個性、科技和民主意識的發(fā)展正在開創(chuàng)一個權(quán)力與群眾之間的距離縮短的新的歷史過程。
馮文光 2001年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