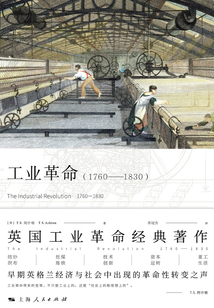
工業革命(1760—1830)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論
從喬治三世登基到其子威廉四世即位,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里,英格蘭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數個世紀以來被當作敞地來耕種的地方,或者被當作公共牧場而無人問津的地方,都圈上了籬笆或者建起了圍墻;小村落發展成為人口稠密的城鎮;煙囪讓古老的塔尖相形見絀。公路被筑造了出來:與那些敗壞笛福(Defoe)[1]時代旅行者良好行為習慣的惡劣交通設施相比,公路則更加筆直,更加牢固,更加寬闊。北海和愛爾蘭海,以及默西河、烏斯河、特倫特河、塞文河、泰晤士河、福斯河、克萊德河的通航之處,都通過靜水線路連接到了一起。北部鋪上了第一條鐵軌,迎接新火車頭的到來,蒸汽貨輪開始在入海口和海峽上定期往來。
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其相似的變化。人口大幅增加,兒童和年輕人的比例可能也提高了。新社區的成長改變了從南部和東部到北部和中部的人口平衡;積極進取的蘇格蘭人帶頭走在一眼望不到頭的隊伍前方;一群群沒有技術但朝氣蓬勃的愛爾蘭人蜂擁而入,這并非沒有對英格蘭人的醫療衛生和生活方式產生影響。在鄉下土生土長的男男女女開始成群結隊地生活在一起,各自維持生計,他們不像是家人或鄰里群體,倒像是工廠勞動力中的一個個單元;工作變得更加專業化;新的技術形式被開發了出來,一些舊式的則淪落了。勞力變得更具流動性,更高的舒適標準也提供給了那些能夠也愿意朝機會中心遷移的人。
與此同時,人們開發了原材料的新源泉,打開了新的市場,發明了新的貿易方法。資本的體量和流動性增大了;貨幣建立在黃金的基礎之上;銀行體系開始形成。很多過去的特權和壟斷被一掃而空,企業在立法上的障礙被移除了。國家開始很少主動參與具體事務,個體和志愿協會則更加積極地參與其中。創新和進步的觀念削弱了傳統上的制裁:人們開始向前看,而非向后看,他們對于社會生活之性質和目的的看法轉變了。
無論這一系列的變革是否被說成是“工業革命”,最終都會被拿來進行討論。這些變革不只是“工業上的”,還是社會上和思想上的。“革命”這個詞意味著一種突然變化,事實上,突然變化并不是經濟變革過程的特點。人際關系體系有時候被稱為資本主義,早在1760年前就有其自身源頭,在1830年后獲得了全面發展:這樣一來便存在著忽視連續性這一基本事實的危險。但“工業革命”這個詞語被一個個歷史學家拿來使用,它已非常牢固地嵌入到共同話語之中,另辟蹊徑去找個詞語來取而代之,那會是件迂腐之事。
這一時期社會史的突出特點——把這個時代和此前的所有時代區分開來的、超過其他任何事物的東西——是人口的迅速增長。在葬禮和洗禮數字的基礎上進行仔細估算,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數量在1700年大約有550萬,到1750年有650萬,到1801年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人口數量達900萬左右,至1831年達到了1400萬。因此,在18世紀的下半葉,人口增長了40%,在19世紀前30年里,增長超過了50%。對于大不列顛來講,1801年的人口數量大約為1100萬,在1831年則為1650萬。
人口增長并不是出生率發生明顯變化的結果。事實上,在18世紀前40年中,每千人的出生數看起來似乎提升了一些。農場工往往會建立自己的家庭,而非寄宿在他們的雇主那里,行業學徒制的衰落也導致了早婚和造就了更大的家庭。但從1740年到1830年,出生率看來好像只是存在著非常輕微的波動:對于任何一個十年來說,估計值都沒有超過37.7%或低于36.6%。整個工業革命自始至終,生育率都非常高,也很穩定。
人們也不能把人口的增加歸因于其他國家的人大量涌入。在每個十年里,男人和女人都會乘坐船只從愛爾蘭進入到英格蘭和蘇格蘭,遇到鬧饑荒時,遷移的人流如涓涓細流變成了小河。但是,尚未出現像19世紀40年代后五年的那種愛爾蘭移民潮。另一方面,在整個18世紀,可能有100萬人離開不列顛到海外謀生,主要是去殖民地發展。在這些人當中,大約有50000名罪犯被運到馬里蘭(Maryland)和植物學灣(Botany Bay)[2],大批藐視法律的手藝人把他們的技術知識和技能帶去了歐洲——人們可能會猜想,從長遠來看,這并沒有給他們的故國本土帶來不利。總的來說,不列顛并不是個接納中心,而是個海外新社區的孵化場地。
正是死亡率的下降導致了人口數量的增長。在18世紀前40年里,毫無節制地喝著廉價的杜松子酒以及時斷時續的饑荒和疾病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但在1740年至1820年間,死亡率幾乎持續不斷地在下降:在1740年之前的10年里,死亡率估計是35.8%,而在1821年之前的10年里,估計為21.1%。許多具有影響力的東西都在降低死亡率。根莖作物的引進讓人們能夠在冬季飼養更多的牛,也因此全年都能供應鮮肉。小麥替代了劣等谷物,人們加大了對蔬菜的消費,這些都增強了對疾病的抵抗力。個人衛生標準更高了,加上肥皂越來越多、棉制內衣越發便宜,這些都降低了感染的危險。在墻體內使用木材的地方用上了磚頭,屋頂使用了巖石而不再是茅草,這都減少了害蟲的數量;工人住所里很多有害的制造工序都被清除了,這樣一來家庭更加舒適了。較大的城鎮進行鋪路,排水,并供上了自來水;醫藥和外科手術的知識發展起來了;醫院和診所增多了;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諸如垃圾處理和正確埋葬死者這類事情上。
因為沒有可靠的數據作為支撐,人們不可能說出哪個年齡段的人從這些改善中受益最大。在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3]的自傳中,有段耳熟能詳的文字這樣講道:
新生兒死在父母前頭可能看起來不合乎自然,但這完全是件可能的事情;因為不管生多少個孩子,在他們長到九歲之前,在他們具備心理的或者身體的能力之前,有一大批孩子都夭折了。我并沒有譴責大自然過度的浪費或者不完美的工藝,只是覺察到這種不利機緣對我的幼年生存極為不利。我體質很弱,性命也難保,因此在每個弟弟洗禮之時,父親慎重起見就重復使用我的教名愛德華,萬一長子有個三長兩短,這個源于父輩的名字可以在家里仍然能夠叫下去。
這段話寫于1792—1793年間。到了這個時候,情況可能是,嬰幼兒生命的大量浪費要比吉本出生的時代要少一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兒童和年輕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會更高一些。在思考早期工廠勞力的構成之時,記住這一點至關重要。
不列顛人口增長之時,正值商品產出也處在快速增長的時期,這種巧合使人們草率地進行總結概括。有些作家作出論斷說,正是工業的增長導致了人口的增長。如果說這種推論是正確的話,那么工業增長必然會發揮其影響力,它并非通過出生率(正如我們所見,出生率保持穩定)而是通過死亡率來進行的。上面所提到的在生活藝術上的一些改善當然依賴于工業發展,但人們會輕率地把這種情況看作是死亡率下降的主要組成部分。因為人口在快速增長,不只不列顛如此,西歐和北歐的其他大多數國家也都一樣,但從工業革命的性質來說,那里什么都沒有發生。
其他一些作家顛倒了因果關系,聲稱人口增長憑借著其對商品需求的影響刺激了工業的擴張。然而,人口增長并不必然意味著對生產的商品有更大的有效需求,也不必然意味著全國范圍內人們所感興趣的產品的產量之增長。(如果確實是這樣,我們理應發現18世紀愛爾蘭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應發現19世紀埃及、印度和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可能恰好給所有人帶來的是一種更低的生活標準。人口對維持生計所造成的壓力曾在1798年讓馬爾薩斯(Malthus)[4]感到煩惱,這個幽靈決不是什么臆想出來的怪物。事實上,它所帶來的直接壓力比馬爾薩斯所假定的要小一些。但若19世紀中葉之后,在美國沒有鐵路,沒有北美大草原開放,沒有蒸汽機船,不列顛可能會從痛苦的經歷中得出這樣的謬見:因為有一雙手就有一張嘴,所以但凡人數擴大必然導致消費增長,也因此導致產量的增加。在不列顛,在18世紀以及此后,碰巧就在人口增長的同時,其他生產要素的增長也在進行,因此人民的——或者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生活標準才能得以提升。
耕地面積有所增加。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對沼澤和濕地的排水上,放在了把那些破舊、粗野的公共牧場(通常被說成是荒地)一塊塊切割開來并轉變成可耕地之上,放在了把土地用樹籬圍住以便讓莊稼和牲畜更多產之上。看到這些發展的一位觀察家這樣寫道:“運用這種方式,以損害個人為代價,把有用的領土增添到帝國版圖之上,這比‘光榮革命’[5]以來通過任何一場戰爭所獲得的領土都要多。”幾種新作物被引進了過來。蕪菁讓牛群擴大規模變得可能,馬鈴薯在北部成了廣受歡迎的食物,它在土地的利用方面帶來了大量的經濟實惠。后面在談到農業變革和土地變革時會講得更詳細一些。講到這里足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先前被排除在經濟活動體系以外的土地正在參與進來,而且被更好地加以利用。今天,那些用眼睛去觀望的人們能夠在山坡之上辨認出移動的邊疆。
與此同時,資本的迅速增長正在進行著。那些收入足以撐得起主要生活需求之人的數量正在增長:儲蓄的力量正在增強。隨著1688年爭端的解決,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狀況激勵人們去拓寬眼界:經濟學家口中所稱的時間偏好則有利于積累。階層結構也同樣有利于積累。通常認為,與主張財富分配更趨于平均恰好具有現代觀念的共同體比起來,那些財富分配不均的共同體更偏向于儲蓄。從1688年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6]到1812年的科洪(Colquhoun)[7],統計學家們估計,不同社會階層的收入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新機制的興起,包括國債的出現,加大了從前幾代人身上延續下來的那種差距。
正如今天我們所了解到的那樣,公共債務產生于威廉三世(William Ⅲ)[8]發動戰爭的緊急需要。直到1815年其數額達到8.61億英鎊為止,公共債務都在穩步增長——它幾乎完全是接二連三發動戰爭的結果。并非所有的公共債務都掌握在不列顛人民自己手里:在1776年,可能有1/4或更多的公共債務把持在荷蘭人手中。但到了1781年荷蘭卷入對不列顛的戰爭以后,大量的債務開始掌握在這個國家的手里——由貴族、鄉紳、律師、退休商人以及富裕階層的寡婦和未婚婦女所掌控。在1815年可能大約占1/11的以及在1827年占1/12(根據亨利·帕內爾爵士的估計[9])的聯合王國人民的貨幣收入,都是從納稅人(包括窮人在內)身上征集來的,而這些貨幣收入都轉移到了相對富裕的政府公債持有者手中。按照這種方式,漸漸地,財富到了那些好攢錢之人的手里,而不是到了那些愛花錢之人的手中。
然而,積累本身并未導致資本品的創造:人們不但樂意存款,而且愿意有效地利用那些積蓄,當時這種愿望增強了。在18世紀早期,地主利用積攢下來的資財改善自己的地產,商人用之拓展他們的市場,廠主則拿來雇用更多的勞力;退休和有閑階層的一些積蓄已經借貸給了當地的土地所有者、農場主或零售商,或者投資到收費公路信托機構的股份上。在鄉村銀行家(這些人在冠以鄉村銀行家的名頭以前存在了很長時間)崛起的幫助下,資本市場逐漸被拓寬了。國家提供的大量金邊債券讓人們習慣了非個人投資的觀念,于是他們開始把積蓄投到那些空間上距離很遠、性質上屬于投機性的企業身上。結果并不總是帶來好處,在1720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10]破裂而讓成千上萬的人破產之時,這點已昭然若揭了。但總體來講,資本流動性的不斷增強對社會是有益的,就像它所做的那樣導致了利率的大幅下降。
幾個世紀以來,國家對于獲取利息持敵視態度,或者說至少是懷疑態度。國家是習慣上的債務人——而且所通過的法律禁止超過指定利率去貸款。1625年,法定利率從10%降到了8%;1651年降到了6%,1714年為5%——每一次“自然”利率都會隨之下降。在18世紀早期,大量的可貸資本讓財政大臣們降低向國家債權人所付的利息變得可能。戰爭期間,威廉三世政府不得不把利率升到7%或者8%(《高利貸法》不適用于國家);但在1717年,永久年金的利率降低到5%,1727年則降至4%。最終,在18世紀50年代,佩勒姆(Pelham)[11]再次降低利率,而且通過把很多債券轉變成一種單一債券,在1757年推出了利率為3%的“統一公債”(Consolidated Stock),我們把它簡稱為“統債”(Consols)。這些轉變并非強加在不情愿的公眾身上,它們反映了在共同體內利率的普遍下降,而非讓利率開始下降。這一時期,沒有任何單一市場利率可以被拿來參照,但是從英格蘭銀行股價的攀升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個進程;商人和廠主的賬簿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這個時代的很多經濟活動都由一小群合伙人所掌控,他們個個要么有資格得到自己的年利潤份額,要么全部或部分地把它投到公司中以賺取利息。在18世紀早期,允許以這種方式對金錢進行再投資的利率正在持續下降。例如,伍斯特郡的一家鐵器制造公司——愛德華奈特公司(Edward Knight and Company),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對未分配的利潤向每個合伙人以5%的利率進行賒貸,但到1735年利率降到了4%,1756年就只有3%了。如果一群人正在考慮把他們的積蓄投資到某些嶄新的大型資本公司,比如一家收費公路,他們首先會估算一下把資本全部歸還給他們所需的年數。如果現行利率是5%,歸還資本得需二十年,這事值得去干;如果以4%的利率去投資,可能會延長到二十五年;如果以3%去投資,則會花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年來補償最初的開支。資本能夠獲得的利息越低——以一種固定方式進行提前鎖定的優勢就越小——資本的功效就會被延伸得越長。
早在1668年,喬賽亞·蔡爾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12]就評論道,“時至今日,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在其向貨幣利息所支付的,且通常是已支付的精確比例上變得更加富裕或者是更為貧窮的”。他繼續觀察到,“利率從6%降低到4%或者3%……這必然會讓國家的資本存量翻一番”,他還說,“貴族和鄉紳,他們的財產大多數情況下在地產上,可能不久便在他們擁有的一切之上,五十不是五十,反而要寫成一百”。盡管歷史學家很早就對利息、資本和福祉的關系展開了闡述,但從未真正強調過利率在工業革命前的半個世紀里出現下降的重要性。如果要對18世紀中葉經濟發展步伐加快尋找一個單一原因——這樣做可能是錯誤的,但假設我們必須這樣子去找。在工業革命中,挖得很深的礦井、造得堅固的工廠、構造合理的運河以及大而結實的房屋,這些都是相對廉價的資本之產物。
還有一件事是必不可缺的:源源不斷地供給勞力、土地和資本必須被協調起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存在著大量的企業家,人們快速去發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渴望找到新市場,愿意接受新觀念。“這個時代在創新之后正走向瘋狂”,約翰遜博士(Dr.Johnson)[13]曾經說道:“人們會以新的方式去干世上的一切事情;會以新的方式去把人絞死;泰伯恩刑場(Tyburn)[14]自己也無法免受創新狂熱的影響。”時代心理的情緒和態度順風順水。在此前的兩個世紀里,宗教和政治差異撕裂了社會,如今卻已消解彌合了;如果說18世紀不見得是個信仰的時代,但至少它踐行了基督教的寬容美德。由行會、市政當局、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工業條規已經完全失效或者被人們束之高閣,場地向首創和進取精神的淬煉敞開著大門。蘭開夏和西賴丁已經從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對工業立法法規的一些具有較多限制性的條款中得到豁免,其發展變化最為顯著,這可能并非意外之事。很多村莊或者未經特許而變成的城鎮——就像曼徹斯特和伯明翰這樣的地方,它們發展得最快,這當然亦非偶然之事,因為工業和貿易早就從那些公共管制的殘余機制仍在運轉的地方抽身而去。
在17世紀的時候,人們看待法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從在普通法法庭中柯克(Coke)[15]判決的時代觀念轉變到了確實更加傾向于財產權的觀念,但對特權懷有敵意。1624年,《壟斷法》掃除了大量的既得利益,一個半世紀以后,亞當·斯密(Adam Smith)[16]可以這樣說英格蘭人,說他們“是所有民族的偉大榮譽,最起碼服從那討厭的壟斷精神”。正是這個《壟斷法》勾勒出了專利體系的脈絡,無論專利體系是否正在激勵工業實踐中的創新,它都不容易起到決定性作用。它為發明家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它允許一些特權狀態保留過長的時間,而且有時它經常擋了新發明的道:例如,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可以阻止其他工程師建造新型蒸汽機,甚至在特權之下妨礙了他自己。很多制造商——并非所有人都出于純正的動機——反對法律的實施并鼓勵盜版。曼徹斯特開始形成一些協會,其他工業中心則對專利權人主張的權利之合法性提出質疑。1754年,“藝術、制造業和商業促進會社”成立了,該協會向那些愿意將其發明設計拿來供人們自由處置的人提供獎金。除了給予大量的年度撥款以投票支持對農業協會[18]和獸醫學院[19]的使用之外,議會自己還設置了一些獎金:例如,在托馬斯·洛姆[20]的紡絲機專利到期之時獎勵了他14000英鎊,給予發現疫苗接種的詹納[21]30000英鎊,給予有著多種發明創造的卡特賴特[22]10000英鎊,以及給予發明“騾機”的克朗普頓(Crompton)[23]5000英鎊。作為一位出色的工業家,在沒有任何諸如此類的金錢刺激下,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24]下定決心“從這些奴性枷鎖中解脫出來,這些枷鎖意味著,自私自利地害怕他人抄襲我的成果”;后來,安全燈的發明者,漢弗萊·戴維爵士(Sir Humphry Davy)[25]、克蘭尼博士(Dr.Clanny)[26]、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27],為了礦工的利益,他們全都拒絕為其發明申請獲取專利。拿掉專利體系這套裝置,探索發現會像它所做的那樣獲得快速發展,情況至少可能是這個樣子。
有些對于技術革命的描述是以這樣的故事開始的:一個懷揣夢想的男孩正在觀察蒸汽頂起爐子上的水壺蓋,或者一位貧窮的織工目瞪口呆地凝視著妻子的紡車,雖然翻倒在地卻仍在旋轉。勿需多說,這些都不過是浪漫小說罷了。還有些描述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發明是那些無名的磨坊技工(millwright)、木匠或者鐘表匠的成果,他們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只是偶然的機會創造了某些發明,而這注定給他人帶去名聲和財富,自己卻窮困潦倒。確實,有這么一些發明家——諸如布林德利(Brindley)[28]和默多克(Murdoch)[29]——他們幾乎沒有什么學識,但卻擁有天生的才智。確實,還有一些發明家,比如像克朗普頓和科特(Cort)[30],他們的發現轉變了整個工業,但留給他們的卻是在貧困潦倒中終了一生。確實,一些新產品是由于意外之舉才出現的。但這些敘述帶來了危害,它們混淆了在工業實踐中系統性思想落后于大多數創新這樣的事實;它們呈現出來的是在經濟體系中獎懲分配完全非理性的畫面;尤其是,它們過分強調在技術進步中機運(chance)所扮演的那部分角色。正如巴斯德(Pasteur)[31]所言,“機運只喜歡有準備的頭腦”:大多數發現只是在反復不斷的試驗和出錯以后才得到的。很多發現包含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先前的獨立想法或工序,它們一起進入到發明者的腦海中,結果以多少有些復雜和有效的機制原理呈現了出來。以這種方法,例如,克朗普頓就是把珍妮紡紗機的原理和滾筒紡紗的原理相結合發明了騾機;鐵制軌道在煤礦中已使用了很長時間,連接上機車便創造了鐵路。在這些被稱為交叉變異之物的例子中,機運所起到的作用真的必定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然而,其他對工業革命的解釋正在誤導人們,因為它們把發現描述成個體天賦的成就,而非看作是一種社會進程。正如現代著名科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32]所評論的那樣:“發明是在一個擁擠的舞臺上演的一出戲劇。”掌聲往往送給了在最后一幕中恰巧站在舞臺之上的那些人,但演出的成功取決于很多演員的緊密合作,以及那些幕后人員的通力協作。那些創造工業革命的技術之人,無論作為對手還是合伙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英格蘭人或蘇格蘭人。
既不是半仙也不是英雄,
而是心靈手巧、不辭勞苦的智人后裔,
很幸運能在風調雨順的天氣里插秧種植,
而非在嚴寒或者暴風中進行,但當時間慢慢成熟,環境的巧妙穿梭
呈現出難以想象的機遇,
他們抓住時機……
[上面這些話出自我們這個時代的棉紡技工戈弗雷·阿米蒂奇(Godfrey Armitage)之口。]
發明出現在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但它在一個由樸素的農民和毫無技能的體力勞動者組成的共同體內很難茁壯成長:只有當分工業已展開之時,這樣一來人們致力于一種單一產品或者一種工序,發明才能碩果累累。18世紀伊始,這種分工已經存在,工業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專業化原理強化與延展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強化與延展的結果。
此外,與只追求物質目標的共同體相比,發明更有可能出現在那種重視精神層面的共同體中。英格蘭科學思想的溪流發源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33]的學說,在波義耳(Boyle)[34]和牛頓(Newton)[35]的才賦下得以拓展,這是工業革命的主要支流之一。的確,作為哲學家和學者的牛頓心腸太好,以至于毫不在乎他帶給世界的觀點能否立刻“派上用場”;但是,相信通過觀察和實驗可能會取得工業進步的觀念則基本上是通過牛頓才來到18世紀的。自然哲學正在從它與形而上學的糅合中擺脫了出來——再次運用了分工的原理——并分拆成生理學、化學、物理學、地質學等單獨的體系。然而,這些科學尚未專業化到脫離普通人的語言、思維和實踐之地步。正是因為去了一趟諾福克(Norfolk)[36],到那里去學習新的種植方法,那位蘇格蘭地主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37]才開始對土地的構成產生興趣;他的發現讓其成為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地質學家,而這些發現某種程度上歸功于那些從事挖泥土和炸石頭來為英格蘭開鑿運河的苦力。像富蘭克林(Franklin)[38]、布萊克(Black)[39]、普里斯特利(Priestley)[40]、道爾頓(Dalton)[41]和戴維(Davy)這樣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他們與不列顛工業中的領導人物保持親密接觸:在實驗室和工場之間有著頻繁的往來,像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喬賽亞·韋奇伍德、威廉·雷諾茲(William Reynolds)[42]、詹姆斯·基爾(James Keir)[43]這樣的人,他們不管在哪里都像在家里一樣。那些在皇家學會成員名單上的工程師、鐵器制造者、工業化學家、儀器制作者的名字表明,在這一時期,科學和實踐的關系是多么密切啊!
發明家、設計家、工業家、企業家——在快速變化的一段時間里人們不容易把一個“家”與另一個“家”區分開來——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來自這個國家的四面八方。有些貴族——像18世紀早期的洛弗爾勛爵(Lord Lovell)以及稍晚一些的霍爾克姆的柯克(Coke of Holkham)[44]等——發起了農業上的改進;還有些貴族——比如說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45]和高爾伯爵(Earl Gower)[46]——則創建了新的交通運輸方式;另外還有些貴族為化學工業和采礦工業的創新作出了貢獻。牧師和堂區長——包括埃德蒙·卡特賴特和約瑟夫·道森(Joseph Dawson)[47]在內——摒棄了精神療法而去尋找織布和冶鐵方面更為有效的方法。醫學博士——他們中間有約翰·羅巴克(John Roebuck)[48]和詹姆斯·基爾——則從事化學研究,并成為大型工業的巨頭。在理性主義哲學的影響下,學者們從人文主義轉向自然科學,有些學者從自然科學轉向了科技。律師、士兵、公務員以及比這些人地位更低的人,他們在制作中發現了改進的可能性,而這些改進比在其最初從事行業中所提出的改進要大得多。一個理發員——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49]——變成了最富裕、最有影響力的棉紗廠主;一位客棧老板——彼得·斯塔布斯(Peter Stubs)[50]——建立了一家備受尊重的銼刀貿易公司;一位校長——塞繆爾·沃克(Samuel Walker)[51]——成為了英格蘭煉鐵工業中的北部領軍人物。在1780年,熱情洋溢的威廉·赫頓(William Hutton)驚呼道:“每個人的財富都握在自己手里。”不用說,這話從來就不是對的,或者甚至也不是只對了一半;但是,任何仔細觀察18世紀中后期英格蘭社會的人都會理解說出這樣的話是多么可能的啊,因為在這個時代各種不同層次人們的流動所達到的程度比此前或者可能此后的任何時代都要高。
人們經常觀察到的是,工業的成長與那些不服從按照既有法律在英格蘭建立起來的教會機構之群體的興起存在著歷史性聯系。在17世紀,清教徒的集會圍繞著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52]而云集于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53],包括福利家族(Foleys)、克勞利家族(Crowleys)和漢伯里家族(Hanburys)在內,他們打算在諸如斯塔福德郡、達勒姆郡、威爾士南部這些更遠的地方建立起偉大的機構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公益會(Society of Friends)教徒在谷物加工、釀酒、制藥和銀行業的發展上起到了顯著作用;達比家族(Darbys)、雷諾茲家族(Reynolds)、勞埃德家族(Lloyds)和亨茨曼家族(Huntsmans)的貴格會教徒在一段快速變化時期開始主導煉鐵工業的命運。在工程學上,有像托馬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54]這樣的浸禮會教徒和像詹姆斯·瓦特這樣的長老會教徒;在煉鐵上,有像約翰·羅巴克和約瑟夫·道森這樣的獨立派人士,也有貴格會教徒;在棉紡上,有包括麥康奈爾家族(M'Connels)和格雷家族(Greys)在內的一位論派教徒。此外在棉紗上,最偉大的發明家塞繆爾·克朗普頓是伊曼紐爾·斯維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55]的門徒,人們可能記得,斯維登堡自己就是金屬加工和采礦技術方面的權威人士。其他的工業家——這些人中有威爾士南部的特邀嘉賓——則從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56]的教義中汲取力量。但衛斯理的首要呼吁是面向窮人和無特權之人的,而且與開始受循道宗影響的工人們的那種更大的節制、勤奮和自律相比,循道宗的效應在企業加速成長中則很少看到。
很多解釋提出了工業和不信奉國教的這種緊密關系。有人提出,那些找出新的禮拜形式之人在世俗領域自然也會另辟蹊徑。有人認為,在不信奉國教獨特的教義和導致商業成功的行為準則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有人主張,把不信奉國教者從大學中以及從政府和行政部門中排斥出去則迫使很多人去尋找出路,以在工業和貿易上去施展才能。每種主張可能都有些道理,但更加簡單的解釋在于這樣的事實:一般來說,不信奉國教者構成了中產階級中更有教養的那個部分。在1707年合并之后,活力的源泉從信奉長老會的蘇格蘭川流不息地流進(雖然合并之后沒有馬上注入)英格蘭,這種源泉推動了經濟運動,而中產階級中更有教養的那個部分在經濟運動中起了作用,考慮到這點,以上這個觀點便有了支撐。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家詹姆斯·瓦特來自蘇格蘭,在他建造發動機事務的八個助手中,有七個也同樣來自蘇格蘭。約翰·辛克萊爵士(Sir John Sinclair)[57]、托馬斯·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58]、約翰·麥克亞當(John Macadam)[59]、戴維·馬希特(David Mushet)[60]和詹姆斯·博蒙特·尼爾森(James Beaumont Neilson)[61]把他們蘇格蘭人的精神活力和性格特色帶到英格蘭的農業、交通和煉鐵中去。蘇格蘭高地人和蘇格蘭低地人同樣都經過長途跋涉來到蘭開夏的產棉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喬本特(Chowbent)這個小村莊稍作停留,在這里一位名叫坎南(Cannan)的同胞引領他們來到那些向他們的各種才能提供機會的中心。在那些南下在紡織業上發了財的人之中,有詹姆斯·麥加菲(James McGuffog)、詹姆斯·麥康奈爾(James M'Connel)、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喬治(George)和亞當·默里(Adam Murray),還有——那些擁有在今天而且不只是在蘭開夏感到榮光的名字之人——約翰·格萊斯頓(John Gladstone)和亨利·班納曼(Henry Bannerman)。這些移民及其他人并不是目不識丁的農民。有些人是在牧師家里長大的孩子,即使那些地位低下之人也在當地鄉村學校或者自治市學校至少受過相當不錯的初級階段教育。
如果說蘇格蘭的基礎教育體系比這一時期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先進的話,那么蘇格蘭的大學教育也同樣超前。科學探究的沖動及其實際應用并非來自牛津或者劍橋——在那里火炬燃燒殆盡,而是來自格拉斯哥和愛丁堡。許多年輕人被起初在格拉斯哥后來在愛丁堡擔任化學教授的約瑟夫·布萊克的學識和個性所吸引,他們在思想和實驗的方法上得到訓練,而這些方法后來直接指向工業目的。在他們之中,有詹姆斯·基爾,他是化學工業和玻璃工業上的先驅,如果這個圈子可以擴大到那些并非布萊克的正式弟子但對布萊克的教導和友誼感激頗深之人,那便還有約翰·羅巴克、詹姆斯·瓦特以及那個聰明睿智但非常不幸的鄧唐納德伯爵(Earl of Dundonald)——亞歷山大·科克倫(Alexander Cochrane)[62]。
在布里斯托爾、曼徹斯特、北安普頓、達文特里、沃靈頓以及其他地方,由熱衷于教育的不信奉國教者所建立起來的各種學院卑躬屈膝地為18世紀的英格蘭默默奉獻著,它們做了大學為蘇格蘭所做的部分事情。它們面向所有人開放,不分信仰,并提供課程,這些課程包含數學、歷史、地理、法語以及會計,實際上,它偏重于神學、修辭學以及猶太古史。在它們的學生之中,有丹尼爾·笛福(以及當時所稱的克魯索)、約翰·科普(John Cope)[63]、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64]、托馬斯·馬爾薩斯以及威廉·海斯利特(William Hazlitt)[65]——所列舉的只是他們之中在文學和公共事務上赫赫有名的幾個人罷了。對于我們的直接目的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是科學思想的溫床。它們中有幾個用“哲學工具”全副武裝起來,并提供了用來做實驗的設施:它們的教師包括那些具有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和約翰·道爾頓的品質之人;它們中間出了一系列未來的工業家,在這些工業家中,有約翰·羅巴克(他在前往愛丁堡和萊頓前在北安普頓接受訓練)、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66]、約翰·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67]、本杰明·戈特(Benjamin Gott)[68],以及——屬于后面一代人的——約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69]。
除了不信奉國教的學院,許多城鎮里還有像全國性的藝術會社(Society of Arts)那樣致力于改進生產方法的機構。非正式的科學家和制造商團體在蘭開夏和英格蘭中部地區開始出現,就像在愛丁堡和格拉斯哥一樣。棉紡技工在多大程度上是從他們在曼徹斯特文學與哲學會社里與托馬斯·珀西瓦爾(Thomas Percival)[70]和約翰·道爾頓的接觸中受益;或者伯明翰及其所在的省欠了月亮會社(Lunar Society,在該會社中,伊拉斯謨·達爾文(Erasmus Darwin)[71]、理查德·洛弗爾·埃奇沃思(R.L.Edgeworth)[72]、約瑟夫·普里斯特利、詹姆斯·瓦特、馬修·博爾頓、喬賽亞·韋奇伍德把他們強大的頭腦對準了生命問題,而且竟然瞄準了謀生問題)多少情,這些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不斷增長的土地的、勞力的和資本的供給局面讓工業擴張成為可能;煤炭和蒸汽為大規模生產提供了燃料和動力;利率低下、價格上漲以及對利潤很高的預期,這些都產生了刺激作用。但在這些物質因素和經濟因素的背后以及這些因素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與境外之地進行貿易開闊了人們的世界觀,科學則拓寬了他們的宇宙觀:工業革命也是一場思想革命。如果它表達了人們在理解和控制大自然上的進展,它也就注意到了人們開始以新的態度去對待人類社會的問題。在此再次指出的是,那束最亮的光芒來自蘇格蘭,特別是由格拉斯哥大學發出的。過分強調在塑造普通男女的生活上思辨性思維所起到的那部分作用,無疑犯了一種學術性錯誤:說約翰·衛斯理、托馬斯·潘恩(Tom Paine)[73]、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74]和“演說家”亨特(Orator Hunt)[75]就像大衛·休謨(David Hume)[76]或者甚至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77]一樣都產生了非常大的直接后果,這是有道理的。但在對引起工業革命之動力的各種描述上,至少有一本蘇格蘭的道德哲學作品是繞不過去的。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會被看作是后來幾代人在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一種上訴法院。這本書所作出的判斷是那些不愛進行專題論文研究的人從中為企業和政府等機構制定他們的行為準則的素材。正是在這本書的影響之下,那種由國家指導和管控的、多少固定不變的貿易量和就業之觀念,幾經周折逐步讓位于在一種自由的和擴張的經濟中無限進步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