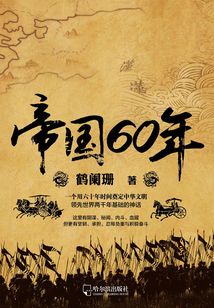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邊境太守之死
馮敬死于大漢帝國六十年,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六十年為一甲子,具有某種神秘的氣息。僅在八年后,漢武帝就開始了對匈奴的全面戰爭。這足以說明,帝國在六十年的發展中,取得了引以為傲的成果。抵御外侮必須提到日程上來。
一
公元前142年,大漢帝國雁門太守馮敬在匈奴軍隊的進攻下壯烈殉國。馮敬的離世,使大漢王朝多年以來用尊貴的女人和龐大的資財以換取和平的愿望再一次被擊碎。無論皇帝還是平民都需要認真考慮一下,這一政策是否還應該繼續,抵御外侮是否應該被提上日程?
至少在馮敬剛剛入土為安后,沒有人可以回答上面的問題。景帝當時已重病在床,再有一年,他將和馮敬一樣永遠地離開人間。直到八年后,他的兒子武帝才用實際行動解答了這個困擾先輩多年的問題。開國之初確定并執行如一的“和親”政策因武帝向匈奴開戰不廢而廢。
一個隱而不現的規律是,奠定封建帝國基調并將影響力滲透到帝國政治生活中的開國帝王,所留下的政治遺產都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后任繼承并發揚光大。“和親”政策從制定初衷而言絕對是一項優秀的政策,因為它符合了當時的形勢,但卻只經過四代帝王的“發揚”就宣告結束。在武帝龍馭上賓后,“和親”政策雖再度歸來,意義卻已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武帝時的大漢帝國已經具備了改變這項政策的想法和能力,那么就是高祖皇帝在制定這項政策時有苦衷。
由馮敬之死上溯到60年前的公元前202年,高祖皇帝擊敗優秀的對手項羽而建立漢朝。兩年后,在邊境負責防御匈奴任務的韓王信突然叛國,憑借熟悉帝國地形的優勢,與匈奴聯合勢如破竹一直進軍到晉陽。局勢危急,高祖皇帝只好御駕親征。由于天氣惡劣,加上指揮官高祖皇帝輕敵冒進,所帶領的一支先頭部隊被匈奴誘困于平城白登山,而身為主力部隊的步兵卻沒有及時趕到,等于提前退出了戰場。
四面之圍下,高祖皇帝感到了恐懼,親征前的意氣風發變成了絕望。這場戰役在大漢帝國歷史上被當作恥辱屢屢提及,卻很少有人指責高祖的輕敵冒進。早在戰端未開時,高祖皇帝十次派出使者到匈奴“視察”,十人回來的報告都是可以開戰。只有一人在第十一次“視察”匈奴后認為不可戰,此人叫劉敬。大漢王朝建立時,他以戍卒的身份向高祖皇帝建議建都長安而得到重用。
在白登,高祖皇帝對沒有聽從劉敬的意見而深深懊悔。隨行的謀士陳平面不改色,這位帝國最有智慧的謀士仿佛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讓任何事起死回生。他請求高祖皇帝讓自己只身赴敵方軍營,并保證馬到成功。
許多年后,匈奴故意露出一角讓高祖等人飛馳而出的原因始終是個謎。所以,陳平只身赴匈奴軍營面見匈奴單于的老婆所使用的計策也就成了“秘計”而不被天下人知。史書分析說,因韓王信另外兩個與匈奴約定本該露面的叛將始終沒有露面,匈奴擔心兩人會重新回歸漢營,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放掉了高祖。這一分析即使屬實,民間也始終相信是陳平與匈奴單于老婆的那次密談解了白登之圍。高祖抽身而退后,對劉敬的欣賞與對匈奴的懼恨與日俱增。
按劉敬的說法,匈奴人在最短的時間里可以號召起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三十萬,大漢帝國初建,沒有實力與這樣的一個對手抗衡。武力對抗已經被毫無懸念地排除,那么用戰國以來風行的“仁義之說”作為武器又如何呢?這是中原政權在武力不允許的情況下通常采用的另一種策略。但劉敬認為,這種策略仍舊不可行。一個最清晰的證據是,當今的匈奴單于冒頓是殺父自立,并將自己的老母娶為妻子,并且這已成為匈奴的顯風俗。受這種風俗影響的人根本不懂“禮義廉恥”為何物,教化之說,無異于天方夜譚。
那段時間,每當高祖皇帝走過長樂宮的前殿,就陷入無名的沉思中。這座新建成的宮殿并沒有給他帶來一絲欣喜與安慰,旗幟張揚、衛兵林立的長樂宮如同高祖的心情,每每在大臣們離開后就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即使是在開國之初,雖然經歷了秦末、楚漢兩場大規模戰爭,以及大漢帝國的人口數銳減的情況下,僅從人口數上來看,匈奴仍然是弱方。當時的匈奴專家就說,匈奴人口數不過是大漢帝國一個大郡的人口數。不過,一國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是看其在一場戰爭來臨時可以動員的士兵數量,而不是全國人口的數量。匈奴雖然在大漢帝國建立初年不足一百萬人口,但其每次戰爭動員的人數要遠遠大于大漢帝國,尤為重要的是,大漢帝國即使可以動員起與匈奴相等的軍隊,戰斗力上卻不能抵匈奴騎兵的十之二三。
高祖皇帝在頻繁的會議中,希望眾大臣能拿出一個良策。但是沒有人給他,激進分子認為該與匈奴開戰,他們用擊敗了最兇狠的對手項羽這一證據證明帝國的軍隊所向披靡,戰敗只是暫時的。保守分子雖然認同劉敬“仁義之說”不可用的意見,但仍舊提出以“仁義”為武器對付匈奴。更有人提出,以萬里長城作為抵御匈奴的屏障。高祖當即否定了這一愚蠢的意見。倘若真按此人的意見,那么在所有城樓都部署上足夠的駐防軍,并供應他們的糧草,即使把全國的人力物力都動員起來也不足以支撐一年。
最終,還是劉敬提出一套策略,這套策略最終被高祖采納,近而成為大漢帝國六十年處理與匈奴關系的政策。劉敬認為,武與文既然不能成為與匈奴打交道的武器,那么,只有先“穩”住匈奴再談其他。他提出了三條。第一條,將皇家尊貴的女人(長公主)嫁給匈奴單于為妻;第二條,每年送給匈奴大量錢財和他們所缺少的物品;第三條,派遣大漢帝國的知識分子到匈奴去“諭以禮節”。
按劉敬的說法,長公主一旦成為匈奴單于的老婆,那么,與大漢帝國的皇帝就建立了子婿關系,而單于所生的兒子就成為了帝國皇帝的外孫。站在倫理的角度,任何人都相信,沒有女婿與岳父為難的,自然,更不會出現外孫打外公的事情。而向匈奴贈送大量匈奴缺乏的物品,是希望使匈奴從經濟上依賴大漢帝國,這種想法在文帝時仍有市場。再次,通過不斷派遣帝國的知識分子去勸諭匈奴放棄傳統的道德觀念,接受中原的道德觀念,由此最終使匈奴由“未可以仁義說”變為“可以仁義說”。
相比而言,從情感上攻擊對手比從經濟和道德上攻擊對手更經濟,但其效果是否與良好的愿望一致,還值得商榷。劉敬也指出,這是一個緩慢的、需要很長時間方能發生效果的方法,所以他對高祖皇帝說:“然恐陛下不能為。”
許多年后,有人對劉敬開了“和親”先河的事情口誅筆伐,認為這是中原政權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并且影響極為深遠、極為惡劣。劉敬深受戰國策士文化所影響,“和親”政策的第一條就明顯帶了戰國策士“旁門左道”的痕跡。但是,既然高明如高祖皇帝這樣的人,也不能拿出切實有效對付匈奴的辦法,那么,劉敬的策略也只能被時人看作是高明的了。一個這樣“旁門左道”的提議都能被采納,也說明了大漢帝國的張力之大,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亦說明這個帝國的可塑性之高。然而,雖然劉敬的初衷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但事情的發展卻不能如其所愿。
第一個被嫁出去的高貴女子是一位諸侯的女兒,等于說,劉敬和親政策的第一條就被高祖皇帝否定了。在劉敬看來,之所以要將皇帝的女兒嫁給單于,是希望得到單于的尊重由此而成為匈奴國王的王后。但呂后卻以“自己只有一女”為由,拒絕了高祖皇帝的請求。在隨同人員中,有許多被迫出關到大漠中負責教化的帝國知識分子,和那位高貴的女人一樣,他們也不愿意離開中原,去和存在語言障礙的匈奴人接觸。這年的年末,按照與匈奴約定的條款,大漢帝國將一批金銀和匈奴人缺少的棉花、酒等物送到了匈奴,真正的“和親”政策開始了。這一年是公元前198年,大漢帝國建立的第九個年頭,也是歷史考驗“和親”政策的第一個年頭。
二
馮敬是60年來匈奴大規模寇邊的多達八次戰役中陣亡的最高級官員。帝國初年,為防備匈奴、烏桓、西南夷、東南越族等少數民族,帝國特設邊郡21處,邊郡的最高軍事與行政長官為邊郡太守,除了負有教化當地百姓的道德義務外,太守還獨立指揮一支人數不少的軍隊。高祖與呂后時代,這支軍隊由帝國的適齡男子組成,朝廷規定,適齡男子一生中必須要到邊地當兵一年。文帝時,為了讓這些適齡男子可以安心在家務農,所以采取了“徙民實邊”政策。這一政策的弊端就在于,所徙的民大都是犯罪者,朝廷以優厚的待遇為誘餌,鼓勵他們到邊境去當兵,另外,還在邊疆招募一些部落民。于是,帝國邊境線上的軍隊大都是由朝廷招募自愿前往的罪人和邊疆的部落民勉強拼湊而成,根本不具備與匈奴抗衡的戰斗力。從“和親”政策出臺直到武帝向匈奴宣戰,匈奴侵犯帝國邊境多達八次,帝國沒有阻擋住一次。
馮敬死后,直到帝國與匈奴進入戰爭狀態,再也沒有一次匈奴侵犯的記錄。馮敬無疑成了60多年“和親”政策的一個總結,也是“和親”政策即將被打破的開始。這項一直被視為“旁門左道”卻又不得不執行的“和親”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挑戰來自于雙方。平心而論,無論是匈奴還是大漢帝國,都沒有把這項政策視作長期國策。
高祖皇帝在世時,邊境沖突并非是匈奴人引起,而是因為犯叛國罪的封王在山窮水盡之下往往投靠匈奴,而匈奴也樂于接納。帝國方面曾提出過譴責,但沒有實力做后盾的譴責對匈奴而言是耳旁風。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匈奴單于冒頓只是縱容歸附來的漢人騷擾帝國邊境,自己雖然不反對卻也不支持。呂后時代,匈奴開始主動出擊,在公元前182年,對帝國邊境的狄道(今甘肅省臨洮南)實施軍事打擊。但引起這次軍事沖突的很可能是大漢帝國邊境指揮官的意氣用事。
自“和親”政策執行以來,帝國邊境線上的指揮官大都是隨高祖皇帝東征西討的激進分子,作為武人,他們不理解朝廷,甚至會故意違反朝廷所制定的政策。在朝廷實行邊境貿易時,常以愛國者自居,對匈奴進行或隱或顯的打擊,由此引起的邊境沖突不在少數。這次沖突被帝國解圍后,第二年的年末,匈奴又攻擊狄道。這一次,責任在匈奴一方,他們不但殺死帝國士兵,還掠走了一大批漢人。讓人并不奇怪的是,一向以陰毒而又具備很多政治家都不具備的政治智慧見稱的呂后,姑息了匈奴的這次犯境。姑息,這可能是第一次,但絕對不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賢王率領十萬騎兵攻擊帝國邊境北地、河南地,上郡指揮官雖奮勇而戰,卻因不能阻擋匈奴騎兵的進攻而殉國。同時,在上郡,右賢王還捕殺帝國吏卒,極為囂張。于是,朝堂之上,人聲鼎沸,文帝派出大將灌嬰,發兵八萬五千向右賢王反擊,右賢王最終被帝國的正規軍擊敗,退出上郡。據匈奴單于后來給大漢帝國的報告中稱,此次犯境,純是右賢王的自作主張。不過,匈奴人把責任推到帝國這一方,他們認為是帝國邊境的官吏冒犯了右賢王。文帝并不深究,因為他知道弱者與強者之間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
八年后,公元前169年,匈奴再侵狄道,帝國邊兵依舊無法阻擋。三年后,公元前166年冬,匈奴新任單于老上單于派出十四萬騎兵入侵朝那、蕭關,并將帝國北地都尉殺死,同時掠奪大量人口與牲畜。文帝派出張相如帶兵十萬擊匈奴,一個月后,老上單于撤出塞內。四年后,公元前162年,匈奴接連入邊,殺掠人民,搶奪畜產甚多。僅云中、遼東二郡就各被掠走萬余人。又是四年后,公元前158年,匈奴三萬兵入上郡,三萬兵入云中,文帝將軍隊屯飛狐、句注、細柳。這月末,漢兵至邊,匈奴離去。景帝時代,匈奴寇邊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第二次是公元前144年,匈奴入雁門;第三次是公元前142年,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戰死。
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是,公元前166年冬,文帝接受了晁錯的建議,讓有罪之人去邊境充實力量后,匈奴的進攻才開始頻繁起來。這只能說明大漢帝國的實邊政策讓匈奴失去了安全感,同時,邊境的帝國將領也時常跟匈奴發生不必要的摩擦,對匈奴的頻繁寇邊,不能不說是一個催化劑。一方面是帝國對匈奴的積極防御,另一方面是喪失安全感的匈奴通過發動戰爭來增強安全感。這樣一來,“和親”政策的破產就在意料之中了。
劉敬倘若還在人間,不知該對此做何感想。事實上,劉敬并非是一個智慧型人才,而僅僅有一點小聰明。按他所言,匈奴單于一旦娶了帝國尊貴的女人,所生下的兒子將來會成為單于,顯然有失武斷。沒有任何資料表明某位匈奴單于是有著漢人血統的,是帝國皇帝的外孫。下嫁的公主在匈奴的影響力如何,以及后代是否有“貴為太子”者或位顯權貴者,歷史并無記載。匈奴單于敢把自己的父親當成敵人來射殺,又怎么可能指望這樣的人來尊重岳父呢?劉敬希望通過派遣知識分子去改變匈奴的風化,也幾近于一個人的意淫。很有意思的是,這種意淫最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公元前192年,呂后將一位高貴的女人嫁給冒頓單于做老婆,幾個月后,冒頓單于給呂后寫了封信。在信中,冒頓單于說希望可以與呂后結為夫妻,按照匈奴風俗,這很合情理。匈奴的單于死后,他的老婆將會成為他兒子的老婆。但就大漢帝國道德觀而言,這顯然有違倫理。呂后大怒,卻不能與匈奴翻臉,只好回信說明中原習俗與匈奴習俗的不同,并且將自己說成是一個老女人不能與匈奴單于般配。匈奴單于在接到信后,回道:“沒有聽過中國的禮義教誨,好在陛下不追究。”這也正說明了劉敬“和親”政策“諭以禮節”的失敗。
三
大漢帝國的陸軍是由守衛皇宮的南軍與守衛京師的北軍組成的,兩支部隊加在一起不足十萬人。每當匈奴犯邊時,帝國集合起來的軍隊以南北軍為主力,再加上從郡國征來的士兵,勉強超過十萬。帝國軍隊的戰斗力與匈奴軍隊的戰斗力相比并不強。南北軍的主力主要是步兵,所以,即使大漢帝國有與匈奴一戰的決心,軍隊的戰斗力也不允許。但當匈奴軍隊一入邊,騎兵失去了在遼闊草原上的優勢,南北軍就有了發揮的余地。這也就是為什么匈奴不能在帝國境內長久待下去的原因。
作為大漢帝國的敵人,匈奴是強大的。在與大漢帝國接觸前,這個游牧民族不僅征服了丁零、東胡、樓蘭、烏孫等許多部落,甚至在后來西遷后,還成為東、西羅馬帝國的嚴重破壞力量。而匈奴之所以會成為震蕩歐亞大陸的力量,它的軍事力量該是主導因素。
與大漢帝國不同,匈奴完全以騎兵為主。匈奴人大都善騎射,這是因為從小就開始培養的緣故,匈奴兒童到四五歲能騎羊時,就學習用小弓箭射鳥和鼠類,到十八歲時,已經能夠力彎大弓,此時就編入“甲騎”,成為正式戰士,過著“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的戰斗生活,一直到年老不能出征時為止。他們甚至在馬上做買賣、吃飯、開會,在馬上睡覺。在使用武器方面,匈奴人主要以適合遠距離攻擊的弓箭為主。匈奴的弓箭手能夠在五六十米之內達到很高的命中率,而有效射程則達到175米。當近距離接觸時,刀與鋌就成了他們的攻擊武器。因此,大漢帝國的步兵在匈奴騎兵快速而又兇狠的攻擊下,往往不能取得半分便宜。奔馳在平原上的匈奴騎兵,不論是襲擊還是逃避,都靈活機動、敏捷迅速。這又是大漢帝國的騎兵所不能匹敵之處。
發動一次戰爭,軍費支出龐大。漢王朝軍費的來源主要有三項,即按人征收的稅項——人頭稅(口賦、算賦)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賦),以及按戶征收的稅項——家庭資產稅。漢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所以這些賦稅數量相當少,根本不可能讓大漢帝國有發動與匈奴戰爭的實力。此外,邊境的建設上也有很多問題。匈奴騎兵雖然不善攻城,但帝國邊境線綿延幾千里,由于軍費缺乏,結果往往沒能構筑堅固的城堡抵擋匈奴騎兵的攻擊。所以,當朝堂上的激進分子想要動員全國兵力與匈奴開戰時,這些因素都被皇帝考慮在內,無論是身受其害的高祖皇帝還是陰冷毒辣的呂后,更或者是守成令主文、景二帝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在錯誤的時間與匈奴全面開戰就等于葬送帝國的前途。
馮敬并不是優秀的將軍,人們始終認為他只是個悍將和出色的行政管理者。殉國前兩年,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改變了大漢帝國的刑罰制度。在帝國外交上,這位行政管理者始終在建議皇帝和他的同僚應該改變政策。而他的殉職,或多或少只是個人因素——在公元前142年的匈奴寇邊戰中,他一馬當先直至殉國。
帝國近六十年的時光,四位皇帝與出色的丞相領導下的朝廷始終不肯與匈奴殊死一搏,即使有最激進與最有能力的將軍和智慧超群的朝廷大臣的頻頻吶喊也不能改變帝國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當時的帝國現狀造成了這一切妥協,那么,更深層的原因應該就是,大漢帝國雖然才建立六十年,但作為中原民族,這個帝國主要民族的年齡已經近于高齡了。或者說,漢民族發展到大漢帝國時代,已經處于慣性階段。這是一個擁有著十分勤勞然而欠缺進取心民眾的帝國,正是這些民眾,經過努力,讓大漢帝國的主體民族變成了一個安土重遷的農耕民族。根據千百年來的歷史經驗,這樣的農耕民族,當他們沒有感覺到人口過多和土地不足時,是絕不會對外擴張、征伐異族的。匈奴的頻繁但卻為時短暫的寇邊,并沒有讓大漢帝國感覺到土地不足。這或許就是大漢帝國能隱忍六十年并還能繼續隱忍下去的一個原因:匈奴,包括后來的諸多少數民族不會將中原綽綽有余的土地掠奪殆盡。
所以,“和親”政策就必須要堅持下去。帝國所等待的只是一個機會,但這種機會并不是侵略和擴張,而是回擊。只不過,在機會沒有到來時,還需要韜光養晦,奉行被許多人視為恥辱的“和親”政策來保持暫時的和平。從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0年的六十年間,大漢帝國共送了十二個尊貴的女人去匈奴。這些人的名字并沒有被記錄在冊,或許在大漢帝國看來,這終歸是一種恥辱。
這種恥辱終于在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終結了。終結點就在雁門的馬邑,漢武帝在得到一位大臣“希與匈奴開戰”的上言后,毅然決定與匈奴撕破臉皮。武帝派人遣兵三十余萬設伏于馬邑,欲以此誘匈奴單于圍而殲之。但被匈奴單于發覺,單于引兵還。自此之后,“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邊,不可勝數”(《史記·匈奴列傳》),西漢和匈奴由此轉入戰爭狀態,戰爭取代了“和親”。
四
由于匈奴的文字記錄往往刻意忽略了宦官中行說的人生,所以這位出使到匈奴,并幫助匈奴消除“和親”政策帶給匈奴的危害的智囊往往不被大多數人所知。
中行說是文帝時的一位宦官,此人的道德談不上敗壞透頂,但其不討人喜歡應該有據可查。很可能就是討厭他的官員在遞給文帝的出使匈奴使者名單中,把他列在了第一位。中行說當時就跟文帝表示,自己不想去匈奴。文帝卻對他表態,無可更改。中行說臨走前,對文帝說:“我此次前去,肯定不會給我大漢帶來好處,只能帶來壞處。”文帝顯然低估了這句話,更低估了中行說的能力和復仇的信念。中行說到達匈奴的時間是公元前176年。一年前,匈奴右賢王侵犯帝國邊境,在此事解決后,匈奴老上單于希望大漢帝國能繼續執行和親政策。中行說來到匈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匈奴單于表忠心,他開始用自己對大漢帝國“和親”政策的背后目的的了解來向大漢帝國復仇。
他試圖向匈奴單于說明,西漢“和親”政策的目的,就是通過送給匈奴大量“漢物”以求改變匈奴的消費結構,從而使匈奴在經濟上依賴西漢,直至臣服于西漢。
首先,他讓匈奴改變對大漢帝國棉花與絲綢的依賴。他常讓騎兵穿著絲綢衣服在荊棘里快馬飛馳,從而讓絲綢壞掉,以此來證明絲綢的好看不中用。其次,通過傳授文字、計算來提高匈奴民族的文化素質。再次,教唆匈奴單于對待漢民族的人在態度上應該傲慢。最后,通過自己對漢邊境的了解,幫助匈奴制訂與大漢帝國作戰計劃。
但如上并不是中行說的全部,當一批大漢帝國的知識分子希望通過用中原文化來改變匈奴的野蠻風俗時,中行說用下面的話來警告這些人不要浪費精力:“匈奴對百姓的約束簡潔不繁,容易施行;君臣禮節簡單,可以長久保持情誼;一國的政治,猶如一體。所以匈奴雖然動蕩不寧,但繼位的必然是單于的子孫。中原雖自稱有禮義,但親屬之間日益疏遠,互相殘殺,以至于讓外姓改朝換代,都類似于此。哎!你們這些住在土石房屋中的人,不要多費口舌,喋喋不休!只要記住漢朝輸送給匈奴的繒棉絲絮,好米酒曲,數量夠、質量好就行了,何必說三道四呢!”接著他又威脅道:“如所給的物資數量足、質量好就算了;如果數量不夠,質量低劣,一到秋熟時,匈奴就用騎兵踐踏你們的莊稼!”中行說在大漢帝國諸多優秀人物群星閃耀的歷史上,不過是滄海一粟。即使是他投靠匈奴,很多人仍然堅信,他的出謀劃策并不是大漢帝國沒有同化匈奴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應如晁錯所言的那樣,匈奴人的衣食不仰賴土地,所以他們勢必經常侵擾邊境,往來遷移,時來時去。即使大漢帝國傾全國之財物施舍于匈奴,在短時間內也不能改變他們的習俗,甚至是永遠無法改變。而那種通過貿易來維持雙方和平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至少在晁錯看來,“和親”政策的初衷就不是以和平為出發點的。所以,兩國的開戰只是時間問題。
在匈奴的問題上,晁錯雖然主張要以軍事打擊為主,但他和呂后時代的樊噲、與他同時代的賈誼不同的是,他有著清醒的認識。大國戰敗成為小國,強國失敗成為弱國不過在頃刻之間,所以,絕不能輕易開戰,一旦決定開戰,就必須有十足的把握。晁錯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使人欽佩不已,他承認與匈奴和親是“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但在經濟基礎與全民的仇恨心情沒有達到一定程度時,發展大漢帝國的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隨著漢武時代的到來,大漢帝國的糧食、軍備都已充足,前幾任帝王的忍辱負重與勵精圖治最終體現出了價值。在漢武帝將要與匈奴開戰時,有大臣認為不可。漢武帝就舉出春秋齊襄公復仇滅紀來作為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論依據,在漢武帝看來,齊襄公能為九世祖復仇是君子所為。而當年高祖皇帝白登之圍,相繼的幾位皇帝受到的屈辱,不過才三世,就是百世,也要堅決復仇。
馮敬死于大漢帝國六十年,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六十年為一甲子,具有某種神秘的氣息。僅在八年后,漢武帝就開始了對匈奴的全面戰爭。這足以說明,帝國在六十年的發展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果。抵御外侮必須該提到日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