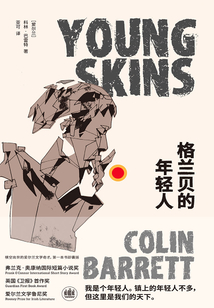
格蘭貝的年輕人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克蘭西家的孩子
你或許從未來過我的家鄉(xiāng),但你應(yīng)該知道這類小鎮(zhèn)。國道旁的某條岔路,路盡頭的某個(gè)工業(yè)區(qū),一座擁有五間放映廳的電影院,方圓一英里內(nèi)大大小小上百間酒吧。大西洋近在咫尺,海岸線蜿蜒參差,海岬上海鷗肆虐。盛夏的傍晚,星羅棋布的牧場上彌漫著肥料的氣味,牛群悠閑地抬起頭,望著小伙子們駕著裝有V8引擎的汽車呼嘯而過,你追我趕地疾馳在鄉(xiāng)間小道上。
我是個(gè)年輕人。鎮(zhèn)上的年輕人不多,但這里是我們的天下。
今天是星期天,為期三天的懺悔節(jié)已經(jīng)臨近尾聲。星期天是凈化心靈、悔過自新的日子。你應(yīng)當(dāng)為自己犯下的過錯(cuò)痛心疾首,并發(fā)誓不再重蹈覆轍。這是一個(gè)還沒日出你就盼望著日落的日子。
雖然已經(jīng)過了晚上八點(diǎn),天依然很亮,溫煦的光線里蘊(yùn)含著愛爾蘭西海岸七月傍晚的動人憂傷。我和塔格·坎尼夫坐在多克里酒吧的露天吸煙區(qū)。這里是酒吧的后院,地方不大,鋪著水泥地面,俯瞰流經(jīng)鎮(zhèn)上的小河。飛蟲在我們的頭頂飛舞。上方是懸臂撐起的帆布頂篷,鮮艷的糖果色條紋;微風(fēng)拂過,篷布如船帆般蕩漾。
我們臨河而坐,潺潺水聲讓人心曠神怡。周圍坐了十幾個(gè)人。這些人我們都認(rèn)得,至少是眼熟;他們也認(rèn)得我們。許多人對塔格敬而遠(yuǎn)之,在背后管他叫“巨嬰”。他身高體壯,性情乖戾,動不動就大發(fā)脾氣。他定時(shí)服用鎮(zhèn)定劑,不過偶爾出于逆反心理或是盲目自信,他會故意不吃藥。有時(shí)他會告訴我,還把省下的藥賣給我,有時(shí)他干脆只字不提。
塔格異于常人。他來自一個(gè)被悲傷籠罩的家庭,自己也仿佛鬼魂附體。他的本名叫布倫丹,是坎尼夫家第二個(gè)名叫布倫丹的男孩。他的母親在塔格之前曾生過一胎,那個(gè)嬰兒只活了十三個(gè)月便夭折了。后來塔格出生了。四歲那年,他們第一次帶他去格蘭貝公墓。他們在一塊孤零零的藍(lán)色墓碑前放下一束花,墓碑上斑駁的鍍金字母刻下的正是他的名字。
我此時(shí)仍宿醉未消,而塔格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他滴酒不沾,這無疑是件好事。我端著一杯啤酒慢條斯理地喝著,酒里的氣泡已經(jīng)跑光了。
“頭還暈嗎,吉米?”塔格用刺耳的嗓音大聲問。
他的心情不錯(cuò)。非常、非常不錯(cuò),卻也非常、非常亢奮。
“還有點(diǎn)兒懵。”我承認(rèn)。
“星期五你去了奎利南酒吧?”
“奎利南,”我說,“然后是牧羊人,然后是凡丹戈。星期六又從頭來了一遍。”
“帶了哪個(gè)女伴?”他問。
“馬琳·戴維。”
“我的天,”塔格說,“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他用舌頭舔著后槽牙。
塔格今年二十四,我二十五,但他看上去比我老十歲。據(jù)我所知,他還是處男。記得上學(xué)那會兒,教會女校的姑娘和保姆都用愛慕的眼神望著塔格。他從小到大一直是個(gè)英俊的男孩,但從十六歲開始發(fā)胖,之后就再沒瘦下去。渾身的肥肉帶給他一種陰郁的氣質(zhì),即便是日常的坐立行走也令他疲憊不堪。他喜歡把頭剃光,穿深色的寬松衣服,把自己打扮成《現(xiàn)代啟示錄》里白蘭度的模樣。
“好吧,我和馬琳是青梅竹馬。”我說。
這是實(shí)話。在我交往過的女孩當(dāng)中,馬琳最接近真正意義上的女友。就算我們從未兩情相悅,卻也從未疏遠(yuǎn)過,即使去年馬克·卡卡蘭讓她懷孕之后也依然如此。圣誕節(jié)之后,她把孩子生了下來,是個(gè)男孩,取名為大衛(wèi),以紀(jì)念她過世的父親。
星期五我在凡丹戈酒吧遇見了她。酒吧里還是平常那幫人。穿超短裙的姑娘蹬著細(xì)高跟鞋,披著爆炸式鬈發(fā),裸露的前胸和肩頸用皮膚噴霧劑染成紅褐色。脖子粗得像驢的小伙子穿著桌布圖案的格子襯衫,農(nóng)場的小子把袖口挽過胳膊肘,似乎隨時(shí)準(zhǔn)備被叫回家,把初生的小牛從母牛熱氣騰騰的陰道里拽出來。凡丹戈儼然一個(gè)大蒸籠。霓虹燈旋轉(zhuǎn)閃爍,干冰煙霧氤氳,情欲激蕩的低音震顫著無窗的四壁。我和德西埃·羅伯茨坐在吧臺前,一杯接一杯地灌著烈酒。這時(shí)她步入我的視野。其實(shí)她早就看見我了,只是在周圍游弋了一陣才走過來。我們心照不宣地笑了笑,對即將發(fā)生的事心知肚明。
這份默契讓我感到安心,雖然我也不明白它何以如此長久。
馬琳和她的母親安吉住在一起。安吉是個(gè)隨和、務(wù)實(shí)的女人。她常常凌晨三點(diǎn)不睡覺,坐在廚房餐桌前,一邊翻閱電視雜志,一邊小口啜著涼茶。她見到我很高興,給水壺接滿水,問我們要不要喝茶。我們說不必了。她說小大衛(wèi)在樓上睡著了,注意別吵醒他。一進(jìn)馬琳的臥室,我就趴在涼爽的羽絨被上。她童年時(shí)代收藏的毛絨玩具全堆在床尾。我試著回憶每一只長著紐扣眼睛的小豬或兔子的名字,馬琳把我的褲子褪到了腳踝處。
“布普西,溫妮,弗蘭普斯……魯珀特?”
我的小腿毫無亮點(diǎn),幾條蒼白羸弱的肌肉,卷曲叢生的黑毛。每次照鏡子,這些丑陋的腿毛都讓我厭惡難當(dāng)。馬琳的手指卻溫柔地揉捏起這些腿毛。她慢慢往上摸到我的大腿,低聲說:“翻過來。”當(dāng)一個(gè)姑娘面對如此煞風(fēng)景的小腿還愿意騎到你身上的時(shí)候,你必須心存感激。
“她是個(gè)好姑娘。”塔格說。
一只蒼蠅落在他的光頭上,在發(fā)茬間亂轉(zhuǎn)。塔格似乎沒有覺察到,我卻忍不住想伸手。
“沒錯(cuò)。”我喝了一小口啤酒,淡淡地說。
話音未落,馬琳就推開酒吧的雙開門,走了進(jìn)來。在小鎮(zhèn)上這種事時(shí)有發(fā)生:你剛念叨起誰的名字,嘭!那人就出現(xiàn)了。她穿著毛邊牛仔短褲,墨鏡架在紅色鬈發(fā)上,正津津有味地舔一支冰激凌甜筒。她穿了一件淺黃色的露臍衫,恰到好處地展現(xiàn)出產(chǎn)后通過有氧運(yùn)動恢復(fù)的健美腰肢。一個(gè)日冕文身環(huán)繞著她的肚臍。她天生一雙碧眼,如果不是臉上粉刺瘢痕密布,她完全算得上一個(gè)美人。我的馬琳。
馬克·卡卡蘭跟在她的身后。馬琳見到我,朝我努了努下巴,算是打招呼。她的神色中頗有幾分無奈,因?yàn)樗纳磉呌锌ㄌm,而我的身邊有“巨嬰”塔格·坎尼夫。
“馬琳來了。”塔格說。
“嗯——哼。”
“她真的跟那個(gè)卡卡蘭在一起了?”
我聳了聳肩。既然他倆已經(jīng)生了孩子,出雙入對自然也很正常。順理成章的事兒。我告訴自己,無論她想和卡卡蘭干什么或是不干什么,都與我無關(guān)。我還告訴自己,如果一定要對這事有所看法,我應(yīng)該向這個(gè)伙計(jì)表示感謝,因?yàn)樗嫖覔醯粢活w意外淪為人父的子彈。
“最近她打扮得很性感,”塔格說,“你不過去打個(gè)招呼?”
“星期五晚上我已經(jīng)招呼夠了。”
“最好別惹麻煩。”塔格說。
我的手掌滑到酒杯上沿,蓋住杯口,手指輕敲著杯壁。
“你聽說克蘭西家孩子的新消息了嗎?”短暫的沉默后,塔格說。
“沒有。”我說。
“恩尼斯科西有個(gè)農(nóng)夫說,他見過一個(gè)男孩,長相與克蘭西家孩子相符。他還看見——聽好了——兩個(gè)女人,兩個(gè)三十多歲的女人。她們在農(nóng)夫家附近的小餐館吃飯。他和其中一個(gè)女人說過話。聽好了,據(jù)農(nóng)夫的判斷,她是——德國人。當(dāng)時(shí)她們問他,不對,是她問他羅斯萊爾渡口的下一班輪渡幾點(diǎn)?她說話帶著德國口音。她們身邊有個(gè)金發(fā)男孩,一個(gè)安靜的金發(fā)男孩。那是幾星期前的事了。農(nóng)夫到現(xiàn)在才把兩件事聯(lián)系起來。”
“德國口音。”我說。
“沒錯(cuò),沒錯(cuò)。”塔格說。
他的眉毛興奮地抖動著。塔格對克蘭西家孩子的事幾乎著了魔,但普通大眾對此事的熱情已消磨殆盡。韋恩·克蘭西,十歲,梅奧郡哥特拉波教區(qū)的小學(xué)生,三個(gè)月前失蹤。當(dāng)時(shí)他去都柏林參加學(xué)校旅行。前一分鐘他還跟兩名老師和其他同學(xué)站在市中心繁忙的三岔路口——紅燈亮起,汽車止步,男孩女孩們簇?fù)碇^了馬路——下一分鐘他就不見了。最開始大家還以為小韋恩只是走散了,迷失在大都市的人流中,但人們很快意識到:他并非迷路,而是失蹤了。整個(gè)五月,他失蹤的新聞?wù)紦?jù)了國家各大報(bào)紙的頭版。大眾的猜測是韋恩在那個(gè)三岔路口被陌生人拐走了。警察廳發(fā)動了全國搜尋,孩子的父母也在鏡頭前含淚哀求……結(jié)果一無所獲,到今天依然杳無音信。孩子沒找到,尸體沒找到,連一條可靠的線索也沒有。哥特拉波離我們鎮(zhèn)很近,所以最初每個(gè)人都密切關(guān)注事情的發(fā)展。但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我們漸漸把這件事淡忘。
塔格卻拒絕忘記克蘭西家的孩子。他忍不住為這個(gè)沒有結(jié)局的故事提供各種離奇的解釋。在他想象的土壤中,一個(gè)接一個(gè)“假如……呢?”像黑色花朵一般競相綻放。他獨(dú)自一人的時(shí)候會整晚琢磨那些填滿石灰的無名墳?zāi)埂⒇溬u兒童的跨國組織、地下人體器官交易、邪教崇拜。
我對他說,別再想了。
“她們可能是同性戀,”塔格說,“德國女同性戀。你知道,她們生不了孩子。不準(zhǔn)人工授精,也不準(zhǔn)領(lǐng)養(yǎng)。也許她們已經(jīng)別無選擇。”
“也許吧。”我說。
“克蘭西家的孩子看上去像雅利安人。你知道嗎?金頭發(fā),藍(lán)眼睛。”塔格說。
“每個(gè)孩子看上去都像雅利安人。”我不耐煩地說。
馬琳旁若無人的大笑響徹了整個(gè)后院。她和卡卡蘭剛在一張四人桌前坐下,同桌的也是一對兒:斯蒂芬·加拉赫和康妮·里普。卡卡蘭又高又瘦,一副營養(yǎng)不良的樣子,跟我一個(gè)德行。看來馬琳就喜歡這種類型。她此刻正為了加拉赫說的什么話哈哈大笑。同桌的其他人,包括加拉赫,都不免尷尬,但馬琳仍笑個(gè)不停,還連連拍打加拉赫的肩膀,像在求他別那么幽默。
“但對那個(gè)孩子來說,那并不是最壞的結(jié)果。甚至連‘結(jié)果’也說不上。”塔格說。
酒吧侍者推門進(jìn)來,她手里的托盤上擺了四杯香檳。馬琳揮手召她過去,把酒杯一一遞給同伴;每只酒杯的杯口嵌著一顆草莓。卡卡蘭付了錢。馬琳把包甜筒的餐巾紙放在桌上,我注意到她無名指上戒指的閃光。
“我說得對不對?”塔格說。
他探過身,用肥厚的手抓住我的小臂搖晃起來。
“太他媽的對了,塔格。”我說。
我話里的火氣讓他眉頭一皺。其實(shí)我想說的是:我還有別的事要操心,塔格,我沒心思聽你沒完沒了的嘮叨。
“哦。”塔格說。
他把手縮回去,插在腋下,像是手指被門夾了一下。
“你的心情不好,是因?yàn)椤彼h(huán)視四周,抽了抽鼻子,“因?yàn)轳R琳。那個(gè)淫蕩的婊子馬琳。”
我不悅地彈了一下舌頭,朝他豎起了中指。
“我想跟誰滾床單是我的事,塔格,輪不到你說三道四。”
他往后一靠,整個(gè)人似乎大了一圈。
“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想說誰就說誰。”
“你他媽還真是個(gè)巨嬰!”
塔格握住桌子的邊緣。我感到桌面在顫動,然后它升了起來,杯墊紛紛滑落。我連忙抓起酒杯,后仰著躲閃。塔格猛地一掀,桌子翻過來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周圍的人驚叫著跳起來。
我兩條腿先后落地,不緊不慢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兩眼始終與塔格對視。他噘著嘴,似笑非笑,呼吸急促而粗重。
“對不起,塔格。”我說。
他的鼻孔劇烈地翕動了幾下,慢慢平靜下來。
“沒關(guān)系,”他說,“沒關(guān)系。”
他用一只手摸著自己凹凸起伏的光頭,面帶疑惑地看著四腳朝天的桌子,好像這事跟他毫無關(guān)系。
“好了,”我說,“走吧。”
我喝光殘酒,把空酒杯放在鄰桌上。
我跟在塔格身后往外走,人們忙不迭地讓到兩旁。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巨嬰又發(fā)瘋了。巨嬰又出洋相了。怪胎巨嬰和他的怪胎兄弟吉米·德弗盧。
“嗨,馬琳!”路過馬琳那桌時(shí),塔格歡快地打起招呼。
馬琳如往常一樣淡定。她身邊的卡卡蘭一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樣子,生怕引火上身。
“你好,大塊頭兒。”馬琳說。
她看了看我。
“還有小塊頭兒。”
“我是不是該說聲恭喜?”我說。
我托起她的左手,拉直她的手指細(xì)細(xì)打量起來。馬琳把手縮回去,用右手遮住。
“晚了,”我笑道,“我已經(jīng)看見了。挺像樣兒的一塊石頭。”
“是的。”卡卡蘭說。
“真不賴。”塔格說。
我感覺到他碩大的身影從我的身后移到側(cè)面,只等我一句話就要大打出手。
馬琳下嘴唇朝上動了動。她死死地盯著我,眼神分明在說:“你小心點(diǎn)兒。”
“吉米,我現(xiàn)在很開心,”她說,“請你滾蛋。”
出了多克里酒吧,殘陽似血,天邊泛起紅色與粉色交織的晚霞。微風(fēng)中生出一絲寒意。碎玻璃像石子一樣在鞋底咯吱作響。路邊停了一排車,其中有一輛小巧的掀背車,銀色的漆已經(jīng)褪色——正是卡卡蘭的車。它光溜溜地騎在路肩上,仿佛是對后者的一種侮辱。擋風(fēng)玻璃內(nèi)側(cè)貼了一張皺巴巴的“L”形貼紙。
“看這破爛樣兒。”我說。
我用手掌猛拍了一下坑坑洼洼的車頂。
塔格不解地看著我。
“這是卡卡蘭的車。”我說。
“這玩意兒就是個(gè)飯盒。”塔格說完,笑了起來。
“開著這玩意兒帶著未婚妻到處跑,他還真是可憐。”我說。
“可憐,可憐,可憐。”塔格連連點(diǎn)頭。
“塔格,你今天是不是沒吃藥?”我說。
“吃了。”他咕噥道。
他把一只大手平攤在車頂上,嘗試把車左右晃動。車底的彈簧嘎吱直響。塔格向來不善于撒謊,他的身高體重意味著他不需要這種技能。只要你的塊頭足夠大,你就可以口無遮攔。
“你要能把這玩意兒翻過來就牛逼了。”我說。
“小意思。”塔格說。
他晃啊晃啊,車身的擺幅越來越大,整個(gè)骨架嘎吱亂響。路肩的外側(cè)比路面低了幾公分,因此車身略微向外傾斜,也算幫了塔格一個(gè)小忙。當(dāng)車身擺動到臨界點(diǎn)時(shí),塔格彎腰托住車的底盤,用盡全力將它掀起來。這一側(cè)的車輪離開了路肩。一瞬間,這輛車仿佛金雞獨(dú)立,我看見底盤之下縱橫交錯(cuò)的烏黑管道。塔格往前一推,伴隨著刺耳的摩擦碎裂聲,車翻了個(gè)底朝天。車窗全碎了,亮閃閃的玻璃碴濺了一地。車輪在半空顫抖著。塔格伸出手,穩(wěn)住自己面前的車輪。
“好樣的,大個(gè)子。”
塔格喘著粗氣,臉漲得通紅。他聳了聳肩。一輛車從街上駛過。幾個(gè)孩子把臉貼在后窗上,爭相觀看這輛底朝天的掀背車。一個(gè)老頭從酒吧里踱出來。他把破舊的平頂卷邊帽扣在顫巍巍的頭上,然后摘下來又重新戴好。松垮垮的領(lǐng)結(jié)撲打著他皺紋密布的紅臉。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
“還好嗎?”他說。
“好極了。”塔格說。
老頭向我們揮了揮手,從翻倒的車旁走過,完全對它視而不見。
我低頭看了一眼,一只棕色皮手袋在破碎的車窗邊半掩半露。手袋里的東西散落在路邊陰溝里,有紙巾、硬幣、糖紙團(tuán)、圓珠筆、購物小票、一支滾珠式腋下除汗劑、一支黑筒鑲金邊的口紅。我把口紅撿起來,揭開蓋子,然后在副駕一側(cè)的車門上用鮮紅的大寫字母寫下了我的請求:
嫁給我
“我靠,”塔格說,然后咔嗒一聲合了一下嘴,“牛逼,吉米。”
我聳聳肩,把口紅塞進(jìn)兜里。我把其他東西撿起來放回手袋。然后我把手伸進(jìn)車窗,將手袋塞在副駕位的地墊下面。
“去你家吧,大個(gè)子?”我說。
“走。”塔格說。
塔格和他媽住在河對岸的法羅山小區(qū)。和馬琳家一樣,他爸也死了,在墓地里已經(jīng)躺了十年。一次谷倉失火,老坎尼夫在吆喝馬駒的時(shí)候心臟病發(fā)作。塔格他媽從此沉溺于酒精之中。她終日躺在彈簧外露的舊沙發(fā)上,小口喝著杜松子酒,眼睛盯著電視,眼前浮現(xiàn)出死去的家人。你和她打招呼,她會和藹地笑笑,但笑容里充滿了迷惑——她多半不知道你是電視劇里的人物,還是從記憶里走出的幻影,抑或一個(gè)站在面前的真人。有時(shí)她會把我喚作塔格或者布倫丹,卻把塔格叫成吉米。她也會用塔格父親的名字叫他。塔格說沒必要糾正她,反正她已經(jīng)離老年癡呆不遠(yuǎn)了。
我們在卡塞蒂食品店買了些吃的,嚼著薯片踏上河邊的拉纖道。纖細(xì)的蘆葦相互摩擦,輕快的聲響仿佛出自新磨的刀片。岸邊潮濕的石塊黝黑如炭,在水藻叢生的河床上閃閃發(fā)亮。淤泥中淹埋著壓扁的啤酒罐:強(qiáng)弓、荷蘭黃金、卡帕雷克……儼然出土文物。一群群的蚊蚋在空中飛舞,我們經(jīng)過時(shí)它們趁機(jī)飽餐一頓。
上游不遠(yuǎn)處橫著一座木橋。
那座橋已經(jīng)被封禁了。今年春天,一棵大樹被洪水裹挾而下,撞在橋身上,至今依然卡在原地,遒勁的樹干以四十五度角斜倚在破裂的橋身和折斷的欄桿上。木橋的中段往下凹陷,但尚未垮塌。鎮(zhèn)議會沒有清理大樹、修復(fù)木橋,而是在橋兩端各立起一層薄薄的鐵絲網(wǎng),并張貼了措辭嚴(yán)厲的警示牌:擅自上橋者將被處以罰款,如有死傷后果自負(fù)。
鐵絲網(wǎng)已經(jīng)被踩倒了,因?yàn)檫@座橋是通往法羅山的近路。盡管鎮(zhèn)議會明令禁止,像塔格這樣的居民還是經(jīng)常通過這座橋進(jìn)城出城。
快到橋頭的時(shí)候,我們看見三個(gè)孩子在那里玩耍:兩個(gè)小女孩和一個(gè)稍大一點(diǎn)的男孩。女孩看樣子五歲或六歲,男孩九歲或十歲。
男孩長著白色的頭發(fā)——不是金黃色,而是白色。他穿著舊得發(fā)灰的棉背心和亮紫色的運(yùn)動褲,一條褲腿挽到了膝蓋處。兩個(gè)女孩都穿著臟兮兮的粉色T恤和短褲。
男孩的臉上涂著酷似印第安人的油彩——兩眼下面各用拇指抹了一道紅白相間的顏料,加上鼻梁上一道豎直的黑線。他手持一根鋁桿,可能原本是窗簾軌、拐杖,或者漁網(wǎng)架。桿子的一頭被壓尖了。
“你是什么人?印第安人嗎?”塔格問他。
“我是國王!”男孩冷笑道。
“這是什么兵器?槍,還是劍?”我說。
“這是長矛。”他說。
他踏著匍匐在地的鐵絲網(wǎng)走過來,縱身跳上拉纖道。接著他耍了一套武術(shù):先是抄起鋁桿空劈,然后舉過頭頂轉(zhuǎn)了幾圈,再熟練地?fù)Q手。結(jié)束動作是單膝跪地,抖動的桿頭尖端直指塔格的胸部。
“這是我的橋。”他咬牙切齒地說。
“我們想過橋,怎么辦?”塔格說。
“如果我不放行,你們休想過去。”
塔格把皺巴巴的半包薯片遞過去。
“我們可以付過路費(fèi)。國王,來點(diǎn)兒薯片?”
男孩把手伸進(jìn)包裝袋,抓起一大把彌漫著醋味的薯片。他仔細(xì)瞧了瞧手里的薯片,又聞了聞,然后分成兩份遞給兩個(gè)女孩。女孩們把薯片一片接一片地放進(jìn)嘴里,嚼得飛快。她們仰起頭做出艱難吞咽的動作,活像一對雛鳥。
“小鳥真乖。”男孩拍了拍女孩們的腦袋。
她們對視了一眼,咯咯笑起來。
“你們不該吃陌生人給的東西。”塔格說。
“薯片是我給她們的。”男孩用長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你們過橋干什么?”
“我們?nèi)フ胰恕U乙粋€(gè)男孩。一個(gè)金發(fā)男孩。”塔格說,“他長得有點(diǎn)兒像你。離家出走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兒。”
男孩皺起眉頭。他退到鐵絲網(wǎng)上,望了一眼蜿蜒的河道。
“他沒到這兒來。”他最后說,“要不我肯定會看見他。我是國王。我什么都看得見。”
“好吧,但我們總得試試。”塔格說。
放手吧,塔格——我想說卻沒能說出口。有時(shí)真正的友情莫過于此:即便你如鯁在喉,也依然緘口不言。
我回頭望了一眼來路。山丘的盡頭是公路,再遠(yuǎn)一些是低矮殘破的小鎮(zhèn)剪影。我隱約聽見騷動和叫喊——也許只有我聽得見。我想象馬克·卡卡蘭站在多克里酒吧的門口,沖著底朝天的汽車暴跳如雷。馬琳站在他身邊,雙臂交叉在胸前。我?guī)缀跄芸辞逅谋砬椋辞逅M長眼睛里的綠色微光,和她的嘴角勾勒出的一絲笑意。她嘴唇的顏色與我留在車門上的字母交相輝映。我從口袋里摸出那支口紅,遞給一個(gè)女孩。
“另一件禮物。”我說,“好了,我們走吧,塔格。”
塔格從男孩身邊走過。男孩端起鋁桿,把尖端捅向塔格的肚子。塔格握住桿頭,把它擰向自己。他假裝大口喘氣,手在空中亂抓。
“你殺死我了。”他大叫。
他后退兩步,搖搖晃晃地跪倒在地,然后向前撲倒在草地上,像個(gè)五體投地的祈禱者。
“你把他殺了。”我說。
我用腳尖輕踢了一下塔格的肋部。他軟塌塌地跟著動了動。男孩走過來,學(xué)著我的樣子踢了一下塔格的肩膀。女孩們不再作聲。
“你準(zhǔn)備怎么向你媽解釋?”我說。
男孩努力噘著嘴,眼淚還是不聽話地往上涌。
“哎呀,他快要哭了。”我說。
心軟的塔格裝不下去了。他嘴里呼呼兩聲,壞笑著抬起頭。他看著男孩,爬了起來。
“別哭了,小家伙,”他說,“剛才我死了,現(xiàn)在我又活過來了。”
他邁著沉重的腳步,越過鐵絲網(wǎng)上了橋。我緊隨其后。
“國王,再見!”塔格大喊。
我從男孩身邊經(jīng)過的時(shí)候,他惱怒地看著我們,雙臂交叉在胸前,鋁桿搭在肩頭。
“如果你們掉進(jìn)河里,我可救不了。”他警告道。
木橋在我們腳下嘎吱作響。到了橋中央,那棵大樹扭曲的枝椏如同女巫的手指伸向我們的臉。我們必須壓低或撥開樹枝才能前行。
“再跟我說說,塔格。”我說。
“說什么?”
“說說克蘭西家孩子的事。說說那兩個(gè)德國女同性戀。”
于是塔格開口大談自己的猜想。其實(shí)我并沒有聽,但這也無關(guān)緊要。在他喋喋不休之際,我望著他的光頭隨腳步高低起伏,望著他頭上的凸起與凹陷。他肥厚的脖子上深深的皺褶在我的眼里幻化成一張沒有嘴的鬼臉,他左右搖擺的肩膀雄偉如山。我想起克蘭西家孩子的那張照片——塔格從星期日報(bào)紙上剪下來,貼在臥室的軟木板上。就是那張廣為流傳的照片,一張生日聚會的剪影:他長滿金發(fā)的頭上緊扣著一頂皺紋紙壽星帽;他開懷大笑,露出兩顆日后讓人心碎的虎牙;他的雙眼睜得大大的,似乎迷失在那個(gè)幸福的瞬間。我想起了馬琳。我想起了她的孩子。一念之差,那會是我的孩子。我想起她肚臍周圍的日晷文身,想起她緊致的小腹——我可以讓她躺下,看著硬幣從她的小腹上彈起。我們終究都有自己無法放手的事。
殘破的橋身在我們的腳下不住地震顫、嗚咽。等我們到了對岸,踏上堅(jiān)實(shí)土地的那一刻,一陣莫名的感激從我心底涌起。我伸手拍了拍塔格的肩膀,然后轉(zhuǎn)過身,準(zhǔn)備揮別那位年幼的國王和他愛笑的女仆。當(dāng)我的目光越過黝黑的湍流時(shí),我發(fā)現(xiàn)那幾個(gè)孩子已經(jīng)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