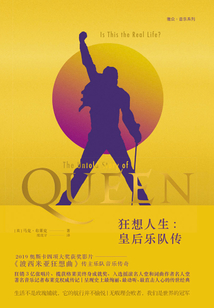
狂想人生:皇后樂隊傳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美麗的人們
你跟那個死基佬講,這將是有史以來最牛逼的事情。
——鮑勃·格爾多夫說服皇后樂隊
參加“拯救生命”(Live Aid)援助非洲大型慈善
搖滾演唱會
你好,世界!
——“拯救生命”溫布利球場現場,觀眾打出的橫幅
我必須要贏得觀眾的心,這是我的責任。那完全是一種掌控的感覺。
——弗雷迪·莫庫里,1985年
1985年7月13日,正值老牌搖滾明星們日子不太好過的時期。他們很多成名于六七十年代,眼下靠往日的輝煌和粉絲的非理智崇拜度日。因為世界上還沒有搖滾明星退休這種事,彼得·湯申德[1]年輕時的使命宣言“希望我在變老前死去”就顯得十分應景了。
這一天,“拯救生命”大型搖滾演唱會在美國費城和英國倫敦同時舉辦,各個年代的樂手們齊聚一堂。演出的共同目標是為埃塞俄比亞的饑荒賑災籌集善款,但實際上還有另一層意義:僅在倫敦溫布利球場就聚集超過8萬觀眾,全球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電視直播,無論演出好壞,都有超過4億人實時見證。在觀眾捐款總計1.5億英鎊以幫助非洲饑民的同時,表演者們或許會成就美名,也可能顏面盡失。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全球觀眾將看到準備不夠充分的鮑勃·迪倫、未能激起人群熱情的齊柏林飛艇樂隊[2],以及宛如兩只孔雀抖動尾羽般爭奇斗艷的米克·賈格爾和大衛·鮑伊。[3]“拯救生命”將成為彼時還是新人的麥當娜、U2樂隊職業生涯中的關鍵時刻,但對亞當·安特、霍華德·瓊斯或湯普森雙子樂隊[4]的青史留名就沒什么幫助了。即使是對當時極受追捧、已拿到多個白金唱片銷量的恐怖海峽樂隊[5]和菲爾·柯林斯來說,也不會有比這更大的盛事了。
群英薈萃的演出陣容中,有一支成立至今已有十四個年頭的搖滾樂隊。樂隊的成員都是千萬富翁(作為全英國賺得最多的公司董事,載入1982年吉尼斯世界紀錄),他們已經拿下數量多到令人生畏的金曲和熱門唱片,其風格不斷變化,包含搖滾、流行、放克、重金屬等等,甚至還有福音音樂。雖然有超凡的現場演出名聲在前,但就算是他們最死忠的粉絲也預料不到今天會發生什么。
下午6點44分,樂隊上場前,由喜劇明星梅爾·史密斯和格里夫·瑞思·瓊斯串場報幕。史密斯扮成一個打官腔的警官,瓊斯扮成他的倒霉搭檔。相聲很簡單,官方對“屁民”,兩人的段子——“有人跟我們抱怨(這場演出)噪聲太大了……這位女士住在比利時”——有助于活躍觀眾氣氛,不過他們幾乎被身后演出的工作人員最后調試設備的聲音淹沒了。終于,史密斯摘下警帽夾在腋下,站好立正,像行禮一樣有請“女王陛下……皇后樂隊!”。
事后采訪時,“拯救生命”的組織者鮑勃·格爾多夫會試圖去描述這四個天賦異稟的人。在“拯救生命”的舞臺上,正如格爾多夫所說,他們看起來“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不像搖滾樂隊的樣子”。
約翰·迪肯(格爾多夫稱他為“緘默的貝斯手”)讓自己站在舞臺的后部,靠近鼓臺的地方。盡管頂著明星才會有的一頭蓬松卷發造型,他看起來似乎更像本來要成為的電子工程師——假如沒搞音樂的話。那天早些時候,參加演出的樂隊站成一排與前來觀看“拯救生命”的王室成員威爾士親王和王妃[6]見面,電視機前成千上萬的皇后樂隊粉絲很困惑,為什么本該站著約翰·迪肯的地方,卻站著一個可能是他們巡演工作人員的路人。“我太靦腆了,不敢去見戴安娜王妃。我覺得我要出丑的。”他后來承認,確實是派了自己的工作人員斯派德代班。
布萊恩·梅,他那又瘦又高、微微駝背的“祈禱的螳螂”體格和濃密卷曲的黑發(“嬉皮士吉他手”,格爾多夫說),似乎從樂隊創立起就沒有變過。梅的搖滾吉他英雄形象下帶著一股自然而然的學術氣質,對于這位理科學士、曾經的數學老師來說,吉他演奏是一項嚴肅的工作。年輕的時候,他會像個網球運動員爭取賽末點一樣,在專注的時候對自己低聲碎念。
與此同時,你可能會想,羅杰·泰勒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堆架子鼓后面度過,他是否會感到沮喪呢?擁有那么漂亮的金發和秀美的容顏(為此他曾經留過胡子為了不讓別人再誤會他是美女),私底下喜歡開跑車和泡模特,泰勒無疑是樂隊里最像明星的人了。最近幾年,他的低音大鼓鼓皮上印著一張自己的臉部特寫,即使你買最便宜的座位都不會錯過此場景。雖然泰勒本人經常坐在鼓的后面不被看到,但他卻不可能不被聽到:他那獨特的、沙啞而高亢的伴唱是構成皇后樂隊聲音的重要元素。
不過,無論三位隊友在接下來的二十二分鐘里做什么,那位被格爾多夫稱為“驚世駭俗的主唱”的弗雷迪·莫庫里都將成為全場的中心。最初,莫庫里曾是一朵華麗搖滾的繁箋花,現在卻大大不同。他剪短的黑發光亮服帖地梳往腦后,曾經由桑德拉·羅德斯[7]為他設計的飄逸綢緞戲服,換成了簡單的白背心和緊身的淺白色牛仔褲。
多年來每次談到性取向時,莫庫里總是和媒體捉迷藏,但這時他的形象顯然是美國同性戀圈流行的“卡斯特羅款”造型。點睛之筆還包括箍在右手上臂的一個鉚釘臂環,以及標志性的上唇一字胡須——幾乎正好掩蓋了他稍微突出的牙齒。莫庫里輕快地跑步上臺,略顯夸張的步態仿佛是一位正在追趕公交車的芭蕾舞者。
也許放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音樂行業大咖或真人秀評委很難理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個三十八歲中年男人作為世界級巨星的概念。然而,在未來的很多年里,莫庫里都擁有著超越時代的、與現在的后起之秀們旗鼓相當的共同點。在“拯救生命”發生的許多年前,那個懷著音樂夢想的藝術生,原名弗羅可·保薩拉的年輕人就告訴任何愿意傾聽的人,他“總有一天會當明星”。當時幾乎沒人相信他。
盡管樂隊一直保有堅定不移的自信,他們還是清醒地認識到,這次來的觀眾并不都是他們的樂迷。于是,一些同行采取的草率做法就不是他們的行事方式了。他們進行了四天的密集強化排練,按每個樂隊只有二十分鐘的設定充分利用到最后一秒,并且精心挑選歌曲,以獲得最大的沖擊效果。上場快速地巡視一圈之后,弗雷迪·莫庫里坐到了舞臺左邊的鋼琴前面。他彈出《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前奏,觀眾立刻沸騰了——還有比這更適合開場的嗎?——他的雙手花哨地交叉,彈出曲調中的兩個高音。第一句歌詞剛剛吐出,觀眾再次熱烈地和聲回應。盡管鋼琴上并未裝飾著燭臺,而是擺放著印有百事商標的紙杯和裝著淡啤酒的塑料杯,但也不會破壞這首歌曲中那豐富的戲劇氛圍。無所畏懼且處于巔峰狀態的弗雷迪,一開口就把這首歌推到了極致,如同傳遞一個讓世界震顫的重要訊息。今天,“拯救生命”將屬于皇后樂隊。
其他樂隊成員也加入進來,伴隨著梅的巴洛克式華麗吉他獨奏,毫無預兆地,莫庫里突然站起,《波西米亞狂想曲》在第一個漸進高潮、激起的熱情還未消退時故意中斷。
弗雷迪的巡演工作人員彼得·辛斯進入視野,將主唱那具有高度辨識性的道具遞給他——帶有半截麥克風棍子的話筒。莫庫里沿著舞臺邊緣踱步,揮舞著拳頭,噘著嘴,高昂著頭。在他身后,泰勒打出了《收音機嘎嘎》(Radio Ga Ga)的鼓點前奏,這是皇后樂隊去年排名第二的金曲。它的配樂使用了時下流行的合成器和電子節拍器,正好和純樂器的《波西米亞狂想曲》相反。
這首歌的歌詞表達的是對當下收音機電臺現狀的不平,以朗朗上口的副歌潤色。它的宣傳視頻借鑒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科幻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的場景,對歌曲銷售幫助不小。此刻,第一段副歌響起時,觀眾模仿著視頻中的場景,成千上萬的手臂在頭頂翻飛,整齊地擊掌。“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那樣的場景。”布萊恩·梅后來感慨道。
從這段起,樂隊已然逆天。莫庫里開始了他的觀眾調教,變換著調子和觀眾進行了一唱一應的對歌,然后接入下一首《一錘定音》(Hammer to Fall)。一首也算是金曲的歌,具有畫面感的重金屬風格就是為溫布利這樣的大體育場而準備的。布萊恩·梅明顯放松了不少,他揮手掃弦;莫庫里此時直接與臺上的攝影師玩起來了,他摟著攝影師轉動還對著鏡頭扮鬼臉,之后又繞著吉他手走動,像斗牛士在挑逗公牛。過一會兒,梅滑步移開后,莫庫里對著觀眾面露壞笑,套弄起麥克風來,現在這玩意正擱在他的胯部位置。
看起來,弗雷迪更像一個淘氣的高中男生,而不是健壯的搖滾巨星,他眼中閃爍著調皮的光芒,表明他并沒有真的把自己和這些玩鬧當回事。“拯救生命”肩負著重要使命,但很多明星的隨意表演導致今天的溫布利球場出現不少令人皺眉的時刻。然而,似乎在皇后樂隊表演時卻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們明白,‘拯救生命’其實就是一個全球點唱機,”格爾多夫說,“而且那位弗雷迪可會當著全世界的面風騷了。”
舞臺上的皇后樂隊可能已經品嘗到勝利的滋味,但幕后卻另有故事。他們并沒有參與1984年11月“樂隊援助”[8]慈善單曲的錄制,很多偉大的、優秀的(和不那么優秀的)音樂明星合力做出這張唱片以幫助埃塞俄比亞籌款。“當時我們都散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呢。”莫庫里后來說。現實情況是,那時候他們剛剛結束了在南非太陽城的巡演,這場表演因為政治原因被黑得一塌糊涂,皇后樂隊正處在重啟全球巡演之前閉門療傷的階段。
此外,雖然樂隊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常常會產生錄音室里的靈感碰撞,但到了1985年,用羅杰·泰勒的話說,皇后樂隊已經“審美疲勞”了。鼓手的直白評價“我們樂隊甚至比我們的婚姻都持久”并不能避免這場“婚姻”也有觸礁的時候。畢竟年復一年的巡回演出、音樂創作,以及一直需要的相互包容,是要付出代價的。
皇后樂隊最近的一張專輯《作品》(The Works),恢復了一些在1982年《白熱空間》(Hot Space)后失去的勢頭,后者偏向舞曲且明顯地缺失吉他,算是一張走得太遠的實驗專輯。皇后樂隊的星光有些暗淡,尤其是在美國。當時出現了數不清的問題:與美國唱片廠牌的爭執;缺乏電臺播放推廣;弗雷迪身邊的人帶來的分裂影響;以及單曲《我要掙脫一切》(I Want to Break Free)的宣傳視頻中,皇后樂隊四個人穿女裝出鏡(在英國很受歡迎,在美國卻并非如此)。
梅、泰勒和莫庫里都制作了個人專輯,尤其弗雷迪的首張個人專輯就是在“拯救生命”前兩個月發布的。脫離了被布萊恩·梅稱之為“母艦”的樂隊,他們都還沒能塑造起成功的單飛藝人形象。原本皇后樂隊的計劃是參加完“拯救生命”后就休息,至少五年內不巡演,也有可能再也不演出了。
事后,“拯救生命”的推廣商哈維·高德史密斯公司會慶幸,皇后樂隊沒有要求在某個更晚一點、似乎更壓軸的時間上臺,但其實這是樂隊有意為之的。很多年前,在等待皇后樂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期,布萊恩·梅曾目睹了大衛·鮑伊在舞臺上化身為“Z字星塵”(Ziggy Stardust)的一面,他無比嫉妒,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輪到自己的樂隊打出名頭。后來,皇后樂隊曾和艾爾頓·約翰共用一個管理團隊,爭取著屬于他們的關注度。今晚,鮑伊和艾爾頓都將在皇后樂隊之后表演,給了樂隊先于這兩位出風頭的機會。同時,皇后樂隊選擇在傍晚演出,正是美國早晨同步直播開始的時間。
《一錘定音》后,莫庫里第一次停下來休息片刻。他將一把白色吉他挎上肩頭,向著人群致意:“下一首歌,獻給今晚在此的,美麗的人們。”他告訴觀眾,“意思就是你們所有人。謝謝你們前來,制造了這個偉大的時刻。”
音樂氣氛再次激昂。樂隊已經表演了被布萊恩·梅稱作“偽歌劇”的《波西米亞狂想曲》,電子流行樂《收音機嘎嘎》和重金屬樂《一錘定音》,是時候來一首近似鄉村搖滾風、歡快的1979年金曲《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莫庫里宣稱他是在泡澡時突發靈感寫的這首歌。歌曲結尾處,弗雷迪不再撥彈吉他,他把它取下指向前方,又握著琴頸舉高至背后,逗著觀眾玩,好像他只要不互動就渾身不舒服。
現在進入最后的高潮部分,羅杰·泰勒敲出《我們會震撼你》(We Will Rock You)那鏗鏘又熟悉的鼓點,第一段副歌莫庫里直接拋給觀眾由他們大合唱。早于皇后樂隊一個半小時上臺的U2樂隊曾進行了奪人耳目的表演,但此時有位粉絲的U2橫幅似乎舉得不是地方了。梅以電吉他失真音快速結束《我們會震撼你》,莫庫里已回到鋼琴旁邊。
皇后樂隊的《我們是冠軍》(We Are the Champions)總是能讓最激烈的批評家都無話可說。寫于1977年的這首歌里的那種大無畏情感——更大、更好、更多,還有輸家去死——與當時流行的音樂情緒不一致。那時,唱著頹廢現實生活的年輕一代的朋克樂隊,就是要將皇后樂隊這種類型趕下王位。“拯救生命”的觀眾里,有些人可能在今天之前從來都不算皇后樂隊的粉絲,絲毫沒有在意這種所謂的對立。《我們是冠軍》是一首堪比好萊塢大片的歌曲,就像去年的《終結者》(Terminator)或者一年后的《壯志凌云》(Top Gun),它是一個逃離世俗的幻境。沒有比它更適合結束皇后樂隊演出的曲目了。
大衛·鮑伊、艾爾頓·約翰和保羅·麥卡特尼都將在皇后樂隊喚起的熱潮后進行表演,他們的努力可算是徒勞了。在短短的20分鐘里,這支完美的大型體育場演出級別的搖滾樂隊,展現了從歌劇搖滾到電子流行,從重金屬搖滾到鄉村搖滾再到力量抒情歌曲的全范圍音樂:每一首歌都引起轟鳴,每一首歌都能被立刻辨識且具有過耳不忘的感染力。這場難忘的表演將對樂隊本身產生持久的影響。“‘拯救生命’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劑強心針。”羅杰·泰勒說。所有休息、療養計劃全部擱置,坎坷的“婚姻”似乎回到了正軌。不過,也如弗雷迪·莫庫里所說:“如果你能體會到我獲得的那種成功的美妙,你是不會想很快放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