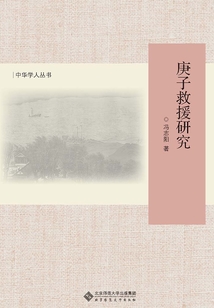
庚子救援研究
最新章節(jié)
- 第16章 中華學(xué)人叢書
- 第15章 后記
- 第14章 附錄五 嚴(yán)復(fù)在《大公報(bào)》上的一則佚函及相關(guān)問題考辨[1]
- 第13章 附錄四 《救濟(jì)日記》
- 第12章 附錄三 三十三名京官籍貫
- 第11章 附錄二 人物小傳
第1章 序
庚子救援是過去研究中甚少論及的一個(gè)題目。志陽自2007年讀博開始,即以此為題,從一點(diǎn)點(diǎn)搜集相關(guān)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個(gè)腳印,把相關(guān)檔案、文獻(xiàn),以及散見于當(dāng)年上海報(bào)刊上的各種有關(guān)救援的公啟、章程、公函、電報(bào)、捐款清單、載回被災(zāi)官民名單、雜記等資料一一找出來,并加以系統(tǒng)梳理、排比與研究,不放過任何一個(gè)細(xì)節(jié),前后歷時(shí)五年終于撰成博士論文,比較完整地把這次救援的全過程呈現(xiàn)出來。論文于2012年被答辯通過后,經(jīng)過數(shù)年沉淀,去年志陽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時(shí)間對(duì)原稿進(jìn)行全面、細(xì)致的增訂刪改,最終定稿。志陽在《后記》中敘其緣起:
記得那是剛剛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課,我的博士生導(dǎo)師周武研究員在講授上海史時(shí)突然提到,庚子國變前后北方社會(huì)出現(xiàn)了一股大規(guī)模的人才遷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從京城遷居到上海,這極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動(dòng),因?yàn)樵诤芏痰臅r(shí)間內(nèi)即有數(shù)千人被從京津地區(qū)救援到上海。然而,對(duì)于這次救援行動(dòng),不但學(xué)界研究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師因而向聽課的學(xué)生們建議,有興趣的可以試著去關(guān)注關(guān)注。我當(dāng)即便對(duì)這個(gè)題目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此后便嘗試著收集相關(guān)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圖書館找到并復(fù)印了陸樹藩的一卷《救濟(jì)日記》和五卷《救濟(jì)文牘》,同時(shí)又從《申報(bào)》《中外日?qǐng)?bào)》等晚清報(bào)刊上發(fā)現(xiàn)了大量相關(guān)史料。知道我有了這些史料基礎(chǔ),周老師又建議我將這個(gè)題目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于是我的讀博生涯便與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為一體。
志陽講述的這個(gè)過程,我自己已不太記得了。但我的確認(rèn)為,與對(duì)庚子年次第發(fā)生于南北的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八國聯(lián)軍之役、庚子西狩、東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議和等一連串重大事件研究得眾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間由上海紳商發(fā)起、組織和實(shí)施的大規(guī)模救援則顯然未受到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眾多近代史著作幾乎不著一詞,這是不應(yīng)該的。而且,就庚子之變的整體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這一塊,也是不完整的。所以,當(dāng)志陽把這部書稿交到我手里的時(shí)候,著實(shí)讓我有點(diǎn)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除了對(duì)志陽的耐心和毅力表示驚訝外,更基于我對(duì)這個(gè)事件本身的復(fù)雜性和艱難性的認(rèn)知。庚子救援發(fā)生在京津淪陷這一被時(shí)人稱為“自有家國以來未有之奇變”之后,與上述一連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纏,互為因果。而且因?yàn)檫@種“深度交纏”,又不能不跟世紀(jì)之交中國的南北、官紳、華洋、新舊諸重關(guān)系深相勾竄纏繞。因此,講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難度,要厘清這一事件背后隱藏的上述諸重深相勾竄纏繞的關(guān)系,則尤屬不易。
志陽此書最著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在于“盡量完整地呈現(xiàn)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講清楚這一救援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得對(duì)事件發(fā)生前后的具體時(shí)空情境有足夠的了解。這一點(diǎn),志陽有充分的自覺。他在《導(dǎo)論》中指出:“庚子救援行動(dòng)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gè)具體的日常世界中,并為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制約。因此,要更好地?cái)⑹龈泳仍录筒坏貌贿M(jìn)入這個(gè)救援事件發(fā)生時(shí)的具體時(shí)空情境中,深入探討庚子國變前后南北間交通方式與通信方式的變化、京城社會(huì)管理方式的變化、京官日常生活的變化等,此外還包括江南社會(huì)的義賑傳統(tǒng),中外貿(mào)易與江浙絲商群體在19世紀(jì)下半葉對(duì)于上海乃至江南經(jīng)濟(jì)的宰制性影響,京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角色,以及華洋之間、官紳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等,這些共同構(gòu)成了與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關(guān)的歷史情境。這些歷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項(xiàng),都不會(huì)比救援事件本身更為簡單,因此筆者相當(dāng)多的精力都花在構(gòu)建支撐庚子救援事件得以發(fā)生的地基上。”正是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志陽依據(jù)自己艱苦搜尋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上海圖書館藏陸樹藩《救濟(jì)日記》及相當(dāng)于救濟(jì)善會(huì)“征信錄”的《救濟(jì)文牘》,盛宣懷檔案中有關(guān)庚子救援的各類史料,以及《申報(bào)》《中外日?qǐng)?bào)》《新聞報(bào)》等當(dāng)時(shí)上海報(bào)刊上所刊登的相關(guān)資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側(cè)重地詳盡論述了這一史所罕見的大救援的緣起、組織、過程及其影響,其中對(duì)救濟(jì)善會(huì)、東南濟(jì)急善會(huì)這兩大救援主體組織的發(fā)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組織機(jī)構(gòu)、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級(jí)成員、成立過程、具體的救援活動(dòng)、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內(nèi)容的梳理尤為細(xì)致入微。此外,書中對(duì)救濟(jì)款項(xiàng)的來源,特別是對(duì)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封疆大吏及粵籍官員的獨(dú)立捐款及其動(dòng)機(jī)、成效,以及救濟(jì)款項(xiàng)在京官間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與分析亦頗有所見。至于對(duì)淪陷時(shí)京城世相與京官生活的摹寫,對(duì)救援場(chǎng)景的敘述,更是歷歷如繪,每每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不過,就個(gè)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賞的還是書中的“余論”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關(guān)鍵詞”。與前六章偏重于敘事不同,這一部分的立意則在于闡釋庚子救援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聯(lián)系及其意義。志陽在完整敘述庚子救援的全過程之后,特別從中拎出絲業(yè)、京官、省籍意識(shí)、東南意識(shí)、義賑等貫穿全書的五個(gè)關(guān)鍵詞進(jìn)行深入討論,并以這種討論來對(duì)庚子救援進(jìn)行總結(jié),不僅形式新穎,亦必有助于從更深廣的脈絡(luò)中理解庚子救援這一事件的由來及其演進(jìn)。如此大規(guī)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極其錯(cuò)綜復(fù)雜的險(xiǎn)惡環(huán)境下展開的救援,絕不會(huì)是一個(gè)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實(shí)際上濃縮著自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中國社會(huì)特別是東南區(qū)域社會(huì)的變遷歷史。這正是志陽想要追蹤的歷史脈絡(luò)。他發(fā)現(xiàn)庚子救援的實(shí)際主持者幾乎是清一色的絲商:最早倡議庚子救援且一直負(fù)責(zé)救濟(jì)善會(huì)救援工作的陸樹藩是絲商,負(fù)責(zé)東南濟(jì)急善會(huì)日常事務(wù)的龐元濟(jì)、施則敬是絲商,另一個(gè)救援組織“協(xié)濟(jì)善會(huì)”的創(chuàng)辦人楊兆鏊也是絲商。可以說,庚子救援行動(dòng)幾乎全是由江南的絲商們籌劃組織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費(fèi)財(cái)力,特別是像庚子救援這樣大規(guī)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財(cái)力支撐。絲商成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開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關(guān)。由于地近江浙產(chǎn)絲區(qū),上海出口貿(mào)易以蠶絲為最大宗,絲商因此而逐漸累積巨量財(cái)富,“成為晚清上海乃至整個(gè)江南地區(qū)最為顯赫的財(cái)富擁有者”。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絲商扮演如此關(guān)鍵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無論是救濟(jì)善會(huì)還是東南濟(jì)急善會(huì),都以京官為最主要的救援對(duì)象。原因何在?志陽的分析認(rèn)為,這是因?yàn)楦魇【┕倥c各省利益之間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由時(shí)人的筆記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幾乎成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學(xué)者以各省京官為最主要的救援對(duì)象詬病庚子救援,認(rèn)為這實(shí)際上是一種利益交換,已背離了“救濟(jì)”和“濟(jì)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為這是一種苛責(zé),毫無道理。且不論庚子救援本身并不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廣泛地澤及普通百姓,救濟(jì)善會(huì)七千余回南者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濟(jì)善會(huì)與東南濟(jì)急善會(huì)在京津地區(qū)開辦平糶局,施衣“數(shù)萬套”,“掩埋白骨幾萬千”,“米面醫(yī)藥不計(jì)其數(shù)”,顯然也并非僅針對(duì)京官。實(shí)際上,救援以“鄉(xiāng)誼”相號(hào)召,以“省籍意識(shí)”為底色,更容易“一呼響應(yīng),事集眾擎”,這是國情,無可厚非。更何況當(dāng)年倡議和主持救援的紳商,后來也并沒有因?yàn)樵仍┕俣@得實(shí)際的利益回報(bào),有的還曾因此而負(fù)債累累,如陸樹藩就因庚子救援而虧欠巨萬,最后不得不將皕宋樓藏書悉數(shù)售與日本還債。其實(shí),無論是救京官,還是救百姓,對(duì)那些慷慨紓難、不顧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覺得還是應(yīng)當(dāng)抱持起碼的敬意。
另外,關(guān)于“義賑”在上海華人社會(huì)整合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志陽在分析這個(gè)關(guān)鍵詞時(shí),有一段話講得很好,他說:“就上海的華人社會(huì)而言,無論何種力量想要參與到義賑事業(yè)中來,都會(huì)被納入到一個(gè)統(tǒng)一的行動(dòng)框架中來。在一個(gè)統(tǒng)一的上海華人社會(huì)形成之前,上海義賑界的聯(lián)合和統(tǒng)一,對(duì)于整個(gè)上海華人社會(huì)的整合,顯然是具有潛移默化的引導(dǎo)作用的。”19世紀(jì)的上海,長期以來并沒有一個(gè)統(tǒng)一的華人社會(huì),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幫的各自為政。正是長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濟(jì)活動(dòng),使得上海華人社會(huì)逐漸擁有了一個(gè)有別于官府的公共領(lǐng)域,并形成了能為上海各省華人都認(rèn)可的華人領(lǐng)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夠調(diào)動(dòng)整個(gè)上海,乃至整個(gè)東南社會(huì)的力量,與統(tǒng)一的華人社會(huì)及其領(lǐng)袖在19、20世紀(jì)之交上海的出現(xiàn)密切相關(guān)。當(dāng)然,一個(gè)統(tǒng)一的上海華人社會(huì)的形象不可能因?yàn)閹状瘟x賑就能成型,但義賑在增進(jìn)幫派林立、互不統(tǒng)屬的各移民群體的上海認(rèn)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無的。
志陽這本書是厚實(shí)的,也是有見地的。厚實(shí)而有見地,一方面說明他在這個(gè)題目上下過切實(shí)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廣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這樣寫出來的著作雖未必炫目,但一定不會(huì)是過眼煙云。
周武
2018年6月14日
寫于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