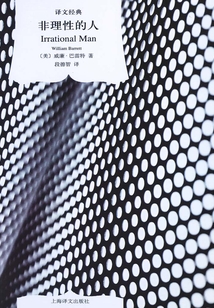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存在主義的問世
基爾凱戈爾曾講到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對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一覺醒來發(fā)覺自己已經(jīng)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這個故事今天講來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我們時代的文明終究掌握了一些武器,憑借這些武器,可以輕而易舉地使它自身陷入基爾凱戈爾故事主人公的命運(yùn):我們可能明早醒來發(fā)覺自己死了,卻從來不曾觸及我們自己的存在之根。時至今日,對原子時代的諸多危險確實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焦慮,乃至驚恐。但是,對于這種境況,一般民眾很少有人反省,進(jìn)行全方位的檢討,既或有之,也難得觸及問題的實質(zhì)。我們沒有反躬自問,那些隱藏在我們文明背后使我們陷入這種險境的終極觀念究竟是什么,我們也沒有探究那隱藏在人們鑄造的大批令人眼花繚亂的器械背后的人的真實面目。簡言之,我們不敢進(jìn)行哲學(xué)思考。盡管我們對原子時代深感不安,但是對于極端重要的存在問題本身,我們卻甘愿和基爾凱戈爾故事中的那個人一樣依舊心不在焉。我們所以會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把哲學(xué)貶黜到完全無關(guān)緊要的地位,而哲學(xué)本身對此竟也欣然接受。
如果哲學(xué)家真要討論人的存在問題,如果社會上再無別的職業(yè)團(tuán)體能夠接替他們的工作,他們就很可以從這個問題開始:在當(dāng)今時代,哲學(xué)本身如何存在?或者問得再具體一點(diǎn),就是在現(xiàn)代世界上,哲學(xué)家如何存在?這個問題并不意指任何高超深邃的、形而上學(xué)的東西,甚至一點(diǎn)也不抽象;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初步答案也同樣具體、平常。今天,哲學(xué)家存在于“學(xué)院”里,是大學(xué)哲學(xué)系的成員,成為多少帶有理論性質(zhì)的大家叫做哲學(xué)學(xué)科的專業(yè)教師。這個簡單的觀察非常實在,幾乎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性質(zhì),似乎并不能使我們深入到玄而又玄的存在問題;但是,理解存在問題的任何努力都必須從我們的實際情勢出發(fā),從我們當(dāng)前的立足點(diǎn)出發(fā)。“認(rèn)識你自己!”是蘇格拉底在整個西方哲學(xué)初露端倪(或非常接近這一開端)之際對哲學(xué)家們發(fā)出的指令;因而,當(dāng)代哲學(xué)家的自我認(rèn)識旅程,便可以從承認(rèn)哲學(xué)這一專業(yè)的社會地位這樣一個事實起步。這個事實盡管有點(diǎn)“污穢不潔”又很平庸,但它所帶有的若干含混性卻饒有趣味。
根據(jù)字典,所謂“以……為業(yè)”,就是公開地、因而也就是當(dāng)眾地供認(rèn)或表明信仰,所以也就是在世人面前公開承認(rèn)從事某項工作的內(nèi)心沖動或神靈的感召。這樣,這個詞原本就帶有宗教的意涵,例如,當(dāng)我們講到職業(yè)信仰時情況就是如此。但是,在我們現(xiàn)今社會里,隨著人的職能的精心劃分,職業(yè)乃成了一項專門性的社會事務(wù),它需要熟練和技巧,是一項人們?yōu)槭杖蟪甓荒懿宦男械氖聞?wù),亦即一種生計、一種個人營生。以職業(yè)謀生的有律師、大夫、牙醫(yī)、工程師,也包括哲學(xué)教授。在現(xiàn)代世界里,作為哲學(xué)家的職業(yè)就是去做哲學(xué)教授;而哲學(xué)家作為一個生存的個體,他的存在領(lǐng)域也和大學(xué)一角一樣無聲無息,鮮為人知。
盡管一些當(dāng)代存在主義者已對哲學(xué)家的這種學(xué)院式存在作出過率直、尖銳的批評,但這仍未引起充分的關(guān)注。一個人為謀得職業(yè)所付出的代價是法國人所謂的職業(yè)缺陷。大夫和工程師容易用他們的專業(yè)眼光觀察事物,因而對他們專業(yè)領(lǐng)域以外的東西通常便表現(xiàn)出十分明顯的無知。觀察越是專業(yè)化,其焦點(diǎn)也越是明顯;而對焦點(diǎn)四周的所有事物也就越發(fā)近乎全然無知。哲學(xué)家作為人,既然在學(xué)院內(nèi)供職,特別是由于人越來越完全地和他的社會職能化為一體這一點(diǎn)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法則,我們便很難指望他避免自己的職業(yè)缺陷。對于當(dāng)今的哲學(xué)家來說,既惹人煩惱又意義深刻的含糊性正出于此。以哲學(xué)為業(yè)在過去并不總具有它現(xiàn)在所具有的這種狹隘專業(yè)的意義。在古代希臘,情況則完全相反:哲學(xué)不是一門特殊的理論學(xué)科,而是一種具體的生活方式,是對人和宇宙的總體看法,個體的人據(jù)此度過他的一生。這些最早的希臘哲學(xué)家,不僅是最早的思想家,還是先知、詩人,也差不多是巫師。他們的思想里充滿著神話的和直覺的因素,即使在那些我們看到他們?yōu)樾纬筛拍疃鞒鲎畛鯕v史嘗試的地方,情況也是如此;他們甚至在賦予舊神祇以新的意義的過程中,也還同舊神做交易;在前蘇格拉底希臘人的斷簡殘篇里,到處都顯露出一種超乎他們自身的偉大的啟示,而他們透露給世人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啟示。即便在柏拉圖的著作里,雖然思想已經(jīng)比較分明、比較專門化,作為理論學(xué)科的哲學(xué)的主導(dǎo)路線也已制定了出來,但哲學(xué)的動機(jī)也還是和潛心研究的專家學(xué)者們的冷漠探求很不相同。對柏拉圖說來,哲學(xué)是一種激昂的生活方式;蘇格拉底生為哲學(xué)而生,死為哲學(xué)而死,他的不朽典范是柏拉圖在其師長去世后50年哲學(xué)生涯的準(zhǔn)繩。哲學(xué)是靈魂尋求拯救,而這對柏拉圖來說,則意味著從自然世界的苦難和罪惡中解脫出來。即使到了今天,東方人從事哲學(xué)研究的動機(jī)仍然和西方人完全不同:東方人為哲學(xué)費(fèi)神的惟一動因是尋求解脫和寧靜,擺脫塵世生活的苦惱和困惑。哲學(xué)決不能夠放棄這些原始的要求。這些要求是過去的一部分,是永遠(yuǎn)消失不了的。當(dāng)代哲學(xué)中,最詭辯的莫過于理性哲學(xué);然而,即便在這種哲學(xué)的飾面之下也依然潛存著這些要求。就連那些矢口否認(rèn)有所謂大智慧的哲學(xué)家,也為人們所呼吁,去回答這些重大問題。尤其是那些從事非哲學(xué)專業(yè)的俗眾,由于他們還不曾意識到專業(yè)化的歷史命運(yùn)已經(jīng)落到哲學(xué)頭上了,往往會發(fā)出這種呼吁。
哲學(xué)的這些古老要求使當(dāng)代哲學(xué)家有點(diǎn)難堪,使他不得不為他之存在于專家學(xué)者和科學(xué)家的知識圈里的合理性進(jìn)行辯護(hù)。現(xiàn)代大學(xué)和現(xiàn)代工廠一樣,都是當(dāng)今時代專業(yè)分工的產(chǎn)物。此外,哲學(xué)家也知道,我們所珍視的一切現(xiàn)代知識,都是專業(yè)分工的結(jié)果。其中的每一種在精確性和力量上都超越了過去所謂的知識,體現(xiàn)了一種巨大的進(jìn)步。現(xiàn)代科學(xué)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知識的社會組織。所以,當(dāng)今哲學(xué)家正是由于其在社會組織中的這種客觀社會作用而被迫成了科學(xué)家的模仿者:他也試圖借專業(yè)化來完善他的知識武器。因此,現(xiàn)代哲學(xué)家格外關(guān)注方法和技巧,關(guān)注邏輯和語言分析,關(guān)注句法學(xué)和語義學(xué);而且,一般說來,他們?yōu)榍蟮眯问降木啥幌О阉械膬?nèi)容全都提取掉。所謂邏輯實證主義運(yùn)動,在美國這個國家(在歐洲各大學(xué),人本主義的氣氛很可能比在美國要濃厚些),實際上是對哲學(xué)家由于自覺不是科學(xué)家,也就是說,不是那種以科學(xué)模式制造可靠知識的研究者而滋生的“負(fù)罪感”的抒發(fā)。哲學(xué)家由于他們的整個事業(yè)極不穩(wěn)定,原本就容易滋生不安全感,現(xiàn)在這種不安全感由于其執(zhí)著于把自己化為科學(xué)家而嚴(yán)重到了難以估量的地步。
專業(yè)分工是我們?yōu)橹R進(jìn)步付出的代價。其所以是一種代價,是因為專業(yè)分工的道路使人離開了其普通具體的理解活動,而他實際上是按照這種活動每天生活著的。人們過去常常說(我不知道這種說法今天是否依然適用),如果要死上12個人,則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意義就將對人類喪失殆盡。今天,沒有一位數(shù)學(xué)家能像一個世紀(jì)多以前偉大的高斯[1]那樣,領(lǐng)悟他的整個研究課題。凡是離開緊迫現(xiàn)實問題而走上了專業(yè)化道路的哲學(xué)家都可以聲言他的地位比得上科學(xué)家,聲言他自己之日益遠(yuǎn)離生活只不過表明知識進(jìn)步的法則不可抗拒罷了。但是,實際上,他的地位還是比不上科學(xué)家。因為靠只有少數(shù)幾個專家才能領(lǐng)會的抽象概念,物理學(xué)家就能夠使原子彈爆炸,而這會改變并且在事實上還能夠結(jié)束普通人類的生活。哲學(xué)家對他所在時代的生活并不曾產(chǎn)生過如此爆炸性的影響。實際上,要是今日的哲學(xué)家坦率的話,他們就會承認(rèn),他們對周圍人們心理的影響已經(jīng)越來越小。既然他們的存在已經(jīng)專業(yè)化和學(xué)院化到這樣一種地步,他們在大學(xué)校園之外的重要性也就日漸衰微。他們的爭辯已經(jīng)成了他們自己人之間的爭辯;他們非但得不到強(qiáng)大民眾運(yùn)動的必要的熱情支持,而且現(xiàn)在同依然留在學(xué)院之外的各類知識分子精英也沒有什么接觸。約翰·杜威乃是對美國非學(xué)院生活有過廣泛影響的最后一位美國哲學(xué)家。
這些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存在主義作為新聞傳來時,我們美國哲學(xué)的一般情景。那時,存在主義是個新聞,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它本身對哲學(xué)還是件不尋常的事情。公眾的興趣確實也沒有完全指向正在討論的哲學(xué)問題。它是來自法國的新聞,因此顯著地表現(xiàn)出法國知識生活能夠產(chǎn)生出來的那種獨(dú)特的色彩與轟動。法國的存在主義在巴黎,是一種狂放不羈的酵素;它把由它的年輕信徒們以匯聚夜總會、跳美國爵士舞、留奇特發(fā)型、穿奇裝異服等形式造成的時尚作為哲學(xué)的裝飾。所有這一切都成了想要報道大戰(zhàn)和德軍占領(lǐng)期間巴黎生活的美國記者們的新聞題材。再者,存在主義還是一種文學(xué)運(yùn)動,它的領(lǐng)袖人物——讓·保羅·薩特、阿爾伯特·加繆[2]、西蒙·德·波伏瓦[3]都是才華橫溢、大受歡迎的作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rèn)美國公眾對這種哲學(xué)本身也感到過好奇。或許這種好奇主要就在于想要知道這個名詞、這個大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沒有什么能像一條口號那樣引發(fā)公眾的興趣了。盡管對所有這一切的感受還很膚淺,但還是有一種真正哲學(xué)上的好奇;因為這項運(yùn)動似乎要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意義傳送給國外許多人,而美國人也想要知道它。尋求意義的渴望雖然被淹沒了,但卻還是蟄伏在美國生活的外向性下面。
從法國傳來的哲學(xué)新聞在戰(zhàn)后歷史上只是個小的細(xì)節(jié)。法國存在主義,作為一種時尚,就像去年的時髦一樣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逝了。誠然,它的領(lǐng)袖人物依然十分活躍:薩特和西蒙·德·波伏瓦依然出類拔萃地多產(chǎn),雖然就薩特來說,我們感到他至少已經(jīng)差不多發(fā)表完了他的全部看法,因而可以說,我們現(xiàn)在已相當(dāng)完全地掌握了他的要旨。阿爾伯特·加繆在他們合演的三重唱中最為敏銳,雖然很久以前就脫離了這個存在主義團(tuán)體,但卻還在繼續(xù)探究原本屬于存在主義深為關(guān)注的論題。作為新聞和轟動,這個運(yùn)動已經(jīng)完全寂滅了;然而,它卻給歐洲最近十年幾乎所有的作品和思想都打上了它的烙印。在嚴(yán)酷的冷戰(zhàn)年代,任何一個其重要性可以與之匹配的思想運(yùn)動都不曾出現(xiàn)過。存在主義作為一種新穎和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運(yùn)動,是十分缺乏創(chuàng)見的戰(zhàn)后年月能夠出現(xiàn)的最好運(yùn)動。如果我們以冷靜的態(tài)度來評估存在主義的話,則即便我們承認(rèn)它附帶有輕浮不實和危言聳聽的成分,我們還是應(yīng)當(dāng)至少指出這一點(diǎn)。
我再說一遍,重要的是,這里有一種能夠走出學(xué)院大門進(jìn)入大千世界的哲學(xué)。這對專業(yè)哲學(xué)家們本來應(yīng)該是個可喜的兆頭;因為它表明,如果你給普通人啃的是些看來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東西的話,他們還是會渴求哲學(xué)的。然而,哲學(xué)家們對這個新運(yùn)動卻一點(diǎn)也不熱誠。存在主義常常是在人們沒有對之進(jìn)行詳盡研究的情況下,就被當(dāng)作激情主義或純粹的“心理分析”,當(dāng)作一種文學(xué)態(tài)度、一種戰(zhàn)后的絕望情緒、一種虛無主義,或天知道別的什么東西而遭到拒斥。存在主義的主要論題,對英美哲學(xué)超然的莊重態(tài)度來說,恰恰是某種丑聞似的令人反感的東西。諸如焦慮、死亡、偽造自我與本真自我之間的沖突、民眾的無個性、對上帝之死的體驗等問題,幾乎都不是分析哲學(xué)的論題。然而,它們卻是人生的課題:人確實要死,人確實終生在本真與偽造自我的需求間奮斗掙扎,而且我們也確實生活在一個神經(jīng)過敏性焦慮增長得很不相稱的時代,就連那些以為自然科學(xué)技術(shù)可以解決所有人類問題的人,也開始把“心理健康”列在我們公眾問題的首位。專業(yè)哲學(xué)家對存在主義的反抗,只是他們囿于他們自己學(xué)科狹隘框架的一個征候。職業(yè)缺陷沒有比這更加明顯的了。精神與生活離異這樣一種現(xiàn)象,早就在一味追求他們自己專業(yè)問題的哲學(xué)家身上出現(xiàn)了。既然哲學(xué)家只在總?cè)丝谥姓紭O小部分,要不是精神與生活離異在現(xiàn)代文明中也恰巧到處都災(zāi)難性發(fā)生的話,這個問題大概就不值得勞神了。如我們將會見到的,這恰巧是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主題之一——或許,總有一天我們會因此而大欠其債的。
即使我們承認(rèn)法國存在主義確有感情用事和幼稚病態(tài)的一面,上述這一切也都不能不提到。薩特的才華——到了現(xiàn)在,他的才華幾乎不容置疑了——也有其無可否認(rèn)的病態(tài)方面。但是,沒有一個人的性情不能顯現(xiàn)某種真理的,因而,薩特的病態(tài)也有它自己獨(dú)特的展現(xiàn)力量。誠然,法國存在主義里有許多只不過是對一種歷史情緒——那場“假戰(zhàn)爭”[4]之后戰(zhàn)敗的混亂,以及德軍占領(lǐng)下被完全遺棄的感受——的表達(dá)。但是,這類情緒難道竟如此無關(guān)緊要以致哲學(xué)家不屑一顧嗎?事實上,詳盡闡述蘊(yùn)含在人的某些基本情緒中的東西,不正是哲學(xué)家一項嚴(yán)肅適當(dāng)?shù)娜蝿?wù)嗎?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它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而這兩次戰(zhàn)爭不只是偶然的插曲,而且還徹底地暴露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一種體驗過這些戰(zhàn)爭的哲學(xué),無疑可以說是與其時代的生活有了某種聯(lián)系。把存在主義作為“只是一種情緒”或“一種戰(zhàn)后情緒”的哲學(xué)家們,執(zhí)著于只有在那些“不”摻和任何人類情緒的經(jīng)驗領(lǐng)域中才找得到哲學(xué)真理的看法,這就暴露了他們對人類精神所關(guān)注的事物令人難以置信的茫然無知。
很自然,一些深深地帶有美國烙印的東西在對存在主義的最初反應(yīng)中泛到了表層。那美國對抗歐洲的舊戲又再次上演了。存在主義的確是歐洲的表達(dá)方式,它的陰郁情調(diào)與我們美國人朝氣蓬勃和樂觀主義的性情格格不入。這種新哲學(xué)并不是法國獨(dú)具的現(xiàn)象,而是西歐大陸政治和精神的整個視界正在迅速收縮這一歷史時期的產(chǎn)物。美國人還不曾從心理上領(lǐng)略過他們自己的地理疆界消失的滋味,他們的精神視界依然無限地展示了人類的各種可能性;而且迄今為止,美國人還不曾體驗過人的有限性的嚴(yán)酷滋味。(人的有限性這個詞對我們美國人來說,依然只是個抽象的詞匯。)像存在主義那樣討論問題的情調(diào),必定被美國人看做失望與挫敗的征候,以及一般說來,也是趨于沒落的文明衰竭的征候。但是,從精神方面來說,美國還是同歐洲文明緊密相連的,盡管兩者的政治權(quán)力的路線現(xiàn)在很不相同。何況,這些歐洲情調(diào)只是指出了美國本身早晚也要踏上的道路;到了那個時候,美國就將最終悟出歐洲人現(xiàn)在講的究竟是怎樣一些東西。
既然在至關(guān)緊要的問題上,整個歐洲文明(我們美國至今仍然既是歐洲文明的后裔,又是它的隨從)的意義,從根本上受到了質(zhì)疑,我們就有必要強(qiáng)調(diào)存在主義之發(fā)祥于歐洲,而不是特別地強(qiáng)調(diào)它之發(fā)祥于法國。看來依然有必要向美國讀者強(qiáng)調(diào):讓·保羅·薩特并不就等于存在主義;如我們后面將會見到的,他甚至還代表不了存在主義哲學(xué)最深層的動力。現(xiàn)在,既然法國存在主義作為風(fēng)行一時的運(yùn)動(甚至一度成為流行的污害),除了留下幾個新貴繼續(xù)殿后之外,無疑已完全死寂了,我們就有可能清楚得多地窺到它的真相——它原本是一棵參天大樹上的一條細(xì)枝。而這棵大樹的根須一直延伸到西方傳統(tǒng)的最深層。甚至在我們以當(dāng)代眼光能更直接看清的這棵大樹的各個分枝上,我們還是能看到有些東西是歐洲許多思想家的合成品,盡管這些思想家中有些人采用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傳統(tǒng)。譬如,薩特思想的直接源頭是德國人:馬丁·海德格爾(1889— )與卡爾·雅斯貝斯(1883— ),[5]以及作為其方法論直接源頭的德國偉大現(xiàn)象學(xué)家埃德蒙德·胡塞爾(1859—1938)。嚴(yán)格地講,只有海德格爾與雅斯貝斯才稱得上本世紀(jì)存在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他們給它打上了決定性的烙印,給予存在主義諸問題以新的更加貼切的表達(dá)方式,而且還一般地構(gòu)建了一種所有別的存在主義者的思想無不環(huán)繞其旋轉(zhuǎn)的思維模式。海德格爾與雅斯貝斯兩人的哲學(xué)都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德國哲學(xué)在本世紀(jì)初期的氣氛由于探求一種新的“哲學(xué)人類學(xué)”——一種對人的新的解釋——而活躍起來。哲學(xué)人類學(xué)由于所有研究人的特殊學(xué)科知識的遽增而成為必要。雖然一般人不把馬克思·舍勒[6](1874—1928)列為“存在主義者”,但是,在這里,我們必須特別提到他。這是因為他對于來自心理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新的具體資料很敏感,然而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他入木三分地領(lǐng)悟了下面這個事實,即現(xiàn)代人就其內(nèi)在本質(zhì)而言,已經(jīng)變得成問題了。舍勒與海德格爾都極大地受惠于胡塞爾,而后者同存在主義的關(guān)系卻極其含混和矛盾。就氣質(zhì)而言,胡塞爾在現(xiàn)代哲學(xué)家中是位卓越的反現(xiàn)代主義者。他是古典理性主義的熱情倡導(dǎo)者,他的惟一的和崇高的目標(biāo),就是把人的理性建立在比過去更為恰當(dāng)和更為全面的基礎(chǔ)上。可是,由于執(zhí)著于哲學(xué)必須擯棄先入之見,才能注意到實際具體的經(jīng)驗材料,胡塞爾就使哲學(xué)的大門突然向豐富的存在內(nèi)容敞開,而這些內(nèi)容正是他的更加激進(jìn)的信徒們要加以發(fā)掘的。在其后期的著作里,胡塞爾的思想甚至躊躇而緩慢地轉(zhuǎn)向海德格爾的論題。這位偉大的理性主義者被徐徐地拖回了“地面”。
但是,鼓舞海德格爾與雅斯貝斯超越他們同代人哲學(xué)水準(zhǔn),并且激勵他們對當(dāng)代知識界發(fā)出新聲的,乃是他們同兩位年代較早的19世紀(jì)思想家——索倫·基爾凱戈爾(1813—1855)與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的至關(guān)緊要的關(guān)系。雅斯貝斯在承認(rèn)這種“家譜”關(guān)系方面更為坦率:他說,真正體驗到基爾凱戈爾與尼采思想的哲學(xué)家絕對不會再在學(xué)院哲學(xué)傳統(tǒng)模式內(nèi)從事哲學(xué)探討。無論基爾凱戈爾或尼采都不是學(xué)院派哲學(xué)家;尼采,雖然曾在瑞士巴塞爾大學(xué)當(dāng)希臘語言學(xué)教授達(dá)七年之久,但他最根本的哲學(xué)思考卻發(fā)生在他離開大學(xué)及其嚴(yán)肅的學(xué)者圈子之后。基爾凱戈爾從未擔(dān)任過學(xué)院教席。他們兩人的哲學(xué)都沒有發(fā)展出一套體系;事實上,他們兩人都嘲笑體系的創(chuàng)造者,甚至否認(rèn)構(gòu)建哲學(xué)體系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他們創(chuàng)造了極其豐富的、遠(yuǎn)遠(yuǎn)超前他們時代、只有下一個世紀(jì)的人才理解得了的觀念。這些觀念不是學(xué)院哲學(xué)的陳腐的論題,甚至觀念也算不上這些哲學(xué)家的真正話題。這種情況本身體現(xiàn)了西方哲學(xué)的革命性變革:他們的中心論題是單個人或個體獨(dú)有的經(jīng)驗,這單個人或個體情愿把自己擺到他的文明的最重大的問題面前接受拷問。對于基爾凱戈爾與尼采兩人來說,這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基督教,雖然對于這個問題,他們持正相反對的立場。基爾凱戈爾給自己提出的任務(wù),是確定是否依然可以過基督徒生活,抑或一種名義上依然是基督教的文明是否必定最終要宣告精神破產(chǎn);而他的所有觀念無非是他在努力身體力行實現(xiàn)基督真理的狂熱過程中迸發(fā)出來的火花。尼采則是以承認(rèn)這種破產(chǎn)而開始的:尼采說,上帝死了;歐洲人要是更誠實一點(diǎn),更勇敢一點(diǎn),對在其靈魂深處發(fā)生的事情眼光更敏銳一點(diǎn),他就應(yīng)當(dāng)知道:盡管他口頭上依然贊成宗教的套話與理想,上帝之死卻已經(jīng)在他靈魂深處發(fā)生了。尼采用他自己的生命來作實驗,以便能夠回答這個問題:接著會出現(xiàn)什么情況?當(dāng)人這個種族終于割斷了幾千年來一直把它和神、和處于塵世之外的超驗世界連成一起的臍帶之后,對它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他拿自己的生命來作試驗,以便深刻地體驗上帝之死。基爾凱戈爾與尼采不只是思想家,更多的還是見證人——是為他們的時代忍受時代本身不愿承認(rèn)是它自己的內(nèi)傷的見證人。處于他們哲學(xué)中心點(diǎn)的,不是任何概念或概念的體系,而是為自我實現(xiàn)而奮斗不已的個體人格本身。無怪乎他們兩人都屬于最偉大的直覺心理學(xué)家之列。
雖然基爾凱戈爾是個丹麥人,但是,那時的丹麥知識界屬于德國的文化圈,他的思想幾乎完全是德國文化滋養(yǎng)起來的,因而最終也可以劃歸于廣義的德國哲學(xué)傳統(tǒng)。因此,總的說來,現(xiàn)代存在主義哲學(xué)是德國天才的創(chuàng)造。它從日耳曼精神的古老譜系中脫穎而出。早在中世紀(jì)末葉,邁斯特·埃克哈特[7]就曾試圖表達(dá)歐洲人靈魂最深層最內(nèi)在的心聲。但是,存在主義所表達(dá)的也是一種徹底現(xiàn)代化的心聲,它既不具有埃克哈特安詳寧靜的神秘主義色彩,也不具有德國唯心主義理智的陶醉狂放與恍惚朦朧。在這兒,這種內(nèi)向性已經(jīng)達(dá)到了直面它的對立面,即具體的生活現(xiàn)實,先前的德國哲學(xué)在其面前只擁有些胡思亂想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說,已經(jīng)達(dá)到直面歷史的危機(jī),直面時間、死亡與人的焦慮了。
然而,與其說現(xiàn)代存在主義起源于德國,毋寧說它是整個歐洲的產(chǎn)物,或許歐洲給美國或其他任何一種文明的這一最后的哲學(xué)遺產(chǎn)現(xiàn)在又反轉(zhuǎn)過來開始排擠歐洲了。通力合作共同構(gòu)建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有不同種族或民族傳統(tǒng)的歐洲思想家,其人數(shù)要比那些依然對法國存在主義有幾分入魔的公眾所想象的多得多。法國存在主義的畫面如果缺了加布里埃爾·馬塞爾[8](1889— )這個人物便算不得完整。馬塞爾是薩特的激烈反對者和有力的批評者,又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然而,令人瞠目的是,他的哲學(xué)源泉完全不是德國的,而是美國唯心主義者喬賽亞·羅伊斯[9]與法國直覺主義者亨利·柏格森。據(jù)馬塞爾《形而上學(xué)雜志》記載,他的存在主義是從純粹個人的體驗中發(fā)揮出來的,或許對我們來說,不管他的哲學(xué)的系統(tǒng)闡明會有什么樣的終極價值,它的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此。個人感受的親切與具體使馬塞爾明白,一切純粹玩弄抽象理智概念的哲學(xué)都是不完整的。但是,開啟這扇經(jīng)驗之門的,卻是柏格森的直覺學(xué)說;因此,任何一部現(xiàn)代存在主義哲學(xué)簡史,都實在少不了亨利·柏格森(1859—1941)這個人物。沒有柏格森,存在主義者進(jìn)行哲學(xué)探討的整個氛圍就會面目全非。他最早堅持抽象理智不足以把握經(jīng)驗的豐富性,堅持時間是一種緊迫的、不可還原的原始實在;而且,從長遠(yuǎn)的觀點(diǎn)看問題,他最有意義的洞見或許是堅持自然科學(xué)定量分析方法測不出精神生活的內(nèi)在深度。由于柏格森提出了上述這些觀點(diǎn),存在主義者極大地受惠于他。然而,從存在主義的觀點(diǎn)看來,柏格森的思想有一種令人費(fèi)解的缺憾,似乎他從未真正地抓住中心問題,即人的問題,而是一直在其四周轉(zhuǎn)來轉(zhuǎn)去,躲躲閃閃。事實上,柏格森思想的一些前提——這些前提固然也只能算是前提——比存在主義者曾經(jīng)考察過的都更為徹底。現(xiàn)在,除在法國外,柏格森的聲望已經(jīng)大降;但是,他的思想之將被復(fù)興是可以想見的。要是到了那個時候,對他的再認(rèn)識就會使我們看到他的哲學(xué)所包含的內(nèi)容比它過去即使為人推崇備至的時候似曾包含的還要豐富得多。
俄羅斯人(自然是白俄羅斯人)貢獻(xiàn)給存在主義三個典型而有趣的人物: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10](1853—1900),利昂·謝斯托夫[11](1868—1938)和尼古拉·別爾佳耶夫[12](1874—1948),他們中似乎只有最后一位為美國人所知。這些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3]的精神產(chǎn)兒,他們帶給存在主義一種獨(dú)特的俄羅斯人的看法:一種整體的、極端的和天啟式的看法。索洛維約夫主要是一位神學(xué)家和宗教著作家,屬于第一代,受到作為預(yù)言家和小說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他還發(fā)展了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diǎn),即在理性主義精神與宗教精神之間沒有任何妥協(xié)余地。別爾佳耶夫與謝斯托夫兩個都是俄國的流亡者,是精神上的世界主義者;但是,盡管如此,他們骨子里依然是俄羅斯式的;而且,他們的作品和那些偉大的俄國19世紀(jì)小說家的一樣,能夠把局外人對西歐精神,即對古典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后嗣的看法展現(xiàn)給我們,尤其是能把俄國局外人對他們的看法展現(xiàn)給我們,這些俄國局外人對任何一種哲學(xué)回答,只要是缺乏他們自己的人性所帶有的那種總體而熱情的感情,都不滿意。
現(xiàn)代西班牙貢獻(xiàn)給存在主義哲學(xué)兩個人物:米格爾·德·烏納穆諾[14](1864—1936)和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15](1883—1955)。烏納穆諾始終是個詩人,寫過一部討論整個存在主義運(yùn)動的最動人又最忠實的哲學(xué)書;他的《人生的悲慘感》這部著作,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是反尼采的,卻滿足了尼采忠實于大地的要求。烏納穆諾曾經(jīng)讀過基爾凱戈爾的著作,但是他的思想所表達(dá)的卻是他自己的個人情感和他土生土長的巴斯克大地。奧爾特加是位更冷靜又更有世界主義精神的人物,著有《民眾的反叛》,因而在美國享有社會批評家的聲譽(yù)。奧爾特加的所有基本前提都源于現(xiàn)代德國哲學(xué):就他進(jìn)行哲學(xué)思考所及的而言,他的精神是德國的;可是他能夠把德國哲學(xué)譯成通俗語言,沒有學(xué)究氣和行話術(shù)語;特別是他能把德國哲學(xué)簡潔樸實地譯成一種完全相異的語言,即西班牙語;結(jié)果,翻譯本身竟成了一種思想創(chuàng)造活動。奧爾特加喜歡用新聞工作者或文學(xué)家的簡明隨便的語言來表達(dá)深刻的哲理。
在德國傳統(tǒng)的外緣,活動著一個著名的人物,即馬丁·布貝爾[16](1878— )。他是一位猶太人,其文化完全是德國系統(tǒng)的,但其思想在走過漫漫旅程之后已經(jīng)成功地重新發(fā)現(xiàn)了它的《圣經(jīng)》的和希伯來文化的遺產(chǎn),并且本身也深深地定泊于這種遺產(chǎn)上了。布貝爾的作品給我們留下一個印象:他是在令人失望的現(xiàn)代尋根活動中獲得成功的很少幾個思想家之一。《圣經(jīng)》人物的形象影子般地活動在他所寫的每件作品的背后。他的思想具有希伯來文化的狹隘性與凝聚力,常常是倔強(qiáng)執(zhí)著、剛愎自用。乍一看,他的貢獻(xiàn)在所有的存在主義者中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可以用他的最動人的《我與你》這本書的書名來概括。基爾凱戈爾說過,“心靈的純潔就在于只去意欲一件東西”,仿佛布貝爾已經(jīng)把這句格言重鑄成:心靈的深邃就在于只去思考一個思想。但是,生活的意義只發(fā)生在這樣一種個人與個人的區(qū)間里,在這個區(qū)間里,他們處于一個人總可以對作為他人的“你”說“我”的這樣一種交往情勢中,這樣一種思想是值得畢生發(fā)掘的。無論如何,布貝爾對于像海德格爾與薩特那樣的雄心更大的體系創(chuàng)造者來說,是一個必要的矯正。
于是我們見到,存在主義在其最有力的代表人物中除無神論者外,還有猶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同最初新聞界的輕率反應(yīng)相反,存在主義思想的嚴(yán)肅性并不只是由對上帝離開世界的絕望產(chǎn)生出來的。這樣一種概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存在主義哲學(xué)同薩特學(xué)派混同起來所致。從上述梗概就當(dāng)看出,薩特學(xué)派所代表的實際上只是存在主義的一個極其細(xì)微的片斷。就存在主義思想的中心推動力而言,至少在一定意義上,一個人究竟在哪一個教派里找到他的歸宿,是完全無關(guān)緊要的。而且,把天主教徒、猶太教徒、新教徒與無神論者在一種哲學(xué)的大標(biāo)題下放到一起,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多相拼湊。盡管依照存在主義哲學(xué)模式進(jìn)行研究的哲學(xué)家投入了不同的宗教陣營,但是,存在主義哲學(xué),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特殊模式,卻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哲學(xué)家的共同點(diǎn)和中心點(diǎn),就是宗教的意義及宗教信仰是因人而異的。他們每一個都徹底地考察了宗教問題;其思想表現(xiàn)出來的信仰或?qū)π叛龅姆穸ǎ嗌贂鼓切╇S俗從眾沿著“外在”道路步入“教堂”的人們感到困惑,是完全可以想見的。烏納穆諾似乎一直瀕臨為西班牙主教革除教籍;布貝爾是個預(yù)言家,在其祖國以色列并沒有多大聲譽(yù);基爾凱戈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為反對丹麥教會的等級制度而戰(zhàn)。另一方面,無神論派對海德格爾染指異端嗤之以鼻。海德格爾曾經(jīng)在一處把他自己的思想叫做“等待上帝”,有位美國哲學(xué)家則批評他是在為神學(xué)開后門。顯然,只要誰體驗到現(xiàn)代經(jīng)驗的深層,并且努力用與這種經(jīng)驗的關(guān)系看待宗教,他就必定會獲得異端的稱號。
現(xiàn)代經(jīng)驗——確實是一個非常模棱兩可的術(shù)語,一個有待界說的術(shù)語——是這些哲學(xué)家之間的“黏合劑”。我們所提供的這個花名冊雖不十分完整,倒也足以表明:存在主義不是一種一時流行的風(fēng)尚,也不只是一種戰(zhàn)后時期的哲學(xué)情緒,而是直接存在于現(xiàn)代歷史主流中的人類思想的一項主要運(yùn)動。過去一百多年,哲學(xué)發(fā)展已經(jīng)顯示出一種引人注目的內(nèi)容拓展,一種趨于直接的與定性的、存在的與實際的事物的進(jìn)步方向,用阿·諾·懷特海借用威廉·詹姆斯的話說,就是趨于“具體與適當(dāng)”。哲學(xué)家們不能再像英國經(jīng)驗主義者洛克和休謨那樣,試圖用簡單觀念和基本感覺構(gòu)建人類經(jīng)驗。人的精神生活不是這樣一些心理原子的鑲嵌圖案,而哲學(xué)家墨守這種信念如此之久只是由于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抽象概念取代了具體的經(jīng)驗。因此懷特海自己,雖然作為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幾乎不能同存在主義者相提并論,然而當(dāng)他把哲學(xué)本身規(guī)定為“批評抽象概念”——為把精神氣球拖回實際經(jīng)驗地面作不懈努力時,他也就分享了內(nèi)在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這種一般的存在主義傾向。
在所有的非歐洲哲學(xué)家中,大概要數(shù)威廉·詹姆斯最稱得上是存在主義者了。事實上,就現(xiàn)在的情況而言,我們會大為詫異:稱詹姆斯為存在主義者可能比稱他為實用主義者還要貼切些。今天依然堅持美國實用主義的哲學(xué)家也不得不認(rèn)為他是這個運(yùn)動的害群之馬。當(dāng)今時代的實用主義者承認(rèn)詹姆斯的才華,卻為他的走極端而犯難,也就是犯難于他的哲學(xué)思考的毫不掩飾的個人格調(diào),他的在心理學(xué)與邏輯學(xué)似乎沖突抵觸之處甘愿使心理學(xué)最終高于邏輯學(xué)的做法,以及他的相信宗教經(jīng)驗的天啟性質(zhì)的思想。在詹姆斯的著作中,有些部分本來簡直可以由基爾凱戈爾寫出來的,而且在《宗教經(jīng)驗種種》的結(jié)尾部分強(qiáng)調(diào)個人經(jīng)驗高于抽象概念,其語氣之強(qiáng)烈一點(diǎn)也不弱于任何一個存在主義者。詹姆斯把理性主義罵得很兇,致使后來的實用主義者發(fā)現(xiàn)他們自己科學(xué)方法中的理性主義殘余也成問題了。而且,把詹姆斯列為存在主義者還不只是個格調(diào)問題,還有原則上的問題:他宣揚(yáng)世界包含著偶然性和非連續(xù)性,而且這個世界的經(jīng)驗中心無可化簡的是多元的與個人的,反對有一個所謂能夠包容到一個單一理性體系內(nèi)的“鐵板一塊”的宇宙。
實用主義對于詹姆斯比對于查爾斯·桑德·皮爾士或約翰·杜威意蘊(yùn)著某些更多的和不同的內(nèi)容。尤其是詹姆斯與杜威的鮮明對照,使得在嚴(yán)格意義上的實用主義借以終結(jié)而存在主義由之開始的關(guān)節(jié)點(diǎn),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來了。把杜威早期與晚期的著作加以比較,幾乎也同樣清楚地顯示了同一個關(guān)節(jié)點(diǎn)。杜威堅持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必須與整個古典思想傳統(tǒng)決裂,這樣,他就也是沿著現(xiàn)代哲學(xué)的一般存在主義方向運(yùn)動的。他看到了哲學(xué)的“否定的”和破壞性的一面(存在主義為此曾經(jīng)受到它的批評者的嚴(yán)厲譴責(zé)):杜威告訴我們,每個思想家,當(dāng)他一開始思想時,就把這個穩(wěn)定不變的世界的某個部分置于危險境地了。在他的結(jié)構(gòu)松散、基礎(chǔ)不甚扎實的整個哲學(xué)背后,隱藏著一股親切的鼓舞力量,這就是:相信在人類經(jīng)驗的所有部分中,一切事物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地里長出來的。思想本身只是完全生物學(xué)上的人為了應(yīng)付環(huán)境而進(jìn)行的躊躇不決、搜尋摸索的努力。人之作為束縛在地球上和時間中的生物的形象貫穿杜威的著作中,在一個意義上恰似它之貫穿于存在主義者的著作中一樣。超出這個意義,他運(yùn)行的方向便與存在主義正相反對了。杜威從未表示過懷疑的,是他貼上“理智”標(biāo)簽的東西,這在他的最后幾部著作里僅只意指科學(xué)方法。杜威雖然把人牢牢地置放于他的生物學(xué)與社會學(xué)的場景中,但是他從未超越這一場景,而達(dá)到恐懼與焦慮從中涌現(xiàn)出來的人的至深的中心點(diǎn)。對內(nèi)在經(jīng)驗(真正內(nèi)在的經(jīng)驗)的任何考察,在杜威看來,都會使哲學(xué)家沿著神學(xué)的方向前進(jìn)而離開自然太遠(yuǎn)。在這兒,我們不得不提醒我們自己留意杜威著手工作時所處的美國褊狹的和過分神學(xué)化的氛圍;而他為了確立世俗理智的效用也不得不奮力拼搏反對這種氛圍。然而,既然杜威強(qiáng)調(diào)生物學(xué)和社會學(xué)來龍去脈的終極意義,連同他把人的思想解釋成基本上是改變環(huán)境的一種努力,我們最終就看到了人的形象,即他實質(zhì)上是有技術(shù)、有技巧的人,亦即有技術(shù)的動物。這樣相信技術(shù)依然是美國一條至上的信仰。杜威生長在一個美國依然在艱苦拼搏致力于疆土開發(fā)的時期,因而他的作品洋溢著一種不可動搖的樂觀情緒,以為我們的技術(shù)可以越來越多地控制自然。從根本上說,杜威與存在主義者的差別正是美國與歐洲的差別。哲學(xué)家并不能夠認(rèn)真地向自己提出他的文明未曾經(jīng)歷過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提出把我們話題的范圍限制在歐洲,而把存在主義看做顯然是這一時期歐洲的產(chǎn)物,實際上是把它看做本世紀(jì)歐洲哲學(xué)的產(chǎn)物。在存在主義這個術(shù)語最寬泛的意義上,整個現(xiàn)代思想所帶有的強(qiáng)調(diào)存在的色彩無疑比現(xiàn)代早期哲學(xué)要鮮明些。簡單說來,這是西方文明日漸世俗化的結(jié)果,在這個過程中,人無可避免地更加傾心于地球此岸世界的允諾,而不是依戀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超驗天國的目標(biāo)。自始就喚起人們對“存在主義的”一詞這種寬泛意義的關(guān)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要把這種意義詳細(xì)貫徹到底,就將勢必沖淡存在主義的特殊要旨。雖然,正是歐洲已處于危機(jī)之中,也正是歐洲思想家集中地表達(dá)了存在問題,而且事實上,也只有他們才敢于提出這些終極性問題。然而,就這種哲學(xué)的意義而言,則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是不可以把它局限于它的發(fā)祥地的。它的意義既是劃時代的,又是世界性的。
讀者在了解了現(xiàn)代哲學(xué)內(nèi)的這種較為寬泛的存在主義傾向之后,便很有理由發(fā)問:為什么存在主義最初竟然會被我國專業(yè)哲學(xué)家們視為一場離奇的和聳人聽聞的“茶壺中的風(fēng)波”呢?我們應(yīng)當(dāng)指出,在英美哲學(xué)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種迥然不同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有若干不同的叫法,或是稱作分析哲學(xué)、邏輯實證主義,或者有時就叫“科學(xué)哲學(xué)”。無疑,實證主義也有適當(dāng)?shù)睦碛梢蟪蔀檫@個時代的哲學(xué):它把無疑是使我們的文明區(qū)別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主要事實——科學(xué),作為其主要事實;但是,它由此出發(fā)又繼而把科學(xué)看做是人類生活的至上支配者,這卻是科學(xué)從來不曾如此而且從心理角度看也永遠(yuǎn)不可能如此的。實證主義的人是一種稀奇古怪的生物,他住在一個由他發(fā)現(xiàn)的在科學(xué)上“有意義的”事物組成的光明之島上;至于普通人天天生活并同他人交往的整個周圍地帶都被投諸外界的“無意義的”黑暗之中。實證主義簡單地接受了現(xiàn)代人的支離破碎的存在,并且構(gòu)建出一種哲學(xué)來強(qiáng)化它。反之,存在主義,不論成功與否,卻是力圖收集人類實在的所有要素以勾畫出人的總體畫面。實證主義的人與存在主義的人無疑是同一個時代之母的產(chǎn)兒,但是,有點(diǎn)類似于該隱與亞伯[17],弟兄們由于性情不合而不可避免地分道揚(yáng)鑣了。當(dāng)然,在當(dāng)代還有一種理論比它們兩個都更有力地要求成為哲學(xué)界的統(tǒng)治者,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人是一種工藝學(xué)意義上的生物、一種忙碌而機(jī)巧的動物,對歷史具有世俗的宗教信仰,自以為他自己就是被揀選出來的歷史的合作者。同實證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沒有一個用來描述人的個體性的獨(dú)特事實的哲學(xué)范疇,從而在事物的自然過程中設(shè)法使人的這種個體性脫離存在而集體化(除非某個人獲得權(quán)力,然而,這么一來,他個人的偏執(zhí)癥卻使兩億生靈遭到浩劫)。從思想上說來,馬克思主義與實證主義兩者都是19世紀(jì)啟蒙運(yùn)動的遺跡。雖然,對于人類生活的陰暗面,甚至一些19世紀(jì)的思想家們早已有所領(lǐng)悟了,但是,這兩派卻至今都還不曾承認(rèn)這種陰暗面。因此,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人的畫面是單薄的,過于簡單化了。存在主義哲學(xué),作為對這樣一種簡單化的反叛,力圖掌握整個人的形象,盡管為此它也就必須去揭露他的存在中的一切黑暗和可疑的東西。正是由于這一方面,它才堪稱對我們自己時代經(jīng)驗的一種本真得多的表達(dá)。
為了證明這一點(diǎn),我們現(xiàn)在就來著手考察產(chǎn)生這種哲學(xué)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特征。
注釋:
[1] 高斯(1774—1855),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德國數(shù)學(xué)家之一。——譯者
[2] 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主要作品有《局外人》、《西西福斯的神話》、《墮落》等。——譯者
[3] 德·波伏瓦(1908—1986),法國女作家、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薩特的終身伴侶。主要作品有《應(yīng)邀而來》、《人總有一死》等。——譯者
[4] “假戰(zhàn)爭”(Phony war),指從1939年10月到1940年4月期間,在雙方?jīng)]有重大軍事沖突的情況下,德軍入侵波蘭、挪威一事。——譯者
[5] 海德格爾和雅斯貝斯分別卒于1976年和1969年。——譯者
[6] 舍勒,德國社會與倫理哲學(xué)家,以研究現(xiàn)象學(xué)的方法而知名。——譯者
[7] 埃克哈特(約1260—1327或1328),萊茵蘭神秘主義派創(chuàng)始人,德國新教教義、浪漫主義、唯心主義、存在主義的先驅(qū)。主張“心靈超越上帝”。——譯者
[8] 馬塞爾,卒于1978年,法國哲學(xué)家、劇作家及文學(xué)、戲劇、音樂評論家。他多方位地深化、發(fā)掘、闡明了人類經(jīng)驗,堪稱第一個法國的現(xiàn)象學(xué)家和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譯者
[9] 羅伊斯(1855—1916),美國新黑格爾主義哲學(xué)家,信仰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又強(qiáng)調(diào)個性與意志。主要著作有《哲學(xué)的宗教方面》、《世界與個人》、《忠的哲學(xué)》等。——譯者
[10] 索洛維約夫,俄國基督教哲學(xué)家和神秘主義者。主要著作有《西方哲學(xué)的危機(jī):反對實證主義者》、《神人身份》、《愛的意義》等。——譯者
[11] 謝斯托夫,俄國非理性主義哲學(xué)家。1922年前往柏林和巴黎。哲學(xué)上推崇基爾凱戈爾,極端反對理性主義。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采》等。——譯者
[12] 別爾佳耶夫,基督教存在主義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大學(xué)哲學(xué)教授,1922年被逐出國。主要著作有《自由與精神》、《俄國共產(chǎn)主義之起源》等。——譯者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著名社會小說家。主要作品有《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有世界性影響,尼采承認(rèn)曾受惠于他。——譯者
[14] 烏納穆諾,西班牙早期存在主義者,認(rèn)為人類“對永生的渴求”,不斷為理智所否定,只能用信仰來滿足。主要作品有《人生的悲慘感》、《基督教徒的痛苦》等。——譯者
[15] 奧爾特加-加塞特,西班牙著名哲學(xué)家和人文主義者。提出“生命理性”概念和“我是我和我的環(huán)境”的口號。主要作品有《沒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民眾的反叛》等。——譯者
[16] 布貝爾,卒于1965年,德國猶太宗教哲學(xué)家。深受尼采哲學(xué)影響。曾創(chuàng)辦《猶太人》月刊,出任過以色列科學(xué)和藝術(shù)學(xué)院第一任院長。20世紀(jì)精神文化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譯者
[17] 該隱與亞伯,據(jù)《圣經(jīng)》,該隱為亞當(dāng)與夏娃之長子,曾殺害其弟亞伯。——譯者